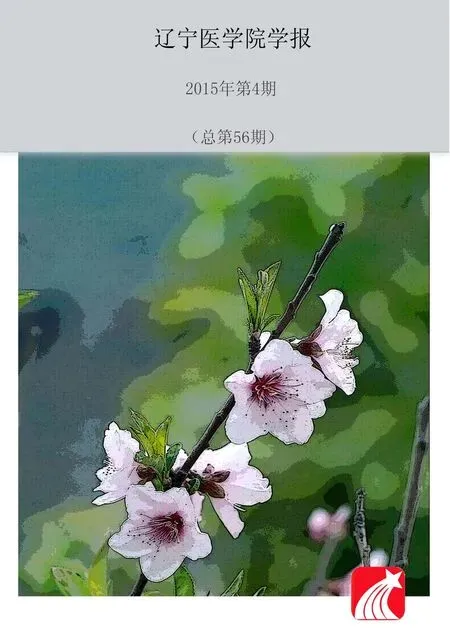话语的权力研究
2015-04-15逄勃
逄勃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辽宁 锦州 121001)
话语的权力研究
逄勃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辽宁 锦州 121001)
话语的权力在很多学科都受到过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学科领域不同,研究范围和视角也不尽相同。通过界定社会权力的属性及话语权力的核心问题将有助于对特定话语类型的权力进行分析。对新闻话语的权力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研究、中观层面研究和微观层面研究。跨学科、跨文化的新闻传播研究发展趋势,也为新闻话语的权力研究开拓了新空间。
话语;话语权力;新闻话语;权力分析
“话语”一词源自拉丁语discursus,意思是“运行或分散的过程”,最早用于语言学中,常用来强调口头或书面语言的高级结构属性,在语义分析和话语分析中,“话语”泛指所有模式和情境下的“谈话”的概念。[1]当“话语”是指与给定的社会实践类型相匹配的语言编码类型及使用时,则可具体称为:法律话语,医疗话语,宗教话语,新闻话语等等。在福柯和其他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将“话语”定义为一个可以进行陈述的符号序列的实体。因此,话语是由主体、客体和其他陈述的关系序列构成的,而生产话语的规则被定义为话语格式。
一、话语的权力
很多学科都对话语的权力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且大多都限定在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学者对语言、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出过许多有趣的研究。有的学者将话语研究限定在语言与权力的一般关系上(Kramarae, Shulz,&O’Barr,1984;Mey,1985);有的针对人际传播领域的话语权力进行研究 (Berger,1985;Seibold,Cantrill,&Meyers,1985);有的学者以人种学方法关注地域文化(Bauman& Scherzer,1974;Saville-Troike,1982)或跨文化传播中权力的作用;而女性研究的学者则已经对男性在语言中的支配地位和权力进行了讨论(Kramarae,Thome,&Henley,1983)。[2]
1.社会权力的属性。梵迪克在他的《话语结构与权力结构》研究中重点关注了在社会情境中作为一个特定的语言“文本”形式使用的话语以及一些涉及支配或权力在语言的变化和风格中的作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Scherer&Giles,1979),他主要关注和研究西方文化背景下,社会或社会交往中权力的作用。他认为社会权力是群体、阶级,或其他社会形态之间,或者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属性。虽然我们也会谈及权力的个人形式,但是这种个体权力与我们系统论述的作为社会互动的话语权力的作用关系不大。
现代西方社会的所有社会控制都是由权力机构限定权力的领域和范围。行使权力控制需要有基础即社会资源,这些资源通常是具有社会价值但却分配不均的社会财产,例如:财富、地位、官衔、身份、知识、专业、特权,甚或是主流群体的成员身份。同时,社会权力的行使和维护是以意识形态框架为先决条件的。这个框架是由社会共享的、利益相关的群体及其成员的基本认知构成的,并主要通过传播和话语获得、确认或改变。
2.话语权力。通过话语进行社会控制即为话语权力的行使,它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话语的控制和话语生产本身。所以话语权力的核心问题就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给谁说或写什么?谁能接近不同形式的或流派的话语或者话语的生产手段?
权力不只出现在或贯穿于话语中,它是隐藏在话语背后的社会力量。有权力的群体及其成员对话语的作用、流派、场合、风格行使着越来越广泛的控制。他们控制着公共话语的主动权,为公共话语设定基调和话题,为文本或谈话设定风格,决定话语的参与者和接受者。话语权越少的人对不同形式的文本或谈话的接近越少,即使是偶尔有机会参与对话也只是被动的回应和简单的接受,并最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对于大多数正式的、公共的或印刷话语类型(包括那些大众媒介),没有话语权的人通常只能是受者。
话语生产模式是由“符号精英”们控制的,例如:记者、作家、艺术家、导演、学者及其他群体以“符号资本”为基础行使话语权力(Bourdieu,1977,1984;Bourdieu&Passeron,1977)。这种符号权力不只限于话语本身,还延伸到影响模式:设置公共讨论议程、管理信息量和信息类型、影响话题相关性,特别是以何种方式公开描绘谁。他们是公共知识、信仰、态度、规范、价值观、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因此他们的符号权力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
二、不同视角的新闻话语权力研究
对新闻话语的权力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研究,主要涉及将新闻话语权力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相结合的媒介环境研究等视角;一个是中观层面,涉及到新闻组织研究,微观社会学等视角;第三个层面是微观研究,主要是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对制约新闻生产的符号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进行研究。
1.话语的“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实践语言观。布尔迪厄认为,语言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现象,语言传播就是包含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实践行为。布尔迪厄把他的语言研究深深地推进到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及纯粹语言学批评都未曾涉及的领域,他论证了“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说话者与他们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转而以一种变形的形式表现出来”(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p189)。这是布尔迪厄的原创性研究:解释语言与权力的关系。
布尔迪厄强调社会环境、权力秩序的决定性作用,更倾向于从实践社会学的关系视角探讨权力关系的支配现象。布尔迪厄的实践主义语言观是试图超越社会科学领域里长期对立的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视角,将语言视为处于实践语境中的行动。他认为,要理解语言的逻辑,就必须要理解语言市场中的语言行为及其权力和资本的关系。换句话说,他强调语言交流中的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他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在传播中(自然也包括话语),生存的物质条件通过语言生产关系决定着话语,语言生产关系使话语成为可能并建构话语”。
2.新闻的“框架”生产——塔奇曼的新闻“知识”。塔奇曼(1978)认为[3],话语的自反性和索引性构成了新闻生产的组织语境。话语的索引性和自反性是构成语境的两大要素,通过“索引性”和“自反性”的循环往复,形成了人们理解解释生活世界意义和秩序的一个个“框架”。新闻话语的自反性和索引性表现为组织内部的协商和借助组织语境进行新闻生产从而证明组织的合法性。
新闻知识是一种历史的现实再建构。社会关系建构了知识,而知识组织了经验,规范了社会意义,这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包含人类活动和权力,而新闻机构正是人类生产知识(社会资源)和权力(分配资源)的机构。新闻的生产过程本身是由新闻价值体系和有关新闻和新闻价值的专业意识形态来控制的,而这恰恰是为精英阶层的兴趣和关注点服务的。同样的,新闻生产的日常组织管理也要服务于机构情境下的新闻采集,如国家的主要政体、警察、法院以及大型公司这些机构为新闻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闻源保障(Fishman,1980;Tuchman,1978)。当记者与机构的倾向和要求发生矛盾时,新闻规范仍旧是指导行动的意识形态。
3.话语分析——新闻话语权力的研究工具。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梵迪克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出发,对新闻制作和新闻理解中的新闻结构与认知过程进行分析,清楚阐释了新闻价值和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新闻制作和新闻理解是在新闻源所给出的定义之上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有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的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设定的意识形态。
无论从宏观社会学还是微观社会学的新闻组织研究,都是从研究者或从权力主体的视角进行研究,虽然有关注社会互动中的权力变化,但仍呈现出对新闻话语权力行使的被控制方,即新闻受众研究的忽视或模糊。
三、新闻话语权力研究的新空间
1.不可忽视的受众效果分析—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同梵迪克在他的新闻话语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对新闻话语的权力进行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分析应该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随着大众传播研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新闻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主导趋势,而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将有助于对新闻话语权力进行更加科学的分析。[3]
在大众传播研究中,运用丰富的统计分析工具来研究传播效果的方法也可以借鉴到新闻话语的选择控制及效果分析中。例如,研究媒介对政治传播的诱因效应就是将微观层面的心理学理论与宏观层面的政治传播理论联系到一起,通过由媒介参与或发起某些议题,忽略其他议题并以此改变某些选举候选人的评估标准的过程。很多的政治信息处理研究还反映了图式理论的基础应用,因为心理图式一旦激活就会促进和塑造信息的加工,从而为个体形成评价和理解他们的社会环境提供原材料(Graber 1988,Fiske and Taylor 1991)。正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媒体在公共话语中不只是起到一个议程设置的作用,通过新闻和舆论的选择和“框架”,媒介在建立构建、辩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标准尺度上起着关键作用(Gitlin 1980,Graber 1988,Gamson 1992,Neuman etal.1992,Shah etal.1996)。西方的大选研究表明,选民对问题形成不同的心理图式链接是基于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与媒体报道的互动;反过来,这些问题的解释也塑造了信息的加工和判断(Domke&Shah 1995,Shah etal.1997)。
2.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新闻话语权力研究。新闻话语权力的巨大研究潜力和空间期待研究者尽可能地开展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大众传播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趋势也是新闻话语权力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自19世纪后半叶起,媒介开始将地方层面的社会互动嵌入到民族国家情境,到20世纪90年代,媒介的高速发展使之冲破国家屏障,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强大支撑。在全球化时代,媒介不仅为各个国家及其人民提供了传播渠道,而且还建立了跨地域跨民族的网络。越来越多的媒介产品的涌入和跨越国界的传播,使得新闻话语的权力结构与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互动中发生着变化并产生了新的社会意义。国家间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或地区差异都可能会影响不同国家受众对新闻事件的感知、解释和描述,尤其是在冲突事件的新闻报道上则会更加典型。依据新国际信息秩序讨论框架,在国际传播中出现的新闻图式西方化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对西方通讯社的主导地位和权力有历史的和专业的依赖,因此,来自和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或者由西方记者来报道,或者使用西方通讯社的报道格式,绝大部分都是刻板印象化的“第三世界”报道,以便能够被这些国际通讯社采用或提供给他们的客户[4](Van Dijk,1984b,1987c)。虽然西方学者通常认为上述讨论是对新闻“自由”的攻击,但是这里面自由只是权力与控制的代名词而已。◆
[1]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Smitherman-Donaldson,G.and van Dijk,T.A.(eds),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Detroit,MI: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Tuchman,G.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78.
[4]van Dijk,T.A.Prejudice in Discourse,Amsterdam:Benjamins. 1984.
An Analysis on Discourse Power
Pang Bo
(Jinzhou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Jinzhou Liaoning,121001)
The discourse power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inmany disciplines.With different disciplines,research scope and perspectives are also different.Defining the attribute of social power and the core issue of discourse power will contribute to analyze the power of specific discourse types.The research on news discourse powe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macro research,mezzo level and micro level.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ew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cross-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also has created new space for the study of the powerofnewsdiscourse.
discourse,discourse power,news discourse,power analysis
H315
A
1674-0416(2015)04-0142-03
[责任编辑:王靖宇]
2015-07-11
逄勃,女,1981年生,辽宁锦州人,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