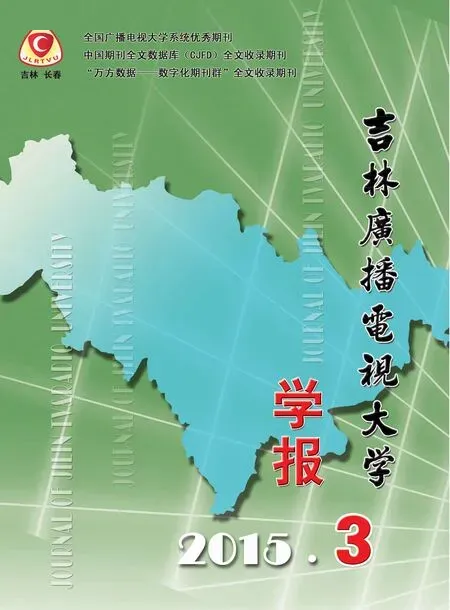伪满洲国戏剧中的殖民现代性景观
2015-04-14何爽
何 爽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3)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开始,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从被动接受逐步转为主动姿态。所谓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各领域所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或者说,是在现代化促动下,在社会各领域(物质、制度、精神文化)发生全面变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应合现代化的属性”。在伪满洲国时期,现代性的进程始终与殖民性相伴随,与民族性相纠缠。殖民者以“进步”、“文明”的姿态,给殖民地输入现代化的器物、制度和思想,在殖民地进行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文化建设,其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对于殖民者来说,是以“现代文明”持有者身份出现在殖民地,无视殖民主义的危害性与非正义性。对于被殖民者来讲,其内部存在着多种态度及相互冲突。一方面,出于对科学、民主、法制的追求,往往呈现出对现代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但在另一方面,又以民族性作反抗,对殖民统治进行反思与质疑。对这一文学景观的梳理与审视,成为探究伪满时期戏剧以及文学整体风貌的一种独特视角。
一、机器、工厂、铁路及都市场景
在伪满时期的剧本创作中,殖民现代性的影响渗透至各个角落,机器、工厂、铁路等现代景观是殖民现代性在物质层面的典型代表。剧作者往往借场景的布置来展示现代化的生活空间,以新式家具、电器、西洋装饰等物件来证明都市家庭的先进性。在剧本《岂有此理》中,震华纱厂的总经理曾道章家中的摆设:客厅堂中置一西式的小圆桌,上面放有花瓶、雪茄、火柴等物。圆桌的两侧,置有沙发椅两把,和别的几把西式小椅。壁上挂的是西洋油画和相片。这些西式物件表征着人物的资本家身份和地位。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律师吕有光(《盲妻》),他的家庭布置也充满现代气息:室内前方偏左有小圆桌一个,桌上放着纸烟盒等零星物品,桌的两旁有两只小沙发……桌上摆着许多书,夹板,纸张和文具皮包、电话机、坐灯等……在左边门的外方是一排书架,架里满排着金字洋装书。剧作者以西洋、西式作为都市家庭的风格,实际上已经将西化、现代、进步做了等号处理。
机器的大量使用、工厂的大批出现,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机器在改变传统生活模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对殖民地人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日伪为掌控满洲经济,大量掠夺钢铁、煤炭、石油等资源,并制定两次“产业五年计划”,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不少剧本站在民族性的立场,揭露现代化工业运营背后残酷的剥削制度,以及日伪强制征集劳动力,奴役与迫害工人的殖民危害性。在《诗人与工人》中,衣食无忧的诗人认为矿工的生活一定丰富精彩,可作为自己诗作的灵感与素材,但是矿井工人却给他展示出一副惨无人道的苦难图。在“热炉子般的太阳蒸着一切”的天气里,工人们仍旧要赶去做工。在“监牢”一样的矿井中“爬进爬出二十年”,“没有春,没有秋”,还要“挨饿挨冻”。可得到的依旧是“闭在地狱里、淹死、烧死和饿死”,亲人们“逃的逃,死的死,成天挨骂挨打的有力没力也得下地窑里去”。而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工人最后为诗人描绘的“有趣”的场景:“几十百个老少吊下去,后半段的人踏着前半段先下去的家伙的尸身,和野狗般贱的死人,被绊着也跟着摔一跤,有的爬了起来,有的再绊着别人,有趣呵……”即使这样残酷的工作,也时刻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而一旦失业,生活将走向更加黑暗的深渊。伪满剧本中大量充斥着这样的失业工人:冬夜游荡在外的乞婆和洋车夫,均是因工厂停工而生活窘迫的贫民(《市场风波》);《受难者群像》中的张妇有孕在身,丈夫原是电灯厂工人,前年被裁工,为帮丈夫多赚钱而小产住院;曾是铁道职业人员的张叔度在失业后成为精神病院的患者(《两个阵营的对峙》[7])。剧作者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工业对工人的压榨,直指伪满所谓“王道政治”的虚伪与荒谬,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控诉与批判。但是在《复活新生命的人们》[8]一剧中,我们在注意到机器给工人带来恐惧感的同时,能够发现对现代性的另外一种认知。机器是工人们赖以生存但又危机众人性命的器物。工人壮飞的父亲被机轮子轧断腿而死亡,他却还要为了生存不得不继续面对可怕的机器、忍受工头的欺辱,以致他将工厂冒出的黑烟看做自己的命运。但是作者并没有将运用资本和暴力压迫劳工的工厂厂主作为批判的对象,也没有深究民众面对现代机器所表现出的无所适从的根源性因素,而是将“壮飞带领众工友到新的地方满洲去,在满洲复活新生命”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中可见,剧作者的根本意图并非是为了探究现代化在进入殖民地社会后所引发的矛盾与纠葛,而是站在殖民者的角度上,营造“满洲国”的和顺假象,并与伪满之外的“残酷”世界形成对比,表现出对殖民性的认同态度。
伪满剧本中出现的更具代表性的现代性符号当属“铁路”,它是日本进行殖民侵略的重要通道,是把持与控制满洲的命脉线。日伪利用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逐步夺取了东北铁路的路权,并且建设大批新的铁路,从而控制满洲经济市场的运营,辅助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侵略活动,参与文化殖民。但是在大部分涉及铁路的剧本中,剧作者仅仅将其作为单纯的交通工具,并没有关注到与现代化交织在一起的殖民性特征。或者可以说,作家在艰难时世下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对铁路所具有的文化寓意的反思,以一种单纯的、赞美的态度来表现对铁路的认同。甚至出现一类专门表现铁路生活的“爱路剧”,尤以《同轨》杂志为主,赞美日本在满的铁路铺设为人们带来的便利和富足,而最终指向都是为日伪大唱颂歌。剧本《同轨之光》中,剧作者将未铺设铁路线的村庄比作“未开化的民族”,铁路的铺设起到了启蒙、教化的作用。“自从发展了山林,铺设了线路,建筑了车站,因为交通的便利,就是这样偏僻的农村,也接受了文化的洗礼,人民的智识,一天比一天的浓厚了,知道了互相亲和。”而这“启蒙者”、“施恩者”无疑是指向日本。在这里,铺设铁路代表的是在现代性照耀下的一种先进和优越之感,而未铺设铁路则意味着愚昧与不开化的落后。这实际上已经将殖民性完全等同于现代性,看不到或者拒绝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将认同现代性、服从殖民性的观念写进剧本中。“以后更成立了爱护村,组成了爱路团,匪贼才失去了立足之地,这村中的人民才能够安居乐业,开发了这无边的丰腴的田园!所以说,铁路所负的使命,不仅是便利交通,而且是沟通文化在使民族的强盛,和国土的开发呢!”伪政府极力倡导人们爱护铁路,不断向民众灌输:“铁路是我们的命脉,爱护铁路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9]而被殖民者应该或者可能存在的反思现代性、批判殖民性的意识被掩埋。表现在“爱路剧”中,剧作者往往设置爱护铁路与破坏铁路的两股势力,在两者的斗争中突显民众爱路护路的牺牲精神。青年民(《同轨之光》)不断向众人解说伪政府铺设铁路的政策和功绩,发现有人企图拆毁轨条、伤害旅客,便组织村民阻止破坏铁路的行径。放送剧《肉弹发雷管》更是塑造了被称为“爱护铁路、爱护人类第一人”的葛布街老甲长,他时刻担心铁路的安全,发现路基被大雨冲坏,便秉持着“为了爱护人类,为了爱护铁路”[10]的理念,将自己当做“肉弹发雷管”,想用自己的身躯阻止火车。这些人物无血无肉,徒具外壳,是伪政府“爱路”概念的化身。
二、教育、法律及警察制度
教育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它与最广泛和最普通的民众发生关系,对教育的把控是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文化专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教育”作为制度的代表,成为伪满殖民现代性的表征之一。伪满洲国建立之初,由于日伪的疯狂镇压和社会动荡,东北地区的学校数量骤减,在校人数也直线下降,“私塾”教育成为中国学生继续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这种教育模式很快遭到变革,日伪提出“改革”教育,建立“新学制”,要求学生重回学校,接受殖民教育。从社会发展的实际角度考虑,私塾式的传统教育难与时代对接,公立学校确实有助于教育公平和社会进步,因此在殖民现代性的裹挟之下,进入学校读书成为接受现代文明的主要途径。在涉及学生教育、学校教学的剧本中,剧作者往往侧重描写学生在接受现代教育后的良好品行,以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剧本《忏悔》中的十二岁学生士信在教室内踢足球,不料将教室的玻璃打得粉碎。经过教师的教诲,士信终于勇敢的承认错误。剧本结尾教师“搬过士信的头,在颊上用力的亲吻了一口”[11],这种温情式的教育方式是与传统的严肃的教育理念形成差距的。同样的教育方式和师生关系也出现在剧本《发奖》中,先生不但奖励学习成绩优异的荷西以书、铅笔、橡皮等文具,还关怀荷西的贫寒家境,供其学费,并同样以“搬过荷西的头,用力的吻了一口”[12]表达师生情谊。剧本专注于表现学生对学校、对教育的渴望心理,而对日伪教育制度中的强制性、不公正性,以及殖民奴役性少有触及。同时有意将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相对比,将笔触放在对现代教育的赞美与对传统教育的鞭笞上,模糊和消解伪满教育的殖民性特质。剧本《两个时代》以伪满成立作为新旧时代的分界线,凸显伪满教育的现代性与人性化。从学校课堂的布景对比:旧式教育是弊陋的教室,桌椅均不完好和整洁,黑板上边挂着总理遗像和遗嘱;新国学校校舍庄严,桌椅整齐,满壁贴着新标语。从教师的态度对比:旧式教师“拿着不少破旧的书本子和粉笔”,走进教室,便叫学生“缴纳茶资和前天糊棚的纸费”[13],无钱缴费的学生只能辍学在家;新的教师向学生介绍伪满的“王道政治”,并且不收学生的费用。在看似现代化的教育之下隐藏着日伪的殖民性,日伪废除原有的教材,换成殖民主义的教材,将“国文”课变为伪满“建国精神”教育,中国民族文化教育被取消。剧本《穷教员》[14]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日伪统治之下的满洲教育现状。对于像教员甲这样的普通小知识分子来讲,伪满所谓的现代性教育制度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更不用提及心理及精神需求。本以为“索薪团”能够为自己带来希望,但是当局却充耳不闻,教员们不得不组织罢课。剧本《谁是博士》讽刺了现代教育制度下培养的两个留洋博士。一个是“英国新学说博士”拍基夏斯,专门研究“拍马屁的哲学”:“带着手套拍马的屁股,马若扔起腿来,正好可以擦擦马的蹄子”。另一个是“国立吹牛大学”的校长博士崔,创立了自己的“吹牛的哲学”:“牛一经吹,不是大腹便便吗?那么一来,人们便都以为是庞然大物了。”[15]剧作者以夸张和荒诞的手法揭穿伪博士的真面目,揭露教育的虚伪性,将伪知识阶层的空虚与道貌岸然展示出来。
另一个制度性的殖民现代性标签应属法律。日伪在满洲制定了严苛的法律体系和警察制度,以更好的加强对伪满的殖民统治,在此时期的剧本中,经常可见到涉及法律的情节与人物。法律作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接受,剧作者在关注法律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的同时,也指出殖民法律的虚伪性。同样是在剧本《谁是博士》中,博士崔与博士拍因为争夺一女子闹上法庭,本想在庄严的法庭之上,让公正的法官予以裁决。不料法官竟是徒有虚名的幌子,得知博士崔留洋归来,任职“吹牛大学校长,兼空军第五师参谋长”时,立刻呈现出谄媚状。当博士拍美言称赞其“将来必由地方法院升到高等法院、由高等法院升到大理院、再由大理院升到立法院”时,法官又飘飘然忘乎所以,连最基本的法律条文都不知道了。剧本《生死漩涡》[16]本意是劝导人们“体察人生、观察社会、常阅报纸”,但是其中有关法律的探讨,也许更令人深思。被迫做女招待的桂玲在走投无路之下,开枪打死了曾经诱骗并抛弃姐姐、现在欺凌自己的摩登男子胡维生,受到法律的制裁。剧作者设置了兄妹二人作为旁观者探讨此事,在报馆作编辑的哥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神圣,而还在上学的妹妹质疑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并提出在“人类的道义、社会的秩序,都直接间接的给予”胡维生这样的人的社会中,弱者该如何寻找出路的问题。同时,对于法律制度的外化代表——“警察”,剧作家也进行了反思。与殖民地法律一样,警察也同样是只保护强者、欺凌弱小的虚伪工具。在《艺术家与洋车夫》[17]中,面对发生争执的洋车夫与艺术家,警察难以断案,原因在于事件发生在“李公馆”门口,警察难以断定艺术家是否是“李公馆家的人”,担心得罪权势。而在肯定了艺术家与李公馆没有关系后,警察也就对此事不了了之了。剧作者以一个幽默而巧妙的细节讽刺了警察的虚伪,以及其背后整个法律制度的失衡。
三、语言
伪满时期,日伪在文化教育上最重要的同化工具是语言,即在满洲普及日语的运用。语言,并不仅仅是人们简单的交流工具,它直接关系到人的思维逻辑,以及整个社会和民族的统一性。因此,根除被殖民地的原始语言,重新灌输殖民者的语言成为文化殖民的重要方式。日伪在满洲中、小学课堂中增添日语教学,在各机关和学校组织日语补习班。同时制定新学制,将日语定为“国语”,实行日语“检定制度”,试图通过语言的渗透和改变达到文化殖民的目的。对于殖民地来讲,这种语言同化并非是平等的,语言的殖民意味着殖民者将自认为更高级的文化价值观念输送至较低级的被殖民者中,而被殖民者对语言的认同也即表征着对殖民性的接受。在不少剧本中,我们都能看到对日语学习的重视。
《农家的乐趣》中父亲教育女儿:
(女儿)改子:放着好好的书不念,学日语干什么?
(父亲)万年:你这混丫头,刚才说什么来的?不是说日本国和咱们好的像一国人似的。你想要是两个人非常的好,就是我说什么你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呀(也)听不懂,你说憋闷不?你这时明白了没有。
改子:爸爸那么明儿我也得学日语。[18]
《在你自己的判别》中小学生自我觉悟到:
沈聪明:“日语是主要的一门学科,也是日满一德一心的唯一工具,如果我们日语不好,不但个人的发展是无大希望的,就是日本的关系,也无从增进。”[19]
与之相对,被殖民者对本土语言的使用和坚守也可以看做是对殖民者的文化反抗。语言的殖民并非一朝一夕或单纯依靠殖民者的主观意愿就能完成的,因此在伪满社会中出现了中文和日文混杂的“协和语”,或者称之为“日满语”。正如山田清三郎所解释的:“所谓‘日满语’,是指在开拓地产生的满语和日语混合的产物,例如把多吃好饭好菜说成多多米西米西之类”。[20]在一些剧本中,剧作者将“协和语”巧妙的运用到民族想象中,借以表明民族性的立场。短剧《黎明》中,一伙匪军冲进了一户农家,剧作者没有写明匪军的性质,但是通过语言透露出人物的身份,读者可以很快判断所来之人是日军。
匪军甲:(狡猾地)当兵的没有?枪的没有?有的拿出来,不怕。
少妇:(强作笑容)没有,什么的没有。
匪军乙:(污蔑地狞笑)哈哈,什么什么的没有?窑子的没有?什么什么的没有?窑子的好。景票知道?景票,我大大的有,哈哈……[21]
同样的手法也表现在剧本《流民三千万》中,“老百姓总是谦虚地模仿着外国兵的口气说:‘我的满洲国人。’可是外国兵一走开,我们的百姓还是讲着中国话,讲他们心里的苦处。”[22]既显示了百姓的生存智慧,也折射出伪满社会的残酷环境。
伪满洲国时期,戏剧从物质、制度、语言等多层面对殖民现代性景观进行书写与想象,透过对这一景观的审视,我们能够感受异质时空下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不同认知态度,有效体察伪满戏剧中复杂而独特的文化内涵。
注 释:
[1]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
[2]刘远弘.岂有此理[N].大同报.1935.11.26,12.10、14、27-29,1936.1.10-12.
[3]杨柳青.盲妻[N].滨江日报.1941.5.23、30,6.12、13、20、27,7.4、11、18.
[4]芳菲.诗人与工人[N].大同报.1935.5.29、31.
[5]王凝.市场风波[J].新满洲.1940.7,2卷 6号.
[6]王突.受难者群像[J].新青年.1938年7卷1期.
[7]洛虹.两个阵营的对峙[N].大同报.1933.8.6.
[8]朱牧.复活新生命的人们[N].大同报.1936.2.28、29,3.1.
[9]同轨之光[J].同轨.1943年10卷8期.
[10]肉弹发雷管[N].盛京时报.1940.3.28.
[11]何任公.忏悔[N].大同报.1934.8.13.
[12]何任公.发奖[N].大同报.1934.8.23,9.4.
[13]瑞海.两个时代[N].大同报.1935.12.17、24,1936.1.14、21,2.4.
[14]金剑啸.穷教员[N].大同报.1933.9.3、10.
[15]若怯.谁是博士[N].大同报.1935.9.27-29,10.1、3.
[16]鹏子.生死漩涡[N].大同报.1939.9.6-10、13.
[17]金剑啸.艺术家与洋车夫[N].大同报.1933.11.12、19、26,12.3、10.
[18]周效频.农家的乐趣[N].大同报.1935.10.29,11.5、12、19、26,12.7、8、11.
[19]在你自己的判别[J].建国教育.1939.11,5卷11期.
[20]山田清三郎.若草山.北满的一夜.P167,万丽阁1941.4.1.转引自[日]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176.
[21]星.黎明[N].大同报.1933.12.24.
[22]塞克.流民三千万[J].文学丛报.193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