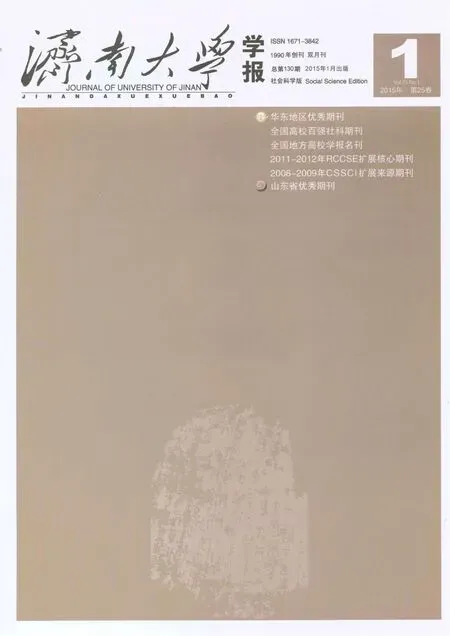《墨子》巧用《诗》《书》立新说
——兼论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2015-04-14董芬芬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墨子》巧用《诗》《书》立新说
——兼论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儒墨两家都言必称《诗》《书》,但《诗》《书》在墨家更多是可以证成自家学说的历史、故事,墨家在援引的同时有意进行改编、拼接。墨家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对《尧典》的改编。儒墨两家都讲禅让,儒家侧重于“死而禅”,而墨家强调“生而让”。顾颉刚对儒家“唐虞禅”叙述的质疑,是因为不明儒墨两家禅让故事的区别,其认为《尧典》是墨家禅让说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本末倒置。
《墨子》;《诗》;《书》;禅让说
一、《墨子》对《诗》《书》的改编
墨子认为直接论证自己的观点,未必能达到目的,而援引其他故事,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因此他提出“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利。”(《非命中》)墨子对“先王之书”非常看重,认为要了解先王的作为,必须去读先王之书。墨子勤奋好学,据载他南游卫国时,车上载书甚多,还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贵义》)墨子开宗立派,必须要在传统经典中寻求支持。
墨家主张“非命”,故对占卜命运之《易》很少提及;其“非乐”思想使他们对《乐》兴趣不大;墨家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礼》往往成为他们批判攻击的对象。所以,传统经典中《墨子》援引最多的就是《诗》《书》,大概引《诗》11处,论《诗》4处,引《书》29处。[1](P83,P160)《墨子》大量援引《诗》《书》,体现出墨家对传统经典的倚重。《诗》《书》在孔子之前虽无“经”名,实际已被奉为经典,《左传》所载春秋大夫们的辞令及“君子曰”“孔子曰”等,常以《诗》《书》中的句子作为论断性的结束语,赋予《诗》《书》以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在《墨子》中,更多把《诗》《书》作为历史故事来征引。
叙事性强、有一定的情节,是《墨子》援引《诗》《书》的第一个特点。如《墨子·尚同中》:
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当此之时,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即此语也。古者国君诸侯之闻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
“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出自《周颂·载见》,下文所引是《小雅·皇皇者华》中的句子,用来说明古代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后世,是因为他们尚同的缘故。所引诗句在这里营造出这样的情景:诸侯驰驱朝聘,争先恐后受教于天子,闻善与不善皆要奔走报告天子。《诗》在这里不是结论,不是权威,而成了显示古代圣人尚同的历史故事。
郑杰文先生说:“《墨子》引《诗》11条中,有7条将《诗》句所述作为历史事实来对待,认为《诗》可反映历史,并以此所反映的史实作为说理的重要论据,来证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对《诗》的作用的认识,这种引《诗》方式,都表现着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2]“以《诗》为史”比较准确地指出《墨子》引《诗》的趋向,《雅》《颂》叙事性强,有情节,历史价值高,更利于墨家的以《诗》证史,所以,《墨子》所引11处诗,除了3处逸诗外,另外8处皆出自《雅》《颂》,有1处引《周颂》,5处引《大雅》,2处引《小雅》。[1](P83)《风》诗抒情性强,历史故实少,不大符合《墨子》对故事性、历史性的要求,故很少征引。
《墨子》引《书》也重其故事性、情节性。如《兼爱下》论兼爱之道乃取法于禹、汤、文、武,故引《书》之《泰誓》《禹誓》《汤说》等为证。其中所引《汤说》如下:
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即此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
墨子引用《尚书》中汤祷雨的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语言,甚至把祷雨辞全文引用,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能以身为牺,祠说于上帝鬼神,《墨子》用这个故事证明商汤的兼爱,说明兼爱本源于古代圣王。
为了突出历史性、故事性,《墨子》在大量引证《诗》《书》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一些调整改编。《墨子》会把本不相连的诗句拼接在一起,以追求比较完整的故事效果。如《兼爱下》:
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这里所引出自《大雅·抑》一诗,“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是《抑》第六章中的句子,毛诗作“无言不雠,无德不报”,这章告诫人们要出言谨慎,话一旦说错就不可弥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出于此诗第八章,这章告诫人们要修德,举止要谨慎美好。虽然出自同一首诗,却原本分属两章遥遥相对,上下文的意思也略有不同,而《墨子》把这四句凑在一起,完成了一个投桃报李的故事,说明报德报怨的道理。意思连贯自然,不仅没有改变原诗句的基本意思,还更加强了诗句的叙事性、故事性。
为了构造比较完整的情节,《墨子》不仅在同一首诗中进行诗句的重新组合,甚至在《诗》《书》之间也做些改编拼接。如《兼爱下》:
《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
墨子所谓的《周诗》,其实前四句引自《书·洪范》,原作“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是说不要结党偏私,要遵行王的正道。后四句引自《小雅·大东》,毛诗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结合上下文来看,说的是“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境遇,算是牢骚话。两处合在一起却表达出这样的意思:文、武兼爱天下,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行走在不偏不党的王道之上,没有偏私,这就是文王、武王兼爱的证明。不得不承认《墨子》这里的剪裁拼接,显得非常巧妙自然,如果不去查证,会以为真有这样一首诗呢。显然,《墨子》这里表达的意思与《大东》一诗原意不同。
墨家视《诗》《书》为史,合理拼接出更为完整清晰的情节,也没什么奇怪的。《墨子》所引之《诗》,在章次、语句、字词上与汉代四家诗有出入,郑杰文先生认为“说明战国时期有多种《诗三百》版本在流传”[2],可能有这种情况,但也更多存在着《墨子》有意拼接、改编的情况。《诗》《书》在墨家眼里是历史典故,在忠实大意的基础上变换个别语词,调整一下句子的顺序,也是平常之事。《墨子》改编后的《诗》《书》自然巧妙、浑然天成,可见他们对《诗》《书》下了很大的功夫,烂熟于胸,才能如此自由援引,合理拼接。
六籍正典本来就是古史,且古代视六经为史、六经为器的不乏其人,如清人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正典也。”[3](P1)《诗》《书》都是三代行政的史实,虽然被儒家奉为经典,但《诗》《书》皆成于孔子之前,是春秋战国读书人必须接受的教育内容,乃天下之公器,并非为儒家所独有。《诗》《书》包罗万象,意蕴丰富,后人见仁见智,都可以从中挖掘出自己需要的东西,墨家也不例外。《诗》《书》本身突出的历史性、故事性,正是吸引墨子的地方,也是《墨子》立说的首选材料。
《墨子》援引《诗》《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以虚为实、多涉鬼神。这也是墨家与儒家及其他诸子最不同的地方。墨子宣扬明鬼、天志思想,《诗》《书》中的鬼神片段,成了墨家立论的至宝。
如《明鬼下》:
《周书·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有周不显,帝明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
这里所说的《周书·大雅》,其实就是《大雅·文王》一诗,颂扬了周文王的丰功伟绩和美好德行。说文王神灵上升天庭,陪在天帝左右,这是古代宗教中祖宗崇拜的情结与观念,体现出诗人对文王深厚的感情和美好的祝福,同时,也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文王在天帝的左右,会庇佑人间的子孙永享天下,传达出君权神授的意思。这些诗句出于作者的想像、意念,是虚写,并非真的在为鬼神写实,但墨子把它当做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来证明鬼神的存在。
《明鬼下》引用《商书》中“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宁”句子,说明大禹的成功,也有山川之神的佐助,这是《商书》之鬼的证明。《夏书·禹誓》勉励将士奋勇作战,提出有功赏于祖、有罪僇于社,故《明鬼下》全文引用《禹誓》,作为《夏书》之鬼的证据:“故古圣王必以鬼神为赏贤而伐暴,是故赏必于祖,而僇必于社。”既然《周书》《商书》《夏书》都有鬼神的记载,在墨子看来,则鬼神必定实有。
墨家认为天有意志,能够赏善惩恶,《天志中》说:
《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
《皇矣》是一首周民族史诗,叙述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的历史,但诗作者却把这些历史从上帝监督、授意的角度讲述出来,以示天命所归。墨子以“帝谓文王”为信史,并加上自己的补充叙述,完成了文王顺从上帝旨意而受到嘉奖的故事。同篇中还引《书·大誓》纣王的故事,说明天所以抛弃纣王,就是因为纣王不尊从上帝。文王顺天意得赏、纣王反天意受罚,《墨子》用这两个故事,证明天志的不可置疑。
《诗》《书》中有许多地方写到天帝鬼神,有些是夏、商、周鬼神信仰盛行的时代烙印,有些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意在制造出神秘宗教色彩,来震慑人心,稳定统治。春秋战国人们对鬼神的怀疑,这是古人理性思想战胜迷信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在维持传统祭祀之礼与强调人的因素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点。对《诗》《书》中的鬼神内容,儒家往往会绕开,存疑不论。墨家却视其为至宝,充分利用,借以宣扬鬼神、天志思想,使得墨家的尊经带上一层“异端”的色彩。
春秋战国之交,赋《诗》余响不绝如缕,《诗》《书》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典,墨家要证成自家学说,《诗》《书》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既可以使得墨家学说易于为世人接受,也在批判儒家方面收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墨子》以《诗》《书》为史,虽然对儒家所赋予的经典性、权威性有所消减,但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对“先王之书”的倚重和尊崇。《诗》《书》在墨家眼里是历史故事,与志怪野史、小说寓言一样,皆可随意资取。
二、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尧舜禅让的故事,是墨家利用和改编《书》最巧妙、最成功的一例。
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4](P30-101)一文,搜罗春秋战国时代关于尧舜禅让的材料,旁征博引,逐条考辨,认为尧舜禅让的故事传说起于墨家,是墨家为宣扬尚贤思想而炮制出的故事。童书业也说:“尧舜禅让说经墨家的鼓吹,渐渐成熟,流入了儒家的学说中。”[4](P22)而对《尧典》《论语》及《孟子》等儒家典籍中尧舜相禅的记载,他们一并质疑。顾颉刚以为《尧典》写定于汉武帝时代:“到了汉代,禅让说已渐征服了整个的知识界,差不多人人都以为这是真事了,于是这件故事便需要一次最后的写定。汉武帝时的儒者就起来担任了这工作。”[4](P96)他还借崔述《唐虞考信录》对《论语·尧曰》中“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章的怀疑,认为“这章确实不是儒家的话”[4](P59),甚至认为《孟子·万章上》中所引孔子的“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也“恐非《孟子》本文”。他骂孟子“扭扭捏捏躲躲藏藏”:“一方面说唐虞不是禅,一方面又说唐虞禅。”[4](P82)顾颉刚的逻辑是:既然已经明确禅让说起于墨家,那么儒家经典中所有关于“禅”的表述,则全部应该被怀疑否定。
顾颉刚把先秦典籍中关于尧舜禅位的材料几乎罗列殆尽,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漏掉了《左传》中的材料。《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了鲁国季文子的一大段辞令,大谈特谈舜举八恺八元,流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凶族的历史功绩,然后说:
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左传》季文子所引《虞书》各句,见于今天古文《尚书》的《舜典》,今天的《舜典》其实就是原来《尧典》的一部分。春秋时代人根据《尧典》的记载,认为尧死后,天下人拥戴舜,于是舜继尧为天子,这同《孟子》的说法相一致。《孟子·万章上》说:
《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还说:
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河南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孟子》一书保存了许多《尚书》的内容,有时直接引用,有时间接转述。从上下文及所述内容判断,后一段也出自《尧典》篇。《左传》和《孟子》关于尧舜相禅的认识,皆来自《尧典》。司马迁《五帝本纪》写尧舜禅让,与《左传》《孟子》的记载大体相同,说明春秋战国及汉代人见到的《尧典》篇,对尧舜的叙述基本一致。
20世纪90年代先后面世的战国楚简,如上博简中的《子羔》《容成氏》,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都谈到了尧舜禅让之事,专家们多以为这些篇目形成于孟子之前。有学者指出《唐虞之道》是现今所见先秦儒家文献中集中论述其“禅让”说最早的一篇专论。[5]可见,孟子之前的儒家学者,也是讲尧舜禅让的。
《论语·尧曰》篇:“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无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也应该是《尧典》中的片段,今本《尚书》没有这几句话,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尚书》就没有。顾颉刚说“尧曰”章不是儒家的话,郑杰文先生认为顾说站不住脚[6]。《尧典》原本就有尧舜相禅的记载,孔子、孟子从来没有否认“唐虞禅”的故事。除《论语·尧曰》篇外,孔子还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也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孟子·万章上》)可见,孔孟皆承认“唐虞禅”的事实。
《尧典》在流传至今的古文《尚书》中分成《尧典》《舜典》两篇,今本《舜典》说: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尧发现了舜,提拔了舜,经多年考查,证实舜的确有才干,尧提出让位于舜。舜辞让不肯。在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二十八年后,帝尧死,百姓如丧考妣,三年丧期后,舜到尧庙谋划政事。这就是今天看到的《舜典》中关于尧舜禅位的记载。《左传》《孟子》《史记》关于尧舜的记载同今天所见《舜典》基本一致,说明《舜典》原本为《尧典》的一部分,流传过程中虽有遗失,但保存下来的这些文字是可靠的,基本能反映出原来《尧典》对尧舜禅位的记载。
顾颉刚对孔子关于“唐虞禅”说法的否定,对孟子“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批评,主要原因是没有弄清楚儒墨两家尧舜禅让故事的区别。
孔孟皆承认“唐虞禅”的事实,但是,当弟子就这个问题请教孟子时,孟子又是另一番说法。《孟子·万章上》: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既然《尧典》中有尧舜相禅的记载,而孔孟又都承认“唐虞禅”的事实,为何当万章向孟子提问时,孟子又断然否定了呢?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孟所讲述的“唐虞禅”与墨家宣扬的“禅让”并不是一回事。韩非批评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韩非在批判儒墨的同时,也清楚地指出两家眼里的尧舜“取舍不同”。
今本《尚书》中关于尧舜的叙述有模糊的地方:在被尧提拔重用之前,舜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舜“受终于文祖”之后到尧去世前的那二十八年,尧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舜是践位还是摄位?《尧典》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笼统,给了墨家加工改编的空间,也成为儒墨分歧的关键。
《墨子·尚贤中》说:
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鱼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家主张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又说:“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同上》)所以,在墨家的故事里,舜是起于耕、陶、渔、贩之庶人,因其贤能,得到尧的举荐而为天子。出于对墨家说法的疑惑,孟子的两个弟子都请教过这个问题。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咸丘蒙问:“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万章上》)换句话说,“尧以天下与舜”“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都是墨家后学对禅让故事的进一步演绎。所以,墨家的禅让故事比《尧典》多了两个情节:一是舜耕历山、陶河濒、鱼雷泽的庶人身份;二是舜在尧还活着的时候登上天子之位,而尧却做了舜的臣下,率领诸侯北面事舜。在墨家的禅让故事中,突出尧的“生而让”,墨家通过这个故事把尧的尚贤让贤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墨家的尚贤主张,顺应了战国时代的潮流和社会变革的要求,尧舜禅让作为尚贤的典范,也广为流传,连儒门弟子都颇感疑惑,墨家此说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战国楚简如《容成氏》《唐虞之道》所述的禅让故事,显然也受了墨家的影响:“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7](P157-158)可见,在孟子之时,儒墨关于禅让的说法越来越相似,正如彭邦本先生指出:“两家的学说有相同的议题、话语以至近似的主张,彼此互有影响并汲取过对方的智性资源。”[5]甚至孟子自己也深受墨家的影响,如“舜发于畎亩之中”(《孟子·告子下》),这是对墨家第一个情节的认同。
但对墨家的第二个情节,孟子坚决予以否定。孟子认为尧荐舜于天,天受之,民拥戴,舜践天子之位是尧丧三年之后。孟子说,如果尧在世而舜践天子之位,居尧之宫,逼尧之子,这就是篡位。关于尧晚年的那二十八年,孟子认为是“尧老舜摄”,他依据《尧典》来驳斥墨家炮制的“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的说法。
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孟子·万章上》)
孟子依据《尧典》的记载,以为尧晚年让舜主政、主持祭祀的二十八年,舜只是摄政,而非践位。不仅尧活着的时候舜未践位,甚至尧死后三年丧期,舜依然未践位,舜正式登上天子之位在尧三年丧期之后,这就是儒家的禅让故事。
两家都讲述禅让,但墨家侧重的是“生而让”,孔孟强调的是“死而禅”。孔孟所谓的“禅”,是尧死之后,由他生前选定的贤者舜继位,而不是由尧的儿子丹朱继位。孔子把由贤人继位叫做“禅”,把由子孙继位叫做“继”,所以他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孔子认为,无论是“禅”还是“继”,只要符合各自的社会礼制,都是合理的。儒家的“唐虞禅”是与“殷周继”相对的概念,与《左传》季文子“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的说法一脉相承。所以,孟子没有自相矛盾,也没有“扭扭捏捏躲躲藏藏”,他借孔子之语大大方方地承认“唐虞禅”,但坚决反对墨家编排的“尧以天下与舜”“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的“生而让”情节。
儒家的“唐虞禅”符合尊贤理想,而墨家的却是出于尚贤的主张。尽管墨家的尚贤与儒家的尊贤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墨家“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的说法,却严重违背儒家的崇礼及“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思想,不仅孟子坚决批判,荀子对此的态度更为激烈。《荀子·正论》篇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指斥禅让说是“虚言”,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孟子反对禅让说,但承认“死而禅”,荀子却从隆礼的角度,连“死而擅之”“老而擅之”也一并反对,表现出比孟子更为决绝的态度。
所以,顾颉刚对孔子语的质疑,对孟子“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批评,是没有对儒墨两家的禅让进行仔细分辨。儒家依据《尧典》的叙述,认为“尧老而舜摄”,尧死后甚至是三年之丧期满以后,舜才践位,是“死而禅”。墨家把它改编为“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的“生而让”。墨家的改编如此成功、高明,使得后人把《尧典》也说成是墨家的作品。
孔孟对《诗》《书》等六籍经典,向来持无比虔诚、尊崇的态度,孔孟所引《诗》《书》皆比较规范、可靠。因为现在看到的《尚书》几经劫难散佚,有太多后人的补苴,孔孟所引之《书》也显得更为珍贵。而墨家向来视《诗》《书》为工具,为历史故事,对传统经典没有儒家的那份严谨,他们取其所需,资以为说,常常以虚为实,随意改编,篡改《尧典》中“死而禅”炮制出“生而让”的故事以宣扬尚贤的思想,这对墨家来说也算稀松平常。所以,墨家的禅让故事是他们利用经典、改编经典最为成功的一笔。《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家的学说来自儒家却又不同于儒家。郑杰文先生也认为从学术传承上讲,墨子的尧舜禅让说来自孔子而有所发展。[8](P222)如果把《尧典》看做是墨家影响下的产物,则是本末倒置。
[1]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M].济南:齐鲁书社,1994.
[2]郑杰文.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J].文史哲,2006,(1).
[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七(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彭邦本.楚简《唐虞之道》与古代禅让传说[J].学术月刊,2003,(1).
[6]郑杰文.禅让学说的历史演化及其原因[J].中国文化研究,2002,(1).
[7]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8]郑杰文.郭店竹简《唐虞之道》与儒墨“禅让说”之比较[C]//刘大钧.简帛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杨旻
B224
A
1671-3842(2015)01-0034-06
10.3969/j.issn.1671-3842.2015.01.07
2014-06-18
董芬芬(1968—),女,甘肃庄浪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10&ZD103);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青年教师科研提升计划骨干项目“《左传》编纂经历与学术地位变迁研究”(SKQNGG1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