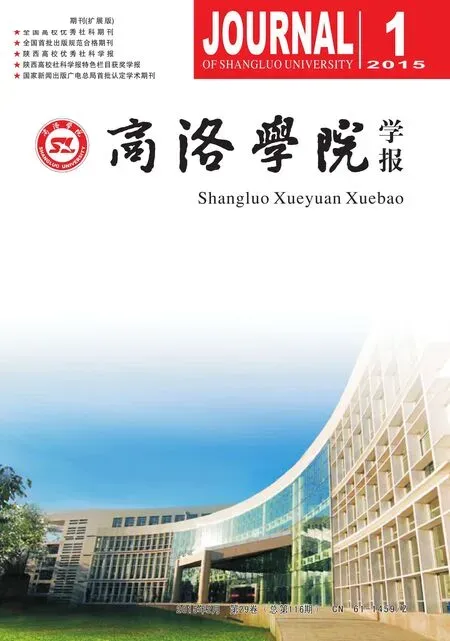唐婚恋传奇中的父母形象
2015-04-11王卫
王卫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唐婚恋传奇中的父母形象
王卫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以往研究者多从唐婚恋传奇的文本出发,在评价其中的父母形象时谴责多于谅解。然结合唐代复杂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汲汲于科举仕进的巨大热情,崇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力量,严格的婚姻制度,崇尚士族而以五姓为贵的婚姻观念等这些因素去探讨这些作为家族利益捍卫者的父母形象,他们在干预子女婚恋时确实呈现出了专制与冷酷,然这专制与冷酷既是受了那个时代集体性声音熏染的结果,又是维护家族利益的需要。因此仅对其严厉谴责而忽略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则有失公允,并且对全面审视父母形象及深入探讨唐传奇作品的艺术成就有弊而无益。
唐婚恋传奇;父母形象;社会环境;家族利益
在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唐传奇以绚丽多彩的内容与精湛的艺术手法,历来备受赞叹,堪称唐代叙事文学的奇葩。其中以青年男女爱情婚姻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下文均简称为唐婚恋传奇)最为精彩动人,代表着唐传奇创作的最高成就。而这些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形象最是光彩夺目,吸引千百年来的读者惊叹不已,研究者探析不止,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作者着墨不多,但对小说情节发展、主人公命运起着重要甚至决定作用的角色——父母形象。对此类形象以往的研究者尚无独立系统的论述,零星涉及的多于男女主人公悲喜剧的归因时,并存在谴责之声高于谅解的现象,由此以来,父母形象便成了唐婚恋传奇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一、父母干预和故事结局导致的误读
读者和研究者对唐婚恋传奇中的父母形象,多谴责而少谅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从相关作品的数量来看。根据李剑国先生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统计唐传奇有112篇,宁稼雨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记载唐传奇共118篇,笔者两相参照,对这一百多篇唐传奇作品进行仔细梳理,可归于婚恋题材的作品有51篇,占将近一半的数量。而在这51篇中涉及“父母”的作品有28篇,占该类题材总数的多一半;并且这28篇包括三大传奇——《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其余25篇(《河间男子》《郭翰》《枕中记》《张果女》《汝阴人》《刘立》《柳毅传》《离魂记》《南柯太守传》《崔书生》《秦梦记》《卢佩》《申屠澄》《樱桃青衣》《定婚店》《琴台子》《卢生》《张老》《裴航》《张无颇》《崔护》《薛媛》《华州参军》《无双传》《韦安道》)也是相关研究者提及较多的篇目。并且在这28篇作品中,父母对其子女爱情婚姻,都直接或间接地有不同程度的干预。
其次,从故事结局来看。笔者对这28篇作品结局审视后的结果是:悲剧8篇,喜剧16篇,正剧4篇。仅看各类剧的数量,会使人产生喜多于悲的假象。因为各类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具体如下:悲剧中《崔书生》《卢佩》《韦安道》这三篇是因为女主人公不见容于公婆而不欢而散;《郭翰》《华州参军》是因男主人公无父母做主而悲剧的;《莺莺传》是因为科举造成二人身份差距而悲剧收场的;《霍小玉传》是男主人公之母为其子另选高门卢氏而悲的。
喜剧《张果女》《汝阴人》《刘立》《张无颇》是父母均参与其中的阴阳婚恋,喜剧的力量较弱;《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这三篇是父母参与男主人公梦中的婚恋,喜剧的色彩更淡;《河间男子》《柳毅传》《离魂记》《李娃传》《张老》《裴航》《崔护》《薛媛》《无双传》这九篇是父母虽百般阻挠,而男女主人公则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得了幸福。因此,在喜剧中没有一部是父母从始至终全力促成的。正剧四部《秦梦记》《定婚店》《琴台子》《卢生》的共同特点则是主人公顺从地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平淡无奇。因此从文本出发,无论从数量还是故事结局来看,这些作品中的父母形象只有一张面孔——冷酷而专制的封建家长。
二、社会环境和家族利益成就的冷酷
可怜天下父母心,古今皆然,而这种理应如“三春晖”般的“父母心”在唐婚恋传奇中却以冷酷面目呈现,引人深思。但结合唐代的社会环境考察这些父母形象冷酷的根源,便使人豁然开朗。在社会环境因素中,深刻影响唐人生活的两个重要的因素是:科举制度与婚姻风尚。前者有助于改变人生的命运,后者有益于家族的利益。《唐语林》记载“薛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1]其“三恨”中前两个便涉及科举与婚姻,可见这两者在其人生中的地位。
首先,有助于改变人生命运的科举制度。学而优者则仕,是封建社会几乎每一个读书人理想。而在唐代,读书人这一理想的实现,则很大程度上凭借当时日趋完善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历史学家毛汉光在《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一文统计,在全唐366名宰相中(不计亲王及生平未详者10人,士族217人,寒门149人),其中经由科举入仕而拜相者达197人之多,占总数的61%。这些数据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极大地激发了时人对科举考试的巨大热情。上文提到薛元超的平生三恨,其中进士擢第处于第一位;中唐诗人王建在《送薛蔓应举》一诗中言:“圣朝开礼闱,所贵集嘉宾。若生在世间,此路出常伦。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晚诗人李频在《长安感怀》中更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如此情形比比皆是,由此可见,科举入仕对唐代士子个人、家族乃至整个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凭借科举,既可出将入相,又可光耀家族,因此无论出身寒门还是生于士族的父母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其中。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李娃传》,荥阳生的父亲常州刺史,虽“时望甚崇,家徒甚殷”[2]3985,但对知命之年才得的儿子依然寄予了把整个家族发扬光大的殷切希望,况且这个儿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2]3985,便对他“爱而器之”,并骄傲地对人称赞说“此吾家千里驹也”。之后又为其应举作了充分的准备——“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2]3985这短短的几句话,既包含了父亲对儿子的精神鼓励和殷切希冀,又有宽裕甚至丰厚的物质资助。戏剧性的是,故事的主人公荥阳生一到长安便忘了父亲的期待,浪荡烟花巷柳,甚至落魄为挽歌郎,让父亲的脸面丢尽,父亲以“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作为借口不愿认亲生儿子,后不得已见了儿子的面却说:“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2]3989甚至以“马鞭鞭之数百”,“弃之而去”,完全不顾人伦父子之情。最出奇的是故事的结局,荥阳生在李娃的爱心帮助和全力诫勉下,重新回到了社会认可的正途上——“生应直言极谏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三事以降,皆其友也”[2]3990,同时也回到父亲早先规划的仕途上,而获得父亲的重新接受——“吾与尔父子如初”。试想倘若荥阳生没有后来的“改邪归正”,那么这个故事皆大欢喜的结局就很难实现。
另外,本文所涉及的28篇传奇作品中,有13篇作品的男主人公都与科举有关,占总数将近一半。《莺莺传》中的张生因要科考而离开莺莺;《霍小玉传》中的李益因“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2]4008而与小玉拉大了门第距离;《枕中记》中的少年卢生在梦中“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县尉,迁监察御史起居舍人,为制诰”[2]527;《樱桃青衣》中那个“在都应举,频年不第”[2]2242的范阳卢子,听经入梦,便在近亲姑姑的帮助下“登甲科,授秘书郎”[2]2243……
诸如此类在唐传奇作品中比比皆是,在将科举视为士子人生正途的社会风气之下,这些男主人公对科举入仕的热衷无不映射着一个个封建家族的热切期待,而父母便成了这种风气的主推手。
其次,有益于家族利益的婚姻风尚。青年男女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而缔结婚姻关系,是中国古代婚姻的显著特点,甚至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着人们的婚姻生活。“唐代,立法者对礼法上的所谓‘媒妁之言’,从法律上明确地加以确认和规范,从而使嫁娶用媒正式成为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有无媒人成为婚姻是否合法的标志之一[3]。在此世风作用下,父母对子女婚恋行为的影响主要有四种情形:第一,强调婚姻命中注定——《定婚店》和《刘立》两篇作品不仅宣扬男女婚姻命中注定,而且前者中的男主人公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不成”[2]1142,后来在月下老人的指引下娶了王氏女方完成所愿;后者刘立与杨氏女的两世姻缘亦在岳父(赵长官)的帮助下玉成。其二,无媒即不成——《崔书生》《卢佩》《韦安道》三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均在无媒牵线无父母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娶了“神仙”妻子,即便这些女子姿容美丽,妇道甚严,孝顺公婆,并有助于家族利益,却最终都因不见容于婆婆而离去,可见连神仙也要屈服于人间的礼法。其三,无父母的男子似乎可以由爱而婚,《郭翰》《汝阴人》《窦玉》《华州参军》《无双传》这五篇中的男主人公均无父母做主,前三部的男主人公得以与异类女子由恋而婚,而后两部的男主人公与现实中女子的爱情婚姻则遭遇了离奇的波折一悲一喜结局。
严格的户婚制度是影响唐人婚恋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恩格斯指出:“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它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都没有的。”[4]75《唐律疏议·户婚》中明确规定:“奴娶良人为妻”条疏:“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即疏,何宜配合。”[5]269并对于违反这个等级规定的人予以处罚:“与奴娶良人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合徒一年。仍离之。”[5]269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在下的百姓必然顺其而行。可见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自由婚姻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故而导致了许多相爱男女离散的悲剧。《霍小玉传》中,男女主人的悲剧主要是由身份地位的差距造成的;《无双传》中,无双的父亲刘震为“朝臣”,岂能嫁女于“父亡”的穷书生,即使这个书生是自己的外甥,即使之前有婚约,在法律制度面前,亲戚之情和口头承诺都是苍白无力的;《李娃传》中的李娃之所以最终能为荥阳公所接纳,不仅因其有“李”姓,更重要的是其通过脱籍从良等一系列自纠行为,逐渐达到了社会所要求的标准。
崇尚士族而以五姓为贵的婚姻观念是影响唐人婚恋行为的第三个因素。唐代承袭了魏晋以来重视门阀的遗风,依然看重大族望姓,“唐太宗重修《氏族志》并非反对门阀制度,其目的仅在于建立李唐王室的新的世家大族的门第体系,来取代六朝旧的氏族体系……这一行为恰恰张扬了门阀观念。律有明文规定,则现实生活的婚恋必须严格遵循,这样从客观上也强化了人们对门第的崇尚。”[6]224可见连至高无上的皇帝尚想通过官修谱牒的方式来提高其家族的社会地位,更不用说一般的平民百姓。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到:“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7]“当时崔、卢、李、郑、王号称‘五大姓’,尤其崔、卢两姓,若能与其通婚,既是一种荣耀,也有利于以后的仕途。”[8]为子女妙选高门,可以扩大家族势力,作为家族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家长,便在干预子女婚姻时,常常无法兼顾其自由爱情,而造成了许多悲剧。《霍小玉传》中,李益之母为重振家门选卢氏为儿媳,便顾不得李、霍二人的山盟海誓,也没有考虑李卢二人的婚姻是否会幸福;《华州参军》中王生之父全然无视崔柳二人的真挚情感,为其子强聘崔氏;《枕中记》和《樱桃青衣》这两个故事中的男主人公邑中卢生和范阳卢生,对高门联姻的热衷更是登峰造极——现实中他们落魄不羁,然于梦中分别与崔氏女、郑氏女结合而得偿所愿。
除以上三类外,还有一类是父母完全从家族利益出发决定嫁女的。《定婚店》《琴台子》《卢生》《秦梦记》《申屠澄》《张老》《张无颇》这七个故事均属由父母做主,将女儿嫁人的作品,然其嫁女的情形各不相同——《定婚店》中,王氏之父王泰因属下韦固能干,将女儿许配给他;《琴台子》中,李希仲带领全家为避战乱而东迁途中,将女儿闲仪嫁于自己的官场同僚崔祈,根本没有考虑二人年龄的巨大差距;《卢生》中,李氏母因卢生悔婚,于是为挽回家族面子在仓促中嫁女于宾客;《秦梦记》中秦穆公因下属沈亚之军功卓著,而将女儿弄玉嫁于沈,作为对其军功的犒赏;《申屠澄》中,虎女父母因为“湫溢”而嫁女于申;《张老》中韦恕因愿赌服输而嫁女于园叟;《张无颇》中广利王嫁公主于恩公张无颇,作为对其恩德的报偿。其中前三例是现实男女的婚姻,后四例则完全是超现实的婚姻,然这七个故事的共同点是父母均以家族利益为先,婚姻关系中男女的自由意志几乎没有显现,唯对父母的安排一律甘愿顺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婚姻“是权衡厉害的婚姻……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4]74故而,在唐婚恋传奇中,父母对子女爱情婚姻走向的干预,更多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很少顾及当事人的真实情感和幸福与否,而呈现出专制冷酷的色彩。
三、结语
“婚姻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所承认的男女两性结合的一种社会形式,它必然要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6]224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之外。无论唐代社会如何空前开放,依然是一个标准的封建社会——依然主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以户婚制保障门当户对的婚姻关系,崇尚士族而以五姓为贵的婚姻观念,再加上整个社会汲汲于科举入仕的巨大热情,这些因素合力“规范”着唐人的婚恋行为[9],而这种“规范”有利于家族利益的巩固与维护,因此父母在干预子女婚恋行为时所呈现的专制与冷酷,既是受那个时代集体性声音熏染的结果,又是维护家族利益的需要。由此看来,仅从文本出发对父母形象予以过分的谴责,而忽略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则显然有失公允,并且对全面审视“父母形象”及深入探讨唐传奇作品的艺术成就有弊而无益。
[1]王谠.唐语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40.
[2]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王伟歌.从中唐传奇看唐婚姻法在文学中的反映[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4(3):40-4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长孙无忌.唐律疏议·户婚:14卷[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6]郝凤梅.悲喜殊同却为何——唐爱情传奇中女主人公结局浅议[J].沧桑,2008(4):51.
[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16.
[8]柳卓霞.等级制度下婚姻与幸福的背驰[J].社会科学论坛,2010(3):51.
[9]王卫.唐婚恋传奇中男性形象塑造的艺术成就探析[J].商洛学院学报,2014,28(1):41.
(责任编辑:罗建周)
A Study on Parents'Image of Tang Marriage Legend
WANGWei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726000,Shaanxi)
From the text of Tang marriage legend by previous researchers,in evaluating the parents' image,there was more condemned than understanding.Combing with the complex social environment of Tang Dynasty,the whole society had the great enthusiasm on imperial officialdom,advocated such feudal tradition as"parents'order,match-maker's canvasses",strict marriage system and the marriage idea of advocating intelligentsia.From all the factors above,parents'image as defender of the family interests is analyzed.They showed their autocracy and cruel in intervening their children's marriage. However,such autocracy and cruel not only are affected by the results of collective sound of that era,but the need to maintain family interests.Therefore it is unfair to just blame it and ignore the deep social behind it,and it does no good to view parent's image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study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Tang legend works.
Tang marriage legend;parents'image;social environment;family interests
I206.2
A
1674-0033(2015)01-0029-04
10.13440/j.slxy.1674-0033.2015.01.007
2014-11-03
商洛学院科研基金项目(09SKY034)
王卫,女,陕西泾阳人,硕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