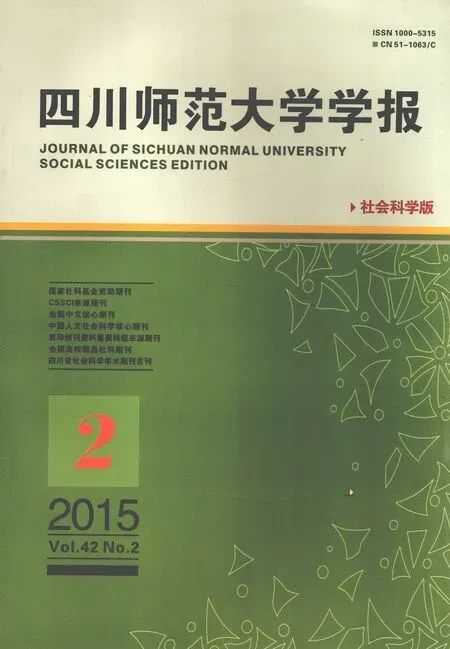从“韩愈崇拜”到“六一风神”
——试论饶锷散文文体学认知的体验化特征
2015-04-11闵定庆
闵定庆,李 玲
(1.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州510006;2.广东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梅州514015)
从“韩愈崇拜”到“六一风神”
——试论饶锷散文文体学认知的体验化特征
闵定庆1,李 玲2
(1.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州510006;2.广东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梅州514015)
饶锷是近世潮州学界大家,致力于国故学研究,著作等身,成就卓著,同时也是潮州文坛的领军人物,在诗、文、联等多种文体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近代转型的加速、传统文艺观的松绑,饶锷趋于认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的个性化创作,能从韩文的“文从字顺”处入手,荟萃欧阳修、归有光、戴名世之所长,形成了渊雅、和缓、绵密的美学风格。饶锷的散文观念,就是立足于这一美学风格进行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的集中体现,既充满了个性化体验的性灵色彩,也突出了近世文化转型期“此在性”与“过渡性”的特点。
饶锷;饶宗颐;欧体;散文;六一风神
饶锷(1890—1932)是近世潮州学术大家,尤以潮汕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成就为最著。他身处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期,在获取新、旧两种文化视野的同时,也陷入了文化选择的“两难”之中:一方面,随着文化转型的加剧,传统的“文道观”、“教化观”迅速崩解,饶锷得以沿着欧阳修“自然创作”的路向,发展出一种自由适性、活泼性灵的写作姿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来自旧阵营的人,饶锷又显得极度焦灼,必须在历史关头做出明确且明智的抉择。饶锷与他所景仰的师友章太炎、高燮、金天翮、柳亚子、温廷敬等人一样,是完全排拒白话文的。他指出,新式学堂斩断了千年“文脉”,“科举废而人才日杂,学校兴而文章日衰”,古文退场,典范不再,新式学堂的学生“安能登其堂而噬其胾哉”[1]38,进而断言新式学堂断然培养不出能触摸到古文神髓的学子。因此,饶锷终其一生都沉浸在古典美文的世界里,始终未把白话文纳入到文学思考与创作的视野中来,他一生的著述彰显着一种“古雅”趣味的祈向。他埋首著述,“于文辞、歌咏之事,漠焉不著意”[1]175,但他的友人一致认为,他的“古文、辞赋、骈文都做得好”[2]2。郑国藩《饶锷墓志铭》更明确指出,饶文虽“非精诣所在”,却能“以桐城义法出入唐宋明清诸大家,无意于古而与古会,当于庐陵、熙甫间别置一席,时贤中罕见其匹也”[1]154。 可见,潮籍学人早已对饶锷散文创作的审美属性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辨识与阐扬。这一认识理应构成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饶锷文体观念与散文创作的有效切入点之一。
一
饶锷对潮州文坛的历时性把握与共时性把握,直观、真切而具体。他在《郑蕃之墓志铭》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吾邑自宋明以还,名卿硕儒、忠义直谅之彦,代有其人。独文章之学,倡之者既寡,而为之者又囿于见闻,相安孤陋,于古人为文义法,往往莫知其然。故历时绵远,而潮人无寸简见称当世。近十年来,揭阳姚君恪先生始本其所闻马其昶、林畏庐诸老之绪论,以桐城文派倡导学者。而潮安王慕韩先生则孤立崛起,亦以古文为后进启示径途。两先生皆余所私昵者。”[1]100这大致勾勒出了近世潮州文坛的两个向度。第一,韩愈刺潮,越八月而去,开启了潮州“海滨邹鲁”的新纪元。潮人祭祀韩公,并在“韩愈崇拜”氛围中积淀了潮汕地区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膜拜韩文的“集体无意识”。但是,潮人长期热衷科举,揣摩时文,不免出现“尸祝”韩公“决以得失,卜以吉凶”,学韩文却“学无渊源,志趣不大”二弊。民国初年,王慕韩崛起于潮州文坛,大力倡导韩文,在他身边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古文创作群体。第二,曾点翰林的吴道镕来潮州主韩山书院、金山书院讲席,京师大学堂首届文科毕业生姚梓芳返潮执教,相继将“桐城文”引入潮州。虽然桐城派在世纪之交迭经经世文派、维新新文体、革命派宣传文、新式报章体等新文体的冲击,已呈强弩之末,但对于相对封闭的潮州文坛而言,毕竟还是比较新奇、比较容易入手的。因此,在吴道镕等领袖式人物的倡导下,潮人出现了“远宗退之而近法桐城”的转向。但是,饶锷有意回避了第三个向度——考据派文风,而这才是饶锷以及其子饶宗颐进行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真正起点。众所周知,阮元抚粤督粤十多年,正值乾嘉学派如日中天,他将乾嘉朴学引入广东,建学海堂,延请考据名家系统讲授考据学方法。其中,学海堂肄业生温仲和于光绪二十年(1894)至潮州金山书院讲学,后任该书院山长,书院改制中学堂,继续担任总教习。他以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考据学家实施国学教育,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两代潮州学人,潮州考据学家群体渐渐形成。温廷敬先从温仲和学,后同受丘逢甲之邀创办岭东同文学堂,成为多年同事,深受温仲和其人其学的影响,走的也是考据学的路子。饶锷、宗颐父子又师从温廷敬,接受系统的考据学训练,故一生谨守考据家法,为文朴茂渊雅,不事雕琢,以事理胜,逻辑性很强。
在饶锷的阅读体验与创作体验中,民末清初的潮州文坛,实为近世中国文坛的一个“缩影”,能对不同创作阶段、不同风格典范实现有效的转换与融合。饶锷是从旧式私塾和传统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最初的也是最本真的反应,便是在潮州文坛“韩愈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作用下,本能地选择崇拜与追摩韩文。但在此后长期的国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性之所近有不知其然者”的文体自觉意识,渐渐从“韩愈崇拜”的旧轨中游离开去。关于这一点,郑国藩《〈天啸楼集〉序》总结出了饶文“三变”的情形:
君文前后凡三变,少作刻意模韩,而未能至,时有枘凿不相容之处;中年出入唐宋明清诸大家,各有其所似,则志于传世,不忘意匠之经营者也;晚近一变,而归于平易,下笔在有意无意之间,则既神明于法,而不复以法囿文,境之上乘矣。[1]4
饶锷《与冯印月书》也与此相一致,直可视为“偏嗜”欧体的“自供状”:
大抵古人为文,各有偏好,而不必尽同也。锷于历代文家研读潜索,不一日矣。顾独酷好欧、戴二家之文者,非文舍欧、戴二家皆无当于我意也,又非欧、戴二家之文已尽文之极至,而欧、戴二家之文之外可无求也。盖性之所近,有不知其然者矣。[1]74
饶锷追述了漫长的探究历代文家的体验,最终以性情之所近,宗向欧阳修、归有光、戴名世一路。看似出语寻常,实则蕴涵了深刻的心灵挣扎,自有不可与外人道的“心曲”。饶宗颐在晚年追忆乃父教谕的时候将这一“偏嗜”讲得更加生动形象:
我上过一年中学,后来就不上了,因为学不到东西。但是我的古文教师王慕韩却有一样东西给了我很大影响,那就是做古文要从韩文入手。我父亲跟他搞不来,但我却信服王师这一套。父亲喜欢欧体,大约也跟他后来身体不好有关系。现在我还是要说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了一腔子气。[2]6
这一取径“欧体”的追述,从性格层面揭示了饶锷文章学理念的价值取向。而杨光祖《〈天啸楼集〉序》同样也从性格的角度总结了饶锷其人其文的特点:“君,循循学者,于书无所不读,而沉浸于考据之学,外虽刻苦,中自愉悦,盖志乎古者也。其为文章,纡徐静正而无怨言;其为人,温恭谨质而无愠色,傥所谓‘养其和平以发厥声’者欤?”[1]7粹然醇厚的儒者气度,中和包容的文人情怀,纡徐从容的文章风格,恰是千载以下对欧阳修其人其文认同与皈依的生动体现。
那么,饶锷“六一”情结形成的根本动因是什么呢?不难想象,在“韩愈崇拜”的氛围中研读韩文,总免不了几分仪式化与神圣化的感觉。这恰与少年饶锷生动活泼、性灵飞动的心灵是格格不入的。饶锷通过“欧体”体验获得文体的自觉,几乎可以说是欧阳修成长体验与文体实验的“再现”。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追忆十岁时曾得韩文六卷,虽“未能悉究其义”,却被韩文的“深厚雄博”、“浩然无涯”深深打动[3]1056。 最终,在北宋“向内转”思潮的氛围中,欧阳修采取了“易行易知”的方法论策略,从韩文的“文从字顺”处入手,实践了一种平易从容、曲尽形容的新文风。“欧体”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文化孤儿”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前进所获得的丰饶成果,凸显了孤独的生命体验所独具的艺术创造力。反观饶锷的成长历程,即可发现,他也是在逆境中摸索着前进的。据《天啸楼藏书目序》自述,他最初埋首四书五经,涉猎时文,后跟随仲兄阅读小学著作、诗文集,兴之所至,不求宗旨,稍长则循张之洞《书目答问》标示的“门径”有序地阅读清代学者的著作,打下较系统、扎实的国学根基。饶锷与欧阳修的早年体验一样,将书籍的聚集与知识的拓展、眼界的提升、心志的养成等融为一体,获得同步性的成长,在最大限度上涵盖了一个年轻人经由经典阅读、体味文体范式、甄别各家优劣的文体自觉的过程。
与此同时,高燮等人的革命家形象与国学家形象,迭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浪漫气质与政治担当,对饶锷产生了极大吸引力。饶锷早年求学于上海法政学堂,接触了许多新派学人,尤其是与以南社核心人物为主的激进的青年汉族知识分子交往甚密,自觉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将高燮、金天翮等视为平生知己。高燮等人一方面积极从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民主革命,另一方面竭力倡导“新国学”运动,将“国故”视为民族复兴的基石,积极整理国故,刊行古籍,成效显著。饶锷浸淫其中,很快从精神上的膜拜发展到行为上的模仿,将高燮等江南学者特有的敏感的艺术感知力、坚毅不拔的革命意志、细腻绵密的学风、柔婉雅致的文风等等迭加在一起,使得革命家、学者、文人三种身份“三而一之”,产生了无可言喻的“浪漫化”效果,在精神气质上更接近冶学者化、文人化与南方化于一炉的“欧体”。
个人成长历程、古籍阅读体验等方面的相似性,极易激发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审美趣味也随之趋于一致。饶锷就这样在人生成长最关键的时期因着自由阅读的优游与文学教育的熏陶,最终情不自禁地向“欧体”靠拢。也正是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他不知不觉间与潮人的“韩愈崇拜”渐行渐远了。
二
饶锷的文体自觉与实践,折向“欧体”一途,首先是建立在追慕欧阳修其人其文的基础上的。
韩愈曾自比于“非常鳞介之品”的“怪物”,不落流俗,犯颜鲠言,刚直倔强,愈挫愈勇。这或许就是饶宗颐先生所说的“一腔子气”吧,但是,这也不免出现如李翱《韩公行状》所言“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与人交,始终不易”等小毛病[4]26。反观欧阳修之为人与为文,韩琦《祭少师欧阳永叔文》说是“可否明白,襟怀坦易,学贵穷理,言无伪饰”[3]2630,其子欧阳发《先公事迹》也说乃父“中心坦然”,“接人待物,乐易明白,无有机虑与所疑忌,与人言,抗声极谈,径直明辨,人人以为开口可见肺腑”,“一切出于诚心直道,无所矜饰”[3]2626。不难看出,欧阳修在为人风格上与韩愈大相径庭——娴雅冲淡,随性为官;真挚自然,平易和畅;明辨是非,以理服人。韩文与欧体虽有“先河后海”的渊源关系,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文风却是阴阳二极。何沛雄《欧阳修与韩愈的“古文”关系》一文对此作了很好的鉴识:“欧阳修的古文,虽然源于韩愈,但他深于史学,更得太史公行文的‘逸气’,加上生性闲雅冲和,故为文纡徐委备,容与温醇。姚鼐把文章分为阳刚、阴柔两大类,韩文得阳刚之美,欧文得阴柔之美,堪作学文楷模,垂范千古了。”[5]饶锷本是个“温恭谨质而无愠色”的人,在本质上与欧阳修的性格是一致的,因而能“养其和平以发厥声”,“其为文章,纡徐静正而无怨言”,最终选择“欧体”一路就显得非常自然了[1]7。
在“文道观”的论述方面,韩、欧取径各有不同,饶锷沿着欧阳修偏于个人性情的路子,在近代文化转型中扬弃了严格意义上的文道观,回归文学本体。韩愈《答李秀才书》有“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6]725的宣言,充满原始儒家阳刚之气的实践理性,使得公共领域的理论对话与交流重归儒家本位,将政治修辞、道德修辞打入“载道”文学之中,原本较为纯粹的文学表达因而被人为提高到了政治精英主义者言说的层面。与韩愈散文崇儒的政治话语形态不同,欧阳修生活在一个儒家文化主导的“尚文”时代,一方面撰《新唐书·韩愈传赞》称赞韩愈“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捂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7]5269,在学术思想上的“拨衰反正”之功与文起八代之衰映照古今,故尔殁后“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7]5269。 另一方面,极力推动“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论所追求的日常化、个性化与诗意化表达的时代思潮,其《与乐秀才第一书》说:“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字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3]663“道”的自然属性,决定了经典撰作与阐释必然呈现个性化与人性化的样态,进而推衍出自然化、个性化的写作状态,从人性本真的层面拓展了文体革新的理论言说的空间。戴名世进而认为,写作要“率其自然”,“文”是“出于心之自然者”,由此推导出“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8]5。亦即从文体自觉的体验出发,强调从具体的创作土壤中发掘个性化表述的空间。但是,在近世文化转型的语境中,在清儒章学诚开启的“六经皆史”说与西方新史学的合力作用下,国学经典的神圣话语系统被全盘改造为历史性记述及解释,严格意义上的“文道观”失去了合理存在的文化空间,于是,古文理论中标语化、口号化的“卫道”、“载道”话语体系消失于无形。饶锷受这一时代话语体系的影响,自然而然地远离了传统文论中的“文道观”,在散文观念的建构与创作实践上得以摆脱种种羁绊,畅情论文,直指心源。
在创作观念上,饶锷认同韩愈“不平则鸣”的创作论,但更倾向于欧阳修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的“自然创作”观。饶锷《天啸楼记》就有这样的“自白”:“余穷于世久矣,动与时乖迕,外动于物,内感诸心,情迫时,辄为不平之鸣,而一于文辞诗歌焉发之。故吾之为文与诗,纵怀直吐,不循阡陌,愁思之音多,盛世之辞寡。是虽生际乱世使然,宁非天下之啸欤?”[1]88《四十小影自题》也说:“既遭时之不幸,乃息迹乎海垠。抱丛残以补佚,将闭户而草《玄》。谓殷之夷乎?谓鲁之连?皆非也。而讯其人,则曰:宁遗世以全我真。”[1]130这一自述,分明有着欧阳修的影子,突出了“自然创作”的有为创作观、自然的个性化表达这两个倾向。自司马迁“发愤著书”发端,“有为而作”的创作论就占据了文学主潮,韩愈《送孟东野序》“不平则鸣”论[6]982及《荆潭唱和诗序》“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论[6]1121,大致划分了“羁旅草野”与“王公贵人”两类感发模式。欧阳修在作家与现实生活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的认知基础上,接受了“外感内应”的创作模式,其《梅圣俞诗集序》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3]612《徂徕先生墓志铭》说:“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3]504遇事而发,意有所指,毫不避讳,这是出于高度的政治自觉、道德自觉与个性觉醒的现实承担与历史承担。这类解说,从真切的个体生命体验切入,表达出了两种极端的士人生活样态。
饶锷认同这一感发模式,将作家之于社会的个性化反应,归结为“处境使然”,对文学创作进行高度人性化的分析,展现出具体而鲜活的“写实创作语境”的认知。与欧阳修一样,饶锷从来就不是一个“被动”反映论者。他将自己对于“纵怀直吐,不循阡陌”的自然创作状态的反思,推展到对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的思考,进而审视友人的创作成就,导引出种种“自然创作”的文体样态的描述与评判。如《蛣寄庐诗剩序》称誉潮安林彦卿多才多艺,“举凡词章、若散若骈,下逮丹青、音律、岐黄、星卜之术,靡不习而能焉”,“又性好客,喜与酒徒贱工者游处,当其剧饮六博,酣呼谐谑,旁若无人,而人见之者鲜不以为狂且妄者也”,触类旁通,故所作诗文“并世交游咸敛手,逊谢莫及”[1]28。《南园吟草序》谈到外甥蔡儒兰的创作,“人言甥诗绝肖其为人,吾谓亦其处境使然也”,“观甥之诗,缘情寄兴之词多”,所以,“其造语清而丽、婉以和,无凄怆激楚之音”[1]31。《柯季鹗诗集序》谈到他与冯印月的交往:“其后于鮀浦得交吾友冯君印月。印月工吟咏,其为诗渊源家学,出入义山、少陵之间,与余旨趣颇合。昕夕酬唱,往往极酣饮大醉,悲歌呼啸而不能已。人或姗笑之,而印月与余不顾也。”[1]35《郑蕃之墓志铭》甚至描述了自己沿着故友的足迹,“吾尝浮韩江而下,登桑浦玉简之巅,见乎峰峦盘缪,江水激荡”,认为“岭东山川秀异之气”郁结于郑蕃之的胸臆,变幻为奇妙的个人表述[1]100。饶锷立足于潮州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个体文学创作的差异性,对每个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创作背景等等进行了深度解析,又对每个作家的个性、才情、智能结构、风格特征进行了高度个体化的归纳与总结,在社会激荡与个人反响之间寻找个性化表达的突破口。饶锷从中总结出“性之所近,有不知其然者”的生命体认与艺术呈现等现象,恰得欧阳修“自然观”的神髓。在人性化的柔性表达映现中,以惊世骇俗的议论、震慑人心的气势、排宕顿挫的感情为主要风格特征的韩文,渐渐退出了饶锷文体实践的视野。
总而言之,饶锷之追摹“欧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但凡个人性情、阅读体验、治学风格、思想感情、人格追求等等多方面的因素扭结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合力”,不断地将饶锷从“韩愈崇拜”推向“六一风神”一途。
三
饶宗颐《〈天啸楼集〉跋》追述了父子间一段极具深意的对话:
往年,宗颐曾固请将诗文稿分类编刻。先君不可,曰:“学问之道,考据、义理为先,文章其余事耳。吾方钩稽乡先哲遗文,焉有余力从事于此?且吾所为文,皆随笔直书,殊乏深意,其日力又不逮,安敢妄祸枣梨?”[1]158
饶锷的这番解说,基于“当下”语境的体验,对当时尚有一定生命力的乾嘉学派和桐城派进行了整合性思考,试图重构散文评鉴的标准。众所周知,桐城派与乾嘉学派一直有着良性的互动,共同努力完成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而一之的“义法”论建构。 戴震《与方希原书》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9]144求理义,就是求“大道”,故而“考据”、“文章”都是围绕着“闻道”(亦即“义理”)展开的。这一表述,可与刘大櫆《论文偶记》“文人者,大匠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之论料也”[10]3互为表里。饶锷自称是个不讲“宗派”却究“法度”的人,“顾吾学虽数变而终不囿于宗派之说,惟吾法之是求”,对散文创作自然也提出了是否应该符合“义法”的要求。他在《答某君书》中说:
夫文章之事,盖难言矣……大别言之,不越二端:一曰散文,一曰骈文。是二者,虽宗派各别,旨趣互异,顾其所以为文之法,莫不有一定矩镬存乎其间。故为文章者,首重义法,次论至不至。精于理,工于言,而又深于法,文之至焉者也。深于法而拙于词、疏于理,犹不失为文也。若理精而言工,无法度以运之,则不成文矣,而况于背理而伤词者乎……不识义法之人,又乌足与以论文?[1]77
在近代语境下,饶锷并未固守桐城藩篱,而是认为这一“义法”论必须有所改造。这与同时代包括桐城名家在内的许多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例如,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所谓‘义’者,有归宿之谓”的说法,就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淡化了“义”的“儒本”意涵,意在凸显具体技法的美学效应,“所谓法者,有起、有结、有呼、有应、有提缀、有过脉、有顿挫、有勾勒之谓”[11]92。 饶锷也在既有框架内细化了“三点论”的有机构成及其变化形式,指出与“三点论”相对应的“精于理”、“工于言”、“深于法”,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要有足够的“协同效应”方可作为全面衡量文章优劣的审美评价标准。“理”、“词”、“法”三者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可组合成以下四种情形:“精于理,工于言,深于法”者,为“至文”;“深于法而拙于词、疏于理”者,“犹不失为文”;至于“理精”、“言工”,却无法度者,是“不成文”的;而“背理而伤词”者则完全可以不予置评了。由此看来,“法”、“言”皆剥离了道德附着的因素,提高到了纯粹的文艺美学层次上去了。饶锷进而又在《郑蕃之墓志铭》中列举“左、史、韩、欧、曾、王、归、姚”之文,作为契合“精于理”、“工于言”、“深于法”标准的典范[1]77,基本上已将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第一流”的作家作品囊括在内了。
因此,“义法”的彰显,使“欧体”所蕴涵的“法度”,获得了一种属于“近代性”与“性灵化”意义上的解读,从而指示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作文”门径。
首先,注重协调“气”与“法”的辩证关系。饶锷《与冯印月书》说:“欧阳公自谓得力韩文,今观其文与韩似不类,然按其义法,寻其声调,与韩靡弗合也。盖退之运法于气,永叔运气于法,殊途同归。”[1]74“法”多存乎“字句格律篇章”的“形迹”之中,“善学古人者”得其神气,绝不会从“形迹”入手[1]74。从自然创作观念来看,欧体似乎更可亲可爱,更容易接近与模拟。当然,饶锷非常肯定韩文,尤其欣赏韩文不随人短长、自得佳趣,故其《答某君书》说:“韩退之尝为文矣,当其大称意时则人以为大怪,小称意时则人以为小怪,其自审成薄不足存,则人以为绝佳,是文章之佳者固众人之所不好也。”[1]76这种“君子固穷”的姿态,也是另一种个性张扬的体现,亦即以另一种方式达到了“各由其性而就于道”的写作境界。《答某君书》还以“吾邑某公”学韩“于古人为文义法盖梦然未之见”为例[1]76,强调“义法”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当下的义理“活法”,早就给人们抉出了正与变、死与活、深与浅等为文之法,因此,在当前“活”的散文语境中,完全可领悟出韩文的神髓,以重构“活”的韩文、“活”的韩愈。同时,饶锷还谈到姚鼐以“义法密而修辞朴”教人的技巧,进而指出姚文却“正坐法太密、词太朴”,殊乏“雄浑之气”,“往往流于薄弱”,唯有《登泰山记》一篇“于法外运气”,“故佳耳”[1]75。相对而言,曾国藩及其门人能扬长避短,后来居上,如曾国藩“厚集声彩”、“充以瑰玮雄大之气”,吴汝纶在乃师基础上进一步探源先秦诸子,“翻去波澜,一归崇奥”,自铸伟词,力矫姚鼐之弊[1]75。可见,“义法”的辩证性存在,实际上最大限度凸显了文章因时而变的“当下”语境。
其次,深明“辨体”之法。欧阳修特别注意散文文体的本色表达。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12]310方苞评欧阳修《真州东园记》云:“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欧公病其词气近小说家,与尹师鲁所议,不约而同。欧公诸记不少秾丽语而体制自别,其辨甚微。治古文者最宜研究。”[13]986《岳阳楼记》通篇运用“传奇体”刻画人物、描绘景物的笔法,不免辞藻秾丽,篇章繁复,缺乏论说文应有的庄重感,因此,欧阳修主张为文要“精择”,“去其繁”,追求“峻洁”的文风,异于范作[3]2372。又如,林纾《春觉斋论文·述旨》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至长无过五六百字者。篇幅虽短而气势腾跃,万水回环,千峰合抱。读之较读长篇文字为久,即无烦譬冗言耳。”[10]45欧阳修长于史学,将其“移植”到史论中,保其真气,去其繁复,使得史论写作有了质的飞跃。饶锷素喜欧文,“块坐斗室,取意所尤喜者,抗声哦诵,渺然有千载之思。久之,业乃大进”[1]100,终于窥欧文堂奥,得旷宕隽永之趣,在方志、书序、传记的写作上充分吸收欧文之长,行文喜从大处着手,不拘于细节刻画和景物描摹,“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1]100,最终锻冶出了超越“意匠之经营”之后的峻洁清雅的体性风格。
饶锷在散文的文体探索方面,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且相当复杂的心灵挣扎的过程。从文体格局转型的层面看,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与国学转型,使得近世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随之出现趋向通俗化、白话化的新变。饶锷以纯粹学者而非政治家、道德家的眼光,重新打量散文创作及其内在规律,最终选择了“古雅”的文言文书写方式,正是为了接续三千年文脉。从写作范式看,他从“韩愈崇拜”、乾嘉学术、桐城故辙“复合型”的潮州文坛中挣脱出来,在欧阳修式的学者化、文人化“人格投射”的作用下,从人性本真、唯美感知等层面切入,思考文体变革与散文创作的转型问题,努力追求一种理精、峻法、雅洁、和缓的文风,以澡雪精神,畅情抒写。这恰是饶锷回应近代文化转型而做出的适度调整。这一文体创造行为,内涵丰富,心态纡徐,胸襟宽容,有别于同时代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板滞的保守态度,又迥异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饶锷能尽可能地挣脱业已僵化的创作模式,自由地发抒性灵,这种深度的解放精神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心态,在创造精神的层面跟上了时代转型的节拍,进而将近世潮州古典文体书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体现了世纪之交文化更新与创造的基本取向与广阔空间。今天,我们应将这种力量视为从不同层面共同参与新文化建设的“合力”之一,在勇于创新的精神层面确实是与“新文化运动”完全相通的。
[1]饶锷文集[M].陈贤武,黄继澍整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
[2]胡晓明.饶宗颐学记[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
[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1.
[5]何沛雄.欧阳修与韩愈的“古文”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1997,(3).
[6]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戴震.戴震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刘大櫆,等.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1]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12]何景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姚鼐.古文辞类纂[M].北京:中国书店,1986.
[责任编辑:唐 普]
I206.2
A
1000-5315(2015)02-0140-06
2014-06-04
闵定庆(1964—),男,江西永修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玲(1969—),女,广东梅县人,文学博士,广东嘉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