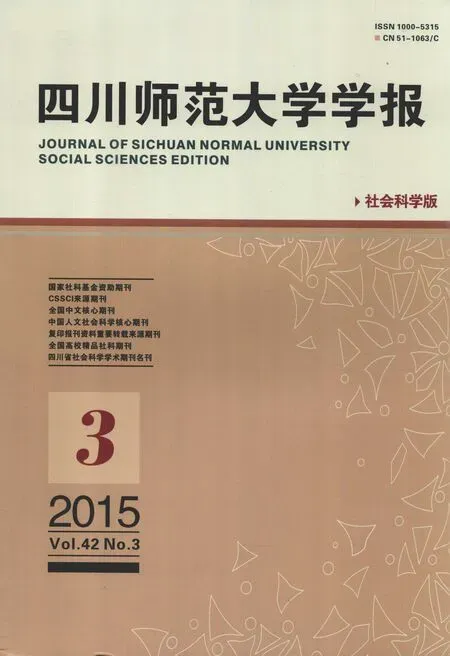苏轼“舟中读《文选》”考论
2015-04-11唐普
唐 普
(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辑部,成都610066)
苏轼“舟中读《文选》”考论
唐 普
(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辑部,成都610066)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六月十一日,苏轼“舟中读《文选》”。由苏轼论及《文选》的文献似可得知,元丰年间苏轼才开始正式阅读《文选》,而且这个《文选》应该是五臣注本,之前苏轼或当见到过国子监李善注本,但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阅读。他对《文选》的评论仅是点滴的、武断的,正反映出他没有深入学习《文选》的事实。
苏轼论《文选》;《文选》版本;庆历新政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六月十一日,苏轼作《题文选》一文,云: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馀人忽遗者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元丰七年六月十一日书。[1]卷六十七,2092-2093
苏轼什么时间开始阅读《文选》?他舟中所读《文选》用的是什么版本?笔者试以苏轼评论《文选》为出发点,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 苏轼论《文选》
宋初,《文选》学习和接受程度较高,陆游云:“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2]卷八,100但庆历、熙丰之后,《文选》学逐步走向衰落。苏轼恰恰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变革时期,他对《文选》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评论《文选》也仅止零星点滴。作为一代文豪,他开启了新的书写文风,“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2]卷八,100。
苏轼评论《文选》,较多地收入《仇池笔记》中,四库全书《东坡志林》十二卷本也悉数收入①。今据《苏轼文集》将其论迻录如下(《题文选》见前引):
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宋玉赋《高唐》、《神女》,其初略陈所梦之因,如子虚、亡是公相与问答,皆赋矣。而统谓之叙,此与儿童之见何异。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范晔作《蔡琰传》,载其二诗,亦非是。……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诗文,皆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1]卷四十九,《答刘沔都曹书》,1429-1430
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谢瞻《张子房》诗曰:“苛慝暴三殇。”此礼所谓上中下三殇。言暴秦无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于是。”谓夫与父为殇,此岂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诸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1]卷六十七,《书谢瞻诗》,2093
五臣注《文选》,盖荒陋愚儒也。今日读嵇中散《琴赋》云:“间辽故音庳,弦长故徽鸣。”所谓庳者,犹今俗云 声也,两手之间,远则有 ,故云“间辽则音庳”。徽鸣者,今之所谓泛声也,弦虚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长则徽鸣”也。五臣皆不晓,妄注。 又云:“《广陵》、《止息》,《东武》、《太山》。 《飞龙》、《鹿鸣》,《鹍鸡》、《游弦》。”中散作《广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尔,而注云“八曲”。其他浅妄可笑者极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举此,使后之学者,勿凭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于萧统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赋》,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赋,而统谓之序,大可笑。相如赋首有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论难,岂亦序耶?其他谬陋不一,聊举其一耳。[1]卷六十七,《书文选后》,2094-2095
苏轼专论《文选》,不外乎有如下的这样几个观点。
其一,萧统编撰《文选》,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同时极力贬低萧统的学识和才力,“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他举了几个例子:《文选引》(按即《文选序》)乃齐梁文章衰陋之犹为卑弱者之见证;“去取失当”之例,则苏李诗及李陵《答苏武书》皆伪而不辨,渊明《闲情赋》失收;至于“编次无法”,则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文误为序的问题。其实这几个问题,苏轼较为武断。萧统与苏轼各自文风不同,苏轼代表的古文派特色,固然会对萧统这样的“齐梁文章”嗤之以鼻。至于“去取失当”,萧统《文选》不录《闲情赋》或当有别的理由,他在《陶渊明集序》中认为《闲情赋》“白璧微暇”[3]200,其实并无苏轼所言“讥之”之意;又,不去苏李诗、缺乏识断的问题,在《题蔡琰传》中他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刘子玄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予因悟陵与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1]卷六十七,2094其实既然是“刘子玄独知之”,即谓在刘知几之前并无人认识到李陵《答苏武书》乃伪作,这样强迫要求萧统必须识断而不当录于《文选》未免显得牵强,并且苏轼自悟苏李诗也当为伪作,且要求萧统并悟,这是不太现实的问题。萧统编撰《文选》,录有李陵(三首)、苏武(四首)赠答诗,但并没有入于“赠答”类,而是次于“杂诗”《古诗十九首》后。像《古诗十九首》,李善注云:“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4]卷二十九,409,说明昭明在编次《文选》时还是较为审慎的。至于李陵《答苏武书》及苏李五言诗,连李善都未辨其伪,怎么能要求萧统必须辨识呢?并且刘知几在《史通·外篇·杂说下》论李陵《与苏武书》时,是针对《李陵集》而言的,其云: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辞采壮丽,音句沉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5]卷十八,525
不仅如此,他认为《与苏武书》“辞采壮丽,音句沉靡”,与苏轼所说“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有天壤之别。最后,关于误“序”的问题,可能情况还要复杂一些。苏轼之后的王观国《学林·古赋序》[6]220-221、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十八《文章门·文选》[7]242、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二《文选·文粹·文鉴》[8]28、王芑孙《读赋卮言·序例》等对此问题也多有论及[9]382。《文选》虽为萧统所撰,但“析赋为序”恐怕并非昭明首倡,将责任归咎到萧统,可能并不恰当。
其二,五臣注《文选》,“盖荒陋愚儒也”,错误较多,“妄注”。他所举的例子有:《张子房》诗“三殇”五臣误注,《琴赋》五臣不晓“音庳”、“徽鸣”,妄注,且误注“《广陵》、《止息》”等为“八曲”。
其三,极力褒扬李善注,“本末详备,极可喜”,对“世以为”五臣注“胜善”的看法进行纠正。在这里他没有举例,只是举五臣误注来反证李善注的“可喜”。事实上,他所举五臣误注“三殇”的问题,实际上并不知五臣本祖李善,以五臣此注来反证李善注“极可喜”,无疑是有矛盾的②。
正如郭宝军所认为的,“苏轼对萧统《文选》编选的批评,建立在其个人的偏好、主观的认识、标新立异的美学追求上,大都从《文选》中的个别失误出发(这种失误并不能肯定全为萧统所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责备、呵斥,为文好骂的行文风格使之又有了人身攻击的意味”[10]362。 其实,在评论五臣、李善注优劣的时候,他也是采用同样的风格,“聊举其一耳”,“不足言,故不言”。
二 苏轼评论《文选》时间、版本考论
基于以上苏轼评论《文选》的有关内容及方法,我们试图来探究苏轼评论《文选》的大致时间及其所用版本的问题。
《题文选》作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十一日,《苏轼年谱》谓“舟中题《文选》”[11]卷二十三,632,《苏轼全集校注》谓作于“湖口”[12]7498,因作年记于文末,故无疑义。《答刘沔都曹书》,《苏轼全集校注》谓“元符三年(1100)三月作于儋州”[12]5332,这已是苏轼晚年的文章了。《书谢瞻诗》、《书文选后》,《苏轼全集校注》皆云“作年未详”[12]7501,7505。
作于元丰七年六月十一日的《题文选》,当是苏轼罢黄州转汝州任途中所作,其所阅读的《文选》,或是他本人藏书。虽然此处苏轼并未论及五臣注、李善注的问题,但通过苏轼其他文章可以一并考知苏轼阅读《文选》的大致时间。《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云:
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请与《文选》及本传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创入也。谨作小楷一本寄上,却求为书,抛砖之谓也。[1]卷五十九,1789
《苏轼文集》谓此二十首“以下俱黄州”[1]卷五十九,1785,《苏轼年谱》谓元丰五年(1082)董钺去,“赠《哨遍》,抒思归之意。并寄朱寿昌(康叔)”[11]卷二十,541。 文云“请与《文选》及本传考之”,当是在苏轼检校过《文选·归去来》之后才有是说。故苏轼在元丰五年之前已阅读过《文选》,至少《归去来》应该是读过的,而且参考过《文选》所录。
又,《书苏李诗后》云:
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春秋之时,三百六篇皆可以见志,不必己作也。[1]卷六十七,2089
此文盖苏轼黄州期间手书李陵赠苏武诗予陈君式后而作,饶学刚系于元丰五年(1082)[13],孔凡礼则系于元丰三年(1080)八月[11]卷十九,486,《苏轼全集校注》谓“元丰五年(一○八二)作于黄州”[12]7486。 苏轼多次谈及苏李诗的真伪问题,而此时他竟在陈君式罢职时,“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并没对苏李诗的真伪产生怀疑。试想,既然苏轼认为苏李诗乃后人伪作,此时他“书以赠之”,即不符人之常情了。由是可知,至迟在元丰年间陈君式罢黄州时,苏轼那时尚未对苏李诗的真伪问题产生疑问。这说明他认真阅读《文选》中苏李诗也当在此之后,正是在元丰七年(1084)六月“舟中读《文选》”前后,而《题蔡琰传》当在其“因悟陵与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之后。
既然如此,《书谢瞻诗》和《书文选后》则当作于《书苏李诗》之后,即元丰年间或者其后。《书谢瞻诗》出《仇池笔记》,题作《三殇》,十二卷本《东坡志林》则收录有《书谢瞻诗》和《书文选后》。王松龄谓:“《东坡志林》所载各篇,上自元丰,下迄元符,历二十年”[14]《点校说明》,1。按:赵用贤为其子赵开美刊本《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云“东坡先生《志林》五卷,皆纪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14],元祐至绍圣仅十余年,赵氏说法不确切。又,赵开美《仇池笔记序》云:“《笔记》于《志林》,表里书也。……兹于曾公《类说》中复得此两卷,其与《志林》并见者得三十六则”[15]。既为表里书,其收文时间范围或许较为一致。由此我们大体可以判断二文或许作于元丰年间或之后。按照孔凡礼先生关于《书苏李诗后》一文的系年,此二文定当作于元丰三年(1080)之后。
由上可知,苏轼较为集中地对《文选》进行评论,是在元丰年间或之后,直至晚年《答刘沔都曹书》一文,较为全面地将他论及《文选》(注释除外)的部分文字糅合到了一起(见前引)。这段文字论萧统集《文选》“拙于文而陋于识”的举例(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篇初误叙问题,苏李诗及李陵《与苏武书》为伪作等),其实在《题文选》、《题蔡琰传》中早有论及,显然是他晚年对自己以前观点的重述。
现在再来看看苏轼评论《文选》所用的版本问题。
首先,可以否定的是苏轼元丰六年“舟中读《文选》”不会使用李善、五臣合注本。宋代六家注本的始祖是秀州州学刻本,是书刊刻于元祐九年(1094),而苏轼《题文选》作于元丰七年(1084)。由此而推之,《书谢瞻诗》、《书文选后》当在《题文选》的前后年间所作,其所用的本子很有可能是苏轼“舟中读《文选》”的同一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是五臣注本还是李善注本呢?《书文选后》专论五臣注及萧统之鄙陋,是故明刊本《文粹》卷四十、《东坡全集》卷九十二题作《五臣注文选》。既如此,当是五臣注本无疑。又,《书谢瞻诗》一文,虽首云“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其实仍然是在批评五臣注的问题,他所用的《文选》本子,亦肯定是五臣注本。如果是国子监本《文选》,苏轼批评五臣注时当会用李善注加以辩驳,事实上他举五臣误注“三殇”的例子,即谢瞻《张子房诗》“苛慝暴三殇”李善注云:“《礼记》曰:孔子过泰山侧,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16]505而苏轼批评五臣注云:“此礼所谓上中下三殇。言暴秦无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于暴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于是。’谓夫与父为殇,此岂非俚儒之荒陋者乎?”并不知五臣注乃源自李善,即使误也当自李善起,又于此前极力称赞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并以之贬抑五臣,失之③。可见,苏轼此时可能看到的仍然是五臣注本,或仅凭自己当年见到国子监本《文选》的印象(详后所论)作出“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的判断后,对五臣注加以批评。所以,从此文来看,东坡一生的确对《文选》没有深读。郭子章《豫章诗话》卷一云:“东坡一生不喜《文选》,故不喜昭明。”[17]254诚为的论。
苏轼生前可能见到的《文选》刊本,五臣注本有五代毋昭裔刊本(蜀本)、天圣四年(1026)平昌孟氏刻本,李善注本有天圣七年(1029)国子监刊本(大中祥符国子监本刊成未印即付烬,故不得而见)。此外,天圣四年平昌孟氏刻本沈严《五臣本后序》云此前“二川两浙,先有印本,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校)本粗而舛脱夥”[16]1461,汪超认为:“由沈严之序,我们可以得知,在天圣四年(1026年)平昌孟氏五臣注本刊刻之前,两浙亦曾刊刻五臣注本《文选》。但今已不传,其具体情况无由得知。沈序所谓二川印本,当指五代孟蜀毋昭裔刻本。”[18]这两个版刻的五臣注本,一因年代久远,二因“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校)本粗而舛脱夥”,在平昌孟氏刻本出来之后,士人不大再对此加以选择。由此则可以判断,苏轼“舟中”所读《文选》,或许可能是平昌孟氏刻本。
三 苏轼所见《文选》李善注本时间考论
苏轼既然阅读评论《文选》所用注本为五臣注本,那他为什么又在《书谢瞻诗》中明确表明“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呢?这表明苏轼应当是见到过李善注本的,并且对当时通行的五臣注本“世以为胜善”的观点表示了否定。但遗憾的是,苏轼在评论五臣注的时候,却举错了例子。这极有可能是受制于当时转迁赴任的特殊环境,他没有条件翻阅李善注本,故有感而发、信笔拈来,加之对《文选》没有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仅凭印象,作出了一些较为武断的结论。
苏轼得以见到《文选》李善注本,极有可能是他入直馆阁之后,而不大可能在其入仕之前。
庆历三年(1043),八岁的苏轼“入小学,师张易简,与陈太初同学”[11]卷一,12。也即在这一年,刚入乡校的苏轼得以读到了《庆历圣德诗》: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1]卷十,《范文正公文集叙》,311
《庆历圣德诗》的作者石介,对宋初“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2]卷八,100这种西昆诗风极为不满,作《怪说》极斥其代表人物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19]卷五,62。同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主持“新政”,其中一项是改革贡举制,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新政阵营里的许多人物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中坚”,“范仲淹是他们的政治领袖,而在北宋散文的发展上,他们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欧阳修是他们的文学旗手”[20]。此时的苏轼刚发蒙入学,这种制度的改变势必会影响他的学习内容,因为“读书求仕成了宋代读书人主要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唯一目标”[10]245-246。
幼年的苏轼,受学张易简、母程氏、伯父涣、刘巨、乡人史清卿等,其父洵“居丧眉州,不出蜀,教二子”[11]卷一,23。乡先生既然对苏轼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人为“人杰”,那么他对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文学创作倾向显然是赞同的,这对苏轼的启蒙意义非同小可。此外,苏轼之父苏洵本人与欧阳修也有交游,“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1]卷六十三,《祭欧阳文忠公文》,1937。 正是在科举和苏洵父子文学创作倾向的影响下,苏轼幼年所习的内容可能会远离《文选》。
皇祐五年(1053),十八岁的苏轼“日益壮大,好读史、论史,间亦好道”[11]卷一,32。至和二年(1055),二十岁的苏轼“已学通经史”[11]卷二,36。 可见,青少年时期的苏轼主要学习的是经、史著作。学成之后,自然是要走入仕的道路。嘉祐元年(1056)秋,苏轼兄弟应开封府解,试景德寺,“榜出,……苏轼第二”[11]卷二,48。嘉祐二年正月,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苏轼“应省试,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无所藻饰,一反险怪奇涩之‘太学体’。梅尧臣得之以荐,欧阳修喜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三月初五,“仁宗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又试特奏名”,十一日,“赐进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苏轼、苏辙皆进士及第。……(欧阳)修喜得轼,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文风为变。 苏氏文章,遂称于时”[11]卷二,51-55。 正是苏轼文章契合了欧阳修的品味,欧阳修选择苏轼作为自己 的 接 班 人, “我 老 将 休, 付 子 斯文”[1]卷六十三,《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1956。 其后,欧阳修举荐苏轼应制科,嘉祐六年(1061)八月二十五日,经过层层选拔的苏轼兄弟受仁宗御试,“苏轼入三等,辙为四等。轼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辙除商州军事推官”[11]卷四,93,开始了他坎坷的为官生涯。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省试中进士及第,乃得力于欧阳修看中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而此次御试时所作赋(《民监赋》)、诗(《鸾刀诗》)竟佚,仅留《重申巽命论》(试题)。这在苏氏文章称雄当时、其集多所刊刻的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后苏轼入仕则应制科,其应制文章则多为策、论。《文选》之于苏轼,其意义几于无矣。
既如此,那么苏轼何时开始比较正式地阅读《文选》呢?这可能是苏轼入直史馆后才得以见到国子监本。治平二年(1065),苏轼又应制科特旨,“学士院试策,优诏直史馆”[11]卷六,137。 史馆为宋代三馆之一,藏书颇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二月丙辰朔,诏赐名为崇文院。西序启便门,以备临幸,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21]卷十九,422。苏轼或可在直史馆期间见到《文选》,而且极有可能是国子监本《文选》。熙宁二年(1069)八月十四日,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试官”[11]卷十八,164,而宋初国子监本《文选》的刊行,也与史馆关系密切。《宋会要辑稿·崇儒》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撰《文苑英华》,“帝览之称善,降诏褒谕,以书付史馆”[22]卷五,261。 可见,史馆雕造书籍并非专于史书。景德四年(1007),“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李善文选》校勘毕,先令刻板。又命官覆勘。未几宫城火,二书皆烬。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对焉”[22]卷四,213。今韩国奎章阁本《文选》附录有国子监校本校勘、雕造及进呈官员姓名,与《宋会要》所言合。可以想象,苏轼在直史馆期间,见到《文选》国子监本毫无疑义,也是很容易的事。 苏轼治平二年(1065)直史馆[11]卷六,137;熙宁二年(1069)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宣告院,兼判尚书祀部,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宣告院,权开封府推官[11]卷八,158,166;熙宁三年差充殿试编排官,罢开封府推官,依旧宣告院[11]卷九,175,191;熙宁四年迁太常博士[11]卷十,195。据《宋史·职官九》所述叙迁之制,殿中丞“有出身转太常博士,无出身转国子监博士”[23]卷一百六十九,4024,可知苏轼正是以殿中丞身份迁任太常博士(即有出身,进士及第)。随着这种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苏轼的眼光显然超越了一般读书人认为《文选》五臣注优于李善注的实用主义,故其会在后来认为李善注“本末详备,极可喜”,这与景德四年监三馆书籍刘崇超所言李善注“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是一致的。正是这种馆阁之士与普通文人对李善注与五臣注审美(或功用)趣旨的差异,使《文选》的版刻在宋代的版刻史上产生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现象,“朝廷刊本是以李善注为主,目前所知的两宋《文选》版本中,国子监刊本没有五臣注。而私刻当中,尤本是李善单注,坊刻则从来没有李善单注本,更多的反而是五臣注本”[18]。
虽然苏轼治平二年(1065)至熙宁四年(1071)之间任职馆阁,有可能得以目睹国子监本《文选》,但可能他并没有认真阅读《文选》,这从他《书谢瞻诗》中论及李善注仅聊聊数言且印象有误的情况可以得见。但在元丰期间,他可能得闲阅读《文选》,如《题文选》即作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他自黄州转任汝州期间舟中。而他此时阅读的《文选》版本,当是五臣注本,《题文选》、《书谢瞻诗》、《书文选后》及《答刘沔都曹书》所论《文选》相关问题,都反映不出他看的这个版本是李善注本。相反,《书谢瞻诗》、《书文选后》在谈到五臣注的问题时,也仅《书谢瞻诗》文首“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数字,但讨论五臣妄注“三殇”时,却恰恰忽略了五臣本祖李善,自相矛盾。
正因为苏轼并没有系统而认真的阅读《文选》,所以他论及《文选》的时候难免片面、武断,没有充分的论证和翔实的材料,只能以“诸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其他谬陋不一,聊举其一耳”。其实这正反映了他一生不喜《文选》,因而也没有认真地学习《文选》的事实。注释:
①明人赵开美刊本《志林》五卷本仅卷四有“张华鹪鹩赋”一条涉及,《文选》虽录张华《鹪鹩赋》,但本文是否与论《文选》,不足证。
②屈守元先生认为苏轼所见李善本此处无注,“今传尤刻李注本,却把李周翰作为李善注窜入”(《文选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版,86页)。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即云李周翰注“乃实本于善也”(《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437页)。今检奎章阁本《文选》,尽管其前有李周翰注,但并未略去李善此注(奎章阁本祖本为秀州本,秀州本所用李善注底本为宋国子监本),此实属苏轼之误。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辨正,亦可参考:郭宝军《宋代文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389-390页。
③关于这个问题,郭宝军《宋代文选学研究》389-390页有较详的辨正。
[1]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陆游.老学庵笔记[G].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79.
[3]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
[5]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王观国.学林[M].田瑞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7]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王芑孙.渊雅堂全集·外集[G]//续修四库全书:第14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郭宝军.宋代文选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1]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13]饶学刚.苏轼黄州生活创作系年[J].黄冈师专学报,1997,(2).
[14]苏轼.东坡志林[G]//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苏轼.仇池笔记·东坡志林[M].影印涵芬楼旧版.上海:上海书店,1990.
[16]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本文选[M].韩国:正文社,1983.
[17]郭子章.豫章诗话[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8]汪超.《文选》在两宋之流布与影响[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6.
[19]石介.徂徕先生文集[M].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20]洪本健.庆历新政人士和北宋散文的发展[J].江海学刊,2001,(6).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2]宋会要辑稿·崇儒[M].苗书梅等点校,王云海审订.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23]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凌兴珍]
I206.2
A
1000-5315(2015)03-0164-06
2014-08-06
唐普(1972—),男,四川邻水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辑部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