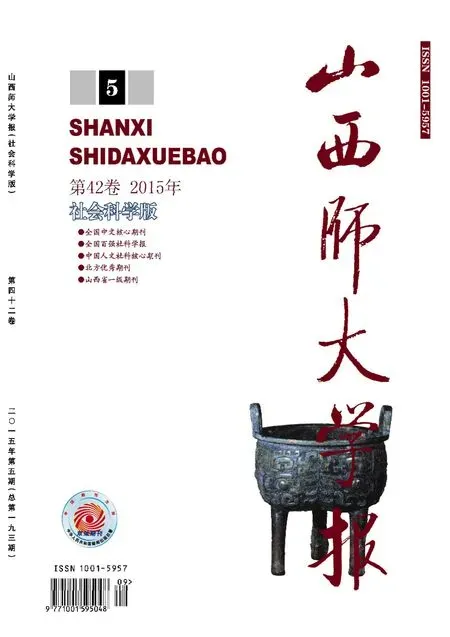女性悲剧命运的众人言说
----乔治·桑小说《莱丽亚》的多元叙述声音
2015-04-11郑朝琳
郑 朝 琳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引言
《莱丽亚》是乔治·桑的早期作品之一,出版于1833年。这部小说引起很大的争议和轰动,一名记者公开抨击乔治·桑,认为这部小说污染人的精神,甚至“要求把一块烧红的煤放在乔治·桑的嘴唇,以烫去这些下流无耻的思想”[1]121。普朗什在《两世界评论》中声讨这名记者,并为乔治·桑及《莱丽亚》辩护。圣勃夫认为,《莱丽亚》虽然存在很多缺陷,但“仍然是一本值得大胆尝试的书”[2]40。莫洛亚把《莱丽亚》和《印第安娜》、《康素爱萝》视为桑最好的三部小说。这部小说的重要吸引力在于它是桑最具自传成分的一部小说,桑甚至对圣勃夫说:“我就是莱丽亚。”[3]50缪塞经常戏称桑为莱丽亚,莫洛亚将《莱丽亚:乔治·桑的生活》作为桑的传记名。这些都表明了作者和小说主人公的亲和关系。的确,在这本小说酝酿期间,桑正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与于勒·桑多、梅里美、缪塞复杂多变的情感纠葛使她对自己的爱情和生活方式进行了反思。她在分析自己和生活时,灵魂就进入了书中,这就是《莱丽亚》。作为表现自己心灵痛苦的作品,桑设计了新的叙事模式,既能映现作者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又能使作家通过写作对父权制文化进行抗争。《莱丽亚》由最初的日记体形式成为了囊括独白、对话和书信等在内的大拼盘,在这些表面杂乱喧哗的叙事形式中,莱丽亚成为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她“与维特、勒内、奥伯曼……这些人物平起平坐,比起那个时代其他一些不可一世的男性自我形象毫无逊色。她为女性赢得了整个浪漫主义运动”[4]196。
《莱丽亚》是一部颇具哲理的小说,桑将传统小说中的背景、情节和故事压缩到最小,这种技法在桑的小说中很少见,尤其是其中的叙事技法给读者和评论家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的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 “最富有诗意的,最有理论性的作品之一……作者努力尝试一种新的散文写作方式”[5]59。在小说中,桑使用多个叙述者的叙述策略:既有小说中的人物,这类人物被称为同故事叙述者;也有一位性别模糊的异故事叙述者,偶尔跳出来讲述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起伏,并对人物和社会进行抽象的概括和总结。如果说《印第安娜》、《瓦朗蒂娜》等小说所采用的叙述方式是对男性话语权威一种迂回的反抗,那么《莱丽亚》中多种声音的交叉则是作者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公然对抗。多重声音的交叉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围绕小说的中心——“你是何人”这个问题展开的,每一位叙述者都用自己的话语回答着这个问题。在多重声音的交叉和对抗中,文本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女性为避免沦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和定型的社会性别角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抗争,虽然结局注定是失败的,但是这种抗争精神却被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作家所歌颂和赞扬。
一、“你是何人”——男人声音中的“她”
桑虽使莱丽亚成为情节中心,却没有让她成为唯一的叙述声音,她是在男性的书信叙述中出场的。开篇斯特尼奥就抛出疑问“你是何人?”[6]1这也是贯穿小说的灵魂问题,众多人物对莱丽亚身份的认知展现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的严酷生存状态。桑使用书信体的策略具有鲜明的特征,通过颠覆书信体的叙事传统和奇妙转换叙述视角等方式表现女性“他者”处境的悲剧命运,传达出女性反抗男权主导话语、争取树立叙事权威的抗争精神。桑一开始就降低了男性的叙述权威,斯特尼奥不再是传统书信体小说中无所不知的男性叙述者,而是一位看不清莱丽亚真实形象却又深爱她的痴心男子。他对莱丽亚身份的询问证明他对后者的爱情不是基于平等与理解的基础之上,他一直想把莱丽亚拉回到社会的既定性别角色中。在这场爱情追逐中,他将自己置于被动的位置,没有采用居高临下的强者姿态说话,使莱丽亚形成表面上的优越感。他在随后的信件中不厌其烦地表露自己对她疯狂的崇拜和热切的爱慕,“我终于被奴役了,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6]8,甚至他乐意“年轻、单纯和驯服地做你的玩偶,做你的受害者”[6]78。莱丽亚在他的叙述中成为他人生的主导力量,决定着他的道德品格和命运走向,她似乎在他那里获得了主体的位置。但是,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女性的“第二性”,将男性权利和话语霸权拱手相让吗?答案是否定的,女性崇拜情结只不过是男性霸权的情欲表达,是男性控制女性的一种形式罢了。他用天使和魔鬼、高尚与平凡、烈火与冰雪等词语来形容她,认为她善良、美丽、圣洁、神秘、残酷、冷漠,时而把她作为领路人、灯塔,时而诅咒她该死,“活像具死尸”[6]37。他用诸多二元对立的词语将莱丽亚描述为天使或者魔鬼的形象,而这正是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被泛化的两种形象。“天使”代表着顺从与忠贞,她们心甘情愿地满足男性欲望和顺应男性霸权;“魔鬼”意味着反叛与主动,她们不愿意服从男性权益,对男权社会形成了挑战和威胁。然而不论哪种形象,都是由男性创造出来的,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和丑化,隐含了社会的性别政治和文本中的男性霸权。桑不仅批判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还揭露了文学文本对女性形象的虐待和骚扰。
小说中的另一位叙述者是特郎莫,莱丽亚将他视为精神上的朋友。特郎莫超越生理性别区分,将莱丽亚比拟为雌雄同体的高尚人物,并对斯特尼奥将女人等同于爱情的观点进行驳斥,反问 “你也认为哪里没有爱情,哪里就不再有男人吗?”[6]36即便是这样的人生智者,在了解斯特尼奥对莱丽亚的爱情之后,也要求她服从社会性别角色,接受斯特尼奥的爱情,成为他的姐妹、朋友和母亲。在他和莱丽亚的通信中,他多次称她为“女人”,而这正是莱丽亚所一直抗拒和反对的社会身份。“女人”这一身份意味着女性作为个体“人”的身份的丧失,特郎莫对莱丽亚称呼的变化意味着即使他没有将后者作为欲望的对象,也不会和女性形成联盟。且当女性损害男性利益时,男性之间会自动形成联盟以维护权威。神甫马纽斯患有典型的“厌女症”,将莱丽亚视为诱惑他的魔鬼和女人,使他在情欲和信仰之间备受煎熬,最终在他的性欲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他杀死了莱丽亚。小说中的三位主要男性人物和莱丽亚形成了不同的关系,都试图将之简化为简单的社会符号:斯特尼奥希望她能在精神和肉体上与他结合;特郎莫劝说她或成为社会中的女人,或接受他的苦行哲学;马纽斯要求她满足自己的情欲,否则就杀死她。每一个男人都在她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欲望,女人在这种欲望下被客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不是主体、超越性、创造力,而是载满流体的客体”[7]230。
莱丽亚清楚地知晓女性“客体”的命运,借助书信、对话来抵抗男性欲望,坚守自己的叙述权威,避免沦为社会性别等级中一名非个人化的成名。面对斯特尼奥对其身份的询问,她拒绝回答,声称“这与你有什么关系”[6]5。她明确拒绝女性身份,称自己为“人”,和斯特尼奥是兄弟和伙伴,表明她不愿沦为没有个性身份的性工具。在斯特尼奥询问特朗莫的故事时,她牢牢把握话语权,不将叙事权威拱手相让,故意保留信息,掌握讲述故事的节奏,以捍卫女性的话语权。在欧洲文学传统中,女性的故事多由男性来讲述。当女性作家“浮出地表”之后,许多女性作家如玛丽·雪莱、乔治·桑、乔治·艾略特等采用男性叙述者的形式以捍卫女性作家的权威。桑让女性人物来讲述男性故事,其本身就是对男性之笔建构女性文本的蔑视和挑战。莱丽亚还积极参与社会公共话语,阐述自己对于文明、社会、历史、宗教、政治和人性的看法。在她眼中,上帝用博爱的谎言欺骗世人,政府从不光彩的来源中攫取财富,文明吞噬着美德和希望。桑借助主人公富有强烈批判意识和思辨色彩的语言反驳了社会对性别的语言歧视,女性语言并不是“软弱无力,鸡毛蒜皮不得要领,缺乏果断而犹豫不决,过于客套流于委婉……说人闲话,滔滔不绝而言之无物”[4]11。在《薇约拉》一节中,莱丽亚充分表明她对男权社会意识形态标准的不屑。薇约拉在小说中的形象极其模糊,叙述者简单交代了她的背景:她是一位意大利人的情妇,后来在他特意为她建立的同名别墅中忧郁而死。为了避免睹物思人,意大利人将别墅和带有情妇坟墓的花园租给了别人。斯特尼奥和莱丽亚对薇约拉这个人物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斯特尼奥认为她的坟墓充满宗教气氛和诗意,她是一个为爱情而死的女人。莱丽亚认为她“不愿接受命运的摆布……毫不掩饰地憎恨这极不公平的权威”[6]76。如果莱丽亚的见解和斯特尼奥的一样,那么她将会和薇约拉一样,成为男人欲望的对象。但是,莱丽亚从一开始就抗拒男性的权威,这使她能够跳出男性中心主义来解读这个故事,那就是:爱情对于女性来说就是死亡,因为她们只能被封闭在“房间”之中,成为男人心中“永恒的女性”。桑突出了为女性利益说话的女性声音,表明女性作家在自我意识产生的同时,也为改善女性同胞在男权制度下被扭曲的命运进行着积极的努力。
二、“我是何人”——女性的自我言说
莱丽亚虽对男性受述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却没有对男性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者说建立自己的形象,这说明父权制文化为女性营造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女性无法进行自我言说。小说形象展示了这个寓意:在姐妹重逢后,布尔西莉要求莱丽亚讲述自己的故事,“人们忘记了我们,不再找我们了,我们能自由地呆一会儿了。讲吧”。女性只有在被男性“忘记”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自由”,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有当女性不再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时,女性才能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小说中,女性之间的叙述包括两部分。
其一,布尔西莉讲述了自己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她梦见一个黑眼睛的年轻男人亲吻自己,这种感觉让她心醉神迷。当她醒来之后,看到了沉睡中的莱丽亚,发现姐姐很像梦中的那个男人,于是发抖亲吻着莱丽亚。布尔西莉不仅认识到莱丽亚的雌雄同体特征,而且从女性那里得到了性启蒙。在父权制社会中,等级制的异性恋是符合文明发展的稳定性别秩序的。在这种秩序中,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部分”,女性的性别身份由男人所创造。桑嘲讽了社会中的性别刻板印象,让女性从同性那里得到身份认同,对父权制的自然秩序给予了有力的挑战。桑深知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奴役和毒害,所以让布尔西莉虽然朦胧地察觉到女性意识,却又最终成为任由男性发泄欲望的妓女。姐姐的故事是妹妹故事的继续。在年少时期,她和布尔西莉虽然有朴素的女性意识,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正如莱丽亚所说:“你的命运注定了,而我没有任何注定的命运。”[6]127布尔西莉自觉将父权制的标准和规范内在化,安心地享受被奴役的命运。莱丽亚则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她努力突破父权制既定的性别角色,试图摆脱女性是“他者”的悲剧命运。她不仅要掌握自己故事的话语权,而且男性不能作为受众参与到她的故事中。她只会对同性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性可以参与到她的话语之中。莱丽亚避开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非线性的、反传统的叙事方式来讲述自己的特殊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她不是斯特尼奥的诗神,因为她认为诗歌欺骗世人;她不是特朗莫苦行哲学的同路人,因为她是无神论者;她不是马纽斯眼中充满诱惑力的魔鬼,因为她官能冷淡。她不是任何男人“声音”中的她,她的形象只能由自己来定义。她打破社会规定的女性角色,希望自己是个男人,或许“还有以自己聪明才智能言善辩统治和领导男人的雄心壮志”[6]134。她借助男性来解决官能欲望和精神追求不能统一的矛盾,却发现男人不能分享她的痛苦,只能享受她的身体。她选择到修道院中隐居来实现肉体的禁欲和精神的禁欲,却让自己进一步遭受精神的折磨,最后成为虚无主义者。当隐居让她感觉无聊时,她又回到现实生活中,希望寻觅到一份柏拉图式的爱情。在莱丽亚的叙述中,她有强烈的自主意识,而这种强烈的意识让她把自己创造成了一个复杂立体的形象。这种形象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可以让人得到不同的阐释,或为双重人格的人物,或为自由的精灵,或为女性意识的先驱者,或为浪漫主义精神的女性代表,等等。莱丽亚用自己的讲述回答了“我是何人”的问题,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被任何人所定义的人。
其二,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莱丽亚是孤独的。首先,叙述者与受述者的交流是单方面的。姐妹二人有同样的家庭起源和同样的性别身份,本应该形成共同的文化圈,以抵御男权社会的霸权统治。而且莱丽亚也让布尔西莉参与到叙述中来,从而共享她的“文本”,结果后者先是对她嘲讽,然后劝她顺从生活,最后给出成为修女或者妓女的建议。虽然受述者直接参与到了讲述过程之中,但作为社会性别等级制度中的一名成员,她却无法理解叙述者的意图,无法肯定女性的自我价值,所以和讲述者无法形成积极有效的交流。其次,叙述者的叙述充满了孤独的气氛。莱丽亚的孤独源于父权制社会的桎梏。男人视她为欲望的对象,无法分享她的痛苦;女人被父权制意识形态所毒化,试图将她拉回到女人角色之中。宗教、道德、文化没有让她平静,反而加重了她复杂的性格。所有的一切都在捍卫着男性中心的父权制,使女性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莱丽亚只能孤独地自我言说。最后,内容强化了叙述者的孤独。叙述者从开始便界定了叙述的内容是心灵的故事,这使得她的叙述局限于自己的内心活动。正常叙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被剥离,增强了内心体验的敏感性、私密性和复杂性,从而强化了叙述者的孤独色彩。桑运用这种女性叙事的技巧,不仅增强了女性的“声音”,强化了女性的悲剧命运,而且表现出对女性救赎方式的积极探索,颇具超前意识。
三、“她是何人”——叙述者的言说
桑还设计了一个全知的叙述者,进一步回答了“她是何人”的问题。这位叙述者在小说中性别模糊,占据叙述权威的位置,具有“全知”的特点。叙述者的形象很少出现,却又能让人感觉到其形象的存在。全知叙述者的叙事风格是传统的、线性的叙事方式,往往包括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叙述者在文本中主要讲述了莱丽亚患病、姐妹易装和主人公死亡等事情,每个故事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这种清晰有序的叙述方式不仅丰富了莱丽亚的形象,也从社会外部因素探讨了女性的悲剧命运。在第一章叙述莱丽亚生病的事情时,叙述者清楚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并以旁观者的姿态讲述了整个故事。当莱丽亚染上霍乱时,医生把她当作研究对象,要求她用嘲笑霍乱的方式来对付疾病。她无法从医生那里得到治疗,只好寻求宗教,神父马纽斯拒绝给予祝福和祈祷。以拯救人的生命和灵魂为目的的医学和宗教,同样将女性排除在了“人”这个范围之外。女性依旧是客体,哪怕是在生命危急时刻,她的目的仍然是为男人服务。
叙述者讲述的另一件事情是“姐妹易装”。在亲王举办的舞会上,叙述者通过姐妹易装这个故事进一步揭示出女性“符号化”的生存状态。莱丽亚的妹妹布尔西莉是社交界闻名的妓女,她经常穿天蓝色风衣出现在各种场合,于是男人纷纷追逐穿天蓝色风衣的人,女人则穿上天蓝色风衣来寻找情人。当姐妹换上彼此的衣服之后,所有的男人都出现了认知混乱,包括疯狂爱着莱丽亚的斯特尼奥。他把布尔西莉当成了莱丽亚,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实际上,“易装”是西方文化中的常见题材,早期见于童话、寓言和民间故事之中,许多出色的作家如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马里沃等也喜欢用“易装”来营造作品人物的身份混乱。由此可见,虽然西方传统文化实行性别二元制划分,但又对性别的流动性和双性合一具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易装能够成为文学中的常见内容。易装的内涵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义,但都因其跨越性别界限,而对男尊女卑的二元制性别秩序构成一定的破坏。对桑而言,她年少时期就经常阅读民间故事,后来又接触过许多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卢梭等作家的作品,可谓是深受文学传统的滋养。当桑提笔进行创作时,却发现菲勒斯中心文化将无数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女性作家压制在“地表之下”,所以她自觉地担负起“写自己、写妇女”的伟大使命,在沿用易装题材的基础上,又将自己的女性意识赋予其中,使传统题材表现出新的立意,发出了女性作家的声音。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的主体性被封闭在卵巢、子宫之中,女性只能作为性别、生殖的人而存在,不能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人”而存在。所以,为了摆脱“他者”的地位,将自己确立为主体,女性必须打破父权制将女性视为客体的藩篱,把自己视为主体、主动者,通过主动选择和积极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存在状态,创造新的自我。莱丽亚和她的妹妹进行了易装,希望通过积极的行动,打破僵硬的性别等级关系,将自己树立为主体。可是,她们的行动遭到了挫败,因为男人是靠服装、面具等外在装饰来判断和定义女人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符号罢了。
小说中叙述者讲述的最后一件事是人物的死亡。在早期小说中,女性均以死亡为结局,这与桑对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切身体验有着紧密的联系。桑在进入婚姻生活后,饱受婚姻的“无爱”之苦;在摆脱了婚姻的桎梏后,虽然她主动追求爱情,却又承受着情爱所带来的折磨与痛苦。因此,桑在死亡、爱情、婚姻之间设定了某种联系。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多以死亡为结局,莱丽亚也不例外。莱丽亚死亡的故事不可能由她本人来讲述,所以叙述者再次出现在了小说的最后一章中。叙述者在小说中的性别也是十分模糊的,有时叙述者好像是位女性人物,“这些粗俗的英雄行为的动力,只是年轻人有的,两个早晨就可摧毁的幻想,和男人的顽固肮脏的野心——人类文明的产物”[6]108。如果是男性叙述者的话,他是不会用“肮脏顽固”来形容男性的。有时叙述者表现得像个男性,如在评价社会时是这样说的:“这垂死挣扎的社会如同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到死都在往脸上涂脂抹粉”[6]117,这句话又明显地透露着对女性的歧视和贬低。叙述者性别的模糊不仅使莱丽亚形象进一步复杂化,而且增强了这部小说叙述声音的复杂化:到底是女性叙述声音还是男性叙述声音在文本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还是二者皆有,平分秋色?这也成为《莱丽亚》小说的一个研究角度。
综上,乔治·桑放弃了传统文学中的线性叙事模式,采用多种叙述技巧来展现女性与父权制文明的对抗,清晰表达出女性对于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深刻认识,标志着作者对女性命运作出了形而上的探索,这也是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叙事技巧上说,乔治·桑建构的多重叙述声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浪漫主义时期充斥在文学作品中的男性英雄主义的叙事声音,也突破了作者本人在《瓦朗蒂娜》、《印第安娜》中的叙述模式,使女性声音上升到叙述主体的位置,彰显出女性作家的写作权威,虽然没有完全从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叙述声音中解放出来,但也不啻于一个重要的进步,对于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 安安.乔治·桑 [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2] (法)圣勃夫.乔治·桑 [M].成钰亭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
[3] Espinosa Maria. ON a translation of George Sand's Lelia [J].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1979,(12).
[4]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 [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Catherine M. Peebles. The Psyche of Feminism: Sand, Colette, Sarraute [M]. USA: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4.
[6] (法)乔治·桑.莱丽亚 [M].吉庆莲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7]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 [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