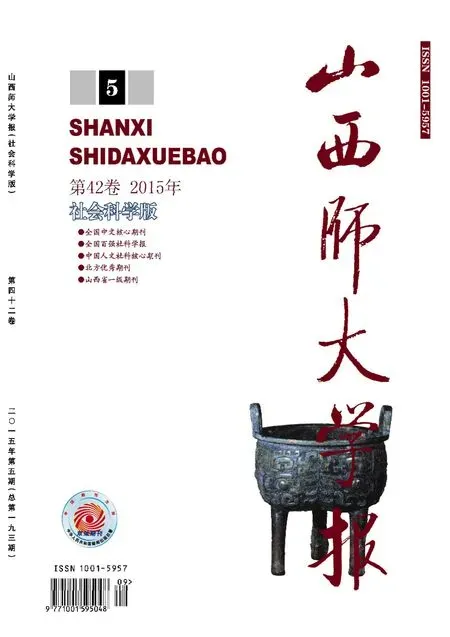再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2015-04-11汪帮琼
汪帮琼,秦 楚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第一原理,是人对自然物质力量的合理运用,是社会生活的本体论前提。面对由强势的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全球化发展,以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劳动概念的被遮蔽,必须重提马克思哲学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并阐释其整体性内涵。
一、重提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一)全球化发展必须寻找能够驾驭资本的有效力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作为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克服生活实践既有的狭隘界限的积极因素,资本主义甚至把局部的狭隘利益变成生活实践的唯一目的。正如比尔·雷丁斯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美国化’,究其眼下的形式而言,也就是全球化的同义词,但是这个同义词意味着,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过程,它不可能让华盛顿和达喀尔具有平等的参与机会。这枚不公正的铸币的正面所展现的是,由全球化命名的跨国资本的吞并过程”[1]2—3。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并未真正走出其地域性的狭隘意义:资本的抽象逻辑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而不惜损害多数人乃至全人类利益;个人脱离整体性的生活实践,其对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的承受能力,不但不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巨大进展而得以及时更新和扩展,反而进一步萎缩和僵化。事实上,不仅发达国家难以超越自己既得的地域性利益,难以放弃进一步发展的地域性价值而选择社会发展的人类整体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样也面临地域性的民族国家意义与整体的人类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不能在中国的地域性历史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在资本的“全球化”层面上展开。要在这样的困难处境中长期生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必须寻找并依靠能够驾驭资本的有效力量,必须深深扎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本体论前提——劳动。
(二)马克思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劳动概念被遮蔽。从黑格尔第一次把“劳动”提高到人类精神的层面来予以考察,到马克思把人定义为劳动的动物并提出异化劳动思想和劳动价值理论,劳动这种古老而不可或缺的人类活动,逐渐成为近代西方思想家严肃思考的重要理论议题。然而,自亚当·斯密把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引入社会伦理思想领域加以肯定性的解读之后,黑格尔那里在人类精神层面得到确证的劳动概念,又被推回到经济学层面加以解读,而且劳动概念被逆转: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成为劳动活动的本质和特征的真正体现,哲学人类学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则压倒性地被遮蔽或否定。在以哈贝马斯、霍耐特、鲍德里亚以及阿伦特等人为代表,根据现代性的框架重新阐释劳动的理论探索中,对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只是立足于认识论并主要在经济学的层面加以肯定性解读。对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层面的劳动概念则避之唯恐不及,这些理论家不是将其看作意识形态,就是将其解读为直接超验的、非理性的苦行。面对西方劳动学说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的这一情境,以吴晓明、张一兵、王江松、王晓升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批判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劳动学说的过程中强调,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本体论意义——作为人的独立存在的本体论前提的“对象性”原则和“感性”原则内在统一的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哲学超越西方劳动学说史的伟大贡献。马克思基于其劳动学说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解答,不是要否定劳动所蕴涵的主体性和理性的力量,而是要改变劳动所采用的资本主义形式;没有劳动及其蕴含的主体性和理性力量,超越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不可能的。[2][3][4][5]
二、社会本体论意义的“劳动”及其整体性
西方劳动学说史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回避社会本体论意义的劳动及其整体性,最终停留于人和自然外在对立的观念上。马克思哲学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坚持人类劳动的整体性内在于自然事物的整体性,因此只有回到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才能把握马克思哲学中“自然”与“历史”的关系,否则,马克思的相关思想难免被带入强势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
(一)自然事物的整体性
1.自然事物的实在整体性无需理论证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首先肯定自然界本身以及人作为自然事物的实在性。在这里,容不得包括宗教创世说在内的任何以“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为预设的、抽象的、需要予以理论证明的问题。[6]130—131“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6]131劳动提供了关于“自然界本身以及人作为自然事物的实在性”的最为直观、有力的证明。在马克思看来,人“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6]167
2.劳动是对自然事物实在整体性的证明。亚里士多德最早在《物理学》中将自然与人为的活动(即技艺和实践)区别对待。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自然不是抽象的、无限的物质要素的总和,而是自然事物有限的整体,它指引种种有机过程趋向完善,也是种种自然事物为实现自身的自然而恒常遵守的法则。人可以有自己的偶然的意图,但这种偶然的意图如果要实现并不断维持其成效,就必须最终遵守内在于自然事物的“自然”。所以,自然是人的一切行动的根本条件和最终根据;在人对其他种种自然事物有任何行动之前,他自己就已直接是自然事物之一,而且自然本身绝不仅仅是“为人的”,而是为一切自然事物的。
关于自然事物自身的实在性,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无疑有着基本的共识。不过,马克思依据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对自然事物的实在整体性的彻底肯定和证明,与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所做的肯定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然事物的实在性是无需理论证明的,“试图证明自然存在是荒谬的,因为很明显有许多这样的事物”[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够辨别自明的东西,那就不会试图用不明显的事物去证明明显的事物。另外,亚里士多德强调,自然事物的整体性和必然性只能通过理论沉思来把握,而人的实践即伦理政治行为发生在自然事物偶性的范围内;相对于理论沉思而言,伦理政治实践离自然事物的整体性更远。而马克思强调的是人的劳动与自然事物的整体性的内在关联,面对自然事物的劳动离自然事物的整体性最切近。劳动之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第一原理,就在于它与自然事物的整体性的内在关系。
3.劳动意味着自然界整体性的优先地位。“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6]124在这里,马克思坚持的是自然事物的整体性对于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类历史的优先地位。马克思认为,对于人类世界具有根本优先地位的,是具有内在生命和法则的自然界,而不是被归结为机械运动及其规律的抽象物质存在。自然界整体性的优先地位意味着,自然事物的整体对同样作为自然事物的人的成就;人的劳动以自然事物的内在关系为前提条件。对马克思来说,自然界是自然事物的整体,种种自然事物遵守自然界整体的恒常法则,自然界本身蕴含着为人的劳动提供可能的整体性。
马克思依据人的劳动对自然事物整体性的原初优先地位加以彻底的肯定。亚里士多德曾经将自然事物的整体性与人的思辨精神联系起来,自然事物的整体性和必然性只能通过理论沉思来把握;马克思强调的则是人的劳动与自然事物的整体性的内在关联。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6]167,劳动的主体,最初是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6]50,最终也将通过历史的扬弃而实现与自然事物的整体性的真正和解:“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6]124人类劳动首先意味着人作为自然事物与其他自然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合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6]201—202”所以,人的劳动内在于自然事物的整体性,而人的劳动的最终保证无非是自然事物自身的整体性而绝非单纯的人为所能及。然而人类历史之“恶”恰恰在于:虽然单纯的人为无力构成自然事物自身的整体性,却完全能够摧毁它。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强调自然事物的整体性通过“人的实践”的“真正复活”。
(二)“劳动”内在于并自觉回归作为整体的自然界
对于马克思来说,无论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感知经验意义上的亲身尝试,或费尔巴哈的“直观”,抑或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都不是人的生命活动之根本,人的整体性的劳动才是其根本。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依靠并可以自觉回归作为整体的自然界,正是整体性的劳动把人的生命活动和动物本能活动区分开来了。
1.“劳动”不能被归结为抽象的经济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历史的永恒必然性,而人的生命活动的社会历史性内容是派生性的。尽管马克思对劳动之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根本是如此明确无疑地加以肯定,以至于后来解释家对此最终都无法彻底否定,然而,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注释家仍然强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属于偶然事物的伦理政治实践,而劳动则被视作马克思观点的缺点,因而是需要加以修补甚至替换的部分。哈贝马斯根据“交往理性”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引人注目的重建就是如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经济活动,它的意义仅仅在于生产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的工具理性并不具备整合现实的整体性,因而在劳动中无法找到人类解放的根本前提。而且,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以至于社会解放的兴趣根本无法在作为经济活动的劳动中表现出来。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劳动之所以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根本,不是由于抽象的物质需要,而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与自然事物有着整体性的内在关系。
2.劳动的自觉整体性。在马克思那里,劳动的根本内涵就在于它与自然事物整体性的内在关联。脱离自然事物的整体性来谈论劳动,劳动最终只能沦为抽象的经济活动,沦为无限制和无节制的、单纯物质要素的排列组合;而脱离劳动的整体性来谈论实践和感性,实践和感性只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抽象的直观。以自然事物的整体性为原初前提的人的劳动的自觉整体性,即劳动所蕴含的主体性和理性力量是马克思哲学的伟大发现。
人的劳动的自觉整体性就在于,它可以通过意识将自身与其局部的自然对象区分开来,进而能够以整体的自然为对象,在整体自然的范围内实现生存。人的劳动实践因其自觉整体性而不同于动物的生存活动,动物并不通过意识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与周围环境区分开来,其生命活动并不能主动超出现成的自然条件,更不用说突破整体自然的节奏和周期。人的劳动实践是一种整体性的自觉活动,人不仅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而且能够通过意识而把自然界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人的劳动实践的自觉整体性表现为:(1)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能进行真正的生产;(2)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3)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4)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3.不能把劳动的整体性从自然事物的整体性中剥离出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绝不意味着自然界仅仅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人类生存的条件或者满足人类抽象物质需要的手段。相反,劳动的整体性内在于自然事物的整体性,不能将它从其中剥离出来。作为种种实在事物的整体,自然意味着人(包括历史、艺术等)和动植物共同的基础、共同的存在和最初根据。“假如马克思强调历史/人/自然以实践为中介的高度统一的话,那么在这种三者统一的结构中,自然乃是最基本的,历史取法自然,历史乃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自然只能取法自身。”[8]马克思从来没有从泛神论角度赋予历史以“独立性”。[9]23法兰克福学派也曾表明,“自然对象的独立整体不得不被保护,尽管这并不忽视它和人类主体相互作用。马克思曾称之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是必须的,但不能以取消它们之间的不同为代价。”[10]305然而,由于回避劳动及其内在于自然整体的关系,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就难免被混同于通过人类历史的所为被变样过了的“被文明化的自然”、“被历史化的自然”[11]17,其结果仍是自然与历史之间相互外在的对立——“工人阶级只有首先征服自然,才能征服人”[12],而社会解放的希望只能变成某种乌托邦式的理念和计划。
劳动的整体性从自然事物的整体性中脱离出来,必然造成历史与自然的根本对立。以劳动为根本的人的生命活动是以自然事物的整体性为根本前提的,然而它又具有历史性的规定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它们的历史性规定甚至达到完全的“非自然”或“反自然”的程度。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和自然的这种对立,其原因不在自然事物之中,而是埋藏于劳动脱离自然事物的历史进程中;而且,自然和历史对立的观念——将人世间那些由人自身的活动所引起的不幸和灾难,归结为所谓自然本身的“恶”的结果——同样是历史进程的结果;这样的观念将随着人类历史的自我改造而得以克服。所以,马克思坚持“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120这样,“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6]122
三、劳动对于人类社会的本体论优先地位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将自然与历史外在对立起来的各种观念,其共同点就在于回避劳动对于人类社会的本体论优先地位。换句话说,它们把历史中的和平与进步归因于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努力,而把历史中的不幸和灾难看成是不可避免的、神秘的偶然,并将它们最终归咎于纯粹自然的反常现象,因而人们最好安心等待救赎或者以幻想的方式去反抗。[2]97—98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实践哲学,同样回避劳动对于人类社会的本体论优先地位。在他们那里,实践根本上是一种根据完全内在的自我意识的绝对创造,而这样的实践并不能应对自然的反常和神秘,也无法面对强势的资本逻辑必然带来的不幸和灾难,最终不能避免无用和失败的结局。马克思在肯定劳动对于人类历史的本体论优先地位的前提下,强调人类能够而且必须面对由工业活动和社会制度造成的人世的痛苦和灾难,担当起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切实进行“革命的实践”——“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6]51。
(一)劳动对于“革命的实践”的优先性
马克思坚持劳动对于“革命的实践”的优先性,即“革命的实践”是以劳动为根本前提的。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首要内容。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生命实践活动的根本,不是理论思维的活动,也不是政治文化的活动,而是作为人类历史的永恒必然性的劳动。然而,回避劳动,强调理论思维的活动或“政治革命”对于人类社会解放的意义,俨然已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传统”。阿尔都塞当年曾反对直接将理论思维归结为实践活动,突出强调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思维”;卢卡奇也不隐讳其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倾向:他明确反对那种“过高地估计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作用”的观点,而以“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作为他“许多论述的基础”;柄谷行人近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代表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也是透过康德来阅读马克思;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回避作为社会本体论前提的劳动,把理论文化的“实践”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
马克思的“革命的实践”,不是理论思维对于其对象的抽象解析和构造,也不是虚幻的政治文化革命,而是以劳动为根本前提的。马克思强调,单纯的理论思维活动或“政治革命”不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增加任何积极的东西。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实践”——“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其必要性和条件只有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才能被发现。也正是奠基于人的劳动及其整体性,这种“革命的实践”才能产生积极的意义和成果。
(二)劳动与“革命的实践”的可能性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3]19在这里,“革命的实践”的可能性首先在于,“革命的实践”的对象即“现存的事物”为什么是能够被改变的?“现存的事物”马克思又称之为“整个现存感性世界”[6]77,其真正所指并不是包括自然事物本身在内的、无所不包的“整个感性”世界,而是人的整个“现存”世界,即整个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这个世界也是具有某种实在性的“整体”,但是从其现存状况来看,它并非最初的、从来就有的“整体”,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整体”存在,它以“资本”这一“非自然”甚至“反自然”的因素为本质。正因为如此,它才是能够被改造的。
其次,对马克思来说,“革命的实践”的可能性还在于,如何才能够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这个问题涉及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揭示“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深藏不露的另一面——它的不幸和灾难。“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6]4—5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马克思最根本的理论任务就是揭示和分析现存世界自身的逻辑——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及其不可避免地给人类历史带来普遍的恶果:贫穷、战争和恐怖。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6]414然而,在当今世界全球性的现代化诉求中,人类社会内部分裂所导致的惨痛代价仿佛是无足轻重的,至关重要的反倒是人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满足人自身的创造性的精神需求。这一点,在法国当代哲学家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中有着更为具体而详尽的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理论、话语和精神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根本的断裂,而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或话语,并不会涉及、揭露这个世界的残酷而荒唐的另一面。[14]这就涉及问题的第二个环节:超越精神的表面的“创造”活动,立足于社会本体论的劳动来进行思考。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立足于“劳动”才能进行对旧世界的揭露。因为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精神的表面的“创造”活动只不过是资本对人的真正的创造性活动——劳动的支配和掠夺,而所谓“人自身的创造性的精神需求”,最终也只不过是资本支配和掠夺劳动的“需求”。对于马克思来说,“现存的整个感性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一个可以充分允许人类的真正创造活动的自由乐园,而是一个充满不幸和苦难的世界。只有从社会本体论水平的劳动出发,才能够揭示现存世界的这一背面;只有立足劳动,人类才能够“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如实面对这个世界中的不幸和苦难,从而进行积极的自我治疗和拯救。
(三)劳动与“革命的实践”的必要性
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的实践”的必要性,首先来自于劳动在现存社会内部所遭遇的不公和不断被挤压直至完全非人化的实际状况。“明亮的居室,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6]133—134
不得不提的是,在新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革命实践”的必要性已经不在于劳动在现存世界所受的压迫和屈辱,因为今天的资本主义表现出不同的状况:信息和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的形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血汗工厂。至于说,现存世界的种种不幸和痛苦,则集中表现为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所以,如果说“革命的实践”还有必要的话,那么,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而后者的原因被归结为自然本身的衰败和腐化,所以“革命的实践”即“真正的自然的复活”,必须依靠自然本身的力量。“自然”在卢卡奇那里是作为一个负面因素即人类所不能掌控的盲目力量而予以理解的;马尔库塞则提出了一个看上去比马克思的“自然的复活”更为激进的特殊的自然主体论。他认为,自然的解放就是要依靠自然本身的感性潜能,把自然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占有中解放出来。本雅明则认为,自然本身也有一部不断地衰败堕落和腐化的历史——也即自然史,而这样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希望同样在于弥撒亚的救赎:弥撒亚的突然降临将会突然遏制自然史和人类历史的衰败颓化,从而带来一种革命性的转变。类似的,根据现代西方哲学的观念,人类历史活动之所以充满危险和荒谬,因为危险和荒谬恰恰是世界的存在的本来面貌,所以,不管人类怎样努力实践,最终都将归于失败。
然而,马克思强调历史的内在矛盾,强调现代工业对原初自然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给劳动所带来的不幸和灾难。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谈论革命的实践的必要性就不能回避劳动在现存世界所遭遇的不公和牺牲。在马克思那里,虽然“革命的实践”的最终意义是包括劳动者在内的人类社会所有成员的解放,它同时意味着“真正的自然的复活”,但是“革命的实践”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医治和弥合现存社会内部的分裂:劳动在现存世界所受的压迫和屈辱。这样的“革命的实践”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劳动是人类历史的本体论前提,劳动在现存世界所受的压迫和屈辱,必然伴随着自然事物的衰败和腐化。劳动在现存世界“受难”不是某种自然的纯粹偶然现象,也不是自然过程本身的必然结果,而必须被按照其本来面貌如实地理解为历史活动合乎其逻辑的结果。甚至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在根本上也是由“非自然的资本”的逻辑所招致的。劳动的屈辱的历史现状如果不能得到改变,任何真正的历史发展在根本上都将是不可能的。
所以,革命的实践意味着人类必须切实而有效地遏制资本的逻辑。对马克思来说,作为“革命的实践”的主体的人类,首先是受难的劳动者。人类历史迄今以资本为最高形式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尽管发生很多新变化,但是它在根本上并不会自我改变。现今社会内部的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6]414然而,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6]414“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多,那么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6]414—415其次,必须强调的是,“解放”是人类而不是自然本身的事业,真正的自然的复活绕不过“革命的实践”。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造成包括自然的腐败在内的不幸和灾难的根本原因;革命的实践所要实现的“人的解放”或“自然的解放”必须诉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能依赖纯粹自然的力量,也不能在幻想中实现;“人的解放”并不是要将人从自然之中解放出来,恰恰相反,人的解放正是真正的自然的复活,而真正的自然的复活必须通过人的革命实践才能实现。
[1] (加)比尔5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吴晓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兼评A5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3).
[3] 张一兵.马克思与劳动意识形态——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批判性解读[J].学习与探索,2007,(2).
[4] 王江松.对现代西方各派劳动哲学的比较研究和综合扬弃[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0,(5).
[5] 王晓升.论马克思的两个劳动概念与两种历史解释模式[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Aristotle, PHYSICS, Translated by RP. Hardie and RK. Gaye,193a3—193a9.
[8] 张文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与历史主义[J].人文杂志,2005,(1).
[9] (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沈力译.台湾:结构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1988.
[10]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M].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1] 广松涉.事的世界观的前哨[M].赵仲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 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145.
[13] 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4]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