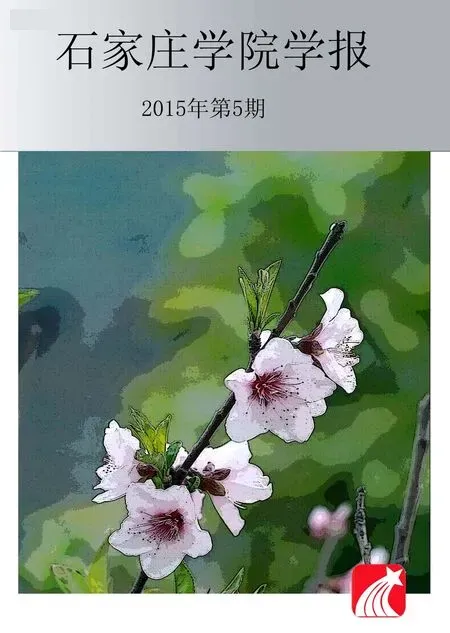《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研究的若干思考
2015-04-11李浩
李浩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研究的若干思考
李浩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蒲松龄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不会有反清情绪,于七之乱也不具备反抗异族压迫的性质,《公孙九娘》“政治隐喻”说不能成立。部分研究者为抬高《公孙九娘》的思想性、艺术性,存在断章取义、选择性运用材料、扭曲作者本意的倾向,过度依赖历史“常识”的解读方法使文章充斥着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但真正复杂的“社会”和“现实”却被隐没了。只有抛弃“后见之明”式的思维方式,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回到现场”,对作者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才能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作出无限接近于事实的客观评价。
蒲松龄;聊斋志异;公孙九娘;诗史互证;反思
《公孙九娘》是《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中的名篇,讲述的是莱阳生与女鬼公孙九娘的凄美爱情故事。建国后,因小说叙事背景涉及清初政治文化生态,《公孙九娘》在很长时期内被视为体现“两结合”、彰显“人民性”的代表作,这种“预设”至今制约着对本文的解读。经过20世纪两次深入的争论、探讨,学界普遍认为:“民族思想”“反清意识”不构成《聊斋》的主导思想,但《公孙九娘》《野狗》《林四娘》《鬼哭》等作品仍可结合作家生平、文本内容进行具体分析。[1]393学术贵乎后出转精,但部分《聊斋》名篇的研究却陈陈相因①学界普遍认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聊斋》研究的持续深化,也不利于彰显对前贤论断原创价值的尊重,王立、赵伟龙2014年撰文重申了上述共识,详参氏著《〈聊斋志异〉研究“炒冷饭”现象的一些思考:新时期以来〈促织〉与〈变形记〉的比较研究》,载《蒲松龄研究》2014第2期。,《公孙九娘》即不幸厕身其间。“社会历史—文学”的批评方法固然提供了有效的切入视角,不过将某种文学批评当做“前提”反复言说,把问世以来即被认为具有理解多义性、阐释拒阻性的文本固化为一种解释,未免令人感到遗憾。在下文中,笔者将对六十多年来的《公孙九娘》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并尝试指出其洞见与不见,以就教于博雅君子。
一
《公孙九娘》以“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始,以“坟兆万接”“鬼火狐鸣”终,贯穿其间的是男女主人公的邂逅、结缘与不合情理的诀别。清人冯镇峦称蒲松龄故作此“迷人之笔”[2]713,但一手导演了爱情悲剧的蒲氏却在文末大呼“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而怨怼不释于中耶?脾鬲间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2]713。蒲氏的暧昧态度使《公孙九娘》的叙事意图在清代点评家处已聚讼纷纭:梓园谓“志表乃第一紧要事,当先问之。此九娘所以恨也,乌得言冤”;但明伦承认“忘问志表,生固多疏”,然“夜往路迷,不可谓非鬼之无灵也,况稷门再至,冀有所遇,此情实可以告卿。既独行于丘墓间,何难再示以埋香之所?乃色作怒而举袖自障,女学士毋乃不恕乎”;冯镇峦、何守奇则认为“二者均失”[2]713-714。以上四人虽仅就事论事,但异议本身彰显了文本的求解性、多义性。建国后,聂石樵、赵俪生、马瑞芳等前辈学者以历史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对《公孙九娘》进行了综合研究,并指出:《公孙九娘》“深刻地同情着于七起义这样一场爆发在康熙年间的农民起义”,莱阳生与公孙九娘爱情的失败是“和严肃的政治性开头相呼应的必然结尾,是一幕政治惨剧的必然结果”,“公孙九娘的悲剧意义,不在于鸳鸯分飞的离妇愁,而在于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愤慨与抗争”,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昔日的血泪史。前辈学者的这些说法堪称文学外部研究的典范,相较于清代印象式的点评,“社会历史—文学”的批评方法尝试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表现出阐释的深刻性。①代表文章有聂石樵《关于〈公孙九娘〉的描写及其历史背景》,《光明日报》1961年9月3日;赵俪生《读〈聊斋志异〉札记》,载《蒲松龄研究集刊》,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0页(案据作者自注文章写于1966年冬);马瑞芳《凄凉哀婉,扑朔迷离:〈公孙九娘〉分析》,《聊斋志异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176页;袁世硕《续幽冥之录,诉弥天之冤:〈公孙九娘〉发微》,载《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3期。当上述结论写入文学史,则进一步成为初学研究《聊斋》的“预设”和“共识”,近几十年来有关《公孙九娘》的研究文章不过是重申这些观点而已。但若我们回到现场,以“了解之同情”重新审视“政治主题”说,则不难发现:即便在《公孙九娘》《林四娘》《野狗》《鬼哭》《九山王》《乱离》《张氏妇》《鬼隶》《韩方》等以清初政治事件为背景、被学界认为需具体分析的篇章中也不存在民族思想、反清情绪,更没有表彰反抗。原因有二:
第一,蒲松龄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不会有反清情绪。据《公孙九娘》开篇“甲寅间”的时间推算,本文创作至早也当在公元1674年或之后,此时南明已亡,郑成功已逝,各地的反清运动也基本平息。自甲申(1644年)以降,“死社稷”“死封疆”“死城守”者众,然“自古南渡灭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于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昪,而其亡也忽焉”[3]363的残酷事实使忠明士人对时局的认识清醒而绝望。“时事必不可为”[4]702,“所不克者,大势已去”[5]222,坚持反清者只是尽节全义,已不期成功。遗民尚且如此,何况未受明王朝特殊恩泽的蒲家?尽管吴三桂在1673年举兵,声称要“共奉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6]86,郑氏子孙仍占据台湾,但蒲松龄《拟上允辅臣请,选日开馆,编辑〈睿算平定三逆方略〉群臣谢表》《拟上特简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台湾荡平,群臣贺表》二文已表明立场,后表中“从此千百里梗化之乡,皆为禹迹;四十年不臣之地,并入尧封”[7]335云云尤足见所谓“孤愤”之士的微妙心理。在蒲氏的家乡山东,前朝官宦、乡绅名流对满清的入主是持欢迎、合作态度的,如:山东士绅领袖谢升拒绝效忠南明,主动攻击李自成“大顺军”,伙同其他四十多位士绅领袖致书清廷,表示“谨扫境土,以待天庥”;甲申年(1644年)降清的“贰臣”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山东,此后仍有大量山东籍官员陆续投降。“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8]315蒲松龄的父亲蒲槃科举失意、弃儒从商,不会有遗民心态,但经商后“数年间,乡中称为素封”的他同多数乡绅一样,有“保证乡村经济的正常,维持生活安宁”的利益诉求。因此,明末山东大乱,蒲槃与宗族结村自保,抵御流寇袭击;1647年谢迁之乱,蒲氏家族不仅谋求与清军合作平叛,战后还捐资修筑了淄川城墙。[9]14-15同乃父一样,蒲松龄对扰乱平民正常生活秩序、寇掠乡里的所谓“义军”深恶痛绝,这点下文还要谈到,兹不赘及。至于蒲松龄的交游,其间固然有遗民②参见张崇琛《蒲松龄与诸城遗民集团》,载《蒲松龄研究》1989年第2期;[英]白亚仁《略论李澄中〈艮斋笔记〉及其与〈聊斋志异〉的共同题材》,载《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1期。,但更多的是出仕清廷者,如施闰章、王士禛、高珩、孙蕙、唐梦赉等。此外,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清认识到元之速亡在于丧失了儒生阶层的支持,故顺治很快采纳了汉族谋臣的建议,承认明代秀才、举人之身份,并于1645年秋8月举行乡试,次年春2月举行会试,此举笼络了包括蒲松龄在内的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蒲氏终其一生都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对现行制度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的书生是不会有所谓“反抗性”与“民族情绪”的。
第二,蒲松龄对于七式的“义军”并不认同。综观《清史稿·杨捷传》《山东通志·兵防志》《莱阳县志·附记·兵革·清代兵事》,知于七为崇祯时武举人,系栖霞强宗,明亡后聚啸山林。其后满清入主中原,时四海未定,清廷遂于顺治七年(1650年)以怀柔政策将于七招安,令其任“栖霞把总”擒贼自效,此后十余年相安无事。顺治十八年(1661年),宋彝秉因私忿告于氏谋反,而于家又杀了“行察之兵”,于七不得不再度举事,次年被济席哈攻灭。[10]1619众所周知,明亡前夕,因白莲教起义与清军的劫掠,山东地方政府已然陷入混乱,权力落入地方豪强、大盗悍匪手中,顺治五年(1648年)的于七“起义”不过是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而顺治十八年(1661年)再度起事更系偶然,很难拔高到反抗异族压迫的层面。“义军”之“不足恃”,时人是有评价的:黄宗羲谓“时乡壮皆民间无赖子弟,闻义旗起,皆相率团聚,以图富贵”[11]204;王夫之云“义军之兴也,痛故国之沦亡,悲衣冠之灭裂,念生民之涂炭,侧但发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脑者,数人而已。有闻义之名,而羡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几幸其得者焉。其次,则有好动之民,喜于有事,而蹒踔以兴者焉。其次,则有徼幸掠获,而乘之以规利者焉”[12]194,“其果怀忠愤者,一二人耳,其他皆徼利无恒,相聚而不相摄者也”[13]701。上述二人都曾“举义”参与抗清大业,他们宁肯放弃遗民式的期待,以实际的经验深刻剖析当时与义者的心态,应当是可信的。[14]60-66于七之党与上述所谓“义军”其揆一也。蒲松龄在《盗户》中对这些以举义为名、行“杀人放火求招安”之实的流民集团有着详细的描述:
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2]1602
蒲松龄对危害良民却被官府曲意袒护的“群盗”深恶痛绝。在《九山王》中,蒲氏以顺治初年“山中群盗窃发,啸聚万余人,官莫能捕”始,以“九山王”覆灭前追悔“今而知朝廷之势大矣”终,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
夫人拥妻子,闭门科头,何处得杀?即杀,亦何由族哉?……明明导以族灭之为,而犹乐听之,妻子为戮,又何足云?然人听匪言也,始闻之而怒,继而疑,又既而信,迨至身名俱殒,而始悟其误也,大率类此矣。[2]354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七据山对抗清廷,而《野狗》劈头就说“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主人公李化龙“恐罹炎昆之祸”,“自山中窜归”[2]106,把平民和“义军”进行了切割。李化龙逃归正因“义军”不足有为,正如曾“与义”的黄宗羲指出的那样:聚啸山林的“义军”“皆偷驴摸犊之贼”,“其父杀人报仇,其子行劫”,“乡村坊落,凡有富名,辄借名索饷,恣啖酒食”,无益于时局,反“徒为民害”[11]189。《野狗》交待“兵过既尽”,群尸起立云“野狗子来,奈何”,则野狗明指下文“兽首人身,伏啮人首,遍吸其脑”的怪物而非清兵,有些学者以“文中是将清兵等同于野狗”佐证蒲氏的“民族思想”显然无法成立。《唐太史命作生志》尤足见蒲松龄对于七起义的态度:
昔莱郡有于七之难,王师一旅,秉钺东征。燕巢危幕,至倾拔木之风;兵弄潢池,大惧炎昆之火!……于是掠禁惟严,肤功立奏:纵俘擒之弱息,欢噪孤城;拉哑叱之娇婴,还归故里。卒之群丑皆奔,二天齐戴,溯所由来,厥砂茂已![7]247“大惧炎昆之火”云云正与《野狗》“恐罹炎昆之祸”句同,蒲松龄对底层民众和名不副实的“义军”始终有着严格的区分。他在文中高度赞扬了唐梦赉劝谏祖泽溥、保全无辜百姓的事迹,而蔑称于七的覆灭为“群丑皆奔”。既然蒲松龄本人没有反清意识,于七起义也不具有反抗压迫的性质,那么《公孙九娘》的主旨自然与此无关了。
二
解读《公孙九娘》等涉及清初政治文化的《聊斋》故事时,人们常会不自觉地受如下推论影响:蒲松龄是关注现实的优秀作家,他想要记叙明清鼎革带来的社会巨变,但囿于清代严酷的文字狱,只得以隐晦的狐鬼故事展现民族创伤、表达反清思想;而正因蒲氏采用了“谈狐说鬼”的形式,才保留了比官方记载更为丰富的史料,使得今人得以窥见当时的反抗斗争。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提醒我们,认为“作家应该认识特定的那个社会环境并完满地去表现他自己时代的生活,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代表”的社会学评价标准实际上是偏颇的:
倘若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单纯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献……就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15]104
《鬼哭》劝行德政,“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愿无出鬼面以吓人”[2]114;《乱离》称姜瓖反清为“姜瓖之变”,盛赞仕清的陕西某公“有大德,故鬼神为之感应”,悲“炎昆之祸,玉石不分”“董恩白之后仅有一孙,今亦不得奉其祭祀,亦朝士之责也”[2]1214-1217;《韩方》讽刺“沿途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与策马‘应不求闻达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类此”[2]2397;而论者常罔顾作者的真实意图,以三文有明末清初的史实便断言蒲松龄有同情起义、反抗异族的思想倾向,与研究《公孙九娘》的路径如出一辙。在这些论述中,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社会”“现实”获得了至高的权力,但“将社会背景和作品的相应内容放在一起,声称它反映了现实”的阐释方式却使真正复杂的“社会”和“现实”被隐没了。重大政治事件真的会影响到每一位作家的思想世界吗?知识精英(无论贰臣还是遗民)论述的时代精神具有普适性吗?文学作品作为无意识史料可以为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佐证,但特定事件的描写等于观念上的认同吗?蓝翎先生1956年曾指出,当时的《聊斋》研究存在“断章取义、寻字摘句,找出一些可以作为社会学、历史学、风俗志资料的细节描写肯定文学的现实精神”“用一般的原则代替具体的分析,以部分的、甚至全部的社会背景代替个别作家和作品的思想立场”[16]的错误倾向,这一论断至今仍有警示意义。
论者为突出《公孙九娘》等《聊斋》故事社会批判性的可贵,常常刻意渲染清代文字狱的残酷。实际上,清初相当一段时期里文人学者尚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17]379;抗清遗民多可保全性命且著书立说,不就征辟朝廷也不予怪罪;至于孔尚任撰《桃花扇》全写南明故事,“王公荐绅,莫不借抄”,康熙亲览后亦未加诛戮。自玄烨亲政(1669年)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南山集》案”起40年间,文禁实较后世宽松,认为《聊斋》的字句敢于触犯时忌是典型的“以后绳前”。《林四娘》虽涉及前朝旧事,但蒲松龄系记录而非原创,不能代表蒲氏的思想,何况王士禛、陈维崧皆有同类创作,足见在当时不犯文禁。《黄将军》未写及明亡以后事,犹有学者以“敢于缅怀明将”而褒扬之,今考顾炎武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作《蒋山佣都督吴公死事略》直接表彰抗清义士、纵论明清易代之势亦为清廷所容,则蒲氏言论本不犯讳。又,乾隆时文字狱最严,而袁枚犹有《人面豆》一文:
山东于七之乱,人死者多。平定后,田中黄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妇,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颈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为人面豆。[18]520
袁枚所处之世文禁严于清初不知几何,而其辞并不隐晦,蒲松龄又何必非在《公孙九娘》中以“幽婚”的形式委婉地传达于七“起义”的史料呢?盖蒲氏之本意并不在此。对于《公孙九娘》等故事,“我们必须避开那种常见的错误,就是把这类文学虚构牵强附会地看作真的是对‘现实生活’的鞭挞”[19]326,更需极力避免的是,为论证某一主题,不惜忽略对文本的具体分析、将作家与真实的历史割裂开来,强古人以就我。事实上,蒲松龄高度依赖现行体制,他对科举、吏治的批判恰表明其忠诚,蒲氏期冀的是通过纠正、改良与重塑社会规范,实现儒家理想的道德与社会秩序,而非另起炉灶。
部分学者认为,《聊斋》中的爱情可以跨越阴阳、物种之别,使“白骨顿有生意”、情人终成眷属,故公孙九娘爱情的失败绝不在“人鬼异类”而在蒲松龄颇具苦心的“政治隐喻”,《公孙九娘》的独特艺术魅力正在于打破了《聊斋》故事大团圆套路的似真幻觉而以彻底的悲剧收场。类似论述常见于近年的单篇分析文章中,其逻辑是通过强调蒲氏的“破例”来突出《公孙九娘》的艺术价值,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偏颇的。综观《聊斋志异》全书,人与异类的爱情故事大致有以下两种模式:
第一类以《娇娜》《青凤》《婴宁》《聂小倩》《莲香》《巧娘》《红玉》《胡氏》《黄九郎》《连锁》《鸦头》《伍秋月》《小谢》《梅女》《嫦娥》《神女》《湘裙》《长亭》《阿纤》《白秋练》《凤仙》《西湖主》《粉蝶》为代表,是典型的“团圆”故事,其基本叙事模式为“相遇→相知→历尽磨难→最终结合(包括女鬼复活、书生高中、二美并行等)”。
第二类以《胡四姐》《侠女》《汾州狐》《林四娘》《金陵女子》《白于玉》《犬灯》《狐妾》《阿霞》《毛狐》《翩翩》《罗刹海市》《公孙九娘》《狐谐》《辛十四娘》《双灯》《泥书生》《狐梦》《章阿瑞》《花姑子》《莲花公主》《绿衣女》《荷花三娘子》《云翠仙》《蕙芳》《萧七》《阿英》《甄后》《宦娘》《阿绣》《小翠》《霍女》《爱奴》《小梅》《张鸿渐》《云萝公主》《葛巾》《书痴》《香玉》《嘉平公子》《封三娘》《素秋》《房文淑》为代表,是“分离”故事。自《搜神记·天台二女》以来滥觞的“夙缘论”在这类故事中得到充分发挥,其叙事结构为“男女因有夙缘而相遇→结合→缘分已尽→女方离去(寻仙、成仙或不知所踪等)”。
不难看出,在第一类故事中,人与异类的恋爱得以顺利进行,而且很多时候女性占据主动,这些“白日梦”让蒲松龄在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代偿,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蒲氏渴望被欣赏、被认同,于是创造出了相当数量的此类故事,但他毕竟是儒家知识分子,讲求积极入世,执着于“此在”,故而在更多的篇章中,蒲松龄以正视人生苦难的勇气,打破了自己营造的温馨幻觉。①笔者曾撰文指出:“假性死亡(生命体征平稳的昏迷、植物状态)—冥府游历、阴司续命(昏迷濒死时的幻觉)—复生(从昏迷中醒来)”是唐前复生故事的核心叙事模式,“女鬼复生”正是对“植物状态”病人逐渐苏醒恢复过程的某种还原,因而从本质上来仍是征实的。即便在刻意虚构的《聊斋志异》中仍是如此,聂小倩“初来未尝饮食,半年渐啜稀酏”;王鼎将伍秋月从坟中挖出,“长呼秋月,夜辄拥尸而寝。日渐温暖,三日竟苏,七日能步”;杨于畏开连琐圹,见“女貌如生,摩之微温。蒙衣舁归置暖处,气咻咻然,细于属丝。渐进汤酡,半夜而苏”,连琐醒后常叹“二十余年如一梦”,皆是其例。说详拙作《从病理现象到文学经典:昏迷与先唐复生故事关系考论》,载《燕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2期。部分学者有意无意地淡化蒲松龄的整体倾向,通过大量列举“团圆”故事来渲染蒲氏如何乐意成人之美,然后将公孙九娘与莱阳生的爱情悲剧视为撕破“瞒与骗”面纱的特例,并以此抬高《公孙九娘》的艺术价值,这显然不符合实际。①我们认为:如果非要说以《公孙九娘》为代表的“分离”型故事有什么“意味”的话,那应该是它们折射出了蒲松龄的精神世界——一生失意的蒲氏通过故事表层男女无常的离合,揭示了人生际遇的可遇不可求和理想与现实的永恒背反。
三
《文心雕龙·时序》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素有“知人论世”的传统,明清之际复杂的政治文化生态更增加了研究者将其与《聊斋》进行“诗史互证”的冲动,这自然是可以的。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文学批评似乎还未以实证的方式具体地描述过文学存在于社会这个事实的详细面貌。这些都表明人们对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深入细微,而仅仅知道其大概罢了”[20]19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部分文学研究者过度依赖简化了的历史“常识”去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没能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回到现场”,“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21]279。本文用大量篇幅对《公孙九娘》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是想强调:在对《聊斋》进行“诗史互证”研究时必须对“预设”“前提”“共识”保持高度警惕,我们要认识到“历史学家本来就有一种职业病,总是把某一境况中的各种潜在性缩小到一个单一的未来”,一元论的线性演进和因果论的自圆其说从来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出于系统利用过去和未来,所有决策机构都被笼统综合到某一逻辑图案中去了,让它们互相对立起来”[22]33,通史的写作尤其如此。宏大叙事对明清鼎革、异族压迫、遗民心理、义军抗争、文字狱的叙述常使文学研究者忽视那些历史细节: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城中逐户用黄纸书大顺永昌牌位祀奉,人以黄纸书顺民二字插鬓边,然后出市行”[23]4571,而一个月后“城中閧传三桂领兵杀入,拥太子即位;人情汹汹,如沸如羹”[23]4574,“民”之善变若此,他们对明清鼎革到底抱有怎样的态度?山东的“义军”何以被视为“盗户”?怎样理解“义军”与胥吏的勾结和对清廷“招安”的暧昧态度?若“义军”是为反抗民族压迫,何以抄掠百姓更甚于“虏”“贼”以致“各乡村人民男妇,尽皆逃窜”[24]85并不得不向清地方政府求救?为什么包括蒲槃在内的山东乡绅都对清军的到来持欢迎、合作态度?康熙五十年(1711年)“《南山集》案”爆发前的文网究竟是怎样的?讨论《聊斋》中涉及明清之际政治生态的篇章显然无法回避上述问题。只有研究者亲自解决了它们而非不加分辨地采用成说,才“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哪一些属于幻想,哪一些是对现实的观察,而哪一些仅是作家愿望的表达”[15]104,最终得出的结论就不至流于比附。《聊斋》研究不能在学科交叉的“外部研究”中迷失自我,也不能架空历史作纯粹的审美批评,更不能把小说文本当做图解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民俗学、宗教学的材料。只有平衡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独断之论”与“考索之功”、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我们才可以在扎实的文本分析基础上作出无限接近于事实的客观评价。
[1]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2]蒲松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济南:齐鲁书社,2000.
[3]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陈子龙.陈子龙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夏琳.闽海纪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7]蒲松龄.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9]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王丕煦.莱阳县志(影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2]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3]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6]蓝翎.《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在哪里:《聊斋志异》札记之四[N].光明日报,1956-02-05.
(责任编辑 周亚红)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es of
Gongsun Jiuniang in Strange Tales from a Scholar’s Studio
LI Hao
(School of Art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23,China)
Pu Songling’s growth environment and life experience decide that he would not oppose the Qing Dynasty,and the Yuqi Rebellion is not a real revolt against alien races’oppression;therefore,the argument that Gongsun Jiuniang in Strange Tales from a Scholar’s Studio(Liaozhai Zhiyi)has political metaphor cannot be established.Some researchers speak highly of Gongsun Jiuniang’s thought connotation and artistic features by garble,manipulation and selective distortion,and their method of excessive dependence on“common sense”makes the articles full of abstract ideological discourse while the complex true“society”and“reality”have been hidden.The modes of thought with hindsight need to be abandoned so as to achiev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text,which has a kind of“understanding sympathy”for the author and infinite closeness to the real fact.
Pu Songling;Strange Tales from a Scholar’s Studio;Gongsun Jiuniang;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history;reflection
I206.2
:A
:1673-1972(2015)05-0034-05
2015-05-11
李浩(1989-),男,河北邢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