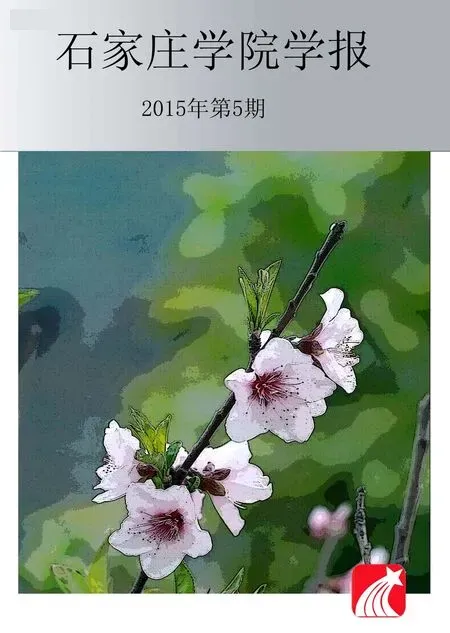“我思”向“我在”的范式转换
——以海德格尔为例
2015-04-11刘兴盛
刘兴盛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我思”向“我在”的范式转换
——以海德格尔为例
刘兴盛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奠定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后世众多哲学家如康德、胡塞尔在这种范式的影响下建构哲学体系。然而,这种范式在奠立伊始即埋下了主客对立、认识与实在难以统一的鸿沟,后世哲学家对这一鸿沟始终难以有效弥合。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显明了“存在”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在此基础上重新整合“思在”关系,实现了对“我思”范式困境的破解。这一思维方式的前提变革,推动了认识论哲学走向现当代更广阔的生存实践哲学。
“我思”;“我在”;认识论范式;转换;生存实践
近代哲学以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开启的认识论转向为标志,认识论一跃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对此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颇有见地地概括道:“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总之,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1]6主客、心物间的差异演化为对立,是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带来的必然后果,而消除这一对立就成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核心问题。由以往对本体的直接断言转向对人的认识基础及其认识能力的考察,是哲学本身的一个进步,标志着人类自我反思的一次重大跃迁。然而,以笛卡尔哲学所确立的纯粹意识之内在性的“我思”为绝对基础和出发点,不仅未能解决主客、心物对立的难题,而且使得“存在”本身进一步陷入被遮蔽、忽视与遗忘的境地。
一、“我思”范式及其困境
(一)“我思”范式的开启
笛卡尔认为,在认识的基础未经考察前就对认识的对象(如本体)进行断言是不合理的,因为认识的基础如果不够牢靠的话,建基于其上的理论大厦只能是假定的、独断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因此必须先找到认识的绝对基础后方能进行真理大厦的建构。为了确立一个绝对牢固的认识基础,笛卡尔接过了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怀疑方法,对一切存在的东西实行普遍的怀疑,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而是为了最终找到一个坚实的确定性,使得确凿的真理体系能够在这一确定性基础上确立”[2]29。他的普遍怀疑工作最终结出硕果:“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诞生了,即普遍怀疑的方法进行到最后唯一留下的是“我思”。
具体而言,笛卡尔认为怀疑者可以怀疑一切,但唯有一个内容不能被怀疑,这就是“我在怀疑”本身,如果怀疑“我在怀疑”,就会导致自相矛盾,因此普遍怀疑之后唯一留下的只能是“我在怀疑”即“我思”的纯粹意识活动,因而“我思”就成为了建基一切真理体系的绝对基点,“我,作为‘我思’从此以后就成了一切确定性和真理的基础”[3]96。“我思”作为基点一经确立,主体随之由外在权威转向自身,从而形成了贯穿近代哲学的主客、心物二元分立关系。对于这种情形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概括道:“‘我’成了出类拔萃的主体,成了那种只有与之有关,其余的物才得以规定自身的东西……物自身变成了‘客体’。”[4]95这里的“我”是作为“我思”存在的,“我思”之“我”成为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事物统统表现为客体的形式,而客体的形式只有通过“我思”才得以具有规定性。
笛卡尔说:“如果我把观念仅仅看成是我的思维的某些方式或方法,不想把它们牵涉到别的什么外界的东西上去,它们当然就不会使我有弄错的机会。”[3]40即是说,唯有纯粹意识之内在的“我思”活动形式才是确凿无疑的,外界之物的“污染”才是导致错误的根源。这表明了在笛卡尔那里,外在世界是使认识犯错的雷池,一旦越入会万劫不复,而为了不致犯错只能将认识锁闭于纯粹的自我之中,亦即“通过堡垒墙上的瞭望孔来注视夜空”[5]157。这已然显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也就是说在笛卡尔开启的认识论范式之初就包含着主客、心物对立难以弥合的因素。
(二)“我思”范式对康德哲学的影响
笛卡尔的彻底怀疑确立了思维形式的确定性,然而仅仅停留在思维形式的确定性上无法指涉认识对象,这样未免空洞无物,毕竟“思维无内容则空”。为了获得认识的内容并且保证自我的同一性,笛卡尔不得不重新请出上帝来作保证。也就是说,在笛卡尔那里,认识的对象和内容依靠上帝的赋予,此即著名的“天赋观念论”的缘起。然而很明显,这样做又回到了近代哲学所努力消解的“神圣形象”那里,康德(Immanuel Kant)对此实难满意,在他看来这样论证是“非常不像样的”。因此,对笛卡尔哲学的批判与重构就成为康德哲学的根本要务。正是在这一批判与重构的过程中,康德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从方法上来看,康德和笛卡尔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具有相通之处。这种方法,笛卡尔称之为“怀疑”,康德谓之曰“批判”。在笛卡尔那里,“怀疑”是将不确定的东西排除在外,取消其作为认识的基础和对象的地位;而康德“批判”的本义是划定界限,其用意也是要将不确定的东西搁置在外。建构批判哲学伊始,康德说道,“现代尤为批判之时代,一切事物皆须受批判……盖理性惟对于能经受自由及公开之检讨者,始能与以诚实之尊敬”[6]3,笛卡尔式怀疑方法对康德哲学的影响可见一斑。二者的不同在于,康德肯定外在之物的存在,但否认对其彻底认识的可能性,而笛卡尔对外在之物虽持怀疑态度,不过最终却承认其可以被认识。就此而言,笛卡尔在彻底怀疑的基础上产生了可知论的结果,而康德的不彻底怀疑却导致了不可知论的产生。
从内容上来看,康德要做的就是笛卡尔未竟的事业,即主体如何由纯粹的“我思”达至外在客体,获得真实、科学、合理的认识。在此意义上,“我思”主体仍然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基点,只不过康德加强了自我的主体性,将上帝彻底排除在认识领域外,因而其“我思”范式比之笛卡尔更为纯粹,在结构上更为合理,从而其论证也更为“像样”一些。如前所述,康德认为外在对象——“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因此以为认识与“物自体”统一是虚妄不实的,隐含在虚幻的统一之后的是主体与客体间真正的鸿沟,康德要重新建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来弥合这一鸿沟。他的办法是将认识对象与“自在之物”区分开来,认识的对象是“自在之物”向我们呈现的表象,这个表象可以被自我所认识,因为它统一于我们的“先天结构”而并非统一于“物自体”。换言之,在康德那里人的先天认知结构将“物自体”刺激人的感官所形成的感性材料“统觉”为认识对象,因此认识对象是认识主体自我构造的结果,这样就实现了认识与认识对象即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因此“康德现在放弃了‘知识就意味着揭露、发现或揭示本来就是那样的东西’这一思想方式,转而支持这样一个替代性的观点:知识就意味着构造、产生或制作我们所知道的东西”[7]61。然而不难发现,这种统一是将表象与“自在之物”剥离和以“物自体”的不可知为代价的,黑格尔对此评价道,以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之分为代价的统一并不能让人满意,康德所遗留的鸿沟并不比他弥合分裂作出的贡献更少。
(三)“我思”范式对胡塞尔哲学的影响
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更为坚定地秉持笛卡尔开创的“我思”范式行进,可谓典型的“我思”理路继承者。笛卡尔在胡塞尔哲学中的位置可以借用一句话来概括:“胡塞尔向其毫无保留地表示敬意并且在三十年里一再返回的唯一人物,就是笛卡尔。”[8]1胡塞尔早期并未自觉到自己的现象学与笛卡尔哲学的关系,但他的现象学观念出自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而布伦塔诺深受笛卡尔哲学的影响。后来胡塞尔意识到与笛卡尔哲学的关系,便不止一次地强调他的现象学是笛卡尔哲学的最终实现,代表着“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9]160,胡塞尔甚至明确地将自己的现象学称为“新笛卡尔主义”。晚期胡塞尔对自己的笛卡尔主义进行过反思,但他始终不曾彻底抛弃笛卡尔主义,即使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中依旧给予笛卡尔很高的评价。
从基本内容方面来看,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他那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终被归结为认识对象如何在意识之中如其所是地被给予。而对这种直接的、原初的、绝对的被给予性的追查和探求,无疑“中止判断”、悬搁之法最为人所熟知。事实上,这种将认识对象存在、主体存在、世界存在等信念预先悬置起来存而不论的方法,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颇为契合。并且胡塞尔悬搁的结果是使认识回归至绝对自明的开端,即胡塞尔称之为的“纯粹的自我意识”或“先验自我”,事实上这种“纯粹的自我意识”或“先验自我”与笛卡尔确立的“我思”也不无一致。不过,不同的是胡塞尔不是依靠上帝,而是借助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概念拓展了“我思”对认识对象的统摄和把握,即通过纯粹自我所具备的内在意识意向性将世界构造为“意向相关物”,从而以此完成认识与认识对象的统一,其实质是“自我对于世界具有本体论的优先地位,进而在本体论上把世界还原为‘内在’的领域,还原为主体的区域”[10]177。不难发现,胡塞尔的方法依旧依赖于笛卡尔和康德的二元区分,“意识”与“世界”的二元区分在他那里是始终存在的。对此海德格尔批评道,这种做法无疑将抽掉丰富世界自身的意义与内涵,使现实世界成为内在于意识的虚幻要素,即丰富对象世界不过是内在意识的“意向相关物”,一切不过是意识构造的结果的一种统一。就是说在胡塞尔这里,对象世界是被意识的意向性所派生出来的。
“胡塞尔一直保持是笛卡尔主义者……不断建设、重建哲学的基础以及居于其上的高楼大厦,为此耗尽了他整个的哲学生涯。”[10]181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他还是说任务并未完成,一切还应重来。他怀着遗憾离去让人感到心酸,心酸之余的反省是坚执于绝对纯粹的“我思”之路,要么割裂主客关系造成不可知,要么只能不断地放弃——重新开始以至于最终无法完成目标,更严重的问题是“存在”本身及其真实丰富的意义却于这一过程中至始至终被忽视、遮蔽和遗忘了。
二、“我思”向“我在”的范式转换
由笛卡尔开启的认识论哲学带来的主客、心物二元对立的困境,经康德、胡塞尔等人的追问与探究最终没有得到有力的解决。其根源在于这些认识论哲学坚执的是绝对的“我思”范式,对此海德格尔说道:“只要人们从Ego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11]因此只有消解“我思”的绝对基础地位,从不同于“我思”的前提出发,才能彻底克服这一困境。根据海德格尔的论述,这一前提就是能够解蔽被忽视和遗忘的“存在”的特殊存在者——“此在”,而这也就是“我在”。
(一)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
海德格尔从“此在”出发对“我思”范式的转换与改造的结晶是他的“此在”的生存论思想,“此在”之生存揭示了“存在”本身,超越了主客、心物的二元对立。而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论思想主要包括“此在”的基本属性、“此在”的生存结构以及“此在”的生存状态。
海德格尔指出,“此在”的基本性质之一是生存。“此在”以生存之属性“去存在”,在“此在”身上显现的不是静观出来的现成属性,而是存在的种种可能。“去存在”意味着“此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生成变化之中,这种生成变化意指多样性的可能。“此在”的另一重属性,海德格尔谓之曰“向来我属性”,亦即“此在”的“我性”,即每一个个体“此在”都是不同于其他存在者的特殊存在者。那么每一丰富不同的“我性”个体如何生存,即其存在的基本结构是什么?海德格尔指出,个体“此在”的生存机制是“在世界中在”,这里的第二个“在”乃是具有动词意义的“存在”之意,就是说“在世”是“此在”存在的基本结构。“此在”并不是处于一个静止不动的孤独世界的孤独主体,而是处在与其他存在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的状态之中,这便是“此在”与他者的“共同在世”。关键不在于其他存在者既包含“此在”又包含非“此在”,关键倒是在于“此在”与世界的关系并非处于一种决然对立、难以弥合的状态,海德格尔指出“此在”与全部在者、世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浑然一体的融合状态。此在不离开世界存在,而这种“在之中”即是海德格尔所意谓的“此在在世”的基本结构。就此而言,“此在在世”不仅是此在自身的意义也是世界的意义,二者彼此不能脱离。此外,诸“此在”、存在者之被揭示、被理解和获得意义在于与“此在”的相互“照面”,在“照面”中,“此在”与存在者相互显现自身。
最后,“此在”在世的生存状态。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与周遭存在者的“照面”、联系的总体构成了“此在”的生存状态,海德格尔谓之曰“烦”,这种“烦”有烦忙、烦神两重结构。烦忙表示“此在”与事物、用具的交道,非“此在”的存在者作为用具与“此在”“照面”,这种“照面”有用具当下的上手状态与现成在手的两种区分。上手是自如的使用,自如的使用并非作为认识的对象而存在,而这却是存在者最本己的状态,这种本己状态意味着对主客、心物二分的超越,意指一种自成一体性。而现成在手则意味着无法如意运用,正因为用具的不能如意运用才导致“此在”去静思之,即理论上的认识,它虽被认识却不是最本己的存在状态。而“此在”对用具的运用必然意味着与其他“此在”的交道,而与其他“此在”的交道就是“烦”的第二重结构:烦神。正是在“此在”运用用具的这种上手与否之间,与其他“此在”打交道的称心如意与否之间,“此在”展现了烦恼、焦虑、担心、关切等状态,一言以蔽之:“烦”。因此,作为“此在”在世生存状态的“烦”既揭示了非“此在”的事物,又揭示了所有“此在”,正是这二者构成了“存在”本身的显现。
(二)海德格尔对“思在”关系的重置
基于这种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我思”不过是“此在”生存的派生样式。换言之,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揭示了所谓纯粹理论认识的虚假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理论认识在实质上不过是一种派生,它是“此在在世”之派生。“此在在世”的重大表现之一乃在于“此在”的“烦”(操劳),此在与世间的其他存在者“最切近的交往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觉知的认识,而是操作着的、使用着的操劳——操劳有它自己的‘认识’”[12]67,即是说对世间万物的显现和觉解并非出于某种纯粹的理论认识,不消说它是一种“揭示”,一种全然不同的对真理的揭示。
海德格尔指出真理在其原初意义上乃是一种无蔽状态,亦即存在自身如其所是地显现自己、展开自己。在世的“此在”在这一过程中的绝对基底作用在于:用具于“此在”的“上手”,即“此在”与用具打交道中的根基地位。海德格尔以锤子为例说明:“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得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源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12]81即是说,“此在”“去存在”意味着的是对“存在”的揭示,“此在”的认识就是在操劳中展开“存在”。一旦“上手”的事物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缺失,“此在”就将它们看做现成的事物而加以凝视,才出现了所谓“此在”对世内之在的静观。即便如此,此静观也与所谓纯粹的理论认识相去甚远,传统认识论范式所讨论的对象只不过是最干瘪、最匮乏的形式,是遗忘了“此在在世”以及用具“上手”的不完整的“残断形式”。
事实上,当与“此在”的现实存在联系起来便可发现,认识论范式内的认识活动实质上是“此在”在世中存在的“派生样式”之一,然而在纯粹的理论认识眼中“世界现象被歪曲了……人们很早就主要是在理论(theorein)的意义上设想超越,即是说,不是在其原始根源的此在的本己存在中寻找它。”[13]然而真正的事实是“此在一向已经‘在外’,一向滞留于属于已被揭示的世界的、前来照面的存在者……此在的这种依寓于对象的‘在外存在’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内’”[12]73。
最后,海德格尔揭示了“此在”在世界中存在所具有的根本涵义:“‘在世界中存在’这个复合名词的造词法就表示它意指一个统一的现象。这一首要的存在实情必须作为整体来看。”[12]62也就是说,“此在”之在世是与“此在”的认识相统一的,必须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此在”是面向未来不断展开自身的存在,而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地显示自己,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不断相遇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此在”“在世界中存在”意味着的是“此在”与世界的相互融合渗透,“人并不是从他的孤独自我透过窗户去看外部世界,他本已经站在户外。他就在这世界之中,因为他既然生存着,他就整个地卷入其中了”[14]230。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主体与客体、认识与认识现象二元分立这回事,“此在”与世界总是相伴而生的,是内在统一、融合一体的。海德格尔以“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批判了歪曲“思在”关系以及对“存在“本身遮蔽、遗忘的做法,而在此的“此在”就是“我在”。总而言之,海德格尔彰显了“我在”所具有的本源的优先地位,完成了从“我思”到“我在”的范式转换。
三、“我思”向“我在”范式转换的意义
海德格尔以“我在”置换“我思”的基底之位,由此完成了思维范式的前提变革,这一颠倒和变革具有深刻的意义。对“此在”进行的生存论分析,使我们得见“存在”本身,而“存在”本身之浮出,意味着一条通往生存实践视域的哲学进路已然敞开。
(一)传统哲学中理论思维方式的优先性
实践哲学是与理论哲学相对的一个哲学致思路向。纵观西方哲学史,理论哲学于其中一直占据主导之地,这种理论高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可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那里得以管窥一斑。在古代哲学家包括柏拉图那里,理论与实践是截然二分的,实践主要被看做是为满足生存而从事的劳动生产,而理论主要指的是沉思,古代哲人认为只有沉思才能超越现存物象发现事物本真,因此他们认为沉思是优于实践的。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柏拉图区分了现象界和理念界两个世界,他的“洞穴之喻”所要表达的是:现象界是不真的,囿于这个世界的人们是缺乏智慧的囚徒,他们过着虚幻不实、庸庸碌碌的生活而不自知,因此日常实践活动是没有意义、不值得过的。只有运用理智进入到理念世界才是进入了意义世界,因而只有认识真理、揭示真理的理论活动才是高尚的和值得做的。因此也只有哲学家才配当王,因为只有哲学家运用对“理念”的认识来治理国家才能使国家达到和谐、完美的状态。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给予了实践以一定的地位,或多或少打开了实践哲学的出口,但是这一出口还未来得及完全敞开就又被他亲手关闭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沉思活动不仅仍被视做与实践哲学有着重大区别,而且依然处于实践哲学之上的位置。与其老师柏拉图类似,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只有理论沉思活动才能被称得上是最高贵和最幸福的活动,只有它才能把握到最高的善以及永恒的真理。及至近代,笛卡尔以其重建哲学根基的工作开辟了认识论转向,认识论转而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随之而来的是以“我思”为代表的自我意识的中心地位的确立,自我意识的主体地位被牢固地奠基,后世诸多哲学家如康德、胡塞尔等依循此种范式行进。对此,海德格尔有所概括,“人们往往专拿对世界的认识作为范本来代表‘在之中这种现象——这还不仅仅限于认识理论,因为人们把实践活动领会为‘不是理论的’和‘非理论的’活动’”[12]69。
这种思维方式源于西方哲学传统中一直以来的根深蒂固的看法:将实践活动等同于为生存奔波劳作而加以鄙视,视其为低等级的活动。大多数哲学家们认为从事为生存操劳的活动是低贱的和耻辱的,而理论活动才称得上是高贵的,人们重视理论活动,以从事理论活动为荣。因此实践活动作为“不是理论的和非理论的活动”就必然一直被轻视,这就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割裂开来了。在哲学认识中,实践活动也被降低到不及理论活动的次要地位,人们认为怎样能认识或者说科学正确地认识才是首要的和值得关心的事,诸多哲学家一直为了这个任务孜孜不倦地寻求答案,因此在传统哲学的视域中理论认识活动居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二)海德格尔对生存实践之根基性的确立
从哲学史上的“惯例”来看,主客、心物二元分立不可弥合的性质,以及存在之被遗忘的境地,是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与上述传统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然而从纯粹意识基础上的理论认识视角出发,必然把认识从实践中剥离出来而后以静观的方式去认识世界,这样就使得认识活动脱离了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受制于此种范式,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困境以及存在被遗忘的境地就一直无法得到圆满有效的克服和解决。
而海德格尔阐发的以“此在”在世为根基的生存论,确立了“此在”在世生存实践的首要性和根本性的地位,把纯粹的理论认识看做“此在”生存实践的一个“派生样式”。这突破了纯粹意识之内在性的局限,否定了理性认识所具有的优先于生存实践的地位,代之以确立“我在”的首要和优先地位。在海德格尔这里,最为根本的是“我在”这一现实载体,而不是撇除了“我在”的纯思之主体。换言之,没有“此在在世”就不会有在此的理论认识,即如果没有“我在”在世就不会有“我思”在此。表明了理论认识活动只不过是实践活动的一种,是“此在在世”的一种生存方式,它从属于在世的“此在”。这一将理论认识植根于“此在”的生存实践地基上的做法,使纯粹的“我思”得以有家可归,从而不再沦为漂浮于半空中的虚无缥缈之物。
海德格尔自觉到以“我思”为基础的认识论哲学原则的缺陷和弊端,从而代之以“我在”为基础的存在论哲学原则。这一转换超越和取代了传统哲学思维范式的立场,开启了全新的哲学视域。在这个视域中由“我思”为绝对始基的认识论范式造成的一系列无法克服的难题、困境和弊端,将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是海德格尔对现当代哲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三)现当代哲学的共识与呼应
海德格尔的这一工作,揭示了传统认识论哲学困境产生的真实根源,即以“我思”作为建立全部哲学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而使人们意识到,不对纯思内在性的框架和屏障进行冲破,是无法实现对主客、心物二元分裂的鸿沟进行合理、有效的沟通的。这为真正弥合这一鸿沟、解蔽“存在”本身的意义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将“我在”及其生存实践活动置于优先于“我思”的地位。
由此出发,我们得以发现由海德格尔开启的这一视域,越来越得到现当代诸多哲学派别和哲学家的共识和呼应,他们纷纷以生存实践为重要立场重新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对“我思”范式造成的困境和弊端进行深刻反省,从而推动哲学不断向前迈进。在众多哲学派别和哲学家的共识和呼应中较为典型的,如:胡塞尔本人晚期对自己笛卡尔主义的反省,强调要“回到生活世界”,认为科学认识要植根于生活世界之中;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以生活世界为中心的哲学”,提出哲学要立足人的现实生活,并且强调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生活实践关系;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对语言进行的哲学分析,指出作为“生活样式”的“语言游戏”优先于人对世界的认识关系,等等。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通过对“我在”的自觉以及对“我在”在世的生存论分析实现了对生活世界根基的揭示,从而克服了以“我思”为绝对始基的认识论哲学范式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和困境,凸显了“存在”本身的意义,最终推动认识论哲学走向现当代更广阔的生存实践哲学。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德]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隐退[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德]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5][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6][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7][美]汤姆·洛克摩尔.在康德的唤醒下——20世纪西方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MACDONALD P S.Descartes and Husserl:The Philosophical Project of Radical Beginnings[M].Albany: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
[9][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美]威尔顿.另类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视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1][法]F·费迪耶.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哲学译丛,2001,(3):52-59.
[1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
[13]张汝伦.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J].哲学动态,2005,(2):4-5.
[14][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张转)
The Paradigm Shifts of“I think”to“I am”:A Case Study of Heidegger
LIU Xing-s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Sociolog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
Descartes’viewpoint“I think therefore I am”laid the epistemological turn of modern philosophy.Under the influence of Descartes’paradigm,many great philosophers such as Kant and Husserl constructed the philosophy theory later.However,the paradigm of“I think”buried the gap which is difficult to unify the subject and object,understanding and real.Heidegger,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ival theory of“being-there”,demonstrated the paradigm shifts from“I think”to“I am”.This transformation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the“existence”,and promotes the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to the more extensive living practice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era.
“I think”;epistemological paradigm;“I am”;conversion;survival practice
B804;B516.54
:A
:1673-1972(2015)05-0028-06
2015-07-17
刘兴盛(1990-),男,辽宁鞍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