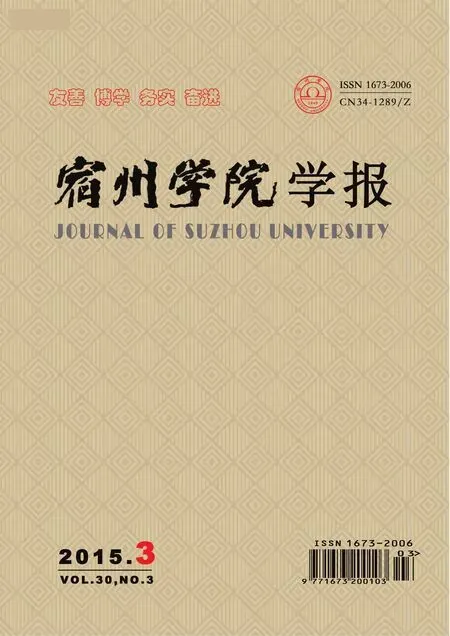论古代书法评论的人格化批评方式
2015-04-10张学峰
张学峰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1 问题的提出
古代书法评论,从观念到表述、从风格描述到风格判断、从语言技巧到批评技巧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模糊特征和拟人化特征。这种模糊性和拟人化,从语言学层面来看,主要与古代文学传统或诗学传统密切相关;从思想史层面来看,主要与儒家、道家思想相关。古代书法评论的人格化批评方式,是这种模糊性和拟人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本质上说,“人格化”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知方式,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书法评论的人格化批评方式,主要指拟人化的思维方法和语文手法。它给作品赋予人格特征,以此区分和判断艺术品质。从思维方法上来看,这种拟人化方法带有鲜明的童年特征,因为儿童对世界的感知常常表现出拟人化的倾向。现代心理学揭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儿童常常会把周围无生命的东西看作有生命、有感情的;并常常尝试和它们对话交流。这种儿童思维方法的一个逻辑前提是“人最了解他自身”,也间接地表明人的身体或许是认识对象的起点,确切地说,身体可以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参照物。因此,人格化的批评方式,可以被看作以自身为认识参照物对书法进行的一种分析和理论思考。
当然,书法的人格化批评方式绝不能因此被看成儿童化,实际上,它是古代文史传统的一种历史产物,寓含了丰富的文化伦理。或许,正因为书法寓含丰富的文化伦理,古代文人儒士才没有把它仅仅视为一种书写行为。
古代书法评论的人格化可以归纳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品评等级。可以追溯到曹魏时的“九品中正制”和魏晋人物品藻风气,即以人物的等级、身份特征和身份差别,来评论书法。其二,是用人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来比拟书法的形态特征。前者偏向于等级、类别、气质的划分;后者偏向于具体形态、行为的描述。在具体的书法评论中,两种形式时常合用。一般来说,根据具体形态或行为的描述,揣度作品的造型特点;根据类别和等级,揣度作品的美学风格和成就高低。在这种人格化的描述中,人物的身份、等级起决定性作用,它决定了被描述者艺术品位的高低。当然也有一些只含人物身份,不含等级意义。
下面依据不同历史时期,举例说明。
2 南北朝时期
袁昂(461-540年)《古今书评》曰:“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骨。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止沓拖,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1]“谢家”是两晋望族,“谢家子弟”文化学识、道德修养、政治名望高出时俗同辈,因此,即使外在形象存在“不端正”,也无妨风骨显现,甚至这种“不端正”,本身还体现了风骨。“举止沓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端正”,但是“河洛间少年”如此,就不具有此种意味。所以袁昂认为,王子敬(献之)书法中出现的“拖沓”和“不端正”,不是一种高级美学品味,而王羲之书法中出现的“不端正”,却是风骨和内在精神气质的显现。显然,袁昂认为“谢家子弟”与“河洛间少年”有雅俗之异,正偏之别。“婢为夫人”,因为缺乏一种身份自信,所以她只能是“举止羞涩,终不似真”,貌似正室之形,难掩卑微之质。在袁昂的批评中,可以根据人物身份等级,断定各人的书法作品孰高孰低。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古今书人优劣评》曰:“张芝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止沓拖而不可耐……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有一种风流气骨……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状虽未长成,而骨体甚峭、快……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尚风轨,殊不卑寒。袁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退缩。张融书如辩士对扬,独语不困,行必会理。”[1]81-83与袁昂雷同之处,不必重述。这段文本比拟人物选择多样,有儒士、道士、仙人,有儿童、少年、成人,有男人和女人,有皇帝、贵族、平民,这是一个社会人物的群像图。在这些人物作态里面,有些完全是一种文化想象,在现实中是看不到的,如“凭虚欲仙”“仙人啸树”。“汉武爱道”则是一种带有历史典故意味的风格上的想象。后文将要提到的张怀“若吴人之战”,李煜“犹嫖姚十八从军”,明人“赵子昂书,如程不识将兵”,包世臣“玉局如丙吉问牛”“山谷如梁武写经”,康有为“《张猛龙》如周公制礼”等,都属此种类型。古代评论家使用这类语言,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确切地比拟作品风格或类型,而是因为当时书法术语概念还不够缜密,且与文学评论界域不清,一些诗词评论之类的诗话、词话皆用此类拟人、拟物化的比拟性语言。从技术性层面来说,因为知识系统的层级不够细密,他们没有能力区分专业表述语汇,而且对这种区分也没有细致辨别的兴趣。更为有趣的是,在古人眼中,文史不分反而彰显某种博学和融和汇通能力。
3 唐、宋时期
唐代张怀 ,评论隋僧智果曰:“而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轻进易退,勇而非猛,虚张夸耀,毋乃小人儒乎。”[1]201张怀 借用一种历史典故——“吴人之战”来论述智果。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也可归结为一种拟人化手法。历史真实发生,典故是历史的一种演绎与阐释。从文化发生学角度论,神话传说偏于虚拟,历史典故偏于实际。但是,在古代书论中,历史和传说经常混为一谈,如黄帝造物、仓颉四目造字。
“小人儒”与“君子儒”相对,带有极强的贬义,一般泛指品德低下、见识肤浅的人。“小人儒”行为举止不能表现出高级趣味。显然,张怀 认为智果书法水平不高。但是“小人儒”“君子儒”行为举止本身,只是某种内在素质的外露。对这种行为举止进行心理学和文化学释读,是古人采用模糊、中庸的语言表达观点的一种技巧。这种语言表达技巧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也是其伦理观念、等级观念的体现。
李煜(937-978年)《书述》曰:“壮岁书亦壮,犹嫖姚十八从军,初拥千骑,凭陵沙漠,而目无劲敌……老来书亦老,如诸葛亮董戎,朱睿接兵,举板舆自随,以白羽麾军,不见其风骨,而毫素相适,笔无全锋。”[1]299“嫖姚”当是霍去病的代称。根据李煜的描述,壮岁所书是彪勇猛进、意气张扬,老年所书是从容而自信。在李煜的言词中,可以看到不同年龄阶段人的书法特点。
苏轼(1037-1101年)曰:“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1]314“君子”“小人”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两种对立范畴。“君子”是可视为世人楷模的典范。古代书论经常借此概念判断书法水平高低。根据苏轼的观点,“君子”和“小人”不会因为相貌好丑、能言善辩、书法工拙而变得难以分辨或混乱不堪。苏轼好像是在强调“君子”和“小人”的本质区别。他并没有认为“君子”书法即“工”,“小人”书法即“拙”。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或许提示了苏轼的某种通达。
朱长文(1039-1098年)《续书断》曰:“邕书如宽大长者,逶迤自肆,而终归于法度,能品之优者也。”[1]341从“宽大长者”四字,就知道朱长文对李邕书法是褒扬的。因为“宽大长者”在儒家看来,一般都是值得效法的。
黄庭坚(1045-1105年)论书曰:“王著如小僧缚律,李建中如讲僧参禅,杨凝式如散僧入圣。”[2]黄庭坚这段著名书论被明清书家奉为珠玑之言。他借用佛僧修行悟法的等级之别,比拟王著、李建中、杨凝式三人书法在境界上的差别。“小僧缚律”指佛僧被律法束缚,不能融通或自我体认;“讲僧参禅”指佛僧讲经宣法,能够有所禅悟,有所体认;“散僧入圣”指佛僧不为形式所拘,散漫洒落超凡入圣,直登圣域。这种拟人化手法,表明了佛学对宋代文人在方法论上的实际影响,超越了儒、道的规约,扩大了意义的来源和作用,也没有人物身份的伦理学暗喻。
米芾(1051-1108年)评论李邕曰:“李邕如乍富小民,举动强屈,礼节生疏。”[3]米芾的这种评论很像在描述一个人。“乍富小民”贬义味较重,米芾此处的用语透露出文人儒士在身份意识上的自觉。就书法来说,“举动强屈,礼节生疏”,实在难以和艺术造型特征衔接。但是,可以推测,“强屈”与“生疏”表示了某种不合规范。因此,米芾批评李邕书法存在某种不合规范(米芾最心仪的是晋人书法,晋人书法美学应该是他的美学标准。李邕作为唐代书家,和晋人的书法美学出入较大),借用“小民”来比喻书法之做作、俗气,不懂章法之弊。
米芾评论苏舜钦曰:“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3]124“五陵”指西汉咸阳一带的帝王陵墓群,汉朝政府迁徙了六国后裔、郡国豪杰、列侯、富人、乱民等各式人物聚居于此,因而形成了任侠、豪放、纨绔、轻薄的社会风气和地域文化特征。经过唐代诗人的文学想象和转述,“五陵少年”带有一种游侠之类的浪漫色彩。它是历史典故和文学典故的结合。“访云寻雨,骏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表达了“五陵少年”逍遥、放达、轻狂的行为特征。由此,“五陵少年”变成了一种美学意象,这种意象亦真亦幻。
4 元、明、清时期
元人论书:“鲜于困学,如云间公子,玉骨横秋,富贵风流,仍复度世。胡绍开,如拙工铸鼎,模范未精,沉重(亻瓜合起来)哨,似奇实陋。姚先生,如上帝阴兵,举世不识,恍忽变现,要以气胜。卢疏斋,如丛祠野屋,绘画风雷,虽复骇人,却非尘俗。张大经,如油翁献技,钱孔不濡,运杓自然,不过熟耳。苟正甫,如近郊田叟,老不作业,意度贞淳,恨乏京样。王参政,如勤妇作缣,致力机轴,虽愧罗绮,亦复迟坏。周景远,如头陀学佛,颇见小乘,苦行继修,或可证果。”[2]229这里出现的人物身份是“公子”“拙工”“上帝”“油翁”“田叟”“勤妇”“头陀”。除了“上帝”,其他人物可以在现实中看到。“油翁”是一个文学典故,从白居易作品《卖油翁》而来,奇怪的是,此处没有察觉身份、等级的尊卑暗示。作者似乎专注于以上人物的工作方法、工作业绩、工作心理,不论“公子”还是“拙工”,“田叟”还是“勤妇”,他们似乎没有按照儒家“士农工商”“君子小人”或“男尊女卑”“君臣父子”等级标准被描述与评论。因此,自然令人想到:它是否和蒙元政治环境儒士文人的特殊处境有关?或者,此评论者非汉族人;再者,此人儒家道统意识淡薄。
明人论书:“赵子昂书,如程不识将兵,号令严明,不使毫末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鲜于伯机,如渔阳健儿,姿体充伟,而少韵度。”[2]414这里的“如程不识将兵”“如渔阳健儿”,属于典故一类。前文中“嫖姚十八从军”“子阳据蜀”,后面提到的“如李光弼代郭子仪将”“如唐明皇随叶法善游”等,都是如此。古代书法评论爱用历史典故,表明古代史学观念对一般文人书家存在一种广泛影响。文学典故在古代书论中也大量出现。文学典故和历史典故的使用,能显示作者的博学和通识。从文化史角度论,它显示了古代文史知识发展的连续性、延绵性,显示了传统的坚凝。这归功于儒学的作用,它也是儒家文化特征之一。
董其昌(1555-1636年)的《画禅室随笔》曰:“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也。”[4]董其昌认为书法临帖如同乍一见到陌生人,不要被外在相貌表象所蒙蔽,应注意观察其言谈举止和精神气质。这种以人际交流方法来比喻人“书”交流,容易被读者理解。“耳目手足头面”也很容易把它和字的点画结构作比照。这种以人的身体来比划书法,和苏轼的“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之论,荆浩的“筋、肉、骨、气”之用笔论,方法如一。由此可知这种评论方式已经形成一种传统。
冯班(1602-1671年)的《钝吟书要》曰:“鲁公书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1]554众所周知,“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句出《论语》,是君子三种变相的两种,子夏以之描写孔子的人格特征。冯班以君子端庄严肃而又蔼然温和这种双重美德,比拟颜真卿书法的美学特征。颜真卿因为忠烈拒降,被后世奉为儒家楷模,他是儒家标榜的“正人君子”。冯氏所论和下文刘熙载“书如其人”论同出一辙。假如借用清代杨宾之说,即颜书有“台阁气”。
清代杨宾认为:“帝王书有英伟气,大臣书有台阁气,僧道书有方外气,山林书有寒俭气,闺秀书有脂粉气。”[2]584傅山论书曰:“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4]以人的品格和个性独立来要求书法家,在傅山身上表现得格外显眼。傅山对子孙的训示,对赵孟 的批评,虽然也是其个性所致。但是,由此也能窥探到儒家价值观念在傅山身上发挥的真正效用。
刘熙载(1813-1881年)《书概》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1]715杨宾是18世纪前期书论家,他根据人物的身份,归纳书法的美学特征。杨宾的归纳透露出明显的政治威权意识。也就是说,政治身份的尊卑,决定了书法美学品质的高低。这种观点是“书如其人”之论的一种简单推论。假如帝王是个半文盲(如朱元璋)或武将(如赵匡胤),对书法基本不懂,那么他的书法还有“英伟气”?可笑的是,康有为却认为朱元璋和弘历(也可能是伪作)胸次绝伦,书法技艺高超。由此可见,在文人书家的意识里,盲从政治威权(或者说正统)已经不是偶发现象。他们在评论书法时,时常泥陷其中。由此,也能管窥“书如其人”论的历史真实性。
刘熙载这种“书如其人”理念,为儒士阶层普遍接受。在刘熙载眼中,书法是人格的一种外在化表现。相对来说,刘熙载此论比杨宾要切实一些。因为“贤哲”“骏雄”“畸士”“才子”,不是纯粹以社会或政治地位来区分,而是以人物性格与德行来区分,这种区分具有较多的文化性。换言之,它还没有越出文化的边界,没有让政统完全支配书法学统。刘熙载下面这段书论直接表现了书法的精英主义特色和儒士本位主义。
“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归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1]713为什么其他人物表露出的气质不是书法艺术?其实,原因很简单,其他人物缺少道德伦理性和文化修为,如“妇”“兵”“俳”“门客”。易言之,只有“士”,才是价值的典范,才具有真正的艺术精神。
包世臣(1775-1855年)的《艺舟双楫》中评论书法20家:“……玉局如丙吉问牛,能持大体;端明如子阳据蜀,徒饰銮舆;山谷如梁武写经,心仪利益;海岳如张汤执法,比用重轻;子昂如挟瑟燕姬,矜宠善狎;伯几如负暄野老,嘈杂不辞;京兆如戎人砑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6]丙吉、子阳、梁武、张汤为历史人物一类,燕姬、野老、戎人、龙女可列为另一类。这两种类型和其描述对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与其说它们是书学评论,不如说是一种文学修辞。下面这段文字更是如此,康有为(1858-1927年)的《广艺舟双楫》曰:“《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晖福寺》宽博若贤达之德。《爨宝子》端朴若古佛之容……《杨大眼》若少年偏将,气雄力健。《道略造像》若束身老儒,节疏行清。《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李仲璇》如乌衣子弟,神采超俊。《广川王造像》如白门伎乐,装束美丽……《司马升》如三日新妇,虽体态媚丽,而容止羞涩……《李超志》如李光弼代郭子仪将,壁垒一新。《六十人造像》如唐明皇随叶法善游,《霓裳》入听……《定国寺》如禄山肥重,行步蹒跚……《太祖文皇帝神道》若大廷褒衣,端拱而议……《慈香》如公孙舞剑,浏亮浑脱。《杨 》如苏蕙织锦,绵密回环……《舍利塔》如妙年得第,翩翩开朗。”[1]832-833
康有为对46个碑进行了集中评论。如果把评论对象进行调换,不会发觉任何不妥。对古代书论存在的“遣词求工”这种现象,宋人米芾早有察觉:“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益远,无益学者。”[1]360米芾指出的这种“比况奇巧”“遣词求工”现象,到19世纪末康有为这里仍然存在。而且,米芾自己有时也会如此,如前面摘引的米芾书论。由此可见,这是古代文人书家的一种集体倾向,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家族性相似”。如果询问原因何在,应该考察书法知识的生成系统和传播空间,考察书论家的精神传统。
把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刘熙载《书概》的批评手法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发现,三者的文学化语言习惯有细微的差别,儒学道统的渗透力深浅不一。康有为的骈文语言批评手法追溯源头,要远到公元3世纪。后来,萧衍、庾肩吾论书,语句对仗排比,都吻合这种文赋语言传统。在唐人书论中(如孙过庭),还能够看到不少文赋式语言,北宋之后,这种前期传统渐渐消褪,新传统形成。包世臣和刘熙载属于宋后之新传统;相对而言,康有为属于前期传统。康有为熟练地使用历史或文学典故,显示出康有为独特的修辞能力。这种修辞能力不注重理论分析和解释,增加了意义的模糊性。必须说明,北宋后的新传统,才是古代书法评论进入成年期;前期文赋传统则是幼年期,有过多的早期文学语言痕迹。而康有为的这种“返古”现象,也许出自他惟古是从的性格渊源。
5 人格化批评传统的成因、意义
上述分析业已表明,人格化的批评方式在古代书论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只要愿意检阅,这种人格化的批评方式俯拾皆是。
在古代,文人儒士的知识习得和知识构成基本一致,他们接受的都是四书五经教育,或者说,都是一种类型相近的文史教育。因此,他们的经史意识或文史意识远远胜出其他意识;文学语言和文学思维超级发达,形象思维能力远远胜出抽象思维能力,感性认知超出理性认知。因而,林语堂先生说:“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充满着‘普通的感性’。缺少抽象的辞语,像妇人的口吻。中国人的思考方法是综合的,具体的而且惯用俗语的……”[7]
因此,在古代书法评论中,可以看到经史知识的肆意蔓延,看到文学语言的轻松使用,看到文史典故的随机挪用,看到感性多抽象少。同时,人们往往也被这种经史知识和文学修辞折服,以致于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批判。
余英时先生说:“在学术上,传统的儒学是博雅与通识兼顾而尤其重视会通。”[8]进而言之,古代书法的人格化批评传统,可谓是这种会通的表现形式之一。质言之,书法的人格化批评方式,表现出文人儒士“博雅与通识”的一面,也表明古代书法评论是儒家文化体制的一种历史产物。
细致一点论,儒学道统为古代书论人格化的批评方式提供了价值判断的动力和标准,也可以说,儒家文化培育出的道德感和文化伦理,使人们在认知方法上偏爱人格化。文学化的语言习惯,培育了形象思维优先的语言选择习惯,这种习惯增加了古代书论的模糊性和拟人化。儒学道统和文学化的语言习惯,又是一种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中,它们扩大并坚守了自己的语意场。
在古代,儒学和文学是一种主干与枝干的关系。可以认为,儒学道统是以上问题的根本所在。李幼蒸先生说:“儒家的文章学或思想表达学,可以被称为泛形式主义的。”[9]古代书法评论,大概能够算作“儒家的文章学或思想表达学”。而这种文章学在思想层面上没有多少实质差别,所以完全可以称为“泛形式主义”,因而导致“关心思想性和思想内容的僵化同时存在”[9]552。换言之,古代书论的这种人格化批评方式流行与泛化,根本原因是思想的僵化和内容的高度趋同。但是,它也是文人儒士“关心思想性”的一种尝试,因为他们一直在试图呈现或激活过去的历史和人文。在无料可选、无方可用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方法和出路。
苛刻一点说,古代书论的人格化批评方式是儒教社会单调性与封闭性在文化上的一种显现,是古代文人书论家逻辑水平和抽象思维能力相对欠缺的一种显现。然而,应辨析这种书法批评传统在文化学上可能存在的人文意义。因为就文化的社会性和族群特征来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相对稳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因此,它有值得尊重的一面,或者说,存在某种合理性。易言之,中国书法的人格化批评方式作为一种古代艺术批评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是儒家文化主动选择的结果。人格化的艺术批评方式,把“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作为一种度量方法,甚至一种参照系,使得“人”占据意义的中心,掌握意义的比拟与推导,使得“人”承载着多重意义。
在儒家文化圈,人们熟悉这种思维方式,因此言者与听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基本畅通。这种艺术批评方法虽然存在前文所论的致命弱点,倘若从积极方面来论,它或许又是最人性化的,因为它只关注人,关注人之行为和历史,关注人之伦理。当然,也不能夸大这种人性的力量。因为人性如同沙漠中的沙丘,颗粒不变,形态万变;因为人性有其历史性,而且执之太久。
[1]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3-75
[2]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65
[3]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90
[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M].屠友祥,校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54
[5]潘运告.清前期书论[M].桂第子,译注.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84
[6]祝嘉.《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疏证》[M].成都:巴蜀书社,1989:42
[7]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8
[8]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58
[9]李幼蒸.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