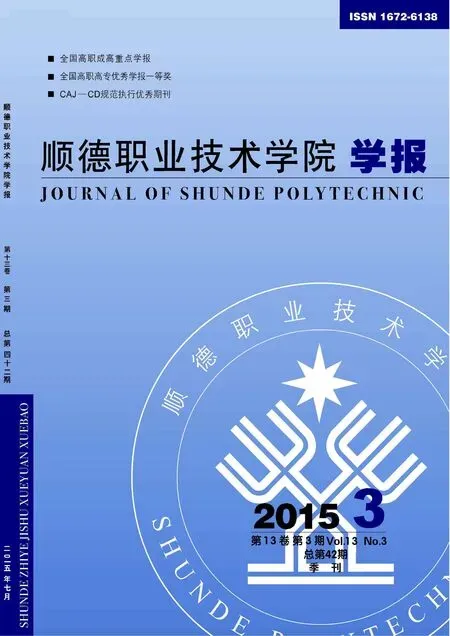自我存在的矛盾
——高觉新、祁瑞宣人物比较分析
2015-04-10雷欢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雷欢(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文·史·哲研究
自我存在的矛盾
——高觉新、祁瑞宣人物比较分析
雷欢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在《家》与《四世同堂》中,自我存在的意识在高觉新和祁瑞宣二人身上是不可忽视的。出于长子必须要担负的责任,高觉新和祁瑞宣选择了为家庭自我牺牲。这想要追求自我与自由的存在,与他们身为家中长子的社会身份相矛盾,存在与责任的矛盾,便是他们痛苦的根源。从二人灵与肉、情与理和新与旧的矛盾入手,着重分析他们自我存在的矛盾和痛苦。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家庭情况,二人自我存在的矛盾虽然有着不同,但又是极为相似的。
高觉新;祁瑞宣;自我存在;矛盾
《家》的故事发生在五四时期的内陆四川,《四世同堂》则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攻陷的文化名城北京。虽然一个是贵族的大家族,一个是四世同堂的小家庭,但是两者都陷入了社会思想和社会矛盾的巨变之中。高觉新和祁瑞宣身处的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的追求越来越深入人心,但传统的长子身份却束缚着他们,他们必须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来。家庭的责任与个人的追求是矛盾的,为了家人生活的稳定,作为长子的高觉新和祁瑞宣必然会做出他们的选择和牺牲,而这一牺牲,便注定了他们自我存在的痛苦。
1 新与旧背后自我存在的困境
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化中人的觉醒、自我的独立意识开始影响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而抗日战争时期,饱受苦痛的人们也开始觉醒与反抗。对个体而言,自己所负的最根本的责任,便是维护自己基本的权利。故而在高觉新和祁瑞宣看来,追求自我便是他们心心念念、难以抗拒的权利。但“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中的某一点上,都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都一定要在矛盾的一端与另一端之间产生某些摇摆性,只是这种摇摆的幅度因人而异”[1]44。
高觉新和祁瑞宣所处的时代都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相矛盾的时代,都是自我意识繁盛的时代,同时也是传统旧文化留存的时代。新文化对个人解放、自我独立的呼唤,唤醒了高觉新的心灵。《新青年》等杂志是新文化的集中地,它们无不介绍着新的导向。而祁瑞宣也是如此,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对新文化的理解、对自我意识的看法是更为鲜明和深刻的。
高觉新和祁瑞宣深刻地认识了到新文化的作用,他们看到了自己身上“新”的一面——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如高觉慧和高觉民,他们是在新文化的影响下走上反叛的道路的,但是引导他们这一走向的却是他们的大哥高觉新。在《家》第六章中,“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的被忘却的青春”,“这些刊物里面的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样地点燃了他们弟兄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便是充分的证据。五四新文化使高觉新恢复了青春,也让他对新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同。身处这一思想文化激荡的时期,高觉新的这一特点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哪怕他遵守的不过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刘半农的“作揖主义”,这都是高觉新自我存在意识的鲜明体现。
而也正是遵循了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刘半农的“作揖主义”,高觉新自我存在中新与旧的矛盾才得以进一步体现。高觉新追求的并不是真正的新文化,也不是追求个人真正的解放,他的“作揖主义”让他妥协于封建制度,从思想中寻找维护旧制度的依据。他引导着高觉慧与高觉民接触了新文化,但之后,却反过来压抑他的兄弟继续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不论是去劝高觉慧不要参加学生运动,还是写信叫逃婚的高觉民回家,这都是他向旧的家庭制度即旧文化的妥协。
祁瑞宣也是同样,他与高觉新不同的是,他不仅受过新式教育,而且还是高等的新式教育。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有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造。”祁瑞宣是在大学毕业后才从事教师工作的,且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英国大使馆还有一位外国友人,故而祁瑞宣对独立自由的人格和自我体会得更加深刻。但和高觉新一样,祁瑞宣妥协于旧文化,妥协于他“小家”的责任。
祁瑞宣深知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但他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心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祁瑞宣也深知国难当头,应当率先救国,应当逃出北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中去,但是长子的责任,让他不得不忍受着良心的鞭笞,在沦陷的北平继续教书。祁瑞宣并没有采取“不抵抗主义”,他的思想是新思想,他的理念也是新的理念,但是他的行为却和高觉新一样,是在传统旧文化下的旧作为。
萨特认为:“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2]8高觉新和祁瑞宣对自我存在的认识一开始便是矛盾的。他们都受过新文化的影响,他们都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学会了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审视他人、审视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行为,并意识到了自我存在的重要性。但在同时,他们却又无时无刻不在遵从着旧文化。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内部矛盾,为之苦闷烦恼的同时,却是打心底认同这种矛盾的存在。正是因为知道这种矛盾的存在,他们才越发的痛苦,而也正因为痛苦,他们越发地认识到这种矛盾。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死循环,让二者身处新与旧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2]6故而,虽然新文化在高觉新与祁瑞宣身上扎了根,但是旧文化的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在二人的心中,他们更应当是家中的长子,是一个担负起家庭责任的人,而非一个能不顾家庭断然出走的人。“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2]5社会的巨变,往往意味着思想文化的激荡或是家庭生活矛盾和困难的加剧。因此,长子的考虑必须是全面的,是涵盖整个家庭情况的,而不能再从个人的理想与信念去考虑,长子的所作所为只能去符合大家的普遍要求。故而,当新与旧的矛盾升级到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矛盾时,或者家与国之间的矛盾时,高觉新和祁瑞宣最后都做出了让他们痛苦不已的选择——放弃自我而对所有人负责。
2 灵与肉背后自我存在的迷茫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9因而,作为《家》和《四世同堂》中矛盾性格最为突出的高觉新和祁瑞宣,他们的存在便是当时那个复杂社会的投影,是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总和。高觉新处于五四新文化崛起,封建旧势力顽固残存的时期,祁瑞宣则身处国难当头的时代。在这两个阶段,新与旧、保守与突破、自我与家族等,激烈的冲突不断发生。这种种的矛盾,便构成了高觉新与祁瑞宣徘徊不前、想要顾及所有人而力不足、矛盾不已的现状。
人“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1]39高觉新性格中的善是十分明显的,不论是对兄弟的支持,对妻儿的爱,还是尽量讨好高家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这些都是他灵魂与精神最本真的体现。为觉慧与淑华的出走提供经济基础,关爱自己的妻子、体贴呵护,关心教育自己的孩子,调节晚辈与长辈之间的矛盾,高觉新的善良,尽管显得懦弱,但是不能否定的是,他极尽所能地调和着一个大家族的矛盾,为着一个家族的生存与发展做着自己的努力。可以说,高觉新的自我存在意识注定了他只会是一个“博爱”之人。但同时,也正因为他过于善良的懦弱,这种“善”,便变成了“恶”。过于懦弱的他,“先是放弃了到大学深造,到德国留学的‘美丽的幻想’,放弃了‘那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钱家表妹’,而在父亲去世以后的大家庭中,又放弃了与大家族成员的争斗。”[3]高觉新善良到不敢反抗“恶”,他长房长孙的责任与义务让他害怕伤了他的那些长辈,但一旦选择成全他那些长辈的愿望,那他就不得不做了旧制度的帮凶,而此种行为反过来却最终夺去了他的爱人、妻子和孩子的生命,也导致了他难以消除的痛苦。觉新的人道主义让他对所有人和善,但是高老太爷等顽固的封建分子并不会理解他的人道主义,反而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高觉新在精神上难以认同家长的作为,在行为上却不得不迁就,这极为矛盾的自我存在便导致了他的苦难。
祁瑞宣同样是一个善良、温和,对家人关怀备至的人。他的善极为明显,为了不使亲人伤心,他娶了和他根本没有感情,更难以理解他的妻子韵梅;为了祖父四世同堂的美好梦想,他一次次忍受来自二弟的非难;为了三弟祁瑞全的理想,哪怕会引来家人的责难,他在深思熟虑后便毅然决然地帮助他逃出北平。在北平沦陷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祁瑞宣不得不作为一个亡国奴继续去工作;而在祁瑞全生活困窘之后,他也照旧收留了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弟弟。但这一次次善良的举措,不仅避免不了父亲的自杀,避免不了二弟的死亡,避免不了自己的女儿被活活饿死,也避免不了他在抉择之中痛苦不已。
“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2]2。“由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选择,所以要承担责任,不但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要承担责任。”[2]1身为家族的长子,高觉新与祁瑞宣是负有责任的,特别是对祁瑞宣而言,他的存在对祁家至关重要。高觉新面对家庭与自我的矛盾,祁瑞宣则面对家与国的矛盾,这去与留的矛盾,无不是在灵与肉的矛盾之中。但“自由只有通过它的自由选择才能阐释它存在的意义。”[4]143“一个人有自由意志,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当他愿意这样生活时,他是自由的。第二,在他可以选择这一生的行走方式和道路时,他是自由的。第三,他的自由表现在:他作为那样一个人,怀着这么一种意愿;在任何情况下都沿着这一人生道路走下去,并以此方式恢复自我。”[4]142高觉新和祁瑞宣都选择了为了家庭承担责任,但这一选择并不能让他们感受到自由。只因责任使得二人选择了家庭,这已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必须和必然的选择了。若是真正的自由选择,在排除长子身份与家庭责任之时,盘横在高觉新和祁瑞宣心头的,必然是他们都已经错过的“独立自由的人格与不可剥夺的个性权利”[5]。高觉新与祁瑞宣的自我存在并没有自由意志,这也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们并不愿意这样生活。高觉新对高家是失望的,但他不得不为它的生存苦苦支撑;祁瑞宣则是希望能逃出北平投入反战战争,而不是做一个北平城内奴颜婢膝的亡国奴。第二,他们所希望的那种个人自主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不能去选择的。第三,他们作为家中的长子,只是出于责任和对家人的情感才一直为之付出,他们是在强迫的情况下沿着这条人生道路走下去的,其结果便是在这种矛盾的形式中迷失了自我。
“善”与“柔”的性格决定了高觉新和祁瑞宣不能像他们的兄弟那样激烈地反抗,但他们亦有他们的反抗方式——支持弟妹出走。在《家》中,高觉新说道:“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高觉新的主导性格是“柔”,但他的“刚”并不是不存在的,他将他反抗的希望寄托在了觉慧的身上,通过支持觉慧和淑华的出走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以此得到到一定的安慰。但我们必须看到,此时的高觉新依然是选择了他的人道主义,一方面是支持自己的兄弟姐妹追寻未来,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呆在高家,为剩下的人的生活出谋划策。祁瑞宣也是同样,明知会引来家人的非议,他还是毅然决然的送走了祁瑞全,而自己,则是抛弃了那个为国家捐躯的理念,一直困顿地呆在北平城中。支持弟妹出走是高觉新和祁瑞宣沉默中的一次爆发,是自我存在最为真挚的一次体现,是他们所认定的存在与理念的表达。但可惜的是虽然意义深刻,却改变不了他们灵与肉的矛盾,他们的灵魂依旧痛苦着,在兄弟出走后仍在行动上难有作为而痛苦着。高觉新与祁瑞宣希望通过别人来完成属于自己对家庭或对现状的反抗,而自己却仍身处家族制度的深渊,并为之得以长久存在而付出努力,这本身便又是一次难以调和的矛盾。
3 情与理背后自我存在的困惑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思想源远流长,尤其是儒家思想,更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而“仁”、“礼”、“孝悌”等思想也得以传播下来并被不断遵循。在“孝悌”思想的影响下,不论大家族还是小家庭,“百善孝为先”都是长辈对晚辈最基本的要求,这一传统传承至今,敬老爱幼依旧是我们倡导的美德。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孝悌”应该得到传承,但过犹不及是不可取的,而当国难当头,“忠”与“孝”便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了。当情感盖过了理智,当孝心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当对国家的“忠”面临着对家庭的“孝”,高觉新与祁瑞宣的苦难与矛盾便也开始了。
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高觉新,“孝悌”被他时刻谨记着,身处一个贵族大家庭的他,自然要做一个符合这一制度的“贤子孝孙”。面对爷爷的命令,一一遵守;面对贪婪的长辈,一一讨好;面对妻子,因为对“孝”的遵守而放任妻子一人面对分娩生产的险境甚至死亡。我们可以看到,高觉新谨守的“孝悌”已经成了毫无反抗、明知有错还要继续照办的“愚孝”。反抗便是不孝,而不孝带来的,也许就是整个家庭的责难。于情,高觉新愿意挑起整个家族的重担,这是符合长子的责任心的,百善孝为先,有这种考量并不为过,更何况他天性善良,并不希望身边的亲人受到伤害;于理,对这个腐化堕落的家族负责却是极不明智的作为,“孝悌”并不只是毫无条件的盲目尊崇,盲目的孝悌,结果是可怕的,更何况高觉新长辈的要求多半并不合理,要包容那些顽固甚至腐朽的长辈,他自我存在的判断在这一刻早已失去了应有的魄力与决断。在情与理的不断徘徊中,一切都走不出“情”这一范围的高觉新,便被“情”断送了所有希望。
而祁瑞宣虽然身受西欧先进思想的影响,但“忠”与“孝”的矛盾在他身上也是难以调和的,他的自我存在同样迷失在了情与理的矛盾之中。忠孝难两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面是对家庭的孝悌,另一面则是对国家的忠诚,这让只能在“忠”与“孝”之间选择其一的祁瑞宣痛苦不已。祁家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没有丰厚的财力,除了祁瑞丰,一家人也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于情,他应该留在家中尽孝,否则祁家在战乱年代是难以继续生存的;于理,国家正当大难之际,强敌未灭,何以家为?他更应该投入战场去挽救更多的家庭。但若是走上了战场,祁瑞宣尚未拯救他人,他的家人便已经因生计而毁灭。情与理的矛盾在这一刻胶着在一起,祁瑞宣的自我认识也在忠孝之间难以抉择。
高觉新与祁瑞宣除了身受“孝”文化的影响之外,还有“长房长孙”这一特殊身份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嫡长子继承制从周朝发源一直到现代社会,它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对高觉新而言,“愚孝”与“孝悌”是决然不同的,百善孝为先有其应该得到的世代传承的意义,只是高觉新的自我认知到后来更偏向于“愚孝”,才导致了那难以挽回的可悲结局。
高觉新身为高家的嫡长子,他便要负起这个长子的责任,负起对整个家族的责任。“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2]2“长兄如父”,他便要如同一个父亲般去调和整个家族的矛盾。高觉新的父亲在临终前对觉新要求:“我把继母与弟妹交给你,你好好地替我看顾他们。你的性情我是知道的,你不会使我失望。”这一句话,便足以体现高觉新往后的走向。不论做什么、思考什么,他都不能跳出这个“家”的范围,处处都必须为这个“大家”做考虑,这便又是一场情与理的矛盾。情感让高觉新愿意为整个高家所谓的和睦而妥协让步,但是每一次的让步,带来的都是兄弟的责难以及自我理智的痛苦,“他做人家要他做的事,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他做这些事,好像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在不断地服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受害者不断放弃自我的过程。高觉新虽然不满于旧家庭、旧制度,却依然为维护旧家庭而努力,正如觉慧在日记中所说的“大哥天天打牌,为的是讨别人的喜欢。”高觉新让“情”控制了自己的行为,一边又受着“理”的冲突,他看到了高家以及其他大家族种种的不合理之处,但没有一次能如高觉慧或者高觉民一般从正面发起挑战。高觉新的自我认知充满了情与理的矛盾,因为高觉新懦弱的性格,使得情与理在他身上越发难以调和,也越发让他痛苦。
而对于祁瑞宣,忠与孝更是一个难以选择的问题。国难与家难,选择国家必然家亡,选择家庭则内心煎熬,愧对自我。人应该“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担负起来。”[2]8祁瑞宣身为家中的长子,必然要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在面临着走与不走的问题时,祁瑞宣想到了家庭的困境,“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最终,他不得不做出了自己留在家里尽孝,而让弟弟出去尽忠的选择。情感让祁瑞宣为他的家人做出了一步步的退让,但这也是他痛苦的原因。去沦陷的学校上课,去英国大使馆工作,无论哪一个都让他的自我认知痛苦无比——他已经成了一个无耻的亡国奴。而在“孝悌”方面,祁瑞宣也是两难的,面对好吃懒做的弟弟祁瑞丰,祁瑞宣虽然厌恶,却从不曾忘记过身为兄长的“悌”:“不该,他不该,对老二取那个放任的态度!他是哥哥,应当以作兄长的诚心,说明老二的错误,不应该看着弟弟往陷阱里走!”这是出自情感而非理智,特别是在祁家家境困顿的时候,身为米虫的祁瑞丰为家庭带来的,只有灾难而已。情与理的矛盾在祁瑞宣身上不曾有过调和,尤其是在家国情怀之下,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是尤为痛苦的。
为了协调整个家族的矛盾,也出于长子的责任,高觉新便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态度,将自己的棱角磨平,妥协于家庭背后的封建势力,使得自己能合乎情意;而祁瑞宣则是为了家庭的生存,不断忍受内心的耻辱感,强迫自己去做颜面无存的亡国奴所做的事。但他们都是新青年,高觉新能看到高觉慧与高觉民新文化的合理之处,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日趋没落的家族的颓势无法挽回,他在兄弟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于是为激进的新一代文化人的兄弟出了一份自己的力。而祁瑞宣则是保持着那份报国情怀,让自己的弟弟代替自己逃出北平,走上了报国的战场。但情与理的矛盾依旧困扰着高觉新和祁瑞宣,作为两种矛盾的结合体的二人,他们自身的矛盾都难以得到调和,更何况家族的矛盾,在此种情况下,他们的难处与痛苦便变得尤为明显。
“人的意义不是先在自明的,不管是单个的人还是群体意义上的人,只有在存在中才能体现出他的主体性和确定性。而现代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一种自主性的存在,才能算是活着,此外都只是行尸走肉。”[6]高觉新和祁瑞宣的自我存在本身便是矛盾的,他们在孝悌与忠孝之间徘徊不定,自然难以肯定自我。而一个在封建家庭之中,一个在国家战乱之时,对自我存在的认识便越发困难。故而对高觉新和祁瑞宣而言,“行尸走肉”便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方式了。
灵与肉、情与理、新与旧等种种的矛盾,对高觉新和祁瑞宣的自我存在认识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高觉新与祁瑞宣自我存在的矛盾有其不同的地方,但更多的却是相似之处,一如自我与社会的矛盾,自我本身存在的矛盾等。作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觉醒了自我意识的青年,他们却只能按着传统的方式去生活,并对此无能为力。身为长子的他们,都为家庭而牺牲了自我,这相同的选择,注定了相同的痛苦。
[1]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3]陈少华.转型期父子关系链中的文化心理:论高觉新的自我牺牲[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4):75-81.
[4]胡志明.卡夫卡现象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5]蔡琳彬.老舍小说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探索[D].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
[6]谢春平,黄莉,王叔文.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罪罚与拯救主题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97.
[7](法)让-保尔·萨特.自我的超越性:一种现象学描述初探[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9]马晓丽.论现代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4.
[10]崔国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国现当代小说长子形象悲剧性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11]蔡琳彬.老舍小说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探索[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
[12]吴恒颐.论老舍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D].重庆:四川外语学院,2010.
[13]曾永成.“大哥”觉新:转折时代一个身心分裂的悲剧人格[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22-26.
[14]李锋.《家》中觉新形象的双重隐喻[J].世界文学评论,2008(2):199-201.
[15]杨云云.矛盾者:析《家》中觉新形象[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7):9-13.
[16]顾云清.浅论高觉新的双重性格[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46-47.
[17]陈少华.转型期父子关系链中的文化心理:论高觉新的自我牺牲[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4):75-81.
[18]宋辰博.论现代文学中长子形象的意义:以《四世同堂》长子形象为中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33-37.
[责任编辑:钟艳华]
The Contradiction of Self-existence:A Comparative Character Analysis of Gao Juexin and Qi Ruixuan
LEI H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Zhejiang 321004,China)
In The family and The Yellow Storm,consciousness of self-existence is clearly expressed in the two characters:Gao Juexin and Qi Ruixuan.As the eldest sons,they must bear correspondent responsibility and have no choice but to sacrifice their own lives to save their family.Obviously,the pursuit of self-existence and freedom is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ir social status as the eldest son of the family,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existence and responsibility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ir suffering.Starting from the conflicts of body and soul,emotion and reason and the new and the ol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suffering of Gao Juexin and Qi Ruixuan's self-existence.From the analysis,it is easily seen that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and family circumstances make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ir self-existence different,but great similarities could also be found at the same time.
Gao Juexin;Qi Ruixuan;self-existence;contradiction
I206
A
1672-6138(2015)03-0074-06
10.3969/j.issn.1672-6138.2015.03.016
2015-04-22
雷欢(1991—),女,浙江嘉兴人,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