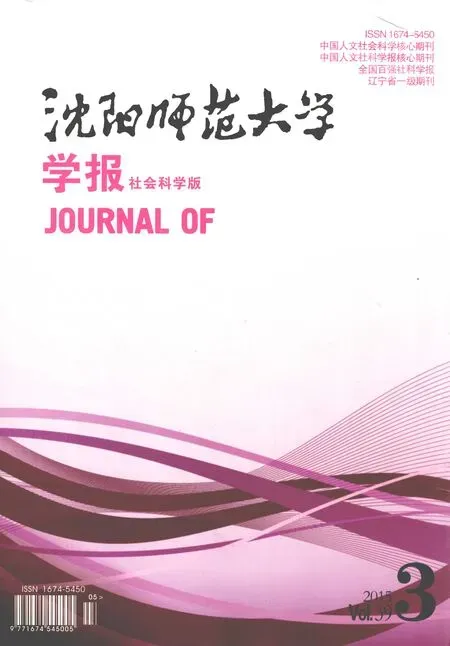《左传》中的断章赋诗现象
2015-04-10张艺赢
张艺赢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左传》中的断章赋诗现象
张艺赢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断章赋诗在《左传》中十分普遍。所谓断章赋诗就是在特定场合,截取《诗经》中某句或某段,改变原有意意旨而赋予全新的意义。断章赋诗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礼节上不可或缺的,有时还有讽谏作用。
《左传》;断章赋诗;春秋
先秦时期,诗歌舞乐活动十分发达,早期是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能够接触到的,后来孔子创办私学,才使得《诗经》能够被广泛认识,但是在孔子的观念中,《诗经》并不是可以随意提及和探讨的,这一点从《论语》中他提到的对《诗经》的评价和态度,就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诗经》的重视程度。因此春秋时期的诸侯、士大夫往往需要通过引诵《诗经》章句,来言志或实现外交方面的目的。这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一种风尚,关于这一风尚,在《左传》中有非常多的记载,本文就从“赋诗断章”的概念着手,着重分析研究《左传》中断章赋诗作用,并探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关于断章赋诗的概念
断章赋诗也可称为赋诗断章,要解释这一概念,可以先将其一分为二来理解。
首先,赋诗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赋诗言志,是指春秋时代诸侯士大夫常在各种政治、外交、社交等场合朗诵《诗经》(包括逸诗),借以言明自身情感或表明观点立场,这就是“赋诗”。
其次,《左传》中所记载的文人士大夫赋诗言志,往往是断章取义的。这里的“断章”是“截取某句某段”的意思,当时的“断章取义”,是人们崇尚的习以为常的一种礼义风尚,“断章取义”这个词在当时是一个中性词,与今义大不相同。所谓“断章取义”就是指可以不顾及整篇诗的意旨,只取其中某段或某句,来曲折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可以说,断章取义只是借用《诗经》的章句作为自己的话语,所取的可以是句子的字面意思,也可以是其比喻意思,也可以不管全诗原本用意,赋予诗歌完全不同的用法或意思,完全脱离了原诗的本旨。
关于断章赋诗的概念,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说“赋诗断章”就是引用。“盖‘断章’乃古人惯为之事,经籍中习见。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同作者之运化;初非征援古语以证明今论,如学者之考信。”[1]“为我所用”,与“发明《诗》之本旨”不相同,“不得混为一谈也”。《谈艺录》中说:“盖触类旁通,无施勿可,初不拘泥于《诗》之本事本旨也。”[2]另外朱自清先生也在《诗言志辨》中界定过断章赋诗的概念。
值得说明的是《左传》中所记载的“赋诗断章”,一般是赋诗中的某一句(直接引用)、某一章(标明所赋为某诗某一章,如襄公十四年所载“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以取其最后一章之意),也有时仅仅列出篇名,一般这种情况下取的都是首章所要表达的意思。
将以上论述加以概括总结,那么断章赋诗的概念可以概括为:春秋时代,诸侯、士大夫、文士常常在政治或外交场合,通过引用《诗经》章句来表情达意,曲折地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但往往改变所引所诵诗歌要表达的原意,取其表面意思或比喻意思,又或者赋予其全新的意思,这种引诗或诵诗的手法就叫做“赋诗断章”。
二、《左传》中的“赋诗断章”
“赋诗断章”这一说法最早记载于《左传》[3]襄公二十八年,其中有一段文字直接提到赋诗断章,原文如下:
庆舍之士谓卢蒲葵曰:“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庆舍的家臣卢蒲癸为迎合庆舍,不顾同姓同宗之忌,娶庆舍之女为妻,他说他这样做,就像“赋诗断章”那样,只取对自己有利有用的一面。用“断章赋诗”来比喻“余取所求”十分恰切。另一方面,一个大夫的家臣竟对赋诗断章有深刻了解,也足以说明“断章赋诗”的风气在春秋时期已经十分普遍。
《左传》记引诗赋诗231首,多是断章取义。如此大量的用诗也正是当时赋诗风尚的表现。《左传》中赋诗的作用大概有以下几种: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多朝聘盟会,在这样的场合,诸侯士大夫之间往往会断章赋诗,相互赠答,既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外交礼节不可或缺的一环。往往在宴席间能够赋诗相赠是对对方身份地位的肯定,也是自身学养的一种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中此类引诗多用以表示对宾客的赞颂和褒扬。
顾颉刚先生《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中说:“断章取义是赋诗的惯例,赋诗的人的心意不即是作诗的人的心意。”这也就是说在断章赋诗时完全可以忽略诗歌原始的意义,这种现象比如昭公元年所载,郑简公宴飨赵孟等人的席间,叔孙豹为表尊敬赵文子而如下赋诗:
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
叔孙豹所赋《鹊巢》取的是其中“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是将赵文子比作鹊,自己为鸠,得到赵文子的庇护,免于被杀。原诗是一首描写婚礼的诗,以平实的语言描写婚礼的过程。关于此诗诗旨历来有争议,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鹊喻新郎,鸠喻新娘,诗人代新郎言说或新娘家人在唱赞歌;鹊喻弃妇,鸠喻新妇,这是一首弃妇诗;鹊、鸠并无明确所指,只是自然界的两种鸟,且此诗的叙述者是与婚礼无关的他者。全诗三章,选取了三个典型的场面加以概括,真实地传达出新婚喜庆的热闹。无论此诗正解如何,《左传》中所记的用法无疑是与原诗相去甚远的。
其次,关于春秋时期士大夫赋诗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赋诗言志的作用,对于赋诗者来说可以言志,而对于听诗者来说,则是可以通过所赋之诗来了解赋诗之人的为人和志向的。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左传中赋诗的手段虽多断章取义,但目的也大致相同,例如襄公二十七年所载:
“……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榆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EP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彼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垂陇之宴,赵孟直接要求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印段及公孙段七位郑臣“赋诗以言其志”。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由不同人所赋之《诗》,正因志向意指不同。而其后赵孟对七子的分别评价也彰显了赋诗的更深一层次的目的,也就是观志。比如上面提到的赵孟请七子赋诗言志一段,后面还附有宴后赵孟观七子之志的一番评价,原文如下: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宴飨结束后,赵孟和叔向讨论席间观志的结论,说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因为伯有赋诗为《鹑之奔奔》,本是为刺宣姜淫乱而作,取其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用以攻击自己的国君,人臣刺君王本不应在有使臣的情况下进行,因此赵文子才说这是“床笫之言”“非使臣之所得闻也。”而由此赵孟也实现了观其志的目的。另外,子展得到了赵孟很高的评价,也是赋诗观志的结果。由此可见听赋诗足以观志。
再次,由于《诗经》之温柔敦厚,含蓄委婉,赋诗常用的手法又是断章取义,所以《左传》引诗,另一作用即为讽谏、规劝。
最后,《诗经》在春秋时代,地位之重,应用之广,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正因《诗经》不仅可以言志,也可藉以加强自己说话的力量,或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如在襄公二十六年中所记:
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
这句是中所引诗就是用以证明“无善人”的结果是怎样的,从而证明“善人”是国家的根基。
《左传》中不乏作者对人或事的评论。在作者史评之前常冠以“君子曰”三字。这种笔法,后世史家亦多沿袭仿效,例如史记之用“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之用“臣光曰”。而这些评论中作者也经常引《诗经》章句,以加强言论的正确性及权威性,同时证明“吾道不孤”,“英雄所见略同”。《左传》全书,在“君子曰”后引入诗句的,共有三十馀例,比如襄公十三年吴国趁楚共王去世,楚国有丧之际攻打楚国,结果打败,在君子曰中发表作者的观点:
君子以吴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可见引用《诗经》的目的是证明作者观点。
三、赋诗断章现象形成的原因
(一)诗歌舞乐活动的发展是其形成前提
据《左传》中记载,列国君臣行朝聘盟会必赋诗,这就使得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的活动更经常化、程式化。这就造成后来断章赋诗成为了一种风尚,在外交或政治活动中,赋诗即断章赋诗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形式或不能缺少的环节。
(二)诗歌的多义性
春秋时的“赋诗”“引诗”之所以可以断章取义,与诗的多义性,或者说含混模棱,有很大的关系。多义性是诗歌的共性。
关于多义性在《诗经》中的体现。叶嘉莹在《迦陵论诗丛稿》中她把这些来源归为三种因素:
其一,由于表现的工具——文句的读法与语义所能引起的解释之分歧;其二,由于表现的内容——即作者心中之意识活动的难以确指;其三,由于表现的效果——读者心中所引起的感受与联想之反应的不同。
其中的因素之二,即作者心中之意识活动的难以确指,在《诗经》的接受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比如说《蒹葭》中,“伊人”这一意象,可以被理解成多种含义,它可以理解为努力追求但却始终无法接近的所有目标。
《诗》是否原本就“无定指”,尚可商榷,但《诗》的“作者心中之意识的活动之难以确指”则是无可否认的,春秋时的“赋诗”“引诗”正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个特点,将“古人所作”“援为己诗”。
(三)赋诗断章是赋诗者的主观选择
通过赋诗断章的方式来言志和取意,能够使言辞委婉,避免忠言逆耳美言,近谀怨辞招嫌,同时又使言语具有艺术魅力。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可以使作者言论更有理有据,同时又可以使得赋诗之人更具文学修养和内涵。
(四)断章赋诗可视为古人升华言诗之法
诗以言志,即赋诗言志和引诗言志,是对《诗经》作诗言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诗言志”观念在实践中的又一次体现。春秋时的“赋诗”“引诗”到昭公后就渐渐终止了,但其影响并未因此泯灭,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诗以言志”和“断章取义”的观念更是流布后世。“断章取义”直接影响了汉人对《诗经》的诠释。《诗》的断章可以给文学带来新鲜的内容,若从本质上分析,可以视为读者在文学接受和解读过程中的一种再创作,或者说是对材料的重新解读和扩充,这也侧面反映了文学的读者和使用者对文学重新创造的能力到底有多强。近代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后世的用典实际上就是对断章赋诗的一种沿袭,但笔者认为此说并无道理,二者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勉强说是断章赋诗给予用典这一手法一定的启示作用,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杨抱朴】
I206.2
A
1674-5450(2015)03-0099-03
2014-11-24
张艺赢,女,辽宁铁岭人,辽宁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