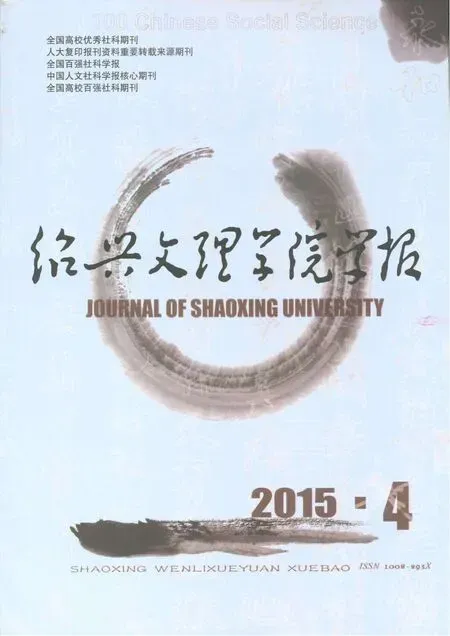近代“边缘人”科举观述评——以沈毓桂为例
2015-04-10翁梓轩,薛玉琴
摘 要:沈毓桂是晚清活跃于口岸城市传教士周围的华人编辑、翻译家。他从自身的科举体验出发,认为以八股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是近代中国贫弱的根源,使社会形成了泥古、重虚轻实的风气,束缚了传统士子的思想,扭曲了书院教育的理念,甚至对西学措施所取得的成效也产生了影响。沈毓桂在中西学结合的基础上,对晚清书院改革和士人的学习理念提出了合理建议,并特别指出广学会对中国振兴所能起到的作用。通过沈氏个案研究,可以折射出“边缘人”群体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遭遇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贡献。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3X (2015) 04-0107-05
收稿日期: 2015-05-27
作者简介:翁梓轩(1992-),女,浙江台州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薛玉琴(1968-),女,江苏淮阴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边缘人”(the marginal man,也译作“边际人”)的社会学概念于1928年由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帕克首先提出。帕克眼中的“边缘人”“和两种不同文化生活与传统的人们密切地生活居住在一起。他不愿意与传统决裂,即使他被允许这样做;而由于种族的偏见,即使他正在努力寻求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却也不能被新社会所接受。他是处于两种社会和文化边缘的人。” [1]
在这一意义上,近代中国的口岸城市里便汇集着这样一群“边缘人”。他们多出生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前半辈子遵循中国读书人谋求人生价值的传统模式——“学而优则仕”。然而那个时代却为他们准备了不一般的后半生历程。他们多因仕途不顺,或迫于生计,少数出于爱好,选择踏出乡关,出外谋求更多的出路。由于受雇于西人有着较高的薪酬,所以这是他们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另有出路,他们一定会弃此而另谋其他。在西人西学的耳濡目染下,这些读书人由于有着文化之根、社会之根,其“接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往往比殖民地人更容易”, [2]22于是他们徘徊于中西之间。
“当边缘人大量出现的时候,这些边缘人可能自己组成一个边缘群体,使有所归属,这个群体可能形成自己的‘边缘文化’(Marginal Culture)”。 [3]“由于边缘人不可能归属于两个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所以他们极其缺乏归属感。” [1]于是,这批孤独的知识分子,不由地在上海聚起一个社会圈子,互相聊以慰藉。这个圈子的成员,涉足文化界、思想界乃至工商界,他们是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学的先进分子。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王韬、沈毓桂、李善兰、蒋敦复、蔡尔康、郑观应等。
就是这样一群中西之间的“边缘人”,在他们“走出”场屋、走近西学之后,如何看待那痴缠了半生的科举制度?下文将以沈毓桂为代表,通过对其科考经历和相关言论的考察,就近代“边缘人”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这一问题进行一番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
沈毓桂出身于“吴江世胄”,却自幼丧父,家道中落,由祖母抚养成人。 [4]15所幸沈毓桂天资聪颖,少负才名,并且“擅书擘窠大字,工篆隶,求者户外履满。” [5]6可见尽管家庭条件并不太好,但祖母仍然尽己所能,使沈毓桂得以接受传统而扎实的教育。“童乌聪慧记依稀”,却“欲授元经素愿违”, [7]11962沈毓桂接下来的科考之路并不顺畅,他长年一边在家乡私塾任教,维持家庭生计,一边继续搏击功名。
“性情纯挚,霭然可亲,出一言如恐伤人”,这是王韬对沈毓桂的性格评价。 [5]6然而,科举之路上长年的郁郁不得志使沈毓桂的性格深处又多了一些愤世嫉俗的因子,这对沈毓桂中年时交游西人、接触西学乃至改变信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849年,江苏大水,沈毓桂为避水灾,于“道光己酉冬,来游沪上”。 [6]488在这期间,沈毓桂同王韬结识。同样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同样为功名所困,尽管两人个性迥然不同,却相见恨晚。在这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两人“为文字交,诗酒之会,无役不与,以此徜徉海上,颇得狂名。” [5] 6沉郁、拘谨的沈毓桂有此举动,实在叫人震惊。沈毓桂“自少至壮读中国圣贤之书,即信之笃而守之固,平居一言一动必准于礼法而不敢稍纵焉。” [7]15059如此的反常行为,不得不说正是其素日压抑于内心的愤懑情绪的集中发泄。
在这一时期,沈毓桂还谒见过西士麦都思,同时,“英商汉璧礼先生,延余教读。” [6]488经历了半辈子传统士人生活的沈毓桂,不论其是为了谋生,还是出于好奇,抑或是其他原因,由此开始了与西人西学的初次接触。此后的数十年中,沈毓桂曾一度随艾约瑟游历传教,而更多的则是从事翻译、办报等文字工作,沈毓桂的后半生,“乐与我辈西人相游处” [11],“或朝夕相亲,或偶尔晤谈” [6]488,并深感获益匪浅。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尽管已经开埠,但民间风气还是相当保守的,像沈毓桂这种前半生一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于这一年岁开始接触西学,并且一直坚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种选择着实令人震惊。究其原因,他的个人性格与人生经历极大地促成了这一结果。沈毓桂自幼天资聪慧,却仕途坎坷,多次科举,一无所成。“余不谙世务,不随人情。家徒壁立,迹类蓬飘。年年冯谖,常同弹铗依人;岁岁邹阳,不免曳裾作客。青眼难逢,知己不易。两鬓已雪,百念皆冰,于是淡然于世俗,而殷然于天道焉。” [6]488然而这一切,在遇到西人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高山流水遇知音,麦都思之后的艾约瑟、林乐知等人更称得上是沈毓桂的伯乐。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西书院给沈毓桂施展抱负提供了绝佳的平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得遇伯乐,终有驰骋之机。科举经历带给沈毓桂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同西人西学带给沈毓桂的存在感乃至成就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毓桂会选择后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对西学的认识日益深化,但科举是沈毓桂心中解不开的结。1865年,已身处西人旁侧多年的沈毓桂再度赴试,并取得了本届参加乡试的资格,成为一名“附生”。在接下来的乡试中,沈毓桂得了副榜,虽失去了参加会试的资格,但有了这一功名,便可以做官了。沈毓桂在19世纪90年代的诗作中,称自己“都门鞭影滇南路” [7]11962,其友人也说沈“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 [5]1,可见沈毓桂曾被授官云南。然而,《挽艾母七绝六章》中却道出了事情的后续,“授官远赴古滇南,自愧才难胜任堪” [7]5030。由于某种原因,沈毓桂未能到任。这次的科举经历,似乎可以窥见沈毓桂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取向。沈毓桂在晚年回忆半生科举经历时,慨然道“八回场屋休回首,憎命文章若奈何”,此中几多无奈,恐怕只有切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二
报刊是西人传播西学的前沿阵地,也是国人了解西方的窗口平台。在那个时代,西人主办的报馆书屋往往汇集着全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具时效性的新闻资讯,更是西学密集程度最高的地方,它那为数不少的西人作者群源源不断地给它供给能量。作为外报的一名华人编辑,后来还擢升为报刊主笔,沈毓桂接受的西方文化数据量不可谓不大,这些文化炸弹持续不断地轰击着沈毓桂的神经,使得他脑海中的西学观逐渐丰富和立体起来,对中学的认识也日益客观和全面。
在沈毓桂致力于报界的二十多年中,科举考试与教育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万国公报》上登载的各地科考情况,包括考试题目、金榜题名录、授职名单等屡见不鲜。这虽是为了满足公报读者的兴趣需求,但也折射出公报编辑沈毓桂对科考的持续关注。
毕竟曾经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熏陶,沈毓桂对科举教育模式的优点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书院教学中,“月有课,岁有考,聘名师,聚俊秀。课其所学,分列等次,给膏火以助寒畯,奖花红以励优异。俾有才者知所励而奋,无才者亦知所愧而勉”。同时,沈毓桂强调了政府对书院及人才培养的重视。“地方贤有司,以书院之兴废,系乎人才之盛衰也。每遇课期,虽督抚司道之尊,亦多拨冗亲临,郑重将事,使多士咸鼓舞奋发,争自濯磨,以副长官好文兴学之意。”正是得益于从中央到地方对教育的重视,“由是文风日盛,人才日多,教化愈行,风俗愈厚。是储才之地,育才之方,舍书院其将安赖乎?” [8]
然而,转视当时国内的教育现状,沈毓桂却太息不已。他与科举,是有过半辈子纠葛的,对于传统教育的弊端以及当时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深有感触。在沈毓桂看来,以八股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是近代中国贫弱问题产生的根源。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抨击科举制下社会泥古风气的形成。沈毓桂曾借唐廷枢之口道出,“吾人经济根诸学术,学术不深即无以识当世之时务,时务不识即无以应万事,万变纷至迭来而各妙其用,一旦临大事当大任,至茫然无所措手足,始悔其前此之不学无术。此固学者之通患,而亦有识者之所忧也。”中国之贫弱,皆出于学术不深,于是唐廷枢“遂弃举业而习洋文。” [9]而学术之所以不深,是由于“当今之世,无论士农工商,悉皆古法之是循,不知新法之是效”。近代以来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国人处变却不求变。“为士者既泥于八股文章,不识致知之义。复泥于一篇诗赋,不识格物之端。为农者既泥于桔槔之用,不解植树以防旱灾。复泥于耒耜之负,不解械器以耕畎亩。为工者既泥于前人操作,不知巧妙之翻新。又泥于依样葫芦,不知枢机之捷用。为商者既泥于往来市肆,不欲抵外国以通商。又泥于买卖己邦,不欲涉海洋以贸易。此皆泥古而罔知善变者也。” [6]229四民之学之所以泥滞不前,皆出于科举制度,一方面,科举制度只考诗赋八股,士人只需将此研究通透,熟练掌握即可,不需有所创新,也无需钻研其他;另一方面,社会上“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使得以科考进阶的所谓“士学”成为显学,而其余的农学、工学、商学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更不用说创新激励机制,于是泥古而停滞不前。以士为首的四民阶层一旦陷入泥古的泥沼,“其关系于国家者甚大。盖既有泥古之心,则出于其心必至害于其事,害于其事必至害于其政。无惑乎国家之时势,日邻于贫弱矣” [6]229。
第二,指责在科考引导下重虚轻实的社会氛围。朝廷以诗赋策论取士,“设书院以奖励,定考试以甄拔”,使得“士之靡然从风者,遂汲汲焉不遑他求耳”。在这种学习风气下,“一切有用之书反摈不寓目。何怪乎既登仕版,茫然于历代兴亡之故,当世利弊之源,一方守御之资,四海边防之策,而极至猝遭事故,溃败决裂,几于不可收拾哉!” [6]218在科举制度阴影下的社会,“崇尚虚文,浸忘实意,贵农桑而贱技巧,重词赋而轻戎兵。卒至士卒单微,器械窳敝。重以承平既久,人民渐多。贫富既有不均,事畜每遇不给,狡猾因而骫法,潢池竟至弄兵。” [6]258社会氛围的重虚轻实,使得国家精英工于虚文,荒废实业,使得国家力量的物质基础——农、工、商业萎靡不振,如此又何谈裨益于吾华之国计民生。
第三,痛陈科举制度对士子们思想的束缚,揭露了科举阴影下读书人的畸形人格。对这一点,沈毓桂深有体会,其三十余载的科考经历,却只能用“休回首”三字来概括。以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极大地囚禁了士子们的思想。“中国读书之人只知四书之义,六经之文,五言之诗,八股之艺,即以为道学之蔑以加。” [10]教育、取士模式所存在的弊端,使得读书人的思想日益僵化,眼界日益狭隘,只知书,不知世,“读书愈多,才名愈著,言语愈傲,识见愈拘。” [11]如此的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一旦仕途不通,便无从转型,只得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窄。
第四,认为由于科举制度的导向作用,书院教育逐渐走上了弯路。19世纪末的中国书院,主要培育三种类型的学生。其一是“专试帖括者”,他们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终岁以五言八股进退人才,肄业弟子员,即使屡列前茅,群推老手,使之掇巍科,登显仕,亦当绰绰有余。然其人于帖括之外,懵然无所觉也。是所得者,乃时文之人才,未可以为人才也。” [8]其二是“专试经古者”,这类学生“每课取词章掌故舆地天算等学,各出数题,使各举所知以对,择其佳者,优给膏奖。肄业弟子员,亦多博学通儒,一时名士。然好古之过,流于迂拘,嗜学之专,懵于世务,使之立说著书则有馀,使之安国治民则不足。是所得者,经古之人才,未可以为人才也。” [8]其三是“专试洋务新学者”,这一类学生是应时而生的新产物,“所取课卷,类皆识时达变之作,旷览古今,洞观中外,原原本本,殚见洽闻,书院人才,于斯为盛。然肄业诸生,大抵皆长于华文,短于西学。不过涉猎近日西人翻译各书,窃取一二,以眩观听……其实仍多扣盘扪烛之谈。……孰知彼固只闻其名,未见其物。问其名则能对,示以物则不识者……即此类推,其所言西国诸事,其又可尽信乎?” [8]当时的中国,对于西方的器物,“俱已仿而行之,行之业著成效矣。而于富强终有所未能立效者”。究其原因,便是由于“今之通西法者未尝无人,然或知其法而未知其理,知其粗而不知其精,知其一二而不知其千百”。在这种情况下,“事事不能不假手于西人,一假手则事权属于西人,即利益归于西人。” [12]
第五,指出晚清政府的西学措施非治本之长策。尽管廷臣疆吏已经“延揽誉髦兼习西学,都中暨各行省俱有同文馆,业著成效。然事机迭出,肆应尚苦乏才”。 [6]515“今中国每事既取法于西人,而翻译制造开矿诸务不能不于西人是赖。虽薪水十倍于中人而不惜。” [6]258由于科举制度仍以诗赋八股取士,使得西学人才后备不足,社会主力仍专注科考;即便19世纪90年代末加以洋务新学取士,学子也多只知表不知里,“博通西学者尚少耳”。对此,沈毓桂深为忧虑,“窃谓此日非得忠智之士,使之练达西国文字、朝章、军政,以与西人周旋,恐不足以维大局于不坏。而不泽以诗书之气作其义烈之心,标榜才华,冀幸富贵,合之古圣贤重道崇儒之本旨,亦奚取焉?” [6]515既有的西学措施“不过暂补于目前,非治本之长策也。凡从事实学,方能收实效,若不从根本用着实工夫,即学习皮毛,亦无裨益于实用也。” [6]488
三
为了解决中国现阶段在教育乃至思想文化上存在的问题,沈毓桂试图从西学中寻找“一些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资源”。沈毓桂发现,“西国之赖乎设立书院已久,几经培养 [2]22,几经历练,而才不可胜用矣。” [6]226西方对书院学校的重视程度同中国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校书院林立,或设于城市焉,或设于乡村焉,或设于京都焉,捐建固赖官绅之助,房租亦充经费之资。” [10]在教学上,“分门别类,不能偏废,亦非一蹴可能,必循序渐进。” [6]488所学内容涉及史学、理学、经学、文字、格致、天文、数学、地舆、音乐、丹青等,“施教则因乎其才,技艺必臻乎纯熟,分班则别乎其等,功课各定夫章程。凡属黎民,不论富贵均需教授,庶令男女,不分愚智,罔有弃材”。 [10]
在自身科举体验的基础上,对于如何整顿中国的教育乃至思想文化,沈毓桂采西学之所长,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主张改革晚清书院制度。沈毓桂通过中西书院的创办,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遂发表《救时策》一文,文中不仅将“兴学校”作为振兴中国的三大纲之一,而且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新式书院的规制。生源上“遴选青年举贡生监……凡童年愿学者,亦进而教之”,“其监院则宜聘泰西通儒,不可滥竽充数。”在培养方案上,“先教以语言文字,俟其渐能与西人问答,能读西书,能作西字,然后视其材质之所近,教以一艺,专而精之,必底于成。其有天姿过人,而欲兼习众艺者,俟其一艺已成,方可更习。学已成者,由官试其所能,给以执照,以闻于朝,因材而器使之,则他日洋务人员,不可胜用矣。”这是各省会西学大书院的情况,至于府厅州县乡镇的西学小书院,“凡聪俊子弟,已习华学数年,文理清顺者,皆可至院肄业,分类学习,学成亦给以执照,俾各行其道而安其业焉。” [11]地方各级根据其实际情况分配教育资源、制定教学标准,而毕业执照的颁发却又能使人才尽其用,这一考虑堪称精细。
其次,建议士子速习当今有用之实学。为了避免将来临事而茫然无所措,士子们应“精其识以择所学”,“相时以动,而探索得宜,尚不虚聪明之用。”沈毓桂还宽慰士子不需有学习西文的担忧,只需“于课余之暇,玩味寻绎”已译诸书即可。而且,熟识西务还能让士子将来“于有洋务之处办理得当,措置裕如”,使上司“异眼相看”。 [6]218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开拓自己的眼界,视野要不止于传统书籍,而要博知,“如用咿唔诵读之功,复用其功于格物之方,致知之学,则识见大矣。” [6]229沈毓桂建议为士者应当学贯中西,“揆今之时,度今之势,专西学而废中学不可也,专中学而废西学亦不可也。二者得兼,庶为全才。” [6]226到了19世纪90年代,沈毓桂注意到,在渐习西学的过程中,少数“专讲西学者,往往见异思迁,食用起居,渐染西习,遂至见弃士林,皆由鲜中学以为根柢之故。”对此,沈毓桂一方面再次强调西学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凡于西学,又皆宜剥肤存液,师其所长,慎勿窃取皮毛”。 [11]另一方面,“以华人而徒习西学,又惧其忘却本来”,故重提“中西并教,庶几一举两得,不至顾此失彼。” [8]
再次,“设广学会以期中国富强”。广学会自成立以来,“专以著书为事”,“举凡泰西生财教民诸新法,有关于中国教养之道者,类多译成华文”,“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加之广学会诸君的人格魅力,使沈毓桂深感,中国如果要振兴,惟仰赖广学会不可。沈毓桂眼中的泰西鸿儒们,“其殷殷为中国求益之心,有求华人之所不能求者,其勤勤为中国剔弊之意,有剔华人之所不能剔者。” [12]在广学会的引领下,“将见中国人才蔚起,于西国之富强无或多变,岂不美哉?” [13]
止于言而重于行,沈毓桂所做即如所说。1882年,沈毓桂开始了他的教育实践,同林乐知“商立中西书院于沪上”,学院以“中西学不可偏废”为宗旨,“假西学为中学之助,即以中学穷西学之源。” [6]515沈毓桂还担任学院掌教,总司院务,这期间他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在校学生的充分肯定,“中西书院议起于林进士乐知先生,而成于沈别驾寿康先生者也。”中西书院的办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开设八载以来,“规制妥善,功课严密,前后来学之子弟,计千馀人之多,其中有游庠食饩者,有海关暨电报招商诸局所罗致者,成就为不少矣。” [14]林乐知与沈毓桂为了中西书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诸形劳瘁”, 在1894年沈毓桂因年衰辞去《万国公报》主笔之后,仍坚持中西书院的掌教兼司理院务工作。1895年监理会派潘慎文接替林乐知担任中西书院监院后,“院中诸事,大有更张”,其办学宗旨已逐渐偏离林乐知与沈毓桂最初的设想,由是沈毓桂于次年辞去书院中的职务,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可以说,沈毓桂的个案特征,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边缘人”的共同特点。他们接受过最扎实、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与近代来华西人密切地居住、生活在一起,真切地接触着西方思想文化。他们结合自身的切身体验,希望藉西学来改善中国的现状,成为近代倡导教育变革的先驱,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