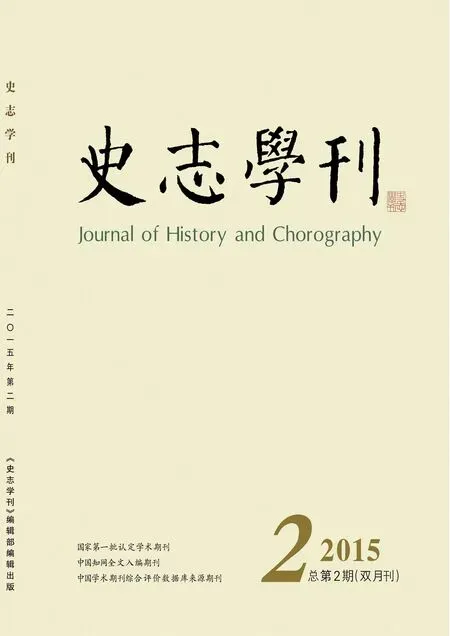知识史:一个简短的回顾与展望
2015-04-09潘晟
潘 晟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当代史学研究新意叠出,精彩纷呈。从史学观念,到方法、理论、具体论题与对象,都表现出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状态。在纷繁复杂的史学流派及其研究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其中存在一些共性或趋势性的东西。就史学研究的宗旨或观念而言,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对不同历史的理解作为一种思想在史学研究中普遍兴起[1]关于史学研究中的“理解”,参见王加丰.“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历史研究,2001,(3):164-179.与理解相关的另一个思想则是“解释”,它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思想倾向,虽然还未见有系统的概述,但采取这一研究策略的著作却极为丰富,尤其是经济史研究,值得我们重视。另外,“认同”作为社会学、人类学中常用的概念与分析方法,它在新社会史研究中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完全可以超越分析方法,而作为一种史学研究的目标和思想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史学博士的就业危机,引发了史学培养模式的实验,出现了以任务为导向的应用型史学研究思路[2]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3):34-48.关于应用史学以及它与相关概念的争论还较多.姜萌.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4):130-136.。在方法和理论方面,跨学科与多元视野成为史学研究的常态[3]跨学科方法,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并作了详细的梳理。参见蒋大淳,李红岩.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概述.史学理论研究,1992,(1):138-156.跨学科在方法和理论两个方面,都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常态,涉及学科与方法很广,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地理学和社会学方法、理论,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而在研究视野的多元化趋势中,有两个相对的问题较为突出,一个是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一个是全球史视野。关于史学的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组织过笔谈,而“全球史”,则《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学术月刊》2005年第1期分别组织了笔谈,首都师范大学组建了全球史研究中心,以致有“全球转向”之说。此外,在技术层面上,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的计量革命之后,目前最引入注目的是GIS技术的应用。。而史学研究实践中,从史料到具体论题,都极大地得到了拓展,各种以论题为中心的史学领域不断发展壮大,如环境史、医疗史、身体史、微观史与新文化史、影视史学、公共史学、网络史学等等,都形成了热点。相比而言,国内对知识史的介绍虽然很早,但是讨论尚不充分,因此略作梳理,以供参考。
一、知识史:旧论题新转变的结果
关于知识史,1987年朱孝远在向国内介绍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时候,就有涉及。他指出,历史学与文学、哲学相结合产生了知识历史或称意识形态史(又称观念史)。它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学科,即研究每个时代所产生的、反映时代与社会特色的、并对社会产生非常影响的一切时代思潮。思潮史研究的对象是思潮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派史学家认为,一切冲击社会的新思潮都应研究,无论是哲学的、科学的、文学的或者神学的观念,从基督教到经院哲学、从牛顿到伏尔泰、从达尔文到马克思,从理性主义到反理性主义,从弗洛伊德到萨特的存在主义,从悲观主义到嬉皮士的性开放运动,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美到现代的女权主义,这一切均属于知识史研究的范围。并指出,知识史在当时的美国,已成为大学历史系学生必修的课程,因为研究社会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文科学生不可少的训练[1]朱孝远.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特征与方法.历史研究,1987,(2).(P142-155)。从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概念的模糊性,即到底是history of knowledge还是Intellectual history?尚存歧义。前者翻译为知识的历史,没有任何疑问;而后者的中文翻译,“思想史”“知识史”“智识史”,各种译法都有。这种模糊性,既有翻译及中英文学术语境的原因,也有西方学术界对于“知识史”界定的原因,即试图表达既不同于“思想”,又不同于“科学”;既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单纯的知识的史学研究。这种模糊性,在西文研究中至今仍然存在。
对于知识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论题,它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有着深厚的哲学与社会学背景,不仅发展出独立的知识社会学,即其在科学哲学、科学史领域,也存在着内史、外史之间的长期争论。综合起来,在对知识的各类早期研究中,以“科学知识”为对象的占据了主流,其研究的目标也基本上以“科学知识”的发展或累积方式为主,并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色彩。二战以后,尤其是后现代批判思潮兴起以后,逐渐被打破,出现了超越科学和文本的“知识史”研究。这与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扩散,尤其是福柯以“话语”为核心的知识考古学引发的冲击有关。
在打破“科学”对知识的垄断之后,新问题随之而来,“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引发思考的关键之一。“知识”的合法性,实质上是以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为参照,承认该体系之外的知识作为“知识”的地位。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非西方的、非“科学”的知识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此,原来非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否能够发展出西方近代科学那样的知识体系的问题 (在中国史中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转变为每个知识体系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自我理性问题,包括西方内部的“非科学”的各类知识系统。从而开启了去西方中心主义和去科学主义的知识史研究路径。这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
二、知识史:社会变迁研究的新视野
虽然知识史被引介很早,但是或许受传统学术史的影响,以此为名的研究并不多[2]如以李零为代表的古代术数研究,以及裘锡圭、李学勤等为代表的出土文献研究,数量庞大而质量上乘,改写或部分改写了今人对于古典知识世界的认识,但是他们都没有以知识史的名义做专门的阐发。。专门对西方Intellectual history做阐述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葛氏将Intellectual history与history of knowledge做了区分,前者译为思想史与他自己的研究相对应,后者译为知识史,与通常概念上的知识相对应,包括操作性的术数方技、文字性的文本,以及仪式性的身体知识等,范围宽泛。他将后者作为说明思想史的资源,所谓思想离不开知识。。此外,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中,第二编“知识传承:东方与西方”,收入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田野研究》、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两篇长文[1]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需要指出的是他自己关于儒学地域化的研究,偏重于知识群体,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P349-466),都从具体知识入手,阐述社会史问题。同期,彭继红发表了《知识史观: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方法论》[2]彭继红.知识史观: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方法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P28-33),稍偏于宏论而影响有限。
此后,各领域一些以知识史为题的研究陆续发表[3]如法史方面,高鹏程.西方知识史上利益概念的源流.天津社会科学,2005,(4):21-27.马哲方面,胡大平.重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史的视角和战略.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5-14.地学史方面,丁一.“源流派分”与“河网密切”——中国古地图中江南水系的两种绘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3):115-125.潘晟.地图的作者及其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邹振环是少数明确以知识史为研究路径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先后出版了《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产生了较好的影响[4]叶隽.晚明学域与观念交易——知识史视野中的“汉文西学”.中国图书评论,2013,(7):99-103.叶隽指出,邹振环对知识史的界定借用了史华慈的“中国知识史研究”的构想,而史华慈的原文不是history of knowledge,而是intellectual hisrory,译作“智识史”更好,且史华慈所谓的知识史研究,更多地接近于知识分子史。。此外,孙英刚对中古知识、信仰与政治的论述[5]孙英刚.神文时代:中古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之关联性.学术月刊,2013,(10).(P133-147),以及潘晟对重构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设想[6]潘晟.重构中古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29(A05版).,都提出了各自的知识史研究思路。
上述研究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将知识史作为思想史的资源,关注的重点是某个时代或地区有什么知识;二,将知识作为与信仰、政治相互阐发的手段,其基础也仍然是某个时代或地区有什么知识;三,关注中西知识的交流、传播、接受;四,关注专题知识的累积、演变、选择与被选择的历史过程,注重知识的历史性复原研究。这些研究方向的工作成果还并不丰富,每个专题都值得长期深耕。
不过,在以上基础上,明确地将知识史作为探讨社会变迁的一种手段或分析工具,亟待展开,其意义或许更为深远。事实上,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样本。从《疯癫与文明》,到《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史》,透过其迷幻的对象、以权力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可以感受到他所想表达的一个中心主题,即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社会如何成为可能这一“命题”,而“知识型”的转变是他用以证明这种可能性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经过哲学化之后,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呈现。不过,这一系列关于知识型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知识”过于形而上,显得不那么“历史”,从而遮蔽了“历史”,尤其是遮蔽了他在《词与物》中表达的“知识”与宏大的社会变迁之间的方法论价值。
另一个关于“现代社会如何成为可能”的经典研究,亦可作为知识史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参考。这是上个世纪早期完成的艾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该著一般作为心理史学的代表为人熟知。但是,通观全书,用来证明近代文明形成的是关于礼仪、日常行为等一系列规范的知识演变过程,由此呈现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从而证明现代社会的可能。
社会变迁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具有极好的包容性。从生产工具、耕种方式、风俗、景观,至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都可以作为专门论题。一个国家、地区,它的变化往往是逐渐发生的,其变化的深度、广度存在着行业、部门、区域之间的差异。它达到一定程度,便造成其社会形态发生变化。通常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形态演变的研究,在讨论生产工具、耕作方式、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方式的时候,注意的是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比如铁、铁的生产规模、农业生产方式、奴婢的数量等等。具体生产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出现,它的数量与规模固然重要,但是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乃至一些组成部分,它或它们的有无,往往并不一定能够充分地证明社会变迁所能达到的程度,尤其是社会形态的变化程度,因为社会的质变并没有固定的数量标准。
以关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唐宋变革论(包括遭到误解的宋代近世说)、资本主义萌芽之有无,以及江南工业化等重要问题的争论为例,之所以长期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很大程度上与争论的双方使用大致相同的史料,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数量、质量展开所致。如果换一个考察的思路,从知识史的角度出发,可能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将相关研究推进一步,或一大步。
以铁的生产为例,若单纯考察生产规模,仅能说明量的问题,而并不能充分说明冶铁工业所达到的水平。能够充分证明冶铁工业水平的是,冶铁技术的工艺,尤其是这种工艺知识的变化过程及其传播方式。如果工艺知识仅仅是某个或某些工匠的经验积累所得,限于工场师徒的口耳传承,乃至即使形诸文字却并无理论推导证明过程而仅仅是经验记录,都表明该工艺水平属于“发现的创造”层次,仍然是一种量的累积的结果,它的传播范围和传承能力有着先天的局限,是一种私密知识,一旦相关的人和事出现断层,它也就随之消失。以这种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工艺,并不能形成生产力的质变。换句话讲,知识的变化层次,很大程度影响乃至决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层次。在这个角度上,知识是一种生产力。
因此,讨论一个时代各层次知识的形式、内容、概念、累积、选择与被选择,描述与被描述,以及传播与传播方式的过程,可由此探索社会各具体组成部分的变迁过程,以及这种变迁与知识的关联程度,并由此而上,探索知识变迁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形态变迁。
从知识史出发,重新审视社会变迁(包括社会形态),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