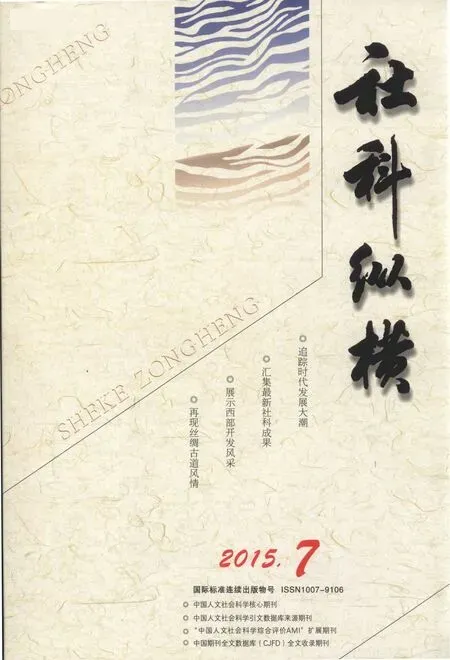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的独特贡献
2015-04-09周明军
周明军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科系 河南 郑州 450015)
英国当代政治思想家奥克肖特已经越来越受到中西方学界的重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其政治思想的研究业已日趋深入。在笔者看来,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的贡献并不在于对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批判,因为进入20世纪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已经逐渐成了西方学界的主流,而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来说,20世纪最突出的成就便是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批判。在这方面,伯林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学者是通过批判自由主义内部的理性主义来调适自由主义内部矛盾的;保守主义学者约翰·凯克斯从保守主义的角度论证了价值多元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列奥·施特劳斯则认为近代政治哲学之所以存在弊病就在于从根本上没有对“哲学”进行反思;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对异化问题的关注上;罗蒂等后现代主义学者则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理性主义的解构之上,即后现代主义要超越启蒙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力图从一种新的视角构建起新的政治理想。
相比之下,奥克肖特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批判无疑是最深刻的,但关键是通过对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批判,奥克肖特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观——“追求暗示的政治观”,这是一种和理性主义政治观相对的政治理解范式。而这一点也正是当下学界还未完全认识到的。
一、中西方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张汝伦等人的努力下,不到十年中国已将奥克肖特的主要著作几乎全部翻译出版,但是从整体来看,汉语学术界对奥克肖特的研究依然处于介绍和解读的阶段。而在西方学界奥克肖特的遭遇也差不多,他生前很少被人关注,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奥克肖特研究在西方进入了一个高潮,平均每隔一年至少有一本专著问世,但是较深入的从整体上来把握其政治思想的研究依然不多,大体上解读性的研究仍然占很大比例。总的来看,目前中西方学界对于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研究最大的争议有两点,第一,关于奥克肖特的学派归属,即所谓的“贴标签”研究;第二,奥克肖特的政治思想是否前后一致。其实,这两点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即对奥克肖特做“标签化”的解读,要么将其归为自由主义,要么将其看作保守主义,或者将其归属为自由至上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最终会认为出现了“两个奥克肖特”。而中西方学界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研究存在的两大问题是:第一,整体把握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的研究还未出现;第二,中西学界都未能重视他提出的“政治是追求暗示”的洞见。
二、追求暗示的政治观——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替代范式
在对理性主义政治观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后,奥克肖特提出,政治活动“既不是从瞬间的欲望中产生,也不是从一般的原则产生,而是从现存的人们自己的行为传统中产生。因为它不能采取其他形式,因此它所采取的形式,是通过探讨和追求在这些传统中暗示的东西对现存的安排所做的改进。……在政治上,每件事情都是作为结果发生的事情,都是追求,但不是追求梦想或一般原则,而是追求一种暗示(the pursuit of an intimation)。”[1]奥克肖特的这番极具启发性的话可以总结为:“政治乃是追求暗示”,也可以认为,奥克肖特提出了一种和主流的理性主义政治观相对应的政治理解范式——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在奥克肖特的启发下,可以将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不同阶段的政治观进行一种新的解释:首先,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政治观都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观;其次,这种理性主义的政治观表现为从“追求至善的政治”到“追求功利的政治”的演进。这就是说,古希腊阶段伦理的或者自然的政治观可以归结为“追求至善的政治”,理性主义政治观在此时已奠定了根基;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可以总结为“追求神性的政治”,此时的政治观是带有理性主义色彩的;近代以来的政治观则表现为从“追求权利的政治(权利政治观)”到“追求功利的政治(功利主义的政治观)”之间的论证范式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未改变其普遍理性主义的特质。而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的独特贡献是,通过对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批判提出了一种“追求暗示的政治观”。
那么该怎样理解这种“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呢?首先,本文以为,奥克肖特对政治的理解所达致的一个理论上的高度就是“追求暗示的政治”,同时这种“追求暗示的政治”乃是一种介于经验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政治或者理性主义的政治之间的中间状态。即奥克肖特认为,政治既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下,也不能只眷顾未来,还应该追求传统中的暗示,但奥克肖特的传统绝非本质主义的,而是一种现实的生活状态,因此政治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达到了一种融贯性的理解。另外,追求暗示就要不断地与传统开展对话,在这种对话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因此奥克肖特提倡的“对话的政治”和“追求暗示的政治”是同一种意义之上的,也因此奥克肖特关于历史哲学和教育哲学的思想是和他的政治哲学紧密相联系的。
其次,“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在关于政治理解上的启示。总的来讲,学界对于政治概念的界定是处于事实和价值之间的,而“追求暗示的政治观”之对于政治的理解不仅兼顾了这种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倾向,而且它还能跳出这种倾向来分析政治问题。具体来说,“追求暗示的政治观”充分认识到了政治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以及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的非科学性或者哲学属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避免一种全然理性主义的思路;在政治的行为方式上,这种政治观拒斥那种暴力和支配的统治,从而提倡对话与说服的政治手段;而在现实的立场上,这种政治观坚持一种中庸的原则。因此,“追求暗示的政治观”的启示在于:政治的复杂性和偶然性意味着对政治不能做极端化、简单化以及规律化的处理,而中庸主义的政治立场则意味着在政治的选择上必须克服教条主义的倾向。
三、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政治观
作为一种哲学和认识论,在关于知识的本性和如何获得知识这两个问题上,理性主义是这样来解答的:首先,知识的标准是理性,而不是启示或权威,因此真正的知识是由全称和必然的判断所组成的;其次,在知识的起源上,真正的知识不能来自感官知觉和经验,而必然在思想或理性中有其基础,或者说,真理是理性天然所有或理性固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或先验的;最后,理性的演绎法是获得普遍必然知识的途径或方法。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理性主义的这些指标能否和政治相结合,或者说,政治知识的标准是理性吗?真正的政治知识都是全称和必然的判断吗?政治知识是天赋的吗?通过演绎的推理方法能够获得政治知识吗?奥克肖特告诉我们:“政治当然并不知道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在政治的世界中,所有一切都源于人类活动,尽管其中有许多结果并非出自人类的计划。就人类活动而言,用必然性和有效性这类语言都是不合适的。”[2]
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政治观,徐大同先生认为,按照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为标准,大体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政治观,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以及近、现代的权利政治观三个时期。[3]但是,不同政治观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不同阶段中人们认识和理解政治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恰恰相反,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却有着近乎一以贯之的理解政治的基本思想方法或思维模式——理性主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思想史不同阶段中的政治观又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理性主义的。
这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肇始于苏格拉底,一般认为古希腊有系统的政治思想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这是由于苏格拉底开始把希腊人对于自然的研究转向了对于人类社会的关注,但是研究对象的转变并未带来新的研究方法。苏格拉底直接把希腊人探究自然现象时所采取的基本思想方法挪用到了关注人类社会上,这就是理性和逻辑的方法。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能够在人类社会中找到和自然领域中一样的某种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且这种方法成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为后世所继承。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即使上帝也必须遵循逻辑规则;到了近代,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与自然法思想结合成了普遍理性主义的论证体系,这一论证体系从某种被假定的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论而得出包括秩序、权利和义务、平等和自由等一系列的政治范畴,以及由这些范畴所构成的一系列严密的理论体系。或者说,这些政治观都是从某个抽象的普遍前提出发,通过演绎的方法推理出某种超越时空的价值标准和制度模式。在古希腊,柏拉图是从抽象的善的理念推理出了理想国;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们是从抽象的上帝出发推理出了神权政治;在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则从抽象的人性法则即自然法出发,推理出了以保护权利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理想。
具体来看,古希腊阶段,在“理念论”上的柏拉图的政治观,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伦理的理性主义;在一种发展意义上的“自然观”或本性论上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的理性主义。中世纪阶段,奥古斯丁的政治观集中体现在其国家观上,而且他重新阐释了西塞罗的共和国定义,这使得他的“双城论”便带有了理性的色彩;阿奎那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或人性论思想,在认识论上阿奎那将理性和信仰平等对待,因此他的政治观便带有理性主义的色彩,可以说,中世纪的政治观孕育了近代理性主义的政治。在近代,权利政治观体现为建立在一种不证自明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自然法论证体系,这是一种典型的普遍理性主义,因为它不仅是自然权利还是自然义务的根基;而所谓的社会契约则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理论,把国家的成立看成是来自人的理性设计,这是对政治问题的简单化;到了功利主义政治观那里,边沁的哲学激进主义的功利原则回应了刚刚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改革的需要,因此其指导现实改革的倾向很明显,因此其学说带有明显的建构理性主义色彩。密尔对边沁的修正主要是否弃了其功利主义中的利己主义倾向,他的论述更为精致,但是他的政治观却依然是理性主义的。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密尔依然深信功利主义能够为法律以及其他政治制度提供一个规范性的理论,这样其政治观就不仅是边沁建构理性主义的继续,甚至还带有了普遍主义的色彩;其次,密尔把个人的选择原则扩展到社会,即他认为功利是可以计算与合成的,这样密尔的功利主义其实也不恰当地将科学方法引入了伦理学之中,并且他又将这样的功利观引入了对政治问题的分析,因此是犯了理性主义的错误。总之,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政治观都是理性主义的。
四、理性主义的困境——用知识论解决价值问题的历史难题
首先,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思路是对政治现象的简单化。亚里士多德曾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所谓科学显然是对开始原因的知识的取得。”[4]而到了近代西方,在罗蒂看来,知识论则成了第一哲学,这种哲学自欺欺人地认为,它可以超越历史环境找到人类知识的基本必要条件。[5]知识论的逻辑是,依靠追求必然的知识就能得到关于客观规律的客观真理,这样的思路比较适合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但却不适合社会生活领域,因为复杂的社会生活根本难以做到客观而科学的分析,这源于人本身的复杂性。这正如赵汀阳所分析的,“依靠理性而获得普遍真理,这是知识论的伟大梦想,可是偏偏不合道理的是,理性其实并不能保证找到真理,至少是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真理……在生活问题上由普遍理性达不到普遍真理,这一荒谬的事实如此不合道理,却又如此真实。”[6]这样的理论随着知识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化,而逐渐也将必然会走进一条死胡同,因为政治现象日趋复杂,而理性主义的政治观对政治的认识所运用的知识却日趋“专业化”,复杂的政治对上简单的知识,这是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死结。这就是说,理性主义政治观在方法上总是用其他领域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来理解和解决政治领域的问题,并一再声称能够找到解决政治问题的一劳永逸的途径,进而最终推广一种所谓“普世价值”的模式和方案。理解政治必须从政治本身出发,正视政治现实,然而理性主义政治观恰是对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不足,这样的思路其实是对政治的简单化。
其次,在奥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的做法属于混淆或文不对题,他认为,科学领域的“技术知识”和政治领域的“实践知识”完全是两回事,而理性主义的政治观的做法是用技术知识抹掉了实践知识,妄图以之来解决政治问题。这就是说,政治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领域,而政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在于它不止是事实领域,因为政治要解决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的不同的需要,因此政治更是一个存在价值判断的领域,这使得在学科属性上存在有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之分,“政治科学可以从任何政治事实出发去研究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政治哲学只能从现实中需要没能满足的那些真正的问题出发。”[7]因此将政治做全然的科学化处理就是不恰当的,而这正是理性主义政治观的做法。
再次,从根本上讲,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思路是混淆了事实和价值问题。关于理性,周德伟先生有一种很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如以逻辑代表理,价值判断代表性,已大致无误,分别为知识及行动之源泉。”[8]也就是说,所谓“理”乃是逻辑推理,它只是知识的起点,只能使人具备局部的知识,而所谓的“性”乃是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它是行动的起点,因此,由“理”并不一定能达到“性”。不难发现,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休谟怀疑论的。理性主义用技术知识抹掉实践知识的作法,不客气地说不仅是对知识的简单化,在政治上还犯了由“理”一定能达到“性”的错误,因此,从根本上讲,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思路是混淆了事实和价值问题。
关于政治的知识,谢尔登·沃林也有一番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政治智慧和政治科学是政治知识的两种形式。政治科学有简洁、可操作和前后关系相对独立的特性,而“政治智慧是个不幸的用语,因为……问题不在于它是什么,而是在于它存在于什么之中。历史,关于制度的知识和法律分析(是与之相关的)……也可以加上关于过去的政治理论的知识。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这个知识的混合型展示了同科学型的对比。它的活动模式与其说是探索风格的,还不如说是反思风格的。它认真留心逻辑,但对经验的不连贯和矛盾对立则更为留心。出于同样的理由,它对严密性并不信赖。政治生活把它的重要性让位给精炼而又不难理解的假设,因此关于它的有意义的陈述经常不得不是隐喻的和暗指的。前后关系变得极端重要,因为行为和事件发生时没有其他背景。所以,这种类型的知识倾向于暗指性和启发性,而不是清晰性和确定性。”[9]而通过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奥克肖特则提出了“政治是追求暗示”的洞见。这种“暗示”的观点和沃林所强调的“暗指性”的政治知识其实是相似的,这其实意味着政治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并没有契合性,或者说,理解属于哲学的或者智慧的政治知识需要探索其他的方法。
[1]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new and expanded edition,pp.56-57.
[2]Michael Oakeshott.The Politics of Faith and the Politics of Scepticism.ed.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Full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0.
[3]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第一卷,总序,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
[4]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M].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1-32.
[5]参见[美]理查德·罗蒂.李幼蒸译.哲学和自然之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5.
[7]马德普.政治生活中的应然逻辑——政治哲学中的立论基础与方法论初探[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32.
[8]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75.
[9]转引自[美]理查德J·伯恩斯坦.郭小平等译.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