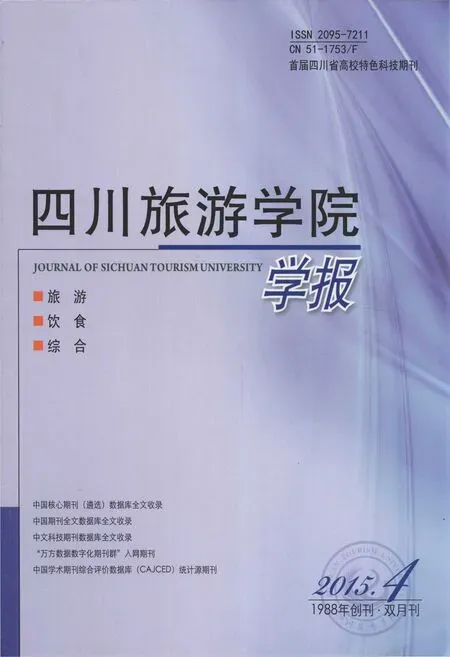清代四川美洲粮食作物的传种及对饮食产生的影响※
2015-04-04王胜鹏
王胜鹏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明清时期,以玉米、番薯、马铃薯为代表的美洲农作物大量传入中国,伴随着四川农业大规模垦殖的步伐进入四川并得到了广泛的种植。长期以来,关于美洲作物传入四川的路径及传播问题已有何炳棣、蓝勇、郭声波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本文在综合诸多研究基础上,一方面阐述清代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传入四川的主要内、外因以及传种情况,另一方面也将着重对清代玉米、番薯、马铃薯入川在民众日常饮食生活中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1 清代美洲粮食作物传入四川的主要外因与内因
1.1 外因——明清时期美洲作物大规模传入中国
中国的明清时期也正是欧洲人航海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随着美洲大陆与欧亚大陆之间的连通,一些美洲作物也以各种方式传播全球,其中也包括中国。不仅有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粮食作物,而且还有花生、辣椒、南瓜、烟草、向日葵等经济作物。它们来到中国后,逐渐被中国农民所接受,并成为了重要的农作物品种,延续至今。四川尽管是中国的内陆省份,但是农业开发拥有悠久的历史,借助于南方丝绸之路、长江水道等交流通道,众多美洲农作物品种通过移民、商人、传教士等群体传入四川,并在四川扎根发芽。
1.2 内因——四川人口的不断膨胀
明末清初,由于连年战争等因素,四川曾出现过严重的人口短缺问题。根据清代官方文献记载,顺治十八年四川人丁数仅为16 000丁。至康熙年间,随着战争结束、垦荒政策的推进,来自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移民纷纷入川,使四川人口激增。乾隆五十一年四川丁数已达8 429 000丁,到道光二十年,更是达到了38 338 000丁。[1]9据梁方仲统计,至清末光绪年间,整个四川总人口已达八千多万人,远超周边省份。[2]266-267人口的膨胀使得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在此背景下,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先后传入四川,成为民众重要的粮食作物,缓解了四川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民食紧张问题,并对民众日常饮食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清代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在四川的广泛传种
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美洲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马铃薯三种,并先后在四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种植。
2.1 玉米
明中后期,玉米从“西番”传入我国,在史料中又被称为“玉蜀黍、御麦、玉麦、包谷、包谷豆、天方粟”等,大约在明末清初时传入四川。《女聊斋志异》《续客窗闲话》中均写到明末四川著名女将秦良玉曾带领当地民众种植“芋粟”(包谷),以解民食不足。四川种植玉米最早的方志记载见于康熙二十五年的《筠连县志》。至乾隆年间,方志记载的玉米种植范围更为广泛,且多集中于盆地周边山区,如珙县、屏山、威远、江安、巴县、灌县、广元等。嘉庆、道光年间,玉米的种植则已遍及四川大部分地区,且在四川盆地平原地区也有种植。嘉庆《郫县志》卷4中就记载当时郫县民间不仅有玉米种植,而且还将其作为“篱寨”使用。在川西北、川西南地区,玉米也逐渐在中山以下取代了青稞、小麦、荞麦等原有主粮的地位。至晚清、民国,玉米已经成为四川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清代对于玉米种植的方式方法也已有所总结。乾隆年间由张宗法所著,反映四川农业发展情况的《三农纪》一书便详细介绍了“御麦”的种植,“植宜山土,三月点种,每棵须三尺许,种二三粒,苗出六七寸,耨其草,去其苗弱者,留壮者一株。三月莳,八九月获。获归苞以本架,透风令干。宜在室中闭户塞窗敲之,不致耗溅,再晒干收储。”[3]207可见,当时在玉米种植方法、收储方式等方面都已有所总结,该书也对四川玉米的种植起到了一定的推广、传播作用。
2.2 番薯
番薯,又称红薯、苕、番苕、甘薯等,源自于中美、南美地区,明末时从东南亚传入我国,大约乾隆年间传入四川。“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4]640,逐渐“栽种遍野”。四川番薯主要跟随两广、闽赣、湖广地区的移民而入川。[5]170在方志中亦能找到相关证据,如乾隆《潼川府志》中就写到当时潼川府里有很多来自闽粤的移民,且喜欢食用红薯,当地人食之甚少。到嘉庆年间,种植食用范围已扩大至土著居民,“薯蓣……先是资民由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6]247。随着民众对于番薯接受程度的加深,番薯在四川盆地及周边许多厅县得到广泛传种,包括黔江、屏山、江北厅、仁寿、内江、忠州、乐至、蓬溪、荣县、大宁、奉节、铜梁、德阳等地,涵盖了除川西山区之外的大部分地区,而灾荒成为番薯大范围扩展的重要契机。道光年间,绥定、保宁、顺庆、潼川四府十四州厅县发生了严重的夏旱秋涝灾害,“各处山田山地粒米无收……民间缺粮,即将所种大小麦、豌蚕两豆及一切日用菜蔬连根食尽,嗣后草木树皮,靡有过遗”[7]116,而番薯产量高、耐干旱、抗虫害等特性使其成为了极佳的“救荒作物”,在四川得到迅速推广。番薯的种植方法也已十分成熟,《三农纪》载番薯“宜高土沙地……耕宜岁前,壅宜大粪,春分后下种。……重耕,起要极深……每穴相去七八尺,横二三尺……凡栽须顺栽,若倒栽则难生。”[3]251可见,当时人们在番薯种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成为番薯广泛传种的重要基础。
2.3 马铃薯
马铃薯又被称为洋芋、阳芋等,原产自南美洲的热带高原地带。1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引入四川的时间相对较晚,据道光二十四年《城口厅志》记载,在1807、1808年前后当地才有马铃薯种植,并被贫民当作食物。马铃薯起初主要在北方各地种植,后来跟随江淮移民进入川、鄂、陕一带的巴山老林区。如嘉庆十七年《江油县志》记载的“羊芋”种植区域就在四川东北部与陕甘交界的地区。嘉庆以后,马铃薯开始沿盆周山区传播,向南传入盆东山区,向西传入龙门山区、邛崃山区,咸丰年间又传入凉山彝区。[5]173得益于马铃薯“宜高寒之地”的特性,至清末民初,马铃薯更向西传播到了川西乃至川西北高山深谷半农半牧区,弥补了番薯和玉米无法在高寒山区种植的不足。
3 清代玉米、番薯、马铃薯入川对民众日常饮食生活的影响
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传入四川,对民众的日常饮食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粮食结构、饮食品种类以及经济作物、禽畜养殖等多个方面。
3.1 玉米、番薯、马铃薯在民间主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何炳棣认为,16世纪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的传入,对我国农业生产累积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粮食革命”[8]。长期以来,四川民众日常主粮多以稻米为主,但是四川多岭谷高山,很多地区并不适合稻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外来物种则弥补了这一空缺,满足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逐渐成为四川民众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个别地区甚至取代了稻麦的传统主粮地位。严如熤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记述了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交界地区玉米、马铃薯等作物的种植和食用情况:“山内溪沟两岸及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间亦种大小二麦,山顶老林之旁,包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苦荞、燕麦、洋芋。……包谷米作馍、作面、作干饭与稻米同,初熟时日包谷棒,穷民连包煮食,或摘子炒食……山民言包谷米耐饥胜于甜饭也。”[9]1031-1032可见,这些地区的山民对于玉米的依赖程度已经超过稻米,食用方式也十分多样,包括煮食、作馍、作面、作干饭或摘子炒食。在道光二十三年《石柱厅志》中更是直截了当地写到当地深山只有玉米可种,贫民皆以玉米为粮,很少食用稻米。至清末,英国人阿绮波德·立德游历四川各地,也多次记述玉米在四川各地的种植、加工以及食用的情景,书中写到在一个小康之家,烤玉米都经常作为招待客人的食品;农民们在没有烤玉米吃的时候,则把玉米面做成“饽饽”。[10]92,105可见,玉米在当时社会各个阶层日常主粮饮食中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食用十分广泛。
除了玉米,番薯和马铃薯同样在四川民众的主食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包谷、洋芋、红薯三种……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也”[4]640。尤其是番薯,作为一种高产作物,被称为“救荒第一物”,“红薯……生熟皆可食,荒旱之年民间种之,可为救荒之备。”[11]492随着四川人口的逐渐增多,番薯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甚至成为“与稻并重”的粮食作物。然而,尽管玉米、番薯、马铃薯的种植满足了民众对于粮食的需求,但是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民众日常饮食的粗糙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
3.2 丰富了民间日常酒类饮品
玉米、番薯传入四川以后,除了作为重要民食之外,还被广泛应用于酿酒,丰富了民众的饮品生活。《三农纪》中就已写到玉米“粒可果,可酿酒”[3]207,在四川多地方志中也都记载了利用玉米酿酒的情况,如嘉庆二十三年《邛州直隶州志》载:“酒之家酿者,有常酒、甜酒、大麦烧酒、包谷烧酒。”[12]91“包谷烧酒”即用玉米酿制的酒,烈度较高,价格低廉,在民间酒类中的地位相对较低,“膏(高)粱为上,玉麦(俗名包谷)为下”[12]134。尽管玉米酒在口感上逊于高粱酒、糯米酒,但由于一些山区广泛的种植玉米,玉米逐渐上升为当地酿酒的主要原料,如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山内无糯谷,则用包米蒸酒。包米难化,采草药作曲,药性最烈,和蒸米七日成酒,名曰七日红,饮少辄醉,癫狂迷性,往往搬刀弄杖。”[9]1032价格低廉的包谷酒满足了普通民众对于酒类饮品数量上的需求。玉米酒广受欢迎,逐渐成为了多地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产品,带来丰厚利润。秀山“县人……煮包菰实为酒,所在为恒业,岁利可数千金”。[13]135玉米酿酒一直影响至今,如酿制“五粮液”的重要原料之一便是玉米,各种作坊自酿“包谷酒”至今还在市场上被广为销售。除玉米外,番薯同样可以酿酒。明代王象晋《群芳谱》就已经写到番薯不仅可以生食、蒸食、煮食、煨食,作粥饭,而且可以酿酒。番薯传入四川后,番薯酒也被民众所接受,在仁寿等地县志中亦有所记载。可以说,玉米酒、番薯酒不仅满足了民众对于酒的多元需求,而且也成为了四川酒文化的重要载体。
3.3 丰富了民间日常菜点种类
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四川后,被加工成了多种食品,丰富了民众的饮食生活。据文献记载,四川民间多是将玉米磨成粉之后做成馍、饼等食品。至清末,玉米或玉米粉已开始成为四川各地部分特色食品中的主要原料。如《成都通览》所列食品中便有“玉麦饽饽、玉米馍馍、玉米花糖、猪油米花玉麦糖”等,是成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食品。在四川一些山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玉米相关特色食品更加多样。张秀熟(1895—1994)在其散文《包谷》中回忆了四川玉米的多种加工食用方式,“大概经过祖先辈长期摸索,发明了‘搅团’、‘拌汤’两种稀饭和一种叫做‘麨麨饭’的干饭。”所谓搅团,即趁锅底水开,徐徐撒包谷面,用棒回旋搅转,搅到浓缩成团,舀来浸入各种菜汤,边吃边喝;拌汤则是趁锅底水开,撇下用温水拌好的包谷面团粒,和蔬菜或豆花之类同煮。“麨麨饭”也就是包谷干饭,锅底水开时,倾面微煮,扎气孔,待到半熟,用竹筷徐徐抄拌,抄成细小团粒,然后蒸熟。如果煮时搀和少量大米则被称为“鲤鱼穿沙”,食时拌和米饭则被称为“金裹银”。此外,其文中还提到了其他多种玉米食品,如玉米珍珍、包谷面馒头、包谷面花卷、包谷面糕饼、包谷面醪糟、包谷面裹红糖汤圆、炒玉米花以及城市里的粑馍、嫩海椒炒嫩包谷等,种类十分丰富。[14]
番薯、马铃薯在四川民间也被加工成了多种食品。番薯在四川多被制成番薯粉,可以和大米、小米等混合一起煮粥,可以作干粮、作饼。据《成都通览》记载,在清末成都的“戏园内之点心糖食品”中有“白糖红苕饼”,以供民众在戏园中食用。明清时期也有番薯入馔的记载,在《成都通览》所列“席上菜目”中便有一款叫“苕泥”的甜菜肴。番薯叶也被认为“可作蔬”,至今四川民间仍有烹制“苕尖”的菜品。马铃薯同样可被晒干磨粉,做饼馍等食品,除此之外,马铃薯也已经开始被民众用于馔肴,“洋芋……土人赖以为粮,邻县贫民来就食者尤众,以之入馔或渍为粉均佳。”[15]55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马铃薯亦被制成“洋芋糍粑”等特色食品,并传承至今。
3.4 间接促进了经济作物种植以及禽畜养殖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四川玉米、番薯、马铃薯的种植间接促进了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为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清中后期,随着玉米等高产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缓解了因人口膨胀而激化的人地矛盾,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从而腾出了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用于种植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如花生、甘蔗、各种蔬菜、茶叶等,进一步丰富了民众的日常饮食生活。玉米等美洲粮食作物的引种也间接促进了四川禽畜养殖业的发展,使民众日常饮食生活中的肉食品种类不断增多。玉米、番薯、马铃薯都可以用作饲料喂养禽畜,且效果极佳。如玉米对于牲畜来说,不管是籽粒还是茎叶都是产热、产脂肪的优质饲料。在清代四川方志中多次提到包谷可“饲猪”,养猪不仅可以用于烹饪,满足民众对肉食的需要,而且还可“卖之客贩或赶赴市集”,换取其他生活资料。番薯的茎叶同样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是牲畜的高效饲料。《三农纪》中就写到番薯的蔓可以饲牛、马,根可以用于养猪。各种经济作物以及禽畜的养殖也成为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川菜发展、定型的重要基础。
4 结语
玉米、番薯、马铃薯在清代先后传入四川,不仅使四川民间粮食结构发生转变,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民众日常饮食品种类,为川菜、川点发展提供了更为充足多元的食材来源。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尽管已经摆脱了粮食紧缺的状态,但是在人口不断增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种植与食用玉米、番薯、马铃薯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陈树平.明清农业史资料(1368—1911)第1册[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张宗法.三农纪校释[M].邹介正,等,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4]杨德坤,曾秀翘,等.光绪奉节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5]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6]何衮,等.光绪资州直隶州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7]王梦庚,寇宗.道光重庆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8]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三)[J].世界农业,1979(6):25-31.
[9]严如熤.严如熤集3[M].长沙:岳麓书社,2013.
[10]阿绮波德·立德.蓝衫国度——英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M].钱峰,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11]富珠朗阿,宋煊,黄云衢.道光江北厅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12]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3]王寿松,李稽勋,等.光绪秀山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14]张秀熟.包谷[J].四川文学,1962(2):39 -41.
[15]高维岳,魏远猷,等.光绪大宁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