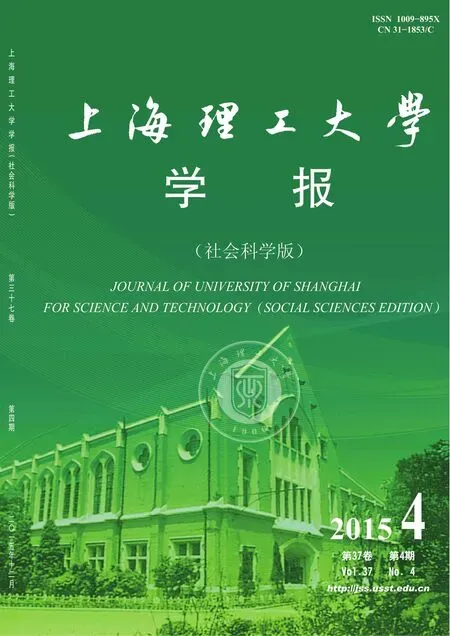纠缠于抛弃与回归的“家园”书写——流散视阈中评卡里尔·菲利普斯的《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
2015-04-02张建萍
张建萍
(中国民航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61)

纠缠于抛弃与回归的“家园”书写
——流散视阈中评卡里尔·菲利普斯的《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
张建萍
(中国民航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61)
摘要:卡里尔·菲利普斯《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虽在题目、人物性别和内容上不尽相同,但从流散视阈中看二者堪称“家园”书写的“连环册”。《最后的通道》中雷拉的流散方向是从“移出国家园”到“移入国家园”,随之又指向“移出国家园”。《一个国家的独立》中弗朗西斯则从“移入国家园”到“移出国家园”,随之又指向“移入国家园”。二人迁徙方向首尾链接后呈现出“连环册”式的“家园”书写特点。通过其菲利普斯思考了流散群族的命运问题。同时他还就英殖民统治的特点和英国加勒比黑人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双重书写;流散视阈;移出国家园;移入国家园
作为同时代非裔乃至所有流散作家中最知名、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天赋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卡里尔·菲利普斯,几乎他所有的作品,从最初的《最后的通道》(TheFinalPassage)、《一个国家的独立》(AStateofIndependence)、《远岸》(ADistantShore)、《剑桥》(Cambridge)、(HigherGround)、《渡河》(CrossingtheRiver)和《欧洲部落》(TheEuropeanTribe),乃至到进入新世纪后他创作的《他乡者》(Foreigners)、《在黑暗中跳舞》(DancingintheDark)、《大西洋之声》(TheAtlanticSound)、《一种新的世界秩序》(ANewWorldOrder)和《将我定义成英国》(ColorMeEnglish)等均展示了其对于“家园”问题的深刻思索,而在这些作品中,以流散群族“错位”经历为基石的《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尤其展示了菲利普斯对流散视阈中家园问题的独特见解。
一、流散视阈中“家园”书写的连环册
《最后的通道》出版于1985年,是菲利普斯的首部小说。这部作品讲述了加勒比未名小岛上的年轻女性雷拉(Leila)在母亲前往英国治病后,决定与丈夫迈克(Michael)、儿子凯文(Calvin)一起移民英国的故事。但在到达英国后她遭遇了母亲去世、被迈克抛弃等变故,生活窘迫的雷拉不得不跟儿子住在伦敦一所被废弃的旧宅里。小说的结尾,怀有身孕的雷拉烧掉了关于伦敦的一切信件和纸张,并渴望能重新回加勒比与朋友米莉(Millie)呆在一起。米莉是雷拉的好友,雷拉曾设法说服她与自己一起前往英国,但米莉坚持留在了加勒比,原因是只有在加勒比她才有自己受欢迎的感觉。在《最后的通道》出版后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86年,菲利普斯推出了第二部小说《一个国家的独立》,这部小说中他采用了与《最后的通道》相逆的路径来叙述,39岁的伯特伦·弗朗西斯(Bertram Francis)同样出生于加勒比的一座无名小岛上,19岁时获得英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后,毅然抛弃了女友佩西·阿其巴尔德(Patsy Archibald)到了伦敦。在英国他先是学习法律,两年后因成绩不佳放弃了学习,之后靠打零工在英国一直过着潦倒的生活。在英国期间他跟家人断绝了联系。二十年后,在获悉小岛即将独立的消息后,弗朗西斯准备以商人的身份重返小岛,希望这场家园回归能结束长期以来的“错位”生活,但却发现曾经熟悉的小岛不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得疏离且冷漠。小说的结尾部分他不得不返回英国,继续“错位”生活。从表面上看,《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在题目、人物性别和内容上截然不同,但仔细研读不难发现二者堪称“家园”书写的“连环册”。
“连环册”式特点首先体现为两位主人公“循环”式的迁徙方向。《最后的通道》中的雷拉流散经历是从“移出国家园”到“移入国家园”,随之又指向“移出国家园”的过程。《一个国家的独立》中弗朗西斯则是从“移入国家园”到“移出国家园”,随之又指向了“移入国家园”。如将二人迁徙方向首尾链接起来则如同在讲述同一故事的“连环册”。其次“连环册”式特点还体现在“循环”式流散意义中。《最后的通道》开始部分雷拉离开加勒比前往英国,但最后又渴望回归加勒比,这是关于流散群族离开“移出国家园”后悲惨经历的写照。《一个国家的独立》中弗朗西斯回到加勒比之后遭遇了疏离和冷漠从而不得不返回英国,这是关于流散群族在回归“移出国家园”后尴尬生活的记录。这两部小说暗示了一种“循环”式的流散本质,即流散群族一旦离开了“移出国家园”,到达“移入国家园”后的“错位”生活使他们心头时刻萦绕着对“移出国家园”的回归梦想,但因其背负的“移入国家园”异质文化烙印,使得其必然不会被“移出国家园”再接受,因此不得不离开。流散群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不断的家园“循环”迁徙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特定生存空间,既不再渴望回归“移出国家园”,也不再渴望完全被“移入国家园”同化,而是凭借着熟悉“移出国家园”和“移入国家园”两种文化的优势,不断地“循环”往复于“移出国家园”和“移入国家园”之间,三者之间构成一种互不可分、全新和平等的关系。这也是当代流散学者如加比·谢夫(Gabriel Sheffer)、罗宾·科恩(Robin Cohen)、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等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流散群族的重要理论内容。很显然因受时代局限,菲利普斯并未在这两部小说中提出现代流散群族的生存模式,但他已经敏锐地感知到这种家园“循环”的流散经历之于流散群族的意义,这已实属难得。
除上述提到的能够体现《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连环册”式“循环”特征外,还有许多特征的存在证明这两部作品可以被视为同一个系列。如二者均有开放式的结尾,《最后的通道》由五部分构成,最后一章题目为“冬天”,记录了雷拉在经历母亲去世和被丈夫遗弃后的绝望。从逻辑上讲,冬天象征着死亡与毁灭,但在四季的轮回中它又同新生息息相关,同时雷拉还收到了一张匿名圣诞贺卡,贺卡代表了祝福,而圣诞节又代表了新生,因为圣诞节原本是古老的异教徒庆祝冬至的活动,借以欢迎冬天之后自然的新生。更重要的是雷拉的怀孕也同样代表了希望。而雷拉为回归到加勒比做准备时烧光所有能够唤起英国记忆的物品时,发现“房间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看起来干净多了”[1]200。大火一般被视为宗教仪式般的净化。无论是冬日、圣诞节、怀孕还有大火都暗示了新生与循环,小说中诸如此类描述很多,读者也不禁开始构想雷拉回归加勒比后的新生活,当然这也为菲利普斯第二部小说打下了基础。《一个国家的独立》的结尾同样也是开放式的,弗朗西斯坐在返回英国的轮船上思索着“如何利用自己的平庸之才在英国生存下来”[2]157,这将读者带到英国背景中。这种所共享的自由开放式的结尾赋予了“家园”无穷的想象空间。此外两位主人公还共享了一些特征。雷拉自始自终被定位为一个被放逐、流亡的人物,即使在加勒比她也是孤独的,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也感觉“像一个看客”[1]50。她作为黑人女性与英国白人男子的私生子,因肤色较浅,被认为是“白人女孩”的她一直受到小岛上黑人的排斥[1]47,而在前往英国的船上,她自己也因肤色上的优越性不屑跟其他黑人待在一起而同样受到排斥。而与此对应的是《一个国家的独立》整部小说也笼罩着孤独的色彩,评论家认为弗朗西斯回归家园后又无奈离开的行为是对传统以乐观主义为特征的回归小说的颠覆[3]40,充满着压抑与悲伤。在其出版后不久,安德鲁·萨尔基(Andrew Salkey)最先敏锐地注意到其中的悲观主义色彩,并写道“在我看来,这是部非常、甚至异常的小说”[4]145。马里奥·里奇(Mario Relich)则认为小说“有着一股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式的惊悚片的寒意……颠覆了对家园所有的期望”[3]53。
可见,虽然《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在出版时间、题目、人物性别和内容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它们堪称流散视阈中“家园”书写的连环册,对此菲利普斯曾说过,“他们是经历了无数次改变的相同的故事,我的责任是讲故事,这让我无法停下来”[5]83。在这一组连环册中,“家园”书写经历了多重变形,而这正是二者所折射出的菲利普斯流散思想的最大亮点。
二、流散视阈中“家园”的多重书写
(一)“移出国家园”的多重书写
无论是雷拉还是弗朗西斯,他们的“移出国家园”都是“加勒比”。在连环册中,两位主人公所经历的“加勒比家园”的顺序依次是抛弃-渴望回归-抛弃。
《最后的通道》中,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加勒比地区往往以肤色深浅决定黑人地位,因此肤色较浅的雷拉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但她的母亲很少提及白人父亲的情况,缺席的父亲代表了充满优越性的英国。雷拉后来前往英国表面上看是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但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对英国生活的向往。这暗示了殖民地人们总是被“移入国”所吸引,认为前往“移入国”就能改变被统治的命运并过上优越的生活。这与当时英国殖民统治方式密不可分。为维护英国种族的优越性,英国常常把本土美化成崇高、富有、神圣的“母亲”,而殖民地人民则是期待着被其教化的子女。而前往英国也被美化成为回归母亲的怀抱,并能够获得母亲的保护。雷拉代表了在这种殖民宣传下来到英国的加勒比黑人,他们在英国的遭遇却大失所望。以雷拉为例,她不顾母亲的反对,与懒散、好斗且没有责任心的迈克结婚,婚后不久儿子凯文出生,而夫妻二人的关系也降至冰点。雷拉期望英国之旅能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婚姻,逃离生活的困境。因此她携夫带子前往英国。她对“加勒比家园”决然抛弃,如在英国下船时决定将过去的一切都抛之脑后,而迈克走出轮船后甚至没有回头看。《一个国家的独立》中,弗兰西斯在英国居住的二十年间中断了跟加勒比家人的所有联系,此外这部小说中还有一位极度渴望离开“加勒比家园”的人物,就是弗兰西斯前女友佩西的儿子里维斯顿(Livingstone),手上常年带着着日本表,“浑身散发着美国著名黑人演员的气质”[2]101。他极度渴望离开加勒比,因为“这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2]103。
《最后的通道》的结尾部分,雷拉强烈地渴望回归“加勒比家园”。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结尾,因为在之后的《一个国家的独立》中,弗朗西斯实现了雷拉的渴望,回归了加勒比家园,但很快又离开了家园。但与雷拉不同的是,雷拉对“加勒比家园”的抛弃是单向的,而“加勒比家园”是这种抛弃行为被动接受者,甚至还借米莉之口阻止雷拉的离开。而弗朗西斯对“加勒比家园”的抛弃是双向的,即在他抛弃“加勒比家园”的同时,“加勒比家园”也抛弃了他。
小说中关于“加勒比家园”抛弃弗朗西斯的场景描述很多。如当他回到“加勒比家园”时,发现小岛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仅没有找到归属感,甚至还被看作陌生人、闯入者和背叛者。卧床不起的母亲甚至明确表示不希望他回来,他唯一的兄弟多米卡(Dominica)早年已死于交通事故肇事托车,而曾经帮助他获得奖学金的老师法瑟尔·丹尼尔斯(Father Daniels)也已去世,原本上学时颇有天赋的板球运动员,也是他曾经的好友杰克森·克莱顿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贪婪自私的政客,并且拒绝资助弗朗西斯的事业,还不断地到处宣讲散布美国是加勒比地区救世主的思想,在他狂热的“向前冲,绝不向后看”中的口号中[2]101,小岛完全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牺牲品。但小岛虽然在经济和外部环境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舒适,有了机场,市场上涌现了许多新品牌,但物质改变只是表面的,其社会结构依然如旧,“人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穷……挣扎在饮食的边缘,缺水也没有照明”[2]19,“人们还跟之前的奴隶一样”[2]212,“现在他们自由了,但还像没有希望和理想的那些被判刑的人一样”[2]18,“岛上,打字机不能正常使用……酒吧二十四小时关门,根本不营业,路面也还是破旧的”[2]131。此外一场大火烧了岛上的图书馆,图书馆有着保存历史的功能,在他被毁后取代的是覆盖全岛的、循环播放美国观价值的电视网络。在弗朗西斯眼里,“独立”成为一场充满欺骗性质的表演,其本质不过是将对加勒比的统治从英国传给美国而已。但同时弗朗西斯也有很多变化,如他的家园回归行为实际上也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他希望凭借独立事件在岛上获取经济利益。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其家园回归注定成为凄凉的旅程。
以雷拉和弗朗西斯为代表的流散群族所经历的“加勒比家园”的顺序依次是抛弃-渴望回归-抛弃。雷拉对“移出国家园”先是抛弃,后渴望回归,这是流散群族在家园迁徙中常见的经历和心态。他们因经济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但在“移入国家园”所经历的种种不如意使他们时刻怀抱着回归的梦想,但回归依然是艰难的,《一个国家的独立》弗朗西斯的回归遭遇便是得力的例证,因为一旦流散群族离开“移入国家园”,双方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均会背负许多不同以往的异质性,也因此他们注定无法回归。正如同《最后的通道》中祖父曾对迈克所说过的“一旦离开,孩子,就跟我们不一样了……再也回不来了”[2]42。而佐证这一观点的还有从加勒比走向世界的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他在《流亡的乐趣》(ThePleasuresofExile)中同样认为“家园”回归是场充满创伤的经历,相比之下,流散群族还不如呆在“移入国家园”[6]47,回归是不必要的。
(二)“移入国家园”的多重书写
菲利普斯对“移入国家园”也进行了多重的书写,但其书写顺序发生了很大改变,依次为渴望回归-抛弃-渴望回归。
《最后的通道》中,雷拉对“移入国家园”英国曾充满幻想,但在英国的遭遇并不理想。如雷拉和迈克到伦敦后住在肮脏的公寓里,因为空间狭小,雷拉不得不睡在卫生间里,而迈克则不得不与西印度房东伊尔(Earl)头挨着脚挤在一张床上,就像贩奴运动中奴隶们在船上的遭遇一样。第二天早晨起床后,迈克“凝视着远方,看着亮光黯淡下去”[1]153。当雷拉意识到没有足够钱偿还欠邻居的一小笔钱时,她非常窘迫,“就像亮光暗淡下去一样,她内心也变得黑暗起来”[1]183。再如雷拉在前往伦敦的火车上发现“这里的房间、街道、汽车似乎永远都在不断地向前运动”[1]144,这让她倍感压力。同时英国缺乏加勒比所有的团结传统,“在加勒比,如果一颗树倒下,其他树木会支撑着它不让它倒下”[1]97,缺乏同类的依靠使雷拉更加孤独。这些都暗示着流散群族在“移入国家园”英国独立地位的丧失,但这也是早期英国加勒比移民最真实的生活写照。雷拉居住的房子“楼上两扇窗户玻璃都是破的……电灯是坏的,房子里漆黑一片,有股被抛弃的味道”[1]161。在一定程度上,房屋代表着居住者,其摇摇欲坠表明居住者悲惨的生活。在加勒比英国文学中像雷拉一样的女性很多,如简·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SargassoSea)中的安东尼奈特(Antoinette)和《简爱》(JaneEyre)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均反映了黑人移民在英国遭受了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
“移入国家园”由最初被流散群族渴望到最后被抛弃的命运在《最后的通道》的结尾表现得淋漓尽致。雷拉在英国变得越来越沉默,她的沉默也是黑人历史在英国社会中的命运写照。尽管黑人在英国的历史根据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但为了保持白人种族的纯洁性,英国主流文化将所有有色群族刻意地忽视,其态度如同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写的“英国如同一个因为受到了邻居异质性的威胁而内心充满了憎恨”[7]151。20世纪后期之后,在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学者努力下,当代英国黑人文化中掀起了恢复英国主流历史中黑人地位的浪潮。而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无疑是对这一浪潮的积极回应。
《一个国家的独立》中虽然并没有太多关于弗朗西斯在英国生活的记录,但他却自信自己在英国的生活经历会赋予他独特的优越感,可以帮助他在重返加勒比后建立一番事业,且这项事业使得他将不再依赖于白人,同时还可以让他结束流浪的生活。但小说最后他离开了“加勒比家园”重回英国“移入国家园”,而“加勒比家园”成为一个没有必要回去的地方,至此他“家园回归”之旅成为一场幻灭的创伤之旅。
在这两部小说组成的连环册中,菲利普斯对流散视阈中的家园问题的思考是,流散群族经历了对“移出国家园”抛弃,到渴望回归,再到回归后遗憾离开不得不重返“移入国家园”的过程。虽然因受时代背景的限制,菲利普斯并没有探究流散群族“家园”迁徙的根源。但这两部作品所折射的流散意义已完全超越了时代,即暗示流散的意义在于,流散群族从离开“移出国家园”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背负了与“移出国家园”人们相异的成分而注定了即使回归后也无法被其完全接纳。同时对“移入国家园”来说,流散群族因与“移出国家园”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生理的、或文化的),同样会被永久地排斥在“移入国家园”之外,也注定无法完全融入其中,所以流散群族最终将如同雷拉或弗朗西斯那样始终呈现出“孤独”的状态,他们的理想命运是不再期待回归“移出国家园”,或完全被“移入国家园”接纳,而是应凭着其熟识两种文化的优势,循环往复于“移出国家园”和“移入国家园”之间,借以保持三者之间的平等共生。
三、错位人生:流散视阈中“家园”书写的背景研究
“家园”书写虽然被公认为是加勒比裔流散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常见的创作主题之一,但其实在很长时间内这是他曾一度非常避讳的词汇,造成这种回避的原因首先是因其不断“错位”的家园迁徙经历。菲利普斯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加勒比的圣基茨岛上,在3个月大时他就跟随父母一起移民到英国北部约克郡,居住于白人工人阶级集聚区利兹,随之接受了整套的英式教育,并进入牛津大学求学。尽管如此,他依然强烈地觉得自己处于英国社会的边缘位置,“与所有英国非白人的小孩一样,我的整个人生都在踮起脚跟,谨慎的生活”[3]3。随着上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大规模抵制黑人种族运动的爆发,加勒比裔流散群族在英国生存变得异常艰难。1978年,菲利普斯动身前往美国,在美国阅读了在英国尚未解禁,被视为非法作品的大量非裔美国文学后眼界大开,并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二十年,且取得绿卡,美国堪称菲利普斯的另一个家园,但他并不完全认同“美国家园”,甚至拒绝外界将自己像对待纳博科夫那样贴上“美国作家”的标签。相比“英国家园”和“美国家园”这两个“移入国家园”,菲利普斯对其“移出国家园”“加勒比家园”也是疏离的,直到1980年他才在母亲的陪伴下首次返回圣基茨岛,此后他不停地在栖息地——英国与美国——之间穿梭[8]18,而这种多重家园的迁徙经历使他始终无法确定自己“家园”归属。而如果从菲利普斯家庭背景上分析他对于“家园”的回避,也能找到蛛丝马迹,他曾写道“我最初对于‘家园’的疏离感是从童年居住在利兹时就有了,利兹是个典型的英国地区,那里的工人阶级家庭往往都有庞大的家族,每个人都有父母、祖父祖母等很多亲戚。而我只有父母和兄弟姐妹,仅此而已。利兹……让我感到紧张”[9]17。8岁时菲利普斯父母的离异更加重了他对于家园的疏离感,之后因独立抚养他长大的母亲身患重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兄弟不得不离开母亲在英国北部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而在14岁到18岁之间,他离开了母亲,单独与父亲居住在一起。因此对长期变迁居住地区,加之缺乏完整家庭的菲利普斯而言,“家园”曾一度成为他极力回避的词汇。
但这种“家园”缺失又不断驱使着菲利普斯不断寻找自我身份的归属,因此“家园”又成为其文学创作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但这也折射出他对“家园”复杂的情感渴望。但他在“家园”上的困境也是所有流散群族面临的问题,这种被“移入国家园”和“移出国家园”双重拒绝的局面使得他们在“家园”问题上产生了永久性的错位,而这种“错位”的人生也铸就了他们对“家园”问题的深刻思考。
四、结束语
《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并未涉及重大历史事件,而是通过聚焦小人物的命运来审视纠缠于抛弃与回归的“家园”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菲利普斯的个人自传,是在描述作者心中对家园归属的复杂情感。迪克特·乐登特(Benedicte Ledent)等学者曾公开声称这些作品是菲利普斯真实生活的文字再现。可以说家园“错位”的人生赋予了他困惑,但是同时也给予了他丰富的创作素材,成就了其文学流散大师的地位。从上世纪80年代起,英国加勒比文学中涌现出了许多对“家园”归属感进行探索的作品,如琼·瑞蕾(Joan Riley)1985年的《无归属感》(TheUnbelonging)、V.S.奈保尔(V.S.Naipaul)1987年的《抵达之谜》(TheEnigmaofArrival)、提摩西·莫(Timothy Mo)1982年的《酸甜》(SourSweet)等。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作家往往都如同菲利普斯一样成长于两种或多重文化之间,其经历的共同特点是“中间性”和“错位”。但值得一提的是菲利普斯是同时代英国加勒比作家中最知名、最有天赋的一位。
参考文献:
[1]Phillips C.The Final Passage[M].London:Faber and Faber,1985.
[2]Phillips C.A State of Independence[M].London:Faber and Faber,1986.
[3]Ledent B.Caryl Phillips[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
[4]Salkey A.Review of Phillips[J].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7,(61):139-167.
[5]Tuomi P.Prize-winning Novelist and Barnard Professor of Migration and Social Order,Caryl Phillips,Leads an International Life of Writing,Academics and Screenwriting[J].Barnard Campus News, 2002,(26):79-125.
[6]Lamming G.The Pleasure of Exile[M].London:Michael Joseph,1960.
[7]Gilroy P.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M].London:Routledge,2002.
[8]李永梅,赵素华.卡里尔·菲利普斯作品中的“渡河”现象透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2(11).
[9]Schatterman R T.Conversations with Caryl Phillips[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9.
(编辑: 朱渭波)
Home Abandonment and Return on Caryl Phillips’sTheFinalPassageandAStateofIndependencein Diaspora PerspectiveZhang Jian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161,China)
Abstract:InTheFinalPassageandAStateofIndependencewhich differ greatly in titles,genders and contents,Caryl Phillips present them as serial stories sharing some circul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home writing.From Diaspora perspective,Phillips focuses on the two migration routes.As to “country emigrated”,the sequence is “abandon-return-abandon”.As to “country immigrated”,the sequence is“return-abandon-return”.At the same time,these two novels also reflect characteristics of England colonial system and the social status of Caribbean Diaspora groups in English dominant history.
Keywords:home;multiple interpretation;diaspora perspective;country emigrated;country immigrated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5.04.008
中图分类号:H 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5)04-0340-05
作者简介:张建萍(1978-),副教授。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E-mail:hellosonsy@aliyun.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5203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民航大学专项(ZXH2012F009)
收稿日期:2014-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