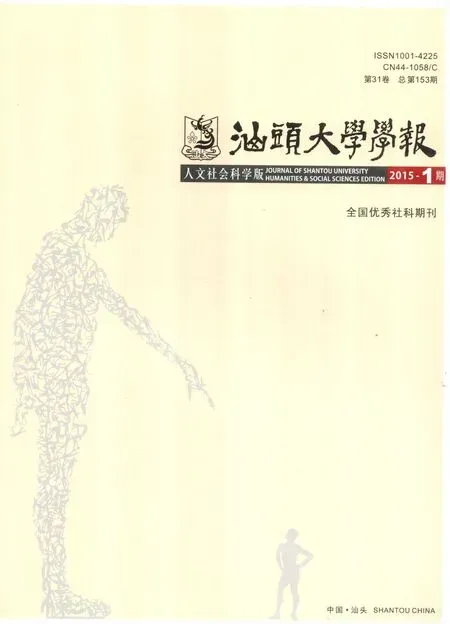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妻”题材作品的主题流变
2015-04-02赵丹
赵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妻”题材作品的主题流变
赵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发端,形成了关注下层平民、关注夫权压迫下的女性的优秀传统,因此中国现代文学30年出现了许多以“典妻”现象为题材的作品,社会现实和文学思潮的变化使这些作品存在对精神悲剧的呈现、对阶级压迫的批判、关注民生、对战争环境下小人物的荒诞命运的同情等不同的主题意蕴,呈现出比较鲜明的流变过程。
现代文学;“典妻”;主题流变
“典妻”现象古已有之,指丈夫将妻子在一定时期内典当、租借给别人。据学者考证,“典妻”“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特别是浙江境内,如宁波、金华、舟山、绍兴、平阳、永嘉、湖州、永康、余姚等地,此外福建、江西、甘肃、辽宁和山西等地也为多发区”[1]。它们反映了封建社会贫富差距大、重男轻女现象普遍的事实。典妻者多因为生活所迫,将妻子典出以换取生活之资。承典者多为没有子嗣承袭香火的上层平民,他们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焦虑中“借”妻生子。在封建社会无后为大的精神压力下,“典妻”制度满足了一部分人延续子嗣的需要,满足了另一部分人维持生活的需要。
“典妻”现象是夫权社会的产物,它反映了封建意识形态下,人们对传续香火的重视和对家庭中的女性的漠视。妻子在家庭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成员,“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为其对于丈夫的附属性质,是丈夫的“财产”,而像其他一般财产一样荒谬地具有了流通性质,从而消解了人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被典的女性也必然在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服膺和现实生活中必然面对的感情痛苦中苦苦挣扎,不断用意识形态消解着自我。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发端,以启蒙和人的发现为主题,形成了关注下层贫民、关注夫权压迫下的妇女的优良传统,“卖妻”、“典妻”的现象因此也在多个角度被关注。这其中产生过较大影响并得到广泛关注的是许杰的《赌徒吉顺》(1925年)、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1930年)、罗淑《生人妻》(1936年)三篇小说。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如台静农的《蚯蚓们》(1927年)、《负伤者》(1927年)、潘漠华的《冷泉岩》(1929年)、含沙的《租妻》(1935年)、路翎的《卸煤台下》(1941年)等未得到足够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后面提到的这些作品大多被认为其艺术水平较为一般而受到忽视,但是将所有这些“典妻”题材的作品历时地进行考察,却可以发现“典妻”这一题材在现代文学的不同时期呈现出来的主题意蕴的流变。
一、《赌徒吉顺》:对封建陋俗的批判和对精神悲剧的呈现
《赌徒吉顺》是在鲁迅影响下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于1925年写于上海,是寓居上海的浙江天台人许杰在现代眼光透视下对自己家乡浙江的传统风俗反思和批判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赌徒吉顺》中,赌徒吉顺因为家庭丰裕,所以对财产的观念非常淡薄,以至于走上了赌博之路,终至于把家产挥霍一空,妻儿也因此生活困苦。沉迷赌博的吉顺有时也会深刻地反省自己,却只能想到继续赌博以翻本,并对此抱有希望,因此在文辅先生劝他典妻时,他是不屑一顾的。但是不幸他又一次赌输,他在消沉中看到妻儿的惨境,受到极大的冲击,大半为了不让妻儿饿死,当然也抱着解脱自己的愿望,他把妻子典了出去。但是典妻所得大大小于他的希望,也不能应他的急需,因此在失望的冲击下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忏悔和自责。
作为现代文学初期最早涉及“典妻”题材的小说,《赌徒吉顺》和现代文学中其他时期出现的其他“典妻”题材的小说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同样是因为贫穷而典妻,吉顺却不是因为天灾人祸而致贫,就像后来大部分“典妻”题材的小说表现的那样。相反,吉顺一开始是一个“占有他父亲的财产,又禀有一身的好手艺,对于经济的收入,感得十分轻易而丰裕”[2]494的伶俐的泥水匠,他是因为游手好闲的个人原因而致贫的。由此,《赌徒吉顺》表现的重心不在于吉顺的贫困,却在于吉顺典妻前后的心路历程,从他典妻前因为自己沉迷赌博无力抚养妻女的自责到“典妻”过程中的狂妄自大到“典妻”后的失望后悔,作家寄希望于他的自我批判和觉醒。
因此,在《赌徒吉顺》中,作家的主要创作意图是批判封建陋俗,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隐疾,他看到了吉顺的愚昧,并且寄希望于他的觉醒,也就是希望以“吉顺”为代表的“典妻”的实施者的觉醒,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摆脱游手好闲的生活,摆脱蒙昧、麻痹的精神状态,行动起来改变这种生活。笔者认为作家的这种创作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的真实性,在读《赌徒吉顺》的时候,我们能明显觉察到吉顺这个人物内在其实有两个并不完全和谐的人格存在:一方面身为泥水匠、赌徒的游手好闲、及时行乐而且不负责任的吉顺的存在;另一方面不断自我批判,看到妻儿的可怜和自己的可鄙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存在。之所以说吉顺身上有“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存在是因为:一是他对自我的批判和反思明显从“人”的起点开始,而远远超越了农村社会中一个“社会人”可以到达的高度,这在和《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有对妻子的“被典”的可惜而绝无对自我反思的皮贩丈夫的对比中更为明显;二是吉顺在自我反思中使用的许多词语如“慰藉”“亵渎”“向上帝忏悔”[2]519明显是知识青年的雅性的语言,和吉顺的身份极为不称,这其实是第一点的外在表现。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许杰是将自己对女性的观感和思考掺入到了吉顺的忏悔里,这实现了作家批判封建陋俗和唤醒麻木精神的创作意图,却破坏了人物的历史真实性。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有作家所处的时代语境对作家的影响。面对民族救亡的任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尝试了器物、制度、革命方面的变革而都归于失败,封建主义沉珂难起,因此李泽厚先生在《启蒙的走向(1989)》中评价五四说,“经过戊戌、辛亥之后,五四主要人物把重点放在启蒙文化上,认为只有革新文化,打倒旧道德旧文学,才能救中国”[3],精神的启蒙成为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的写作宗旨。作为从浙东来到上海的乡土作家,接受了“五四”人的思想启蒙的许杰急欲用新获得的思想资源反思自己家乡的封建陋俗,并寄希望于大众的觉醒,如樊骏先生所说,“当时的乡土文学虽然有的也写到了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的阴影,除了正面描绘军阀混战酿成的祸害外,这些方面的内容一般都相当模糊淡薄;用浓墨重彩渲染的,大多是广大农民思想意识上所承受的封建主义毒害,小生产方式带来的重重禁锢,以及由此造成的缺乏民主主义觉悟的精神悲剧”[4],这也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所说的乡土作家的“乡愁”[5]。
二、《为奴隶的母亲》、《蚯蚓们》等:对阶级压迫的批判
随着五四的落潮、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任务的日益紧迫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阶级斗争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方向。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曾指出,在五四时期的个体的反抗和群体理想的现实构建失败后,面对国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性急的年轻人一般很难满足于‘多研究些问题’和点滴改良,何况这种研究和主张改良并没带来多少成效,于是求‘根本解决’——进行阶级斗争便自然地成了更富有吸引力的方向。”[6]对底层人的关注尤其是阶级斗争的描写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成为文学的最强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尤其助长了这种氛围,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没落,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描写广大的贫民生活,等等。只有这样才是大众的,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必须取用的题材”[7]。如樊骏先生所说,20年代末期后文学创作出现了“从着眼于思想启蒙转向注重社会剖析和农村阶级斗争动向的变化”[4]。
受阶级文学主潮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妻”题材的作品在这一阶段也有相当一部分加重了社会批判的力度,在对下层人民被迫典妻的描写中着力进行对阶级压迫的批判,在这方面的作品有台静农的《蚯蚓们》(1927年)、《负伤者》(1927年),杨邨人的《租妻官司》(1929年),潘漠华的《冷泉岩》(1929年),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1930年),含沙的《租妻》(1935年),施瑛的《棉裤》(1936年)以及路翎的《卸煤台下》(1941年),其中以《为奴隶的母亲》影响最大。
《为奴隶的母亲》是左翼作家柔石于1930年创作的小说。它以春宝娘在被“典”前后的生活为线索贯穿起整个故事。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春宝的“她”因为家庭生活陷入窘境被丈夫黄胖典给正在物色妇女为自己延续子嗣的秀才。在秀才的家里,一方面,春宝娘忍受着像仆人一样繁重的劳务和秀才大妻的旁敲侧击的疑忌;另一方面,秀才对她是极尽体贴的,并不仅仅是只把她当作一个生育的工具。所以在生下秋宝后她萌生了一点小小的希望,比较优裕的环境和对秋宝的不舍让她不想离开秀才家,而想着把自己的春宝接过来一起生活。可是她的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觉察到她的威胁的大妻当然不会允许她的存在,而她对春宝的惦念也被秀才认为是对自己的辜负,因此她终于又一次难逃与幼子的分离。更残酷的是,拖着病体回到破旧的家,迎接她的不是丈夫儿子的热情,而是丈夫的冷嘲热讽,“你真在大人底家里生活过了”[8]245,还有春宝的陌生与隔膜。做出了极大牺牲的她,最后得到的却是母亲权利的被剥夺和两个家庭的怀疑与排斥。
《为奴隶的母亲》是以沉默的母亲形象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发出的最深沉的控诉。在小说中,“她”似乎总是默默的,像一个痛苦的、挣扎却又压抑着的剪影。作者的这个处理明显强化了读者对“她”的痛苦的感受。“她”的不幸归根结底是因为阶级的差距,阶级的差距使“她”不得不两次面临与子生离的悲剧。“她”的不幸还来自于丈夫对她的冷漠,可是这冷漠归根结底也来自于阶级的压迫。“她”的丈夫黄胖本来是个勤劳而能干的皮贩和农户,“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而他也渐渐“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8]224。虽然作品没有描写,但是我们能从“变做”二字看出黄胖原来也是个比较老实而温顺至少没那么暴躁的的农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却使他成为一个又穷又凶的病鬼,并因此对她没有任何温情。
也许有人认为作者笔下的秀才是温情脉脉的,不能说代表了阶级的迫害,笔者并不认同。在《解读〈为奴隶的母亲〉并兼与〈生人妻〉比较》一文中,蓝棣之先生认为秀才地主有富于人性、通情达理的一面,并认为这形成了《为奴隶的母亲》的潜在结构:“贫农少妇在被典情况下,与地主秀才在感情上的安抚与留恋”,但是蓝棣之先生并没有推翻显在结构“奴隶母亲屈辱的非人的悲剧故事”所体现的小说“暴露阶级压迫与掠夺的罪恶”的主题,只是认为显在结构和潜在结构的互相冲突使作品的内涵更为丰富[9]。笔者认为,在这里,秀才虽然对春宝娘表现了一定的温情,但还是他决定了春宝娘苦难命运的延续。他因为春宝娘思念春宝而怀疑她只恋着旧家而可以一改温情把她驱逐,一方面是受着男权意识的支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因社会地位而产生的优越性和支配性。因此,必须认清,秀才的温情只是作者不愿意为了迎合时代观念使人物脸谱化的表现,是使人物真实丰满的技术要求,而不是意味着作者放弃了对贫富差距、阶级压迫的批判。
董炳月先生在《台静农乡土小说论》中将台静农的乡土小说按照不同的内容分为三种,其中《蚯蚓们》和《负伤者》属于从“社会历史层面”“对羊镇人的生存状态作了生动形象展示”的一类,此外还有“文化风俗层面”和“人性层面”[10]。笔者十分认同。发表于1927年的两篇小说《蚯蚓们》和《负伤者》在和“典妻”题材类似的“卖妻”题材中明显寄寓了对于阶级压迫的批判。《蚯蚓们》写李小因为贫穷卖妻的故事,题目“蚯蚓们”便寓意了贫民生命的无足轻重,真如蝼蚁一般,可以让地主予取予夺。故事一开始便突出了“有钱的田主”和“穷人”的极端对立,穷人们因为天灾以及田主的剥削而终于由勉强度日到无法支撑,因此他们向田主借贷,反而被当作乱民被维护田主利益的当局抓走;反讽的是,田主们还在埋怨“穷人们不修好,累得他们的仓里少收成”[11]93。台静农以极端反讽的手法强化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指出地主的剥削是农民无法度日的重要原因。李小不堪面对典妻的事实,却终于在忿恨中认识到“命运的责罚”“不在有钱的田主绅商,却在最忠实的穷人”[11]95,李小最终对命运的坦然接受更凸显了农民面对阶级差距和剥夺的无奈,由此更加深了作者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批判。《负伤者》叙述了吴大郎被强迫将自己的妻子卖给有钱有势的张二爷的故事,以“吴大郎”谐音“武大郎”,暗示了在强权面前穷人的无能为力。
发表于1929年的《租妻官司》是一出以“典妻”为题材的颇具诙谐色彩的讽刺喜剧。它讲述了因“典妻”而发生的一场奇怪的官司:农民李四25年前因被地主催逼谷租而将妻子陈氏租给小商人张三,现因25年期满,张三要将陈氏送还李四并按约索要两百块钱。但是李四现在仍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款项,他因此而拒绝索回妻子,却遭到因破产急需用钱的张三的拒绝,张三因此将李四告上法庭,但是颇具人情的法官却无法依据冷酷的法律给两人一个简单的决断,而陷入两难的境地。《租妻官司》反映了阶级压迫下普遍的民生凋敝,不仅农民李四因地主的剥削而典妻财尽失、走投无路,连本来宽裕的商人张三也因为来自于统治阶级的“人灾人祸”[12]而难以生存。作者由此表现了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阶级压迫的批判,设置“党国旗”和“总理遗像和遗嘱”[12]高悬在法庭的上方,尤其讽刺了当局的腐朽无能和对“平均地权”的民生愿望的背叛。作者杨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3],太阳社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国较早主张革命文学的作家之一,因此在《租妻官司》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阶级差距造成的民生凋敝的敏锐观察和对阶级压迫的峻急批判。
相比于其他“典妻”题材的作品,潘漠华的《冷泉岩》(1929年)因发生在离县城较远的山峡中所以多了一些浪漫的山野气息,虽然也表现了阶级压迫下穷人的不幸命运,可是因为穷人的抗争和穷人之间浪漫而不受世俗拘缚的爱情而使作品较少下层阶级的苦大仇深之态,而多了些浪漫绮丽的色彩。《冷泉岩》中卖妻典妻的故事发生在拐手和拐手的妻身上:拐手的妻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她的前夫是一个无能而懦弱的泥水匠,不满于此,婚后不久她就与前夫的伙计私奔到了冷泉岩,无奈这个伙计是一个偷鸡摸狗之辈,后因偷盗之事败露而脱逃,因此女人和拐手走在了一起。但是拐手租种玉蜀黍的生意渐渐支撑不下去,因此拐手将其卖给了陈姓富翁为后妻,但是她并不十分愿意,后来便逃脱回来。拐手被迫将其送还前夫,但是由于女人的执拗,最终前夫还是将其典给了拐手,两人最终走在了一起。女人被卖两次,一次是卖给陈姓富翁,一次是典给拐手,但是后者是女人自愿的并且只是给既成事实一个形式上的允许,所以不在我们论述范围之内。真正给两人造成痛苦的是第一次卖妻,陈姓富翁之所以要买拐手的妻并且在拐手的妻逃脱之后带人打伤了拐手,是因为当初拐手因为地租的事冲撞了陈家,结下了矛盾。作者寥寥几笔写出了陈姓富翁的阴险、凶恶和冷酷无情,这正对应了作品中“我”的感慨,“这个沉默到死了的大地,冷酷地负着人类,阶级分化了,对峙了,争斗了;几番的更迭,直到最后的阶级对峙的现代;现时在我面前被解剖着”[14]。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3年加入“左联”,潘漠华的《冷泉岩》表现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动态,对农民生存境遇的关注和对阶级压迫的批判是其思想的核心,但是对浪漫爱情的描写和对被压抑的人性的同情使《冷泉岩》更富于文学色彩。
左翼作家王志之以笔名含沙发表的《租妻》(1935年)以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回忆了穷苦人春生哥和春生嫂的故事。春生哥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户家庭,因此从小便经常被欺负,好不容易熬到娶妻生子,但是再也难以靠农事维持下去的春生哥只能面临妻子被觊觎而且被迫租给油盐铺掌柜刘大爷的命运。小说极力渲染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差距,农人之子春生哥即使上过学仍难以摆脱世世代代在田租和天灾的压迫下贫穷的命运,相比之下出生在较有根基的书生世家的“我”虽然做官无望却还可以在油盐店做个学徒,何况穷人春生哥和富人刘大爷之间的差距了。《租妻》通过春生哥的不幸命运表达了对阶级压迫下穷人不幸命运的同情。紧接着《租妻》发表的《棉裤》(1936年)写了一对因水灾逃难异乡的阿德因难以活命而被迫卖妻的故事,虽然最终阿德也没有忍心卖掉妻子,但是买妻的财主和阿德之间简短的对峙已然将阶级的差距及其对穷人的磨难表现得淋漓尽致。
时间到了1941年,路翎的《卸煤台下》可以说是发出了“典妻”“卖妻”题材的小说之阶级反抗的最强音,在这部作品里,代替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这部小说里,路翎延续了他一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写作特点,人物精神上的兴奋和疾苦被大大地放大了。在内容上,这部小说和左拉的《萌芽》有相似之处,同样是在阴暗压抑的煤矿,同样是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的重重剥削以及他们之间尖锐的冲突,甚至《卸煤台下》中工人们的精神领袖孙其银和《萌芽》中的工人领袖艾蒂安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同样从远方来,带着对工人的同情和工人们一起度过苦难的日子,并且为了民族解放、工农解放的信念最后继续向远方流浪。许小东也是一个《萌芽》中樊尚·马厄一样的贫苦的工人,他在家庭、病痛、繁重的工作、稀薄的工资的重重重压下最终倒下了,卖妻只不过是压在这个可怜人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并不愿意卖妻,可是知道妻子在自己身边再也生存不下去,妻子改嫁之后,病弱而疯狂的许小东也被逐出了矿区。
以上作品大多出自左翼作家手笔,时代的潮流使这些作家在关注下层人的苦难生活时多从阶级压迫方面寻找穷人不幸命运的根源,并在创作中寄寓了对阶级压迫的批判和反抗。
三、《生人妻》:对艰难时世下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注
受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一些非左翼作家也逐渐将创作重心放在底层人民的不幸命运上,注重深化作品的社会内涵,不同的是,他们注重的不是对于阶级差距的分析和表现,而是从社会民生的角度对穷人的不幸命运进行思索和表现。
《生人妻》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生人妻》是罗淑于1936年创作的反映“卖妻”现象的小说。在《生人妻》中,罗淑首先生动刻画了一对卖草的夫妇“像两匹极度饥饿的兽”[15]2蠕动着的困苦的生活,为了突出他们的极度困苦像两颗微尘,作者甚至都没给他们名字,只是称为“他”和“她”。无奈中,丈夫将妻子卖给胡大。可是妻子因为在和胡大成亲的酒席上失手打破了杯碟而被胡大愤急之下诬她为“扫把星”。极度委屈的“她”又经了酒醉的小叔小胡的骚扰,刺激之下匆忙出走,却在黑夜中陷在坚硬、凹凸不平的石场。清醒过来的她担心因为自己出走丈夫被连累,在天明时便赶快挣扎回去探看情况,却发现丈夫已经因为被怀疑“撞骗”[15]20被保甲抓走了。
《生人妻》将夫妻作为整体,用两人的情感将两人维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权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割裂与隔膜,而将重心放在表现他们在对困苦、冷漠的生活的共同面对和承担。《生人妻》中的丈夫仍旧有很强的男权意识,体现在他平日里在气躁时会对妻子动手,以至于他一生气妻子就害怕得“拖着腿”[15]8往外走;他甚至在生气时拿起一块灶砖就向妻子头上招呼。但是他对妻子又不是完全无情的,在因为卖妻受到妻子指责时他并不是像《为奴隶的母亲》中的丈夫黄胖一样不耐烦地出门,而是在对贫困的痛恨和迷茫中懊恼不已,和妻子一样痛苦着;更体现他的无奈和有情的是他赎回了妻子多年使用的簪子,重要的不是簪子本身,而是他体谅将要离家的妻子的孤独的心情,希望有一件旧时的东西伴着她。而妻子对丈夫更是有情,她看到被赎回的簪子激动不已,“她说着就走过来伸手去接,但马上她的手又落下去了”[15]9,她知道簪子对她毕竟只是精神上的安慰,而对丈夫却可以是生存之资,“银簪是一柄锋利的剑,给他们划开了心的隔膜,就在那裂缝中涌出淳朴的真诚的感情”[15]9。妻子的有情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惹人注意的细节上:她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孤独漂泊了还关心地提醒“当家的”他的汗衣晾在桑树上,对琐事的关注和当时肃穆悲伤的场景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一句“当家的”体现了她对丈夫的关心和依恋;她在受到胡大的斥责委屈不已时,首先想到的是丈夫,想到如果他知道自己这么痛苦,穷死也不会让自己过来的;她在惊悸中慌忙逃跑,在石场被划得遍体鳞伤,清醒过来马上想到的却是自己逃跑会不会已经连累了丈夫。在这里,妻子和丈夫不再是彼此冷漠的,而是被困苦的生活拴在一起的两只“兽”,即使分开了心还是在一起。
笔者认为《生人妻》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独特的特点,除了时代环境的影响,也是罗淑以困苦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对他们的同情为创作中心的集中体现。罗淑的其他作品如《橘子》、《刘嫂》、《井工》也是以生活在下层社会中的贫民为创作中心的,这和罗淑的成长环境有关,家庭环境相对优越的罗淑幼时起“每日看到的是熬盐工人的非人生活和农村濒临破产的景象,盐工和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刺激着世弥幼小的心灵”[16],人道主义情怀和生活的刺激使罗淑经常要为困苦的劳动人民代言。因此,在《生人妻》中,表现重心不在男权对女性的压迫,贫富的差距也没有得到渲染,而是艰难的时代下小人物生活的困苦和生活的无情,以及他们的无奈,“我犯了什么王法,我该受这活罪?”[14]8
四、《别人的故事》:战争的时代环境对小人物命运的无情拨弄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文学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一大批作家在创作中表达对战争前途、民族命运的忧虑,表现战争生活中小人物的命运,靳以是其中之一,《别人的故事》是“典妻”题材在战争背景下的发展。
在《别人的故事》中,女人的丈夫由于战争去参军了,久等不归的女人和婆婆为了以后的生活便将自家的长工入赘了夫婿,生活本也可以这么平静地继续下去,可是突然间前线的丈夫回来了。面对丈夫、长工、女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他们的生活表面上还是很平静,但是其实下面却潜流涌动。为了不造成新的麻烦,丈夫和长工决定将妻子卖给第三个人,也就是城里油粿铺的老板。似乎事情就这么简单平静地解决了,但是离别时妻子和婆婆突然的相拥而泣让我们知道这其中的人正在经历强烈的心灵上的磨折,“像是预备告辞了,他们都站起来,这时那两个女人才像触到了些什么突然抱在一起了,——只是抱着,并没有哭;可是等他们松开手的时候,我望到四只泪汪汪的眼睛”[17]。
因为荒谬的命运,刚刚出征归来的丈夫就要把亲爱的妻子假手他人,而妻子无疑是这里面最大的受害者。战争召唤走了自己的丈夫,为了生活,她已经屈就自己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在注重贞节的那个年代,我们可以想象无疑她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心理折磨的,不然不会事后在水边默默地哭泣。可是命运就是如此荒谬,在她内心已经慢慢平静之后,出征的丈夫居然回来了,而她就要被卖给另一个陌生的男人,何况这是一个自私冷漠的男人——他对别人的苦难是冷漠的,满心只带着胜利者的喜悦来享受这场嗜血的盛宴——我们可以想象女人在以后的生活将要忍受怎样的磨折。
小说取名《别人的故事》,可是这恰恰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战争的环境下人人都要面对的荒谬离奇的生活。和以往“典妻”题材的小说或者从精神启蒙,或者从阶级、民生的角度对穷苦人的生活深入开掘不同,出现在1942年的小说《别人的故事》放逐了精神、贫穷、阶级等这一切的一切,而是表现出了战争环境下人的荒谬的命运,是战争的大环境对小人物命运的无情拨弄。
以《别人的故事》为收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典妻”题材就此匆匆收尾。“典妻”题材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解读下呈现出不同的主题意蕴,这只是就作品呈现出的最主要的思想内容而言,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妻”题材作品从主题意蕴上进行分类只是为了从总体上对其作理性把握,稍有不慎也许会将作品割裂或者简单化。事实上,有一些情感趋向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笔下同样明显的,比如对备受压迫的女性的同情以及对夫权压迫的批判,这是我们在解读“典妻”题材的作品时应该注意的。典妻、卖妻现象由于法制的完善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但是它以其他形式如“借腹生子”等存在着,这些现象反映了在现代社会女性还处于依附性地位,这些作品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1]徐海燕.略论中国古代典妻婚俗及其产生根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北京大学,等.短篇小说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3]李泽厚.启蒙的走向(1989)[J].华文文学,2010(5).
[4]樊骏.论罗淑——兼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若干轨迹[J].齐鲁学刊,1988(1).
[5]鲁迅.小说二集·导言[M]//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9.
[6]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M]//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28.
[7]北京大学,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42.
[8]柔石.为奴隶的母亲[M]//柔石经典.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9]蓝棣之.解读《为奴隶的母亲》并兼与《生人妻》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1).
[10]董炳月.台静农乡土小说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2).
[11]台静农.蚯蚓们[M]//地之子建塔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杨邨人.租妻官司[J].海风周报,1929(17).
[13]陈梦熊.杨邨人[M]//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下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62.
[14]潘漠华.冷泉岩[M]//应人.漠华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240.
[15]罗淑.生人妻[M]//生人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16]艾以,等.罗淑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4.
[17]靳以.别人的故事[M]//靳以散文小说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331.
(责任编辑:李金龙)
I 206.6
A
1001-4225(2015)01-0040-06
2014-09-25
赵丹(1990-),女,山东聊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