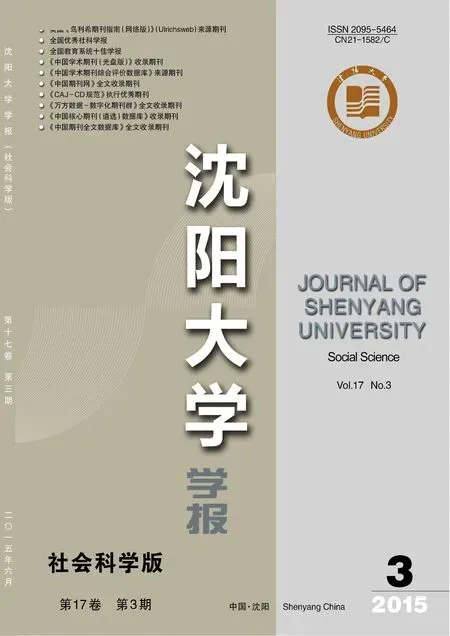康德哲学中的“人的使命”——德意志启蒙哲学背景下的阐释
2015-04-02孙迎智
孙迎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康德哲学中的“人的使命”
——德意志启蒙哲学背景下的阐释
孙迎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通过对康德批判哲学思想的分析和重构,阐释了康德对“人的使命”这一重大问题的解答,即理性的兴趣要求人去探求这一使命,而目的论的结构使得实现“人的使命”得以可能。
关键词:康德; 哲学; 人的使命

一、“人的使命”问题的哲学史背景
“人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the Vocation of Man)是德国启蒙运动后期(Spätaufklärung)[1]的一个重要观念。在18世纪后半叶的德意志,各个哲学流派——莱布尼兹-沃尔夫学派、受英法思想影响的通俗哲学(Popularphilosophie)及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学者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人们以这个概念为中心,热烈地讨论了如何成为人,如何作为人去生活的问题。
1. “人的使命”话题的产生
1748年,约翰·斯伯丁(Johann J. Spalding,1714—1804)匿名出版了《关于人的使命的沉思》一书。此书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赫尔德称其为德语著述领域的新的“经典”[2]。随后,这本小书在德国重印十余次,并被译为多种欧洲文字流传。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神学界,斯伯丁的地位举足轻重。
斯伯丁采取一系列内省的沉思展开他的观点,以一个理性的自我的口吻,向读者讲述他沉思的过程。“我”的沉思分成五个环节:“感性”(Sinnlichkeit)、“精神的愉悦”(Vergnügen des Geistes)、“道德”(Tugend)、“宗教”(Religion)及“不朽”(Unsterblichkeit)。
斯伯丁开宗明义,指出本书的目标是想采取最为“稳妥、高尚和有利的”方式寻求人生的“基本准则”:“我为什么存在,我要以理性的方式作为什么而存在,这些毕竟是值得努力去知道的”[3]2。他认为,“单纯的本性会告诉我,本性的决定无疑是最为可信的”[3]3。
在对本性的反思中,他首先思考了人的感性欲望。人的使命不是满足感性的欲望,享乐留下的只有空虚的感觉。于是,“我”就转入对“精神的愉悦”的思考,但这种愉悦也是不够的。“我”意识到,“我的精神中的自然禀赋就是来探索真理的”[3]13-14。但这最终不能使“我”满足,这只是个人的完善,与“我”的幸福无关。
“我”的幸福还要依赖于“道德”。“我”惊奇地发现,有一种倾向促使更多的人得到幸福。于是,“我”就从单纯的“精神的愉悦”转入了“道德”。通过对道德的反思,“我”发现,正确与错误等观念自然地存在于心灵之中,心灵之中有一位“立法者”(Gesetzgeber),他要求道德的行为。这一“立法者”的概念指引他去寻求最完满的存在者,即上帝的知识。这样就转入 “宗教”环节。
对于这一最完满的存在者,“我要一直努力地去接近他,不靠近那最初的源头,我绝不罢休”。向完满不断前进的希望提升了“我”的价值和使命。“我认识到,同眼前那些生灭变化的事物相比,我处在与其不同的层面。眼前的生活远非我存在的目的……我注定要过另一种生活。当前的时代就是我这一生涯的起点;现在就是我的童年,我在此时得到教育,要向永恒努力”[3]51-52。“我”的使命就是要向着完满发展,“我”的价值即在于此。
在斯伯丁的理性神学看来,宗教从本质来看就是理性和道德的事业。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反思来寻找实现其自身的途径。这样的沉思方式,无疑有着斯多亚派哲学的痕迹,也可以看到沃尔夫思想的影子,他的沉思被认为是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一面可靠的镜子”[4]。
据统计,1740—1850年间,有71部书以“人的使命”为标题,其中大部分是在18世纪最后30年出版的[5]。费希特在1799年回忆道,正是斯伯丁牧师在他“年少的心灵中播下了更高思辨的最初萌芽”[6]。
2. 门德尔松与阿伯特关于“人的使命”的争论
1764年,青年学者阿伯特(Thomas Abbt)同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就斯伯丁的这部著作展开争论。
阿伯特的评论题为《对人的使命的怀疑》(Zweifel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门德尔松的回题为《神谕,关于人的使命》(Orakel,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betreffend)。
阿伯特批评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不断完善”的观念本身就是同人的能力相悖的。比如,人的记忆力如何不断地增长完善?此外,那种认为人类此生是为来世准备,从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7]332。对于人类的使命,人们不会有任何的认识。从本质上看,人类的认识不能算是理性的[7]334。
门德尔松则在《神谕,关于人的使命》一文中捍卫斯伯丁的基本观点。他主张:“别去考虑今生只是为来世和另外的终极目的做准备。他们同时是手段,也是目的。上帝的目的和事物的变迁都是按照明确的步骤进行的”[8]336。他延续莱布尼兹的主张,坚持认为人类存在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而人类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个人的完满。人的使命就是“在理性认识的状态中去完成上帝的意旨,坚持变得更为完善,在完善的过程中幸福”[8]338。
可以看到,门德尔松和阿伯特的观点正好是完全对立的:前者主张理性思辨,后者反对理性思辨;前者思考的对象是单独的个人,而后者考虑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前者是哲学人类学的描述,后者则诉诸于对历史的反思。
这场争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阿伯特的观点促使赫尔德开始了他的历史哲学的思考[9]。Norbert Hinske指出,这场讨论是康德写作《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主要动因[10]。
还要指出的是,门德尔松对于当时德国哲学界的影响很大。《康德传》的作者库恩指出:“1755—1785年间,他(门德尔松,作者注)可谓德国哲学界的泰斗……如果没有深入了解门德尔松,就很难掌握从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到康德的唯心论的德国哲学发展”[11]。
二、“人的使命”在康德哲学中的意义
按照Frederick Beiser的划分,1760—1766年,康德处于形而上学的“幻灭期”[12]。这段时期是他批判哲学的准备时期。康德写于1764—1765年间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的批注》,是了解这段时期康德思想变化的关键文本。在这些批注中,他抛弃了对形而上学知识的单纯追求,转向了对人的关注和探索。
康德提出: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寻求人的使命”[13]175。 “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知道,如何实现他在受造物中合适的位置, 为了作为人,理解他应当怎样做”[13]44。 康德后面的这句评注很容易使人回想起斯伯丁在《论人的使命》一书开头的话: “我为什么存在,我要以理性的方式成为什么, 这些是值得努力去知道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 在康德的主要著作, 如三大批判当中, 并没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人的使命”; 但是从实质上看, “人的使命”的问题就是对人的终极目的的探寻。 从这一点来说, “人的使命”可以看作康德哲学的最终落脚点。
1. 探寻“人的使命”的驱动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人们去寻求这一终极目的呢?答案是人的理性自身的兴趣。康德哲学中,人类理性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有限性。理性自身又不愿局限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它在自身的兴趣驱动之下,总是想要“从经验的领域开始并且逐渐地翱翔直上”[14]A463,B491。在《判断力批判》第76节,康德集中阐释了人类理性有限性,即可能性与现实性、推论的知性与直观的知性、“是”与“应当”。人类的理性在运用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些界限,忽视这些界限,就必然导致理性的越界。这三组区分,看上去是消极的,因为其否定了理性通向无限世界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它们促成了理性的实践转向,通过理性的实践运用,人可以期待一个无限的道德世界。
康德这样解释“兴趣”:“兴趣就是理性由之而成为实践的,亦即成为一个规定意志的原因的那种东西。因此,人们只能说一个理性存在者对某种东西有一种兴趣,而无理性的造物则仅仅感觉到感性的冲动。”[15]也就是说,兴趣是人类所特有的,动物没有理性,只有感性冲动,而作为无限理性存在的上帝,其理性能力没有限制,也不会产生兴趣,只有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的人类,才会产生兴趣。Lewis Beck指出,兴趣具有“动力属性”,“兴趣导致了根据策略和计划引导的行动。”[16]
理性作为高级的认识能力,它产生了心灵的种种兴趣。而对于理性本身来说,理性将它自身视为终极目的,这一终极目的不在自然之中,不依赖外在的东西,“只依赖于自己的理念”[17]。故而,理性的终极目的与它自身之外的事物无关,它的目的在自身之中。这样,理性就对自身产生了“兴趣”。
正是这种理性内在的兴趣,促使理性超出经验的界限,去认识至高的理念。康德指出,作为具备实践能力的理性,不能被束缚在认识自然秩序的层面上,它要求扩展到人们的经验和此生之外。当人们用目的论的视角审视自然界的生物后,发现它们的一切器官、能力都是同它们的使命相适应的。借助同生物的“本性的类比”作出的判断发现,人是例外,人自身就是其目的。因为人的自身中包含着他的终极目的,他心中的道德律要求他不计利害地实践道德律。
而理性的终极意图的对象,就是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三个命题对于思辨理性来说任何时候都是超验的”[14]A799,B827。因为其没有经验的对象,理性在思辨过程中付出的劳作都是无用的。
理性的思辨的兴趣驱使理性去认识客体,努力思考那些超出它能力范围的对象,这就产生了大量的谬误。理性的兴趣更大的意义在于其“实践”的兴趣。理性的思辨应用是为了其实践应用服务的。“一切兴趣最终都是实践的,而且思辨理性的兴趣也是有条件的,惟有在实践应用中才是完整的。”[18]可以说,康德重新构建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并为之重新奠基[19]。
“理性的兴趣”的道德指向同“人的使命”关系何在? 在康德看来, 探讨人的全部使命的哲学就是道德[14]A840,B868。 也就是说,人的使命就在道德之中, 人类的使命不是去实现某一外在的目的, 像自然界中其他生物那样; 人的使命就在于人类自身, 就是去按照道德律行动, 认识“理性终极意图的对象”。 人的使命是理性的兴趣的必然要求。
2. “人的使命”——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奠定了他的批判哲学的基本原则,即理性的自我批判。借助对于知性和理论理性的批判,康德探讨了知识在何种情况下是可能的,理性超越经验的应用不可能形成任何知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论证了人应当按照道德律去行动,这样的人才是道德的。但是这样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即道德和幸福的分离。在康德看来,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完满的善应当是道德善加上相应的幸福。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完满的善是不能实现的。如何才能实现道德和幸福的一致?这就需要假设灵魂不死和上帝的存在。
这样,理论理性留下的空缺就被实践理性的信念所填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于这些公设给出了目的论的证明。康德通过对有机体的讨论,认为人们可以将自然界看作具有内在目的的。人是自然界中万物的最终目的。人超出其他物种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理性,形成了文化。文化的发展促成人去认识到自身的道德意识。道德才是人与其他动物真正不同的地方,道德的人是自然的终极目的。这样,康德就从自然目的论过渡到道德目的论。人在认识到自身道德的时候,就认识到了上帝的存在,这一至高的主宰安排了自然界趋向于道德。而人毕竟是具有感性欲望的,只有设定灵魂不死,人才能在彼岸世界达到人的纯粹状态。
可以看到,道德的人不仅是人们的效法对象,也是人们希望的目标。也就是说,成为道德主体的人是康德三大批判的最终落脚点,这种道德的人正是“人的使命”所在。
作为现实存在的人,他介于自然和道德之间,他不仅应当有对于来世的希望,也应当有现世之中的希望。康德在三大批判中给出的存在于来世的人的使命是成为道德本体的人,康德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讨论了现世的“人的使命”。
在历史哲学范围内,“人的使命”就是人的禀赋的完满,结成一个“道德的整体”,也就是共和国形式的公民社会。这样的使命是在此岸世界可以期待的目标。这样的观点,是同康德的目的论的思想紧密联系的。
康德的道德哲学认为,人的存在以在世界上实现“至善”为必然目的,这也就是人的使命。
在世界上实现至善是人的意志的必然目的,是道德律的目标。但是“至善”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却是短暂的,单靠个体无法实现道德上的至善,故而康德将这一过程放在了“无限进展的进步”中。在随后的历史哲学著作中,康德进一步完善了这种进步的过程。
这个人类整体道德化的目标太过遥远和宏大,如果人类将他的使命的最终目的适当放低,将目标设定为“善的禀赋的提高”,那么在人类群体中可能实现的“最高程度”就是“公民宪政”[20]。这样,康德提出了一个在历史中的较低层次的人的使命。
真正的公民宪政就是“共和国”,在其中真正地实现了自由和法律强制力的联合。而结合康德的《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念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为了实现真正的共和国“宪法”,还需要在国家之外实施一部宪法,就是建立“完美的公民联盟”。这个目标是可以期望的,“经过若干改造性的革命”终究有一天能够实现。这种“人的使命”的实现,是为更高层次的“人的使命”作准备。康德指出,“惟有在这种状态中,自然始能完全发展人的一切自然禀赋”,而这种状态将是“人类的所有原始禀赋在其中得到发展的母胎”[21]。
康德认为,教育是实现人的使命的主要手段。康德在《教育学》的开篇就提出:“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造物”[22]441。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使命。“在人性中有许多胚芽,而现在,把自然禀赋均衡地发展出来,把人性从其胚芽展开,使得人达到其使命(Bestimmung),这是我们的事情。”[22]445对动物而言,它们自出生就按照其使命去行动,因为这植根于它们的本能。但对于人来说,人必须首先对他的使命形成正确的概念,然后去努力实现它。康德将这种使命解释为“人自己从自身中产生善”,并且人能够通过对自身禀赋的发展,达到至善,并配享幸福。但“实现人的使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单靠个体来实现,而要靠种族的延续来实现。在种族延续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人将经验和知识传给下一代,通过不断积累,才有了“关于教育方式的正确概念”,并借此实现其使命[22]446。
三、康德对“人的使命”问题的解答及其在德国哲学中的回响
在康德的哲学中,理性因其自身的兴趣,要寻求终极目的。在理性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借助目的论原则认识到终极目的是“目的王国”中道德的人。这个作为三大批判顶点的终极目的,沟通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鸿沟,使人能在受到因果法则制约的自然界中得到自由,使“必然”和“应然”得以统一。
历史哲学中,康德提到了两个层面的“人的使命”。无论是人类整体的“道德化”的使命,还是实现可能性的“共和国”和“公民联盟”,都处于根本性的地位。围绕使命的实现,康德展开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从“人的使命”在康德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来看,康德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与其说是需要下定义回答的问题,不如说是在追问“人的使命是什么”。
在康德的三大批判和历史哲学中,“人的使命”这个概念可以分成如下几个层次理解:
(1) 作为理性的终极目的的“人的使命”。这种“人的使命”是终极性的,它出自理性的实践兴趣,理性在它自身中寻求其根本目的。而理性认识到的终极目的,就是“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这种道德存在者,就是“目的王国”的成员。
(2) 作为历史终极目的的“人的使命”。在借助目的论原则理解历史的过程中,康德将历史视作人类道德不断完善的过程。这样一种使命,需要人类一代代教化才能实现。这一使命存在于此岸世界,但要完成却遥遥无期。
(3) 作为人为设定历史目的的“人的使命”。鉴于第二种“人的使命”难于企及,人类试图将终极目的的标准降低。人类不要求其禀赋的完全实现,而只要求“善的禀赋的提高”。这样,一种在历史中值得期待的“人的使命”,就是国内实行完美的宪法,国际间结成公民联盟。
综上所述,康德哲学中对“人的使命”的探索,延续了他之前的思想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在他的哲学框架中得以深化和完善。在康德这里,既能够看到斯伯丁那种个人思辨的探索,也能看到阿伯特对于“人的使命”在历史中的“现实性”的要求。康德比较完满地将可能性与现实性统一了起来。从这点来看,康德哲学可以说是德国启蒙哲学的顶峰。
而康德之后,德国哲学家对于“人的使命”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基本上延续了康德这种综合的方式。
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基本上表述的是康德式的实践哲学。他区分了“自在的人的使命”和“社会的人的使命”。作为有理性的人,他存在的目的就是“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23]12。在社会生活中,人还要完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使命[23]20。费希特认为“社会的人的使命”是:在人与人共同完善的过程中,他们相互的热诚“日益坚实”,联合的规模“日益广阔”[23]22-23。
黑格尔哲学中,人的本质就在于其具有精神。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精神的本质从形式上看就是自由”[24]19。这种自由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人的使命就在于实现这一本质。
“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24]260。在国家之中,人可以说是初步地实现了他的自由的本质。
但是客观精神毕竟受到外物限制,不是完全的自由。这就要进入“绝对的精神”,绝对精神在哲学中达到了完全显示自身。这种认识是人的精神本质和自由本质最高和最后的实现。
马克思哲学将劳动看作人类本质的体现。劳动本应是自由的,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出现了人的异化。“人的使命”在于“人的解放”,扬弃异化劳动。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在于其精神,劳动不过是一种自我意识外化和扬弃的抽象精神活动。而在马克思看来,人活动的有意识性不在抽象思辨中获得,而在现实的实践领域中获得。
在异化的处境中,无产者感受到的只是人内在本质的丧失,他的处境同他的本质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无产者在这种冲突过程中逐渐觉醒,他要解放自己,首先要通过扬弃自我异化的实践解放整个人类。“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5]在无产者解放自身的过程中,他也代表着人类的利益。人类的解放将带来这样一种联合体,如《共产党宣言》所言:“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6]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并为“人的使命”的实现给出了最具实践意义的解答。
参考文献:
[1] Schneiders W. Hoffnung auf Vernunft: Aufklärung-s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M]. Hamburg: Meiner, 1990:41.
[2] Herder J G. Selected Early Works, 1764—1767[M].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153.
[3] Spalding J.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M]. Leipzig: Weidmanns Erben und Reich, 1763.
[4] Altmann A. Moses Mendelssohn: a Biographical Study[M].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1998:132.
[5] Jannidis F.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Kultursem-iotische Beschreibung Einer Sprachlichen Formel[J]. Aufklärung, 2002(1):75.
[6] Fichte J G. Sämmtliche Werke[M]. Berlin: de Gruyter, 1965:231.
[7] Abbt T. Vermischte Werke[M]. Stettin, 1780.
[8] Mendelssohn M. Ausgewählte Werke[M]. Darmstadt: WBG, 2012.
[9] Zammito J H. Kant, Herder, 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165.
[10] Hinske N. Das Stillschweigende Gespräch. Prinzipien der Anthropologie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bei Mendelssohn und Kant[M]∥Moses Mendelssohn und die Kreise seiner Wirksamkeit. Tuebingen: Niemeyer, 1994:152-156.
[11] 库恩. 康德传[M]. 黄添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268.
[12] Beiser F. Kant’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1746—1781[M]∥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26.
[13] Kant I. Bemerkungen in den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uö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M]∥Gesammelte Schriften:Vol 20. Berlin:de Gruyter, 1900.
[14] Kant I.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M]∥Gesammelte Schriften:Vol 3. Berlin:de Gruyter, 1900.
[15] Kant I.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M]∥Gesammelte Schriften:Vol 4. Berlin:de Gruyter, 1900:460.
[16] 贝克. 《实践理性批判》通释[M]. 黄涛,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41.
[17] Kant I. Kritik der Urteilskraft[M]∥Gesammelte Schriften:Vol 5.Berlin:de Gruyter, 1900:435.
[18] Kant I.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M]∥Gesammelte Schriften:Vol 5.Berlin:de Gruyter, 1900:121.
[19] 贾玥. 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路径与意义分析[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50.
[20] Kant I.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M]∥Gesammelte Schriften:Vol 7. Berlin:de Gruyter, 1900:327.
[21] Kant I.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M]∥Gesammelte Schriften:Vol 8.Berlin:de Gruyter, 1900:27-28.
[22] Kant I. Pädagogik[M]∥Gesammelte Schriften:Vol 9.Berlin:de Gruyter, 1900.
[23] 费希特. 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M]. 梁志学,沈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24] 黑格尔. 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M]. 杨祖陶,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5]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189.
[26]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94.
【责任编辑刘晓鸥】
“Vocation of Man” in Kant’s Philosophy: Interpretation under Background of German Enlightment Philosophy
SunYingzhi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Kant’s answer to the vital problem of the “the vocation of man” is interpreted, which is, the interest of reason promotes people to seek the vocation and the framework of teleology makes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vocation possible.
Key words:Kant; philosophy; the vocation of man
文章编号:2095-5464(2015)03-0323-06
作者简介:孙迎智(1985-),男,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12-15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志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