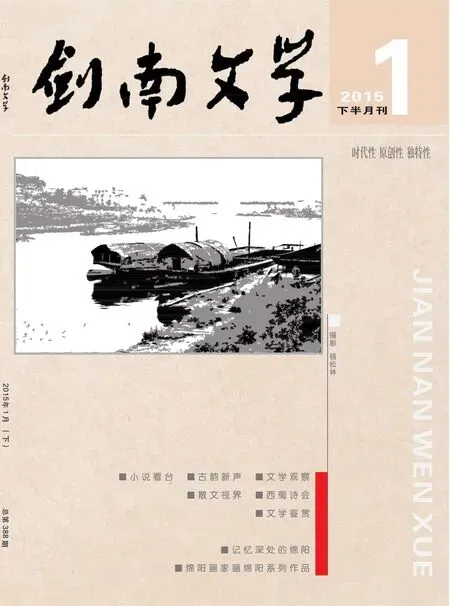笑 脸
2015-04-01张志飞
■张志飞

他在街道转角处,靠着墙似坐似躺,蓬乱的头发或立或卧,蒙了厚厚一层灰,苍蝇飞过他脑袋的时候,都找不到歇脚的地方。一件蓝布衣服裹在他身上,露出黑黢黢的胸膛。两只裤腿一长一短,豁了口的拖鞋和两根脚趾连着。蚊子也不愿意叮他,因为靠近他需要戴上口罩。偶有不知事的小孩走近他,便有一双大手拉回去,撂下一个字“脏”。
他微闭着双眼,木讷得让人怀疑是否还活着。街道上车水马龙,没有人愿意长久地看他。也许有人曾无意中看到他的胸膛在微微起伏,或是不经意中发现他被胡子包围的嘴唇动了动,因此没有人说他是死人。是活人就没有什么稀奇,大街上的活人太多了,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难处。阳光下打着伞的女人,遮住了脸却露出齐胯的腿。男人光着膀子,想让阳光给肌肉注入力量。小贩的叫卖声“凉面饼子,凉粉片粉”随街游荡,城管的吆喝声“卖凉面的快走”不时响起。
如果他是一个死人,身边一定会围着许多看客。里三层外三层,街道会水泄不通。都想看一看人死了是啥模样,有着什么样的表情,脸庞、胸膛、手臂、大腿会有什么变化。看客自己无法体验,相互簇拥壮着胆,用目光去扫视他,甚至有人会用目光去剥开他的衣服,仔细端详一个人怎样失去灵魂。如果他是一个死人,也只能满足看客们一时的好奇心,因为要不了一会儿,穿制服的会来,牵起线不让看客靠近;穿白大褂的会来,皱着眉头翻看他的眼皮;搞民政的也会来,让他免费坐一回厢式车。剩下的事情看客们只能想象,再绘声绘色地摆给没看到的人听,像是自己的人生又多了一份阅历。——这些事都还没有发生,他还没有死,所以身边没有人。街道上有的人脚步匆匆,有的人慢慢踱步,瞟过来的只有眼睛的余光,以及刻在行人心中的两个字“疯子”。
转角处是一家药店,三个门面俨然一个超市。老板心地善良,所以并没有赶走靠在外墙角的“疯子”,因为他标榜的是卖“良心药”,给百姓健康,靠在墙角的这个人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没有病,兴许药店和他还能互相沾光。果然,药店里人来人往,愁眉苦脸地进去,喜笑颜开地出来,手里提着“灵芝仙草”,仿佛见过了太上老君,能够长命百岁,最好多来几次,但愿长生不老。
他的厨房就是人行道边的垃圾箱。他要做的事就是解开里面的垃圾袋,幸运的话解开一袋就够吃了。扔垃圾的人不怕泄露秘密,事情都是在屋子里做的,男欢女爱,饮食吃喝,正常的人都可以理解。一个疯子,如果他能理解,还能叫他疯子吗?
一个小孩从河堤上走下来,戴着奶奶用柳枝给他编织的花环,高兴得像个威武的将军,雄赳赳地走到了街的转角处。小孩或许觉得将军应该在屋子里指指点点,或许是花环戴久了头脑发热,他摘下花环,顺手抛了出去,正好抛到了那个人身上。奶奶一下子攥住他的手,边紧走几步边说:“别惹他!”
他睁开眼睛,闻到了一股清香的味道,抬手摸摸柳枝,凉悠悠地沁人心脾。或许在某一个乡村,绿色铺满了大地,柳枝正随风摇摆,秧苗一田连着一田,像绿色的地毯……
……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小路尽头有几间土墙房子,墙上的粘土涂层有的已经裂口翘皮,涂层里和着的麦壳已经发黑,显示出这房子有些年头了。他从屋里出来,到墙边拿起扁担,挑着撮箕。撮箕上粘了厚厚一层泥土,女人拿着细绳从屋里出来,说道:“你把撮箕上的土巴敲打一下,担着也轻巧些。”他回道:“没有多重,一会儿担秧苗还是要粘上土巴。”女人说:“你笨得很,土巴干了,一敲就掉,你就知道白使劲。”说着女人捡起一根细木棍过来,拿过撮箕倒扣在地上,“砰砰砰”一阵敲打。土块噼哩叭啦掉了一地,女人拿起撮箕再用手掌拍了几下,递给他道:“你看是不是几下就敲掉了?你就是不动脑筋,光使笨劲。”他尴尬地笑了笑,挑起撮箕准备要走,女人说把锄头也带上,又回头对着屋里说:“小丽,把碗洗了就和弟弟写作业,记得煮午饭。”里面“呃”地答应了一声。他走了几步也回头说道:“小丽,别和弟弟去玩水。”“知道。”清脆的声音再次从门里传来,门口多了一张笑脸,“你们也早点回来。”
走在路上,女人唠唠叨叨地说这说那,他闷声不响。女人抱怨他脑筋笨,没文化,啥手艺都学不会,说一个木匠砖工一天要挣一两百元,自己家守着几亩土地,除了够吃,手边花的钱紧张得很。又说好在小丽初中要毕业了,她要不读书了家里负担就会轻一点。他接过话头说:“小丽要是考起了还是要供她读书。”“拿啥供?还得花多少钱,你想过没有?”“我就是没文化才挣不到钱,娃娃有能力学就是要供!”“好好,供她读,你到田里去挖个金娃娃。”两人似乎要赌气,女人脚踏进秧田里,溅了他一身泥水。几滴泥浆扑到了他的脸上,女人扑哧一笑:“你要是长成这样我死也不嫁给你。”他用衣袖擦去泥浆,方方正正的脸上和女人一样,被长年累月的太阳烤成了古铜色。他微愠地说了句“你慢点”,就弯下腰扯起秧苗来。
女人和他扯着秧苗,水田里响着秧苗被拔起时的“沙沙”声,宛如孩子在叭唧叭唧地咂着奶头。秧苗长势喜人,两人心里渐渐高兴起来。扯了一阵秧苗后,女人让他往大田里挑,自己一个人扯。他提起秧苗往撮箕里装,装了一层又一层,都冒出好高了,他还要装。女人看了他一眼说:“你挑合适就可以了,别挣出病来。”他说赶着把秧苗插完,地里还有一点小西瓜,去卖了也能换些钱。女人揶揄道:“勤人跑三转,懒人压断腰。你就是个死脑筋。记得挑到大田里把秧苗散开。”
田野里弥漫着泥水的腥味,一眼望去,青一块白一块,要是往年,早就是绿油油一片了。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剩下的人越来越少,年纪越来越大,活就越做越慢。早些年人多的时候,几家相约共同插秧,一天就能插上一大片,田野里一天变一个样。女人的吵闹声,男人的吆喝声,女人和男人的笑骂声此起彼伏,在一行行的秧苗中穿行,惹得青蛙心里痒痒的,迫不及待地从刚插完秧苗的田里钻出来,在晚上也“咕儿呱咕儿呱”地学舌聒噪。
下午,女人叫他和自己牵起细绳,在大田里插秧。两人一次插两行,从田的两头插到中间,再回头去移细绳。在田里来来回回穿梭,很是耽误工夫,女人说:“真是人多才好干活。干脆叫小丽和小宝来给我们移绳子,我们两个只插秧苗,也好插快点。”他一听这话赶紧板着脸抢白道:“不行。太阳这么大,田坝里遮阴的地方都没有,把娃娃晒黑了。”女人脸上露出笑容,说道:“好好,就只有你心疼娃娃,我的心肠狠。小宝晒黑点倒没啥,小丽晒黑了就找不到好人家啰。”他也笑了,说手脚麻利些就把工夫赶出来了,又回头望了望,说道:“今天好歹要把这块田插完——摸黑也要插完!”女人同意,说剩下的一小块田自己插就是了,他把西瓜弄到城里去卖。
天快黑了,田里的秧苗还没插完。没有了太阳,空气凉爽了许多。王大妈从田埂上走过,叫他们快回去,说身体是本钱,累病了一块田的收成还不够医药费,又说明天来帮他们。夫妻俩站起来舒了舒腰,说这个时候干活才安逸。谢过王大妈,两人又弯腰紧手紧脚地插起来。
小丽带着小宝来到田边,叫道:“爸、妈,天黑了,饭都要凉了,该回去了。”他说了句“你们咋来了”,一见小宝头上戴着用柳枝编的花环,又说:“小宝,太阳都不见了,你戴个帽子做啥?”小宝骄傲地说:“姐姐折的柳枝,我自己编的。”女人叫两个孩子在田埂上移绳子,小丽和小宝叽叽喳喳地吵着:“你的间距大了”“你的间距小了”。夫妻俩心里甜蜜蜜的,仿佛吃下了开心果,卸下了一天的疲劳,还有使不完的劲。
小宝问:“爸,你逮的有黄鳝不?”
他说:“我哪有时间逮黄鳝,秧苗都插不完。”
小丽说:“妈,明天我要上学去了,明天晚饭你要自己煮了。”
女人说:“你念你的书,家里的事你别管。”移完绳子,两人要插一阵才移下次。小丽在这头掐着花草,小宝在那头寻着黄鳝洞,不时用手指捣几下。天色越来越暗,几颗星星在暗夜里愈发明亮。远处插好秧苗的田里已有青蛙在鸣叫,甚至有一只叫声就来自他们插秧的田里。小宝走过去找了几遍,青蛙的叫声却不见了,他只好悻悻地回到细绳边,蹲在那里,听父母脚从泥水里拔出来的“叭哒”声。小丽把手里掐的花草,顺着田埂端端正正地插了一排,她美滋滋地在夜色里欣赏着这花的栅栏。
突然,小宝那头“咚”地一声,紧接着传来了“哇哇”的哭声。几个人连忙跑过去,原来是小宝跌到了水田里。他把小宝拉上田埂,用袖子赶紧去抹头和脸。女人把他拂到一边,拉着小宝问:“小宝,哪儿扎着没有?”小宝抽泣着说:“我瞌睡来了。”女人愤愤地说:“走,我们回去了!今天插不完有明天。这么辛劳,害得娃娃也跟着遭罪。”几个人就一路安慰着小宝往家里走去。
吃过早饭,一家人在地里寻了几遍,大大小小搜罗了几十个西瓜。他把两个大竹筐绑在自行车上,装好西瓜,又用绳子勒住竹筐,看看结实了,就准备出发。一家人帮他把自行车推到大路上,他在“你慢点”的嘱咐声中骑上车向城里奔去。
离城还有二里地,人家密了起来,路上的行人车辆也络绎不绝。他跳下来推着自行车走,指望着边走边卖掉西瓜。他盘算着两筐西瓜有两百多斤,再怎么着也能卖一百多元钱,现在的西瓜行情是一元一斤,从外地运来的什么“冰糖瓜”还要两元一斤,他的西瓜是地里最后一批了,大小不一,卖相不好,管他的,先喊一元一斤再说。
有人喊住了他:“西瓜咋卖?”“1 块。”“有少不?”“你随便挑,哪个值1 块就给你称哪个。”买瓜的人上上下下翻着西瓜,把这个敲敲,那个摸摸,挑挑选选好一阵,终于称了一个西瓜。他接过钱,脸上笑眯眯的,心里乐开了花。
等了一阵,不再有人过来问,他推着自行车又往前走。“西瓜。”他停下脚步:“1 块。”“八角卖不卖?”他犹豫不决。“八角!卖就称一个。”他咬牙嘣出一个字:“称!”
快进城时有一个路口,一个人拦着他,把筐里的西瓜翻了个遍,说道:“1 块钱1 个,我全买。”他赶紧摇头:“那不行,我要称重,8 角咋样?”他虽然没文化,但一二十年的市场经济磨练,多少也积累了点经验。
“哪里卖得到8 角,我看两角差不多。你这是罢园瓜,个小不甜。”
“谁说不甜?我切一个你尝。”
“不用尝。1 元1 个你卖了。进城去城管要撵得你到处跑,哪有时间卖瓜,进市场要交清洁费,再说市场里瓜多,你这西瓜,这卖相,哼!”
“那也太便宜了。”他原想说到6 角7 角的一下子卖了也好,又想今天本来就是来卖瓜,家里秧苗有王大妈帮着插,就算插不完也所剩不多了,让别人赚钱不如自己等着多卖点儿钱,于是不再开口说话。
那人听了,也不再回话,掉头走了。
他回味了半天那人的话,觉得有些道理,决定就在这路口多卖一会儿,兴许运气好,能卖出去呢。
他把自行车推到一棵树脚下,捡出筐里的西瓜放在地上,挨个摆好,数了一下,连同已经卖掉的,共有38 个。“才给38 元,自己两个瓜就卖了9 元钱,地上还有这一堆,哪才值38 元钱。”他想着如果按刚才那人说的卖掉,太划不来了,又想着地里长势好的西瓜都卖完了,眼前这满地的西瓜大的大,小的小,确实没有卖相,干脆不说1 块,直接说8 角,也比一块钱1 个卖掉强。
这时的太阳还很温和,树脚下也凉快,他就放心地坐在地上,等候着买主。
路上的行人三三俩俩,有的进城,有的出城,就是鲜有人来买西瓜。偶有几个人扭头望了几眼,也不开口问价,又径直走了。“今天这是咋了?”他想是不是还不够热,就抬头看看天,“今天是个大晴天, 待会儿热起来就对了。”
又卖掉一个西瓜,卖瓜的人长短要先尝后买,他只好切开了一个小瓜给她尝。“甜还是甜,就是瓤少壳厚,有点划不来。”他想回一句“哪有西瓜光长瓤不长壳的”,又不敢,只好接过钱闷头坐下来。
太阳升起了老高,有几缕光线已经照到西瓜上了,不再有人来买瓜,他不由得着急起来。又有一片光线照到了西瓜上,他蹲起来去攒西瓜,攒了几个,他想到把大的放一边,小的放一边,大的卖8 角,小的卖5 角,该有人买了吧!
把西瓜分成两堆摆好,有人经过,他就喊一声:“西瓜,大的8 角,小的5 角。”
过了五六拨人,又卖掉一个西瓜,是一个熟悉行情的人,他停下电瓶车,对坐在后面的女人说:“街上要卖1 块,走,过去买一个。”女人说:“便宜没好货,是不是陈西瓜。”他听了连忙说:“都是新鲜的,今儿早上才摘的,看看这瓜蒂。来尝尝,甜得很。”这时的生意就像在钓大河里的小鱼,水面宽阔,不知哪条鱼能上钩,鱼漂一动,就要聚精会神,钓着一个算一个。他献着百般殷勤,这单生意终于没落空。
蝉已开始在树上鸣叫。他觉得自己口干舌燥,拿起地上划开的西瓜,切下一小瓣吃了几口。他想早知这样,出发时就该让小丽给他写两个牌子,立在西瓜里,也不用自己费口舌了。想到小丽,他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孩子又听话又勤快,学习又好,上次开家长会,老师说她的成绩排在班上前几名,上高中没问题,再努把力,上“国重”都有希望。每次周末回家,小丽都要用节省的零用钱给小宝买吃的,惹得小宝都想早点去读初中住校了。星期天返校,有时他去送,有时小丽自己走着去。临别时,小丽总要回头对他们笑笑,“乖女子,笑起来美得很!”他想到这里,心里比吃了西瓜还甜,脸上不由得泛起了一圈圈笑意。
攒过几遍西瓜后,已是中午时分了,太阳光明晃晃的,烤得水泥路上涌起热浪。树上的鸣蝉也有气无力,叫一声要隔好一阵才又叫唤。路上已几乎没有行人,连骑车的人也少了。他没有打算吃中午饭,只把切开的西瓜全吃了。他决定到城里去,找着人群卖西瓜。
把西瓜大的放一筐,小的另放一筐,他推着自行车往城里走去。街道两边有绿化树,行人还不少,他喊了半条街“西瓜,大的8 角,小的5 角”,都没人理他。他觉得这样喊有些拗口,就简成一句:“西瓜6 角。”
给人称西瓜很麻烦。车很重,他支不起脚架,两边又不平衡,街边无东西可靠,树在人行道上,他只好用身子抵住竹筐,叉起双脚又要防止车倒,又要提防称盘里的瓜掉,很是费劲。连买瓜人要狡掉付钱的零头,他都没有多余时间去争辩。甚至没等他反应过来,有的买瓜人把钱扔在竹筐里,抱上西瓜就走了。
他这样卖西瓜费时又费力。城管很尽职,他才卖掉3 个西瓜,他们又上班了。他推着车走,不停下来就没人管,一停下来称西瓜,就听见巡逻车在喊:“卖西瓜的,到市场里去。”他不敢停留,生意搅黄了几个,心里很是懊恼。
他推着车在城里转悠,既有躲过城管卖掉西瓜的喜悦,又有遇到路人光看不买时的失望。可以停车的地方没人,有人的地方不准停车,他整个下午就这样不停“躲猫猫”,没有吃午饭,再刚强的汉子也显得疲惫了。
终于等到城管下班了,他在街上遇到一个同村的熟人,交流了一阵一天的经历,得出一个结论:人强不如货硬。又说累死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劳累,命该如此,有啥法。两人一商量,找了一个路边,把剩下的西瓜摆在地上,也不称重了,直接喊“两元钱1 个。”
各自卖了几个西瓜后,天快黑了,想收拾东西回去,又还剩十几个瓜,第二天专门为卖几个小瓜跑一趟,从时间工夫上说不划算,再说隔夜的瓜,又小,更不好卖。两人嘀咕一阵,落一个不如捡一个,一块钱一个卖了算了。
这时的街上人潮涌动,老人穿着对襟的棉绸衣服在散步纳凉,年轻人穿着短袖边走边接打电话,情侣们手牵手,蹒跚学步的小孩踏着叽咕叽咕叫的鞋子,走一步脚后跟就闪亮一下。他闻着这祥和幸福的味道,期待的眼神显得杂乱而迷茫,似乎自己嘴里喊的“西瓜1 块钱1 个”是块石头,会砸碎这幸福的梦境,喊声就逐渐低沉下去,以致于变得懒洋洋起来,不想再叫卖了。
1 块钱1 个,几个小伙子买了当场要吃,西瓜皮扔了一地,他捡进筐里,拿回去喂猪。天黑透了,街对面一群人踉踉跄跄地喧哗着,一个说“一块钱一堆,我全部买了”,一个说“5毛钱1 个,我买半个”,一群人哈哈大笑。等他们走远了,他跟同村人说:“妈的,酒疯子,把我们当叫花子,5 毛钱1 个, 不如拿回去自家吃。”同村人深有同感,愤愤不平地收拾好西瓜,在夜色中两人骑着车往山洼里的家中赶去……
他靠在墙边,把柳枝捏在手里,呆呆地望着它,想要想起点什么,脑筋迷迷糊糊的。他把柳枝放到敞开的胸膛上,脑海里逐渐闪过一幅幅画面:一个男孩戴着柳枝编的花环,在阳光下奔跑;一个女孩回头望着他,冲他甜甜地笑着;一幢接一幢的高楼,洁白的医院病房;一个人站在路边,伸着手向行人乞讨,那人仿佛就是自己。几个画面在脑海里交错闪现,欣喜、失望、欢乐、悲伤等等思绪像一根根利刺扎向他的心里,脑袋针扎般剧痛。他扭了扭身子,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工地上有十几幢高楼,置身其中,让初来乍到的他分不清方向。阿发带着他,边走边给他指指点点。让他记住吃饭的地方,记住睡觉的房子。他看见有的楼外立着高耸入云的塔吊,在上上下下地吊装材料;有的楼外几个人拴着绳子,在钢架上来来回回不知在干什么;有的楼房已经成型了,四面光秃秃的,露着一个个黑洞洞的窗户。
阿发带他见了工头,工头告诉他:这个工地几年都干不完,只要他肯干,不愁没钱挣,又说他没技术,只能算打零工,虽说没人家挣的钱多,也比在家里守着几亩土地强。“我也是农村来的,”工头说,“走南闯北十几年,现在不想回去了。你放心,说是做零工,事情也多得很,看见没有,”工头指着前面一幢光秃秃的楼房说,“三十几层,一百多套房子,每个屋子都要收拾,一幢楼就要干两个月。”
工头拿出图纸,给他安排这个礼拜的工作。他一脸茫然地听着,只晓得砸墙,拆架子,收拾垃圾,到底怎么干心里并不了然。工头让阿发把他带进楼里,现场去给他讲一讲。阿发领着他进到屋里,指着墙上的“x”说:画了x 的要砸了,垃圾挑出去。又来到另一个房间:这几根钢管要拆了,放到门外,下楼时带出去。临走时,阿发对他说:“事情多,你慢慢干。我给工头说了,你是个勤快人,你这个工作没法定量,做一天算一天,你自己把握。别把自个累着了,但是一天能做多少事工头心里清楚得很。记得中午12 点吃饭,你不晓得时间,看到楼下有人往食堂走了,你就走。下午6 点下班,过了6 点你就别做了。工具放到屋里,第二天又做。”
阿发和他同村,出门打了几年工,家里楼房也修了。过年回家,他找到阿发,让他带自己出去打工,阿发爽快地答应了。要上车时,一家人去送他,很是有些离别的伤感。特别是小丽,都哭了。他站在车门上,忍住心伤,强打着笑脸说:“小宝,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千万别去玩水;小丽,加油念书,我去挣钱,供你上大学。小丽别哭,来,给爸爸笑一个。好好,我女子还是笑起来好看。”
他在楼里干了几天,工头很满意。庄稼人本来干的就是力气活,劳累惯了。“海水舀不干,力气用不完。”他这样地想,这样地活,就是阿发有些烦恼。他常常忘记吃饭的时间,工地食堂里的饭只能自己吃,不能给别人带,害得几次吃饭时阿发都去找他,又不知道他在哪层楼里,吆喝一圈转来,饭菜都凉了。
阿发给他买了一个手机。是一款老年机。他喜出望外,让阿发在他的工资里扣。晚上回到宿舍,阿发就教他操作。阿发说,他不需要存太多电话号码,存多了反倒搞不清楚。阿发给他存了三个电话号码:第一个是自己的,第二个是他家里的,第三个是工头的。“看见没有,给我打就按1,给家里打就按2,找工头就按3。接电话按这个键。”阿发让他试试看,先用自己的电话给他打,让他接,又让他给自己打。折腾了一阵后,他终于学会了。两个人非常高兴,说说笑笑半天后,他突然说:“我给家里打个电话,看她在做啥。”阿发表示同意,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话,嘴里自言自语:“给家里打按2。 ”他按了后,电话上显示“正在呼叫”、“对方响铃”、“00:01、00:02”, 阿发叫道:“通了通了,你说嘛!”他就把电话拿到耳边:“喂……你说我是哪个……对嘛, 还没忘我……阿发给我买的新电话。”他看了一眼阿发,又接着说:“家里都好不·……小丽小宝都好不……我也好,我还看到了海,好多水哟!……你说些废话,那么多水我敢下去?……我吃得好,就是海鲜有点吃不惯。……人家只准吃, 不准拿。 要不等我回来时给你们买点。……我挣得到钱,你在屋里莫太累了,庄稼长孬点就孬点。”阿发见他红光满面,异常兴奋,声音高亢,像要有说不完的话,就提醒道:“打电话要付电话费,拣主要的说。”他这才醒悟过来:“打电话要给钱, 你叫小丽来说句话……哦,今天星期二,小丽没回来。小宝呢?……这小崽子,叫他别玩水……好了不说了,你要找我就打这个号码,咦,是好多数?”他转向阿发问,阿发说有来电显示,家里头看得到。他又说了句:“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号码。那……挂了。”
屋子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他捏着电话爱不释手。阿发说把电话揣好,别掉了。他把电话放进衣兜里,又把衣服折了几折,裹住电话,把衣服放在枕头边,这才满意地躺在床上睡去。
第二天,他在干活的屋里找了块塑料布,把电话严严实实地包裹好,又用一根橡皮筋套住,揣进裤兜里,这才放心地继续干活。
中午吃饭时阿发问他,电话响了咋不赶紧接。他说把电话拿出来又没响了。阿发说不可能,让他把电话拿出来看看。他掏出电话,阿发看了差点没笑得背过气去,嘴里“你呢你呢”不知说啥好。阿发说用不着这样,坏了有人修,再说也不值钱,大不了再买一个。他不愿意,阿发只好说那我给你多拨几遍,久了你就记住吃饭时间了。
一天的事情结束后,两个人在宿舍里天南海北,谈天说地打发时间,放松心情。阿发说,他听。他说,阿发就不时指正他。他说要挣钱供两个孩子读书,阿发同意,但是说也要对得起自己,说到年底回家带他去坐飞机。他连忙问要花多少钱?阿发说可以错开时间走,买打折的票比坐汽车还便宜,又省时间,一天之内就可以到家。又说只要有钱,一家人天天都可以像过年。他觉得有些道理,现在自己也挣钱了,仿佛生活向他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在这扇门里充满了阳光,有很多的钞票,只要自己肯干,腰包迟早也会鼓起来,女人不用再劳累,小丽小宝也会长大成人,挣更多的钱,那时自己也要好好享受一番。
两个月后,阿发的父亲死了。阿发回去奔丧,他留在工地上干活。没有了阿发的说说笑笑,他感到孤独无助。几次把电话拿出来,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又觉得费钱。想着女人该给他打个电话,那也需要电话费,再说家里零零碎碎活儿多,不像他这样按时上下班。一时间心里郁闷,他白天使劲干活,晚上蒙头就睡。
一天,他在一间屋里干累了,就停下手中的活,拿出电话,想坐下来把电话看一会儿。他解下橡皮筋,揭开一层一层的塑料布,看到了那个闪着银光的“2”字。他高兴地舒了一口气,身子向后面靠去。突然“咣当”一声,身后的钢管散了架,上面的几截钢管哗地掉了下来,砸在他的头上,砸在他的身上,又弹起来在地面上“咣当咣当”乱叫。他倒在了血泊里,一声没吭昏死过去。
午饭都吃过了,还不见他的人。工头嘴里边骂边去找他。等找到他时,工头大吃一惊,探了探鼻息,感觉他还有气。工头捡起他的电话,从惊慌中冷静下来,快速地在脑中思考对策。
他被送进了医院。工头和公司达成了协议,先由公司垫钱医,工头的责任款在承包的工钱里扣。
工头派了一个知己的兄弟去照顾他。三天后,他醒了。问他,他口齿不清。多问几遍,感觉他精神错乱。糟了,摊上大包袱了,工头想。该说医好就让他走,谁知看这架势他有很严重的后遗症,那该要花多少钱才能搁得平?工头又着急又愤恨,捏着他的电话,眼睛滴溜溜地转,一会儿看看病床上的他,一会儿看看手中的电话。终于,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诞生。
工头给阿发打电话,给他延一个月的假,说丧父之痛大家都能理解,让他在家里安心地把事情处理圆满,工地上的事情兄弟们多干一会儿就是了,他来了工资照发,权当是大家对他的慰问。又问了阿发的详细地址,逐字核对后,说要给他寄点东西。阿发忙说心意领了,不用寄,工头就顺便问了和他同来那个人的家庭情况。
他躺在病床上,睁眼望着雪白的墙发呆。伤口好了,就是脑袋迷迷糊糊的,还隔三叉五地疼。要想起点什么,始终没有连贯的画面:高楼,手机,大海,阿发,他尽力地想,脑袋就炸裂般地疼。
工头伪造了一张他女人的身份证,在外面找了几个人冒充他的亲人。那女人一踏进病房门,当着公司处理事故领导的面,一下子扑倒在病床上,嘴里喊了一声“我的人啊!”就瘫坐在地上,双手拍打着大腿,像有万分的悲痛积压在心里,不能用嘴,而要用手表达出来。他呆呆地望着她,面无表情,想要说点什么,嘴巴却不听使唤。
他的病情大家都清楚。协商结果,用钱解决问题。公司出两成,工头出一成。拿了钱后,由家人把他接回去,从此与公司再无关系。
事情很顺利,一群人拉着他上了面包车,让工头额外付了租车费,就载着他疾驰而去。他消失在了漫天的迷尘之中。
他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他裹着蓝布衣服,靸着拖鞋,漫无目的地走,东张西望地看,蓬头垢面,臭气熏人。路人纷纷避开他,走在前面的冷不丁回头发现了他,愤怒地训斥道:“滚开,疯子!”
他吃完了衣兜和裤兜里的食物,站在街头,迷茫地看着来来去去的人。有的三五成群,谈笑风生。有的昂首挺胸,一本正经。有的两手空空,匆匆而行。有的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眼睛还望着街边的商店。就是没有人愿意停下来, 经过他身边时都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疯子,还是少招惹好。”他已不属于这个世界,就算是人,也是属于多余的人。
实在太饿了,他在街边向外伸出了一只手,摊开手掌,嘴里不时嘟囔一个“钱”还是“吃”字。芸芸众生,如潮人流,总有几颗柔软的心,他的手里有了几张小小的纸币。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去用。有人往垃圾箱里扔了没吃完的东西,他几步走过去,翻出来拿起就吃。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厨房:银灰色的外壳,不锈钢的盖子,两个箱子好比两口锅。只是锅里装着大杂烩,他要在里面挑挑拣拣,一口锅接一口锅地来回找寻。
他虚弱地在街道转角处,靠着墙似坐似躺。时间只有白天和黑夜,白天燥热,夜晚干冷。大地就是一块一块的盒子,在路的两边排成排,一直向远方延伸出去。有的人从盒子里出来,有的人往盒子里走去。他靠在街的转角处,只在不经意间伸伸腿,扭动一下屁股……
好像该吃点东西了,他睁开眼睛,向垃圾箱望去。在垃圾箱边,一个剃成光头的女子穿着睡裙,手伸在垃圾箱里乱翻,脸却向着他在笑。他望着她,她一直向着他灿烂地笑。猛然间,他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悲痛,像有锄头、扁担、斧头、镰刀一齐砸向他的心。他挣扎着直起身,向她伸出一只手,口里叫道:“丽!”
女子见他要起来,吓得走了。他忍住疼痛站起来,跟了上去,边走双手边在衣兜裤兜里乱摸,嘴里冒着一个字:“钱。”他拿着一张5毛纸币,向着女子逃走的方向边追边挥手,声音也由小变大,逐渐清晰:“小······丽!”“上学!”
女子走上河堤,脚步越来越快。他走上河堤,女子已消失在了远处散步的人群中。他头痛得厉害,不得不坐下来,靠着石栏杆歇息。越歇息,他的脑袋越迷糊,顺着石栏杆他又躺了下去。
宽阔的河面只剩下窄窄的水流,曾经被水淹没的卵石上泛着微黄的光芒。河水哗哗地流着,在断崖处激起雪白的浪花。浪花不愿顺流而去,回头向上猛扑。一群燕子在浪花上空打着旋儿,仿佛在嘲笑浪花的无能为力。
下雨了,河堤上漫步的人群四散而去。雨打在他的身上。他把脑袋伸进了栏杆下的石缝里。冰凉的泪水像蚂蚁一样,在他的脸上缓慢地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