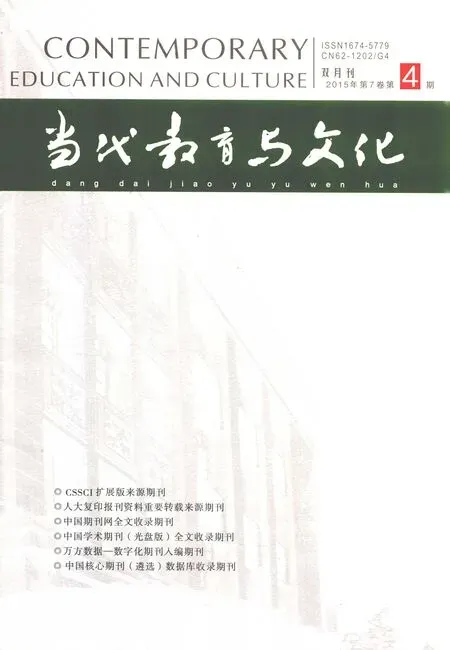回归教学学术:技术时代的教学正义
2015-03-31高小强
高小强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在当下的教育生活中,教师们对待教学技术的态度充满了矛盾。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并存,技术崇拜者与技术恐惧者同在。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非常吊诡的是教师们在教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一方面急于掌握先进的教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又反对技术全面介入他们的生活;他们既无法忍受教学技术的匮乏与落后,也对教学技术在教育领域内的全面渗透充满着警惕与怀疑。本文的重点在于揭示教学技术在自身演进的过程中如何型塑教师的文化品性从而使得教师教学学术精神难以为继,教学正义追求无法实现的原因。
一、基于生活的技艺孕育了思维探险的行动者
前工业时代的教学技术,教育者虽然很少意识到它们是技术性的存在但随时都离不开。它们包括人的身体、语言、文字、书写技术和学校空间技术。在尚无口头语言用于教育之前,身体 (肢体语言)无疑是实施教育的主要手段。语言产生之后,“言传”成为比 “身教”更为重要的教学技术,并共同承担起教育的重任。就各自作用来看,“身教是做示范动作,以供模仿;言传是说明是非要领以传经验。”[1]当社会发展到口耳相传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教育的需要时,应运而生的文字和书写技术使教育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文字和书写技术是继语言和身体之后人类用于教育的新技术。学校产生之前,人类的生活空间就是教育的空间。而学校自其诞生起就成为独立或相对独立因而有别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公共空间,且越来越作为一种体制化的空间而存在,因而是一种具有根本性变革力量的教学技术。首先,学校使教育具备了独立的形态;其次,学校使社会教育和专门教育有了中心和外围的区别;再次,学校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又因为学校空间在直接或间接培养着统治阶层所需要的人员,所以它还是 “教育的技术”和 “统治的技术”的结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产物;最后,学校空间也是包含身体、语言、文字和书写技术在内的一系列教学技术完成整合并发挥作用的主要场域。
不论是身体、语言还是文字和书写技术都为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而学校则为这种交往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空间。这些教学技术已经内化为教育本身,因而无法从教育中剥离出来,如果剥离了,教育也就随之不存。同时,与这些技术有关的知识形式、实践活动以及物质形态反过来又型塑着教师的文化品性,彰显着教师的教学学术。总体来看,教师们在使用这些原始的技术却能表现出追求 “自知”的品格。首先,这样的教师始终表现出一种对智慧的爱,并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爱智慧,而不是仅仅拥有知识,因此他们一直处在创造文化的活动当中。在这种活动中,他们一方面拥有了自知,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教育因此成为师生间经常发生的 “思维的探险”,教师自己也是 “思维的探险者”。这样的教师拥有对世界、对生活的精细的敏感度。在师生共同探求自知与真知的教育生活中,这种精细的敏感度还会进一步持续增长和扩散。其次,教师追求自知,就意味着人就不能像动物一样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 “事实”,而是追求真、善、美的世界。这样的教师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必然是锲而不舍的。回顾历史,不论是古希腊的 “哲学王”还是中国古代的 “圣贤”皆是如此。正如乔治·F·奈勒所说,“哲学解放了教师的想象力,同时又指导着他的理智。教师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从而用比较广阔的眼界看待这些问题。教师通过哲理的思考,致力于系统地解决人们已经认识清楚并锻炼出来的各种重大问题。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工作者——但是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2]这种具有哲学想象力的自知,既需要知道有关人的辉煌伟大,又要知道有关人的悲惨暗淡。因此,关于人之为人即以伦理道德的完善为最高目标的教育就应该天然地比以其它为目的的教育具有更加崇高的尊严。最后,自知也意味着教师个人对个性、批判性与否定性的良好保持。对于真知的不懈追求和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决定了教师永远是处于未完成状态的人。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是无止境的,因此教师的教学学术与文化品性也是出于动态生成中的和未定型的。
二、用于传播的工具造就了阐释知识的劳动者
工业时代的教学技术实质上主要是自然科学技术或工程技术教育化的产物。从其具体的物质形态来看,基本上包括幻灯、投影、广播、电影、电视机等等。自然科学技术或工程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使教育发生了与传统的断裂。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角色在不同程度上被幻灯、投影、广播、电影和电视所替代。教师从教育当中的独奏者变成了协奏者。任何教育成果的取得不再是教师单独努力的结果,而是教师与现代教学技术紧密结合的产物。教育的力量更加强大,但是教师的独立性与个性却日渐被侵蚀。而且,与以前的学校相比,以班级为单位的学校是一种新的教学技术空间。班级授课制是教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革命。[3]从此,学校不论从形式上还是本质上更像是批量制造新一代生产者和劳动者的工厂,而教师和其它教学机器一起从事着效率至上的生产劳动。在学校空间内,包括学校以及教室都具备了监视功能,技术因此侵入到了最为细微的生活空间。随着新的技术进入学校和教室,学校和教室具备了双重身份:既是规训的技术又是一系列规训技术得以施展的空间场域。学校建筑本身也因此成为特殊技术的产物并体现着这一技术的权力。因为学校建筑不仅仅是出于使用的目的,这种建筑物 “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 (如宫殿的浮华),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的一举一动都章明显著,即一个建筑应该能改造人。”[4]
工业社会的教学技术依然主要由教育者主动地引入教育领域为教育服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知识的传授。但是技术本身已经作为商品而出现,因此在其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已经拥有了交换价值,但仍以使用价值为主。具有双重价值的教学技术在以掌握知识为目标的教育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教学技术的改进速度远远落后于学科知识总量的增长速度,但是人们利用新的教学技术让受教育者尽可能多地掌握知识的愿望依然难以遏制。因为在信奉 “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人被视为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学科知识)的 “填充物”。人们对科学知识给人带来的确定性产生了近乎崇拜的迷恋在教育中的表现就是学科知识的传授。于是,拥有知识,尤其是拥有科学知识成为教育者追求的基本目标。又因为这种知识的力量本身就蕴含着权力并形成权威,所以教师的权威就依赖于对精致的、无可置疑的学科知识的把握。这些知识要求教师要准确无误地用纯客观的思维方式教授给所有学生,因此免不了机械重复。教学技术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 “无错误的重复”的需要。再加之工业管理的模式被应用于教育领域,课程与教学目标、内容的制定、实施与评价过程都严格的按照“科学化”“标准化”的程序执行,要求教师更多的是一个知识传输系统上的 “技术熟练者”的角色。[5]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失去了创造性。从此,知识的创造不是学校和教师的根本任务,其根本任务只是把已有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罢了。这使得教师在其受教育的过程中把带有个人 “偏见”的东西排除在外,只为对大量客观知识的记忆,以及对标准答案的拥有而沾沾自喜。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教师知道得很多,并且可以使用先进的教学技术让学生知道,但是,从追求 “自知”到追求 “知道”,教师在满足于拥有大量知识的同时已经失去了获得独立的教学学术的可能性。尽管这些做法迎合了社会的需要,但是这导致了 “知识的阐释者”教师群体的产生。作为阐释者的教师在以学科知识为主导的 “专业化”过程中其个性不但没有增加,而是在加速丧失。这样的教师对于学生而言已经失去了不可替代性,“知识的阐释者”只具有在知识储备上的可数性、可计算性,同时却丧失了文化品性上的独特性,本质上和流水线上的工人没有了区别。
以追随知识的增长和满足科技的进步为目标的学校可以称之为知识统治的学校。和伦理统治的学校不同的是,知识统治下的教师必须依靠一系列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来弥补自己在伦理道德方面 “权威”的丧失所引发的危机。技术作为一种理性化的手段使教师的权力得到了延续和延伸。从伦理型教师到知识型教师,尽管教师的权力因为新技术的使用而增大,但是其权威已经与往日不可相提并论。日常生活中,教师首先要面对的是知识的增长,必须时刻 “学习”并保证 “知道”,这样才能适应知识增长对教师的需要,并美其名曰 “教师博学”。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教师主要以精通自己的学科知识为目的;同时,教师还得适应教学技术的改进。如果教师能够更好、更快地适应技术的要求,也就意味着教育教学的效率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证。因为现代教育的理想从追求真理转变为追求确定性和方法,清晰的理念和毫不模糊的陈述,所以尽管技术的改进也会给教师的教育生活带来一定的不适应,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不适应绝对不会致命。正因为现代教育是以追随知识的增长和满足科技的进步为目标,所以教师的精神世界与心灵都被安置在这个知识和技术的世界当中。教师日复一日做到的就是 “知道”如何通过一切技术手段让学生“知道”并且借助标准化评判技术准确无误地确信学生已经 “知道”,仅此而已。教师和学生就在满足于知其然的氛围中过着紧张但又乏味的生活。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即使拥有再精巧的技术,即使再接受专业化的训练,教师们也无法化解社会对他们的失望情绪以及诟病。原因就在于,如果没有确切地知,就不可能正当地行更不可能高贵地说。对于教师而言,知、行与言说是三位一体的,“自知”的缺失而导致的教师文化品性的不完整才是教师身份危机的真正根源。教师只有在狭窄的学科领域当中可以说是有知识的,他们和传统意义上思想家教育家式的教师相比,只是具备了执行局部任务的能力,而不具备处理社会组织和政治方向这样实质性问题的能力;他们在小事上是清醒的,但在大事上却是盲目的、糊涂的。
三、作为交换的商品型塑了依赖技术的消费者
信息社会的教学技术是对工业社会教学技术的一次革命性超越。同时,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知识与信息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知识的信息化和信息的商品化。知识都被数字化、符号化、商品化了。而那些不能数字化、计算机化的知识,几乎都不被看作知识。同时知识全部商品化,知识的发现和传授变成知识生产和销售,甚至知识就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学习知识成为一种知识的消费过程,完全是一种商品关系。[6]信息技术的这种逻辑一旦产生,它便具备了自身的动力,新的技术便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但是,对于技术的使用者而言,这些技术构成了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一个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外在世界,即使人们能够接近它,但是已经无法完全掌握它。教学技术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超越甚至替代。教育信息技术不过是消费社会的一种新商品,一种大众传媒工具对教育领域的占据。通过教学技术使用范围的扩展,一切教育问题都已经被当作技术问题来处理。
信息技术建构的教育空间已经不再是封闭的班级授课制的学校。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主要包括计算机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远程教学技术等。从提高学习者能动性的角度来看,它有助于学习者克服时空障碍,实现跨时空的对话和交流。似乎营造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空间。这一空间与班级授课制的学校相比,似乎存在着更多的自由。但是与传统的教育自由相比,两种自由的本质是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技术的跨时空的宰制。所以传统的教师在封闭的社会往往是自由的,而现代教师在技术无孔不入的境况下,在这种由网络空间支撑的自由空间里却更加不自由。信息技术开始整合学校,而不再是学校整合技术。学校、教室成为现代技术可以宰制的对象。技术完全控制了学校和教师,教学技术发展成一种既控制肉体也控制灵魂的技术。新技术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凸显使教育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校成为教学技术的营销场所,教学技术为其所新开拓的教育空间俨然是消费领域。现在,当我们去论证技术多么有利于教育,技术如何与教育密不可分,技术应该如何更好地和教育相结合以及技术应该如何在整个教育领域普及时,我们同时在做的另一件事就是通过理论和实践让技术这种商品更加友好地进入尚未引进这种技术的学校或者让新的教学技术能够更加具有亲和力地替换已有的尚能发挥作用的技术。教学技术在学校中广泛使用,其最大的原因是教育产业化的需求和资本流通的推动,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各方的主要诉求,而不是主要为了学生的自身发展或更为广泛的公共利益——内在利益。[7]麦金太尔指出,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的重要差别在于,“每当外在利益被人得到,它们始终是某个个人的财产与所有物。某人占有它们越多,剩给其他人的就越少。内在利益诚然也是竞争优胜的结果,但它们的获得有益于参与实践的整个共同体。”[8]而且,信息技术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存与发展模式。没有出自教育的技术,也没有单纯为了教育的技术。只有为了技术的存在而教育化的技术。但是这种教育化,并不能改变技术作为 “用于交换的商品”的性质,反而越来越以其交换价值的凸显而不停地改变着教育的面貌,控制着教育生活。从而也改变了教育价值观。现代生活的价值观太过简陋,以至于如果不能表现为利益和技术的就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而生活的简陋进一步导致了语言和思想的简陋。[9]因为信息社会的教师相信掌握技术就意味着拥有知识,所以其对日新月异而且信息化的知识的要求是无需知道,或者可以通过技术知道。即他们可以也可能知道一切,但是实质上却可能一无所知。例如,只要具备了操作计算机的技能,就可以通过互联网 “知道”所有想知道而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因此,他们无须占有知识,只需占有技术。他们通过消费技术来消费知识。教师在教学技术的换代和知识的更新过程中只有被动的接受,没有主动的参与和创新。当前的教师不知不觉成为教学技术这种商品的主要消费者及知识这种商品的推销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不知不觉地受到信息化知识和信息技术的双重控制。这种控制不在于知识和技术本身的使用价值,而在于这些知识和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所刺激的新的消费需求。现实生活中的教师往往满足于对教学技术的 “消费”所带来的短暂的愉悦。因此,他们所期待的是技术花样的不断翻新,教师学习和使用新技术正如消费款式不断变换的衬衣一样 (在国内方兴未艾的翻转课堂即是一例)。因为新技术的选择意味着教师掌握或者驾驭更多知识的能力的增强,此所谓 “技术专家型的教师”。“技术专家型的教师”对技术的崇拜使其完全丧失了自己在教育领域所应当秉持的价值或者立场,从而更加不可能具备对教学技术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因为,“技术专家是没有价值意识的,他将所有价值选择的问题,都转化为一个技术性的改良的问题,将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理解为行政问题。”[10]对于教学技术的崇拜也使现代教师由知识的阐释者变成了技术的冒险者,因为他们通过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加以解决从而将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边缘化 (如伦理道德问题),这是信息技术环境下现代教育的根本问题。
四、结语
教学技术从人与人交往的技艺转变为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的技术再到控制一切人的工具;教师从道德的权威到知识的权威再转变为技术的权威;出于技术统治需要的教师,一直想寻求一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手段,这种手段既是平等的也是高效的,于是教师们只会越来越关注劳动和工作领域,而不是行动。但是,教学学术只能产生于教育行动中而在教育工作或者教育劳动中则会被遮蔽,被雪藏冰封。因为 “行动是人以言行为媒介,直面相对并相互影响的活动,具有包容各种异质性因素的品格,使之得以在边界内富有个性地生长,这是教育的专业性。”[11]由于劳动和工作领域是完全可以为技术手段所驾驭的,是可预设、可操作的。于是,教育活动逐渐从行动领域滑入到劳作领域最后跌入到工作领域。教育者自身则从一个追求教学学术的行动者退化为崇尚教学技术的重复劳动者,教育的生活意义以及创造性从此荡然无存。
诚然,教师技术化是现代教学技术对教师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赋予教师的角色,但技术化的教师因此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传统教师文化生活中曾经具有的哲学向度的祛魅,伦理向度的浇薄和艺术向度的隐褪,即以以对话的形式把握、理解和描述和解释教育,大胆地探索、积极行动、创造可能生活为宗旨的教学学术水平的下降甚至消失。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教师对这种教学技术对其教育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表现出的是接受。但是随着技术统治在教育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基于好的生活的向往而生发的反对就愈加强烈。教师在此种意义上所反对的就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对于这种被技术宰制的教育实践方式或者说是教育生活本身的反对。所以,问题不在于教师们在教育生活中应用了什么技术,或者缺少什么技术,而在于以手段的合法性置换了目的的合理性;同样,问题也不在于教学技术的落后或者先进,而在于它本身作为权力工具和载体的物质性。因此,教师对技术的崇拜与恐惧是作为教育者对技术这种控制实体的反对,也就是对技术异化教育生活的反对。当教育的目的已经发生改变之后,一切教学技术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从技术为艺术服务到技术与艺术分道扬镳再到技术创造艺术,技术的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技术的合法性取代了艺术的合理性。如果说传统的教学技术更接近教育的艺术或者说可以被看作是教育艺术的基础的话,工业时代以来的教学技术与艺术之间不再有某种天然的联系。教师对教育艺术的追求被对教学技术的接受所取代。当教学技术开始充斥于教育生活之中时,教育艺术要么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点缀,要么被当作可有可无的仆从。但是,当教学技术的合法性愈加强大时,教学学术的合理性就更应该得到张扬,这也是教师回归教学正义的必然要求。
[1]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0:2.
[2] 桑新民.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人类自身生产探秘 [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3.
[3] 章伟民,曹摇申.教学技术学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6.
[4]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95.
[5] 车丽娜.“教书匠”的式微与教师文化的重建 [J].当代教育科学,2007,(1).
[6] 乜勇,陈晓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教学技术学[J].电化教育研究,2009,(5).
[7] 袁磊,孙杰远.教学技术与民主学习 [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8] 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理论研究 [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42.
[9] 赵汀阳.论可能能生活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4.
[10]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00.
[11] 刘旭东.行动:教育理论创新的基点 [J].教育研究,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