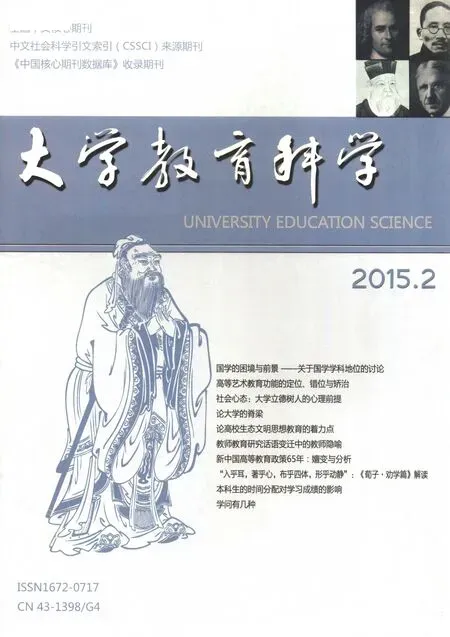教师教育研究话语变迁中的教师隐喻
2015-03-31蒋福超
□ 蒋福超
教师教育研究是以话语为媒介的理论化实践活动,探究教师教育的研究历史,就是要探究话语实践的构成与特征,并反思、审查话语背后的立场与修辞。以隐喻的视角去思考话语变迁下的教师形象,不仅能发现理论发展的清晰脉络,也能挖掘出教师成长之道的流变和存在的问题。
一、作为隐喻的教师教育研究
1.理论意义:隐喻与教师的存在论问题
探究教师教育研究话语变迁下的教师隐喻,就是探究不同理论流变下对“教师是什么样的工作”的不同认识。正如佐藤学所说,教育学关于教师的话语,一直围绕着“教师应当如何?”(ought to)的规范性逼近、或是“如何才能成为教师?”的生成性逼近展开讨论,而“教师是怎样一种角色”、“教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是教师”的“存在论逼近”(ontological approach)却在无意识之中被排除了[1](P206)。当今教师教育研究理论的更迭带来了新的概念及演绎,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有着对“如何培训教师”的形成性问题的执着。然而,忽视了对教师工作本体论思考的教师教育研究,却终究逃不出现代主义的迷宫,教育研究者苦于理论创新,教师和准教师的成长也在被观察、被研究、被指导下迷茫。缘木求鱼式教师专业发展要想回归正途,就必须要从“我是谁”的这一镌刻在古希腊德菲尔城阿波罗神庙里唯一的碑铭开始。或许,此可为该研究的理论价值。
2.实践价值:隐喻与教师教育者的教学
教师教育是发生在教师教育者与教师(或准教师)之间的实践活动。在实践意义上,隐喻视角的教师教育研究对反思“应该怎样指导新教师的教学实践?自己对教学的认识是否恰当?教师教育者的职业特点是什么,有没有基本的素质要求?”等教师教育领域“长期集体无意识的问题”有积极的启发价值[2]。同时,也对解决教师教育者所产生的所谓的“内卷化”(即在外部发展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内部不断精选化和复杂化而出现惰性,从而导致“没有发展的增长”)问题困境,进而避免教师教育工作的异化,也有着实际意义[3]。
二、由外而内、二元化、囿于知识论的教师教育研究话语及教师隐喻
1. 教师是技术熟练者:技术理性话语下的教师教育研究
理论信仰与技术信仰下的教师教育可以从泰罗(Taylor)《科学管理原理》中对技术的膜拜中找到时代背景。现代主义打着“科学”的旗号,以追求效率与规模为诱饵,注重普适性、确定性和宏大叙事。20世纪60年代,工具理性的教师教育研究话语充斥着工程学词汇,如“目标、表现、生产、技术、系统、计划、控制、管理、评价、机构、基础”等等。此时,研究者将教师视为“技术熟练者”,将教师教育视为一种重视技术性技能和市场畅销性的“职业”教育,这就使教师教育变成了狭隘意义上的职业准备。正如罗宾·厄舍(Robin Usher)所分析的,“在职业性实践中,学习变成了一个知识运用的过程,知识本身却被窄化,教育以培养学生适应技能的方式成为个人动机和预定学习结构之间的联接”[4]。拘泥于此,教师发展中关注的便是:如何有效维持课堂秩序,如何提高学生成绩等达到目的的手段,以满足“用户”(如家长、社会等)的市场需求。
“职业”教育观念下的教师教育是由外而内、理论-实践二元化的教育。教师不是以“体验”姿态面对课程与教学,而是被“告知”所谓专业理论与价值规范。教师教育者以专家身份出现,教师作为“课程技师”,往往简单“阅读”他人的教育理论,而且教育理论总被假定只存在于教师生活之外的专家和权威的头脑中,并天真地认为学习完理论后,教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理论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这种教师教育排斥了个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割裂了与现实生活世界的联系,没有意识到教师工作的复杂性。教育教学不是“玻璃盒”,而是“黑箱子”,教师教学不是演绎理论的程序而是艺术,将确定性的科学用于不确定课堂的教师教育模式“过于寻求教师成长的普遍规律,而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教师成长的不同特点与个体性;过于追求不同情景下教师发展的总体性,而排斥了教师发展的现场性”[5]。因此,离开教师的切身体验和生活世界的教师教育课程是简约的、中立的、非真实的,与教师的专业发展无关,与教师自觉的文化价值认同无涉。
2. 教师是反思性实践家:实践理性话语下的教师教育研究
及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转型以及客观主义哲学思潮的式微,作为技术熟练者的教师形象逐渐被解构和批判。转型后的教师教育研究话语出现了变迁,诸如“实践、案例、设计、建构、表达、表现、经验、反映、批判、反思、田野、临床”等医学类、设计类话语走向前台。斯蒂芬(Stephens)也说,教师教育意味着它是一门扎根于用来应对不确定性环境的学科知识和学术成就的一门职业,教师培养(teacher training)表明它是一门确立在用以处理规定性、机械性任务所必需的实践性知识基础上的一门职业[6]。从此,实践被推到了教师教育研究的舞台中央。
以多纳尔德·舍恩(Donald, Schon)为代表的研究者将教师视为“反思性实践家”,将教师教育视为一种“专业”教育。在“反思性实践家”模式中,借助“反思”与“审察”两种“实践性学识”,实现着问题解决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如此,教师成为如建筑师、医生一样的“专家”,教师教育成为不同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教育。舍恩指出,历来的专业是把专业知识和技能运用于时间情景的“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之原理作为基础完成工作的;而当今的专家是投身于顾客所面临的复杂的泥沼般的问题之中,基于“活动过程的省思”,同超越了专业领域的难题进行格斗[7]。
但“反思性实践家”模式力图打破理论-实践的二元化,实现用从“理论的实践化”(theory into practice)向“实践中的理论”(theory in practice)的转换。但如同“技术熟练者”的教师教育模式一样,这种教师教育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只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样式的不同。前者追求客观的严密性与科学性,追求超越具体情景的普遍性和原理性理解,后者从设计理性的语脉变化来表达对具体情景和个人化的教师经验的重视,最终形成教师的专业基础——实践性学识。但“将专业知识完全局限在实践的范围内,似乎并不是一个用来提高整个教师行业水平的完全之策[8](P1)。至此,“教师教育似乎在‘反思性实践家’处定格,是当前教师教育研究的最高成就”[9](P198)。要继续往前推进教师教育的研究,实现新的范式转变,就需要反思上述教师教育研究的共同问题,即两者都限于知识论的狭隘视角。
3. 知识论视角下教师教育研究的困境
究其根本,两者都聚焦于教师知识的来源问题,即是来自于专家的权威性指导抑或是来自于个体实践。因此,“反思性实践家与技术熟练者一样都是从知识、从应该拥有知识这个唯一的不证而明的起点出发的”[9](P200)。知识论关注的是教师教育的方法论问题,而限于知识/方法论视角的教师教育研究具有明显的不足,究其原因就在于两者都是针对问题解决的,没有注意到教师的内心成长。
不论是聚焦于教师理论和技能提升的工具理性下的教师教育,还是聚焦于在个体实践形成情境性知识和技能的实践理性下的教育教育,都致力于解决“如何提升教师教学效能”的问题,只是在如何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产生了分歧。两者都没有进入到教师的内在的伦理性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触及教师的灵魂。而教学却是伦理性、道德性极强的工作,特别是在当今知识唾手可得、教师存在合法性受到质疑的信息时代,尤其如此。
“优秀教师需要自我的知识,这是隐藏在朴实见解中的奥秘”[10](P3)。两种教师教育模式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内心的自我认同与成长,没有在教学境遇中去追问“我是谁?”的问题,将世界外在于教师的生活,抛弃了教师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教师与其他诸如医生、律师、建筑师等职业相比,更需要在工作中拥有完整的自我,唯如此才能关注和塑造学生完整的灵魂。如此,重新思考教师的“存在于世”的本体论问题成为教师教育研究转向的根本原因。
三、从内部出发,从生活出发,走向本体论的教师教育研究话语及教师隐喻
1.教师是“个人”:解放理性话语下的教师教育研究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反思了对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的观点[11]。“平庸之恶”的人放弃了思考,默认并实践着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他们的工作原则上不需要任何感情,阿伦特用“空无的一切”来形容。虽然有时会良心不安,但习惯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行为提供辩解以解除个人道德负担。部分教师,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着为学生的前途着想的旗号,在行使着一定意义上的恶,做着毁灭人的思考、自主、人格、自信、自由意识、创造能力之事,却从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如同佐藤学所说,教师在受“机械原理”所控制的学校里,以“滑稽的教育方法”高居于学生中间,形成伪善性、权势性人格,在被奉为“道德博物馆”的学校里,教师扮演着“道德权势化”(paragon of virtue)的作用,形成狭隘、权势的素质[1](P211)。
因此,要思考教师教育的问题,必须要重新思考教学问题。“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我认同与自身完整(Identity and Integrity)”[10](P11)。古德森在研究教师生活的基础上也认为,教学首先是个道德和伦理职业,他说,“在我看来,这表明教育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始对教师发展理论的重新解构。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已经实现了将教师作为实践者到将教师作为人的转变”[8](P65)。教师的自身完整性就是教师的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所以,教师教育首先应该是伦理学教育,是教师德性成长的过程,教师教育应该先从“我是谁?”、“为什么存在教师”的本体论出发。
因此,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课程概念重建运动的兴起,教师教育研究的话语也在悄悄发生转变,“省察、体悟、生长、德性、精神、气质”等伦理学话语和“生活、体验、理解、存在、描述、阐释、自传、叙事、存在”等文学、艺术学话语逐渐出现。转向的教师教育研究不再将教师教育视为“职业”或“专业”教育,而是“志业”或“智业”教育,教师教育即教师气派的形成过程,即教育教育者与教师或准教师共同增强自身完整性的过程。教师也不再是工具人或实践人,而是一个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成长、完善的人,是一个不断形成和完善其主体性的智慧人。
教师主体性的形成和完善途径可以循着中西方两条路线去寻找。在中国是主张体悟的“慎独”的方法、在西方是现象学方法启发下的“生活体验研究”。传统儒学和西方现象学关照下的教师教育都将目光投向人的内在体验和生活世界,慢慢实现了视域融合。
2.方法论与价值观的统一:中国传统儒学下教师成长的“慎独”与“成人”
如上所述,技术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教师教育研究都是一种方法论意义的教师教育,并没有关注本体论意义上的教师教育的价值观问题,方法论与价值观是分离的。而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特征就是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教师成长方法的“慎独”与“成人”的价值追求水乳交融。
中国传统儒学就是“为己之学”、“成人之学”。个人通过修身成“仁”,通过“诚”达到“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最终“与天地参矣”。在这种“天人一体”的世界观下,认识自我就是认识世界,儒家的方法论就是价值观,它们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体。“上下贯通、内外交融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于是唤醒、呈现、光明、遵循内心本存的天性也就当然地成为儒家哲学的逻辑进程和人道教化的必由之路”[12]。最终,修身的完成也意味着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完善,修身以“成人”是方法,也是价值追求所在。
在修身方法上,传统儒学的思维方向是“反求诸己”的向内生长,并把这种不断深化我们自己主体性的修身活动称为“慎独”。“慎独”就是“修道”之路,最终实现根性的澄明。“慎独”意味着主体可以对进入心灵和思想的各种东西进行检查,也意味着主体可以有意识地建构自己以决定自己的特性和存在方向,并达到自我控制的程度,从而完成自我的政治或伦理的建构,让自我解放成为可能。“慎独”的两个维度是“隐”和“微”。《中庸》第一章说,“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对于“隐”和“微”,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曾注云:“隐,暗处也。微,细事也。”。儒家认为,个性常隐藏于自己不易觉察的习惯和细微之事中,要从习以为常的惯习中发现自我,从细微的生活故事中反思自我。
作为教师成长的“慎独”,不只是师德的修炼,更是探究一个真实的自我,也是自我的自主超越,以合乎与天地贯通的人性。它拒绝一切外在的权力和权威,于“隐”于“微”处对进入自己思想的一切东西进行反思和批判,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写的人。“只有当教师以‘自我探究’之需求为基础、生存于自己的世界,发现自己的‘内心声音’并且忠实于这种‘内心声音’而生存,学习从自己的‘内心声音’里寻求生活方式的妥当性时,才会有真实的学习。所谓真实的学习,无非是探索自身应有生活方式的伦理性学习”[1](P120)。所以,当老师在“慎独”中寻求其教师生活方式的本真意义时,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与技能学习,教师专业发展才变成“他”为成“我”。这种从内部出发的教师成长之路,与西方现象学的方法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3.向内生长、发掘生活:西方现象学视角下的教师主体性成长之道
现象学视角下的教师教育研究主张把经验、自然的态度“悬置”起来,以一种直接面对、朝向事情本身的立场探究教师的存在与发展。它重视教师发展的历程,即“去存在”的过程,而非发展的预定结构与结果;它排除任何先入为主的自然与科学的观点,运用现象还原,直接把握教师发展中自我显现的种种“现象”,从而深刻理解教师成长的规律;它关注教师内在的情感体验,即“非理性”的存在,凸现内在的自我超越;它高扬教师成长的“共在”性,教师是在“他人”之中成长的,而不是孤立发展的[13]。在现象学关照下,教师的生活史和故事等这些在以前被忽视甚至屏蔽的内容,现在却成为教师发展的宝库,成为透视、洞见其教育学价值和意义的描述和解释。教师教育研究从此由对“经验”的关注发展到对“体验”的重新解读,将教师的成长奠基于鲜活的、现象学式的“存在体验课程”中。
在派纳(Pian,W.F.)看来,正如人们不能直接凝视太阳,却能够容易地考察太阳所照亮的地球一样,人们也不能很容易地透视自我,但人们可以通过主体的“传记性情景”(biographic Situation)来对自我进行反观自照[14]。所谓“传记性情景”,是“自我之光”投射在生活世界中的故事和经验,我们可以通过客观的描述其经验,将注意焦点转向生活经验,重视理解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具体因素,返回事物本身,体验“前概念”(preconceptual)的事物,从而揭示被湮没在无意识之中的材料,在探究隐藏着意义的自传故事中,找到“真实的自我”,“只有恢复被压制、被虚构的自我,一个人才能找到既通向自身,又通向世界的通道”[15]。教师自传、回到事实本身等观点的提出,就是要在范式性认识与活泼自在的生活世界的裂缝中,去体验自己真实的、朴实的人生,与自我对话,实现自我分裂、自我解体,寻求教师自我的合法性,最终发展教师“对于教师内在合理性一种追求”的教育智慧[9](P201)。
[1] [日]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 吕立杰,刘静炎.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教与学——西方国家教师教育者自我研究运动述评[J].全球教育展望,2010(5):42-46.
[3] 杨跃.谁是教师教育者——教师教育改革主体身份建构的社会学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71-76.
[4] Robin Usher. Experience, Pedagogy and Social Practice[C].Knud Illeris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Learning[M].New York:Routledge,2010:176-177.
[5] 魏建培.教师学基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72.
[6] Stephens,P.,Tnnessen,F.,&Kyriacou,C.Teacher Train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in England and Norway: A Comparative Study[J].Comparative Education,2004(40).
[7] D.A.Schon.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M].New York:Basic Books,1983:140.
[8] [英]艾弗·F·古德森.专业知识与教师职业生涯[M].刘丽丽,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 高伟.回归智慧,回归生活——教师教育哲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10] [美]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M].吴国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 [美]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M].孙传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0.
[12] 徐小跃.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重要特征[J].河南社会科学,2013(5):39-41.
[13] 姜勇.现象学视野中的教师发展观[J].全球教育展望,2007(2):44-47.
[14] [美]威廉·派纳.自传、政治与性别[M].陈雨亭,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8.
[15] 陈雨婷.教师研究中的自传研究方法[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