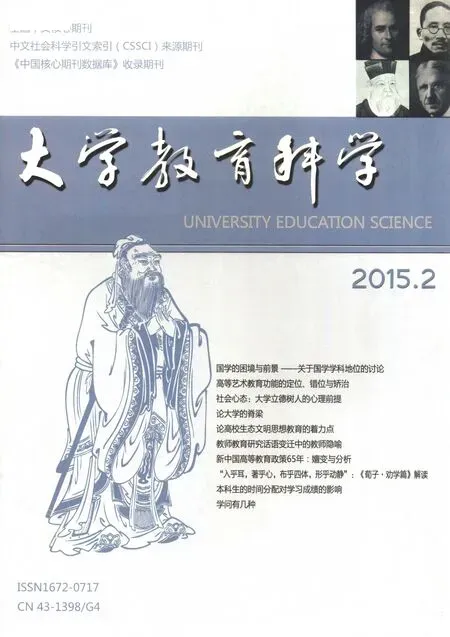法学新兴学科课程纳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中的思考
2015-03-31唐双娥
□ 唐双娥
根据《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法律人才必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法学新兴学科因其新的研究方法、全方位的视野、发散的思绪而具有对法律现象进行新的思考而发展迅速,富有生命力,更能培养学生的法律能力。法学新兴学科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尤其是课程中如何科学设置,值得探讨。
一、学科划分对法学教育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对从事法学教育的师资的影响。由于从事法学教育的老师同时必须完成规定的科研任务,尤其是课题申报、论文发表等任务。结果,从事法学教育的教师在授课时,难免更多地从法学学科出发,而不是从法学教育科学出发。教师也难免缺乏法学内部知识的融合。我国法学学科的大势是学者个体除了自己熟悉的学科,基本上没有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这就限制了学者以及学生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不能及时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造成法学研究视野狭窄、方法单一,既不能准确认识和发现问题,也不能妥当地解决问题,很难满足社会实践和理论创新的需要[1]。
其次,以科研服务的学科分类做法对高校的定位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大学之所以能在时空发展上超越其它任何组织,皆因大学满足了人类社会培育新人以保持其可持续发展进步的永恒需要。正是因为如此,人才培养亦即育人成为大学最基本的价值和无需证明的公理与天职[2]。但是,在以科研服务的学科建设中,我国很多高校定位于综合性、科研型大学,无不主要以科研成果来评价高校。法学学科划分对法学教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第三,课程设置没有充分以问题为导向。法律课程的开设主要以法学中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基本法)为依据;这些核心课程是必须开设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确立法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不单纯是对新办法学专业的评估问题, 而且事关法学教育的大局,既关系到法学教育的规格,更关系到法学教育的发展,既涉及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增强后劲,更涉及到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问题[3]。
显然,“将学科作为教学科研基层功能单位的唯一根据,现在看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其集中表现为学术研究视野狭窄、僵化,将鲜活的现实问题割裂为片面且形式化的研究课题,对学科以外的知识缺乏兴趣;在教学上则表现为:教学内容的条状分布,缺乏与其他学科的照应”[4]。因此,法学教育界出现了这样的呼声:从学科主导转向问题主导,从理论法学转向临床法学。学科划分上的独立并不等于学术上的划地为牢,更不可能以此为据将各种社会现象割裂和封闭起来。法学研究必须把法律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中,尽管客观上存在学科分立,但法学研究者应有融合法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法学内部各学科知识的基本观念,并尽量付诸法学实践[1]。
二、法学新兴分支学科的兴起及法学教育重视法学新兴分支学科的原因
1.法学新兴分支学科的兴起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出现了许多法学新兴分支学科。中共中央2006年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提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何谓法学新兴分支学科?法学新兴分支学科是相对于传统学科而言的,确定新学科的标准大致有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以及研究体系等几项。从形式上看,正常地、系统地开展法学研究的时间不长、研究水平不高或者面临重新建设任务的法学,都可以纳入法学新分支学科。已被公认的法学分科并不一定都是传统学科,如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都似应划入新兴学科[5]。
法学新分支学科之所以兴起,是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较之以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建立,需要加大法律与经济关系的研究,1981年开展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的大论战,经济法学与民法学“分家”,经济法学逐渐成为新兴的独立学科。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法学新学科手册》。该书列举了一系列法学新学科(该书列举的法学新兴学科有的属于边缘法学学科)。21世纪后,我国的建设已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扩展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布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要求在这五个方面都要推行法治建设。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都要求加强法学新兴学科课程的教学,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2.法学教育重视法学新兴学科的原因
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是社会活动的变动性和无限性之间的冲突;任何一种现有知识体系都是对过去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认识和总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导未来的活动,永远无法包容社会和自然界的全部发展和变化[6]。法学新兴学科的兴起,要求我们转变对法学学科的传统观念。何勤华教授提出,转变对法学学科的传统观念、重视法学新学科建设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一顶紧迫任务[7]。除了重视法学新学科建设外,法学教育中也应将法学新学科引入课程设置中。
就法律规范而言,法学新学科以形成新的法律规范为前提,这些新的法律规范对我国的经济、社会运行会产生重要影响,法学教育的受众群体应当对这些新的法律规范有所掌握,不然会导致法学知识的狭窄与片面。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如央视对话栏目的一期节目《反垄断能否捍卫我们的利益》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酒厂的高层以及法务部门对于其执行最低销售价的销售措施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着不认知的情况[8]。法学新兴学科研究的法律规范既有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刑法规范等,通过引入新的研究方法,能开拓全方位的新视野,培养发散的思绪,对法律现象进行新的思考。因此,在法学教育中,在注重传统法学学科的同时,应当加大开设一些新兴法学学科的教育。因为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应运而生的新学科,是发展迅速、富有生命力的学科。这些次级新学科在汲取传统法学知识的基础上,根据各自关注领域又分别自成体系,延伸和深化人们对法学的认识[1]。
如果说21世纪之前我国的法学积极服务于经济建设,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不可动摇的根本任务,那么在21世纪仅仅满足于一般的刑法、民法、法理的教学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9]。法学新兴学科的优势使得其有利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切实提高学生的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目标的实现。
其实,美国1992-2002年高年级课程增减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加大了法学新兴学科课程的开设力度。增加的高年级课程中,相当多的课程为法学新兴学科,如知识产权法、环境法(能源法、自然资源法)、健康保护法、土地利用与规划不动产、体育运动法等[10]。
三、法学新兴学科课程纳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需注意的问题
1.不宜将法学分支学科课程纳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法学新学科分支众多,如军事法学、体育法学、医事法学、科技法学、财税法学等不断被提出。法学分支学科的衍生是直接受日益频繁的立法活动的影响,在对传统的部门法学做深化研究的过程中实现的。但应当注意的是,法学分支学科课程不宜纳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新时期我国法学教育要求“宽口径、厚基础”,教育部将法学原来的七个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在新的分支学科形成之后,原有的部门法学可以概括其研究内容,但却完全无法取代[4]。将法学分支学科课程纳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不符合“宽口径、厚基础”的要求。如有观点认为,“法学与外语”、“法学与知识产权”、“法学与航空航天”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在本科层次是否具有推广价值是值得思考的,不能将二级学科(甚至是所谓三级学科)概念引入到法学本科教育中[11]。因此,在本科阶段,法律教育应侧重与法律专业与职业的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应侧重于法律思维和法律职业技能的教育[12]。
2.法学新兴学科课程的设置应因校而异
法学新兴学科众多,需要开设的新兴学科课程自然也众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规定了16门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这使得包括知识产权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环境资源法在内的新兴学科课程教学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重视。就新兴学科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地位,不同的高校做法存在差异:
第一,单独特别突出知识产权法学新兴学科。北京大学2009版本科教学手册显示,知识产权法学被纳入北京大学大类平台必修课,法学院之外的学生都应选修此课程。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则作为大类平台选修课,供全校学生选修。
第二,将法学新兴学科课程(知识产权法、环境资源法、劳动法)提到与传统学科课程同等地位。如清华大学将法学新兴学科的知识产权法、环境资源法、劳动法作为专业限选课(这种限选是学生都需要选修的课程)。
第三,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是开设两门还是一门的问题。《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规定的是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实为一门课。但不少高校意识到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其实是两门性质不同的课程,一般将其作为两门课程(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开设。如武汉大学、吉林大学都将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作为独立的两门专业选修课程;北京大学则将名称完善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第四,其他新兴学科课程的开设。除了知识产权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资源法之外,其他新兴学科课程是否予以开设?清华大学开设了网络与电子商务法;北京大学开设了体育法、财政税收法、会计法与审计法、青少年法学。吉林大学开设了医事法专业选修课。可见,各高校存在一定的差异。
综上,知识产权法、环境资源法、劳动法这三门法学新兴学科作为新兴学科应纳入法学教育课程设置得到了一致认同;其他的新兴学科如体育法学、科技法学课程的设置,则可能是根据学校的特色和师资而定。
3.边缘法学课程宜作为非法学专业的选修课
法学新学科以形成新的法律规范为前提,区别于边缘法学[4]。法学新学科研究的是其他学科与法的关系,如法医学研究医疗技术、医疗管理、医疗事故和医风医德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为医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军事法学、体育法学、医事法学、科技法学、财税法学等为本体法学新学科,而“法学与外语”、“法学与知识产权”、“法学与航空航天”等则为交叉学科,是法学边缘学科。本体法学新学科随着法学研究涉及生活范围的扩大而产生,以制定新的法律规范为目的,它是法学、法律的纵向深入发展,是法学理论和实践的再深化[13]。“厚基础、宽口径”原则要求“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中设置中应区分法学新兴学科课程与边缘法学课程的开设,并关注法学新兴学科课程而非边缘法学课程的开设。
目前法学培养方案中有一定数量的边缘法学课程。边缘法学课程集中反映在犯罪学、刑事侦查学上。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特设专业中,“犯罪学”归属于法学学科门类下的“公安学类”一级学科之下。这是“犯罪学”首次被正式承认,学科地位也提升到二级学科。同样,在该目录中,侦查学归属于法学学科门类下的“公安学类”一级学科之下。因此,这两门课程应为边缘法学。北京大学2009版本科教学手册显示,司法精神病学、刑事侦查学等边缘法学也纳入了专业选修课。如吉林大学将犯罪学列入了专业选修课;山东大学将刑事侦查学、犯罪心理学边缘法学课程纳入专业选修课。其他开设的边缘法学课程如法律社会学、法律逻辑学。
关于边缘法学课程的开设,我们赞同此观点:由于大学的功能除了培养人才外,还肩负知识创新的任务。为此,大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教学,还需要形成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特色,同时也能适应国家对法律人才的特殊要求,并充分保证某些法学学科按照国家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要求向纵深方向发展,成为国家乃至世界的一流学科[9]。如果能延长学制(中国政法大学4+2),那么对于像湖南大学这类非政法类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可以采取法学学科及该校优势学科或者特色学科所在一级学科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即“法学学科+优势学科”或“法学学科+特色学科”模式。边缘法学不宜纳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但应鼓励开设边缘法学选修课,纳入大学而非法学院的人文素质选修课,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和拓展学生的思维,激发日后学习的兴趣。
[1] 王利明,常鹏翱.从学科分立到知识融合 我国法学学科30年之回顾与展望[J].法学,2008(12):58-67.
[2] 眭依凡.教学评估: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3):87-92.
[3] 李龙.论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J].中国法学,1997(6):57-61.
[4] 时延安.学科、领域与专业人才培养[N].法制日报,2014-1-15(10).
[5] 徐永康.十年来我国法学新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瞻[J].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4):3-7.
[6] 王晨光.法学教育中的困惑—从比较视角去观察[J].中外法学,1993(2):69-74.
[7] 何勤华.重视法学新学科建设[J].法学,1987(2):13-14.
[8] 央视对话.反垄断能否捍卫我们的利益[DB/OL].http://tv.cntv.cn/video/C10316/723a17154d2940 bbb913ed2c38901064,2013-08-25.
[9] 曹建明,孙潮.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与任务[J].法学,1993(2):14-16.
[10] 宋鸿雁.1992-2002年美国法学院课程调研[A].法学教育研究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39-266.
[11] 黄进.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观念、模式与机制[A].法学教育研究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11.
[12] 吴汉东,刘茂林.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若干个问题探讨——基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的思考和探索[A].法学教育研究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2-29.
[13] 李振宇.正确区分边缘法学、本体法学新学科[J].边缘法学论坛,2007(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