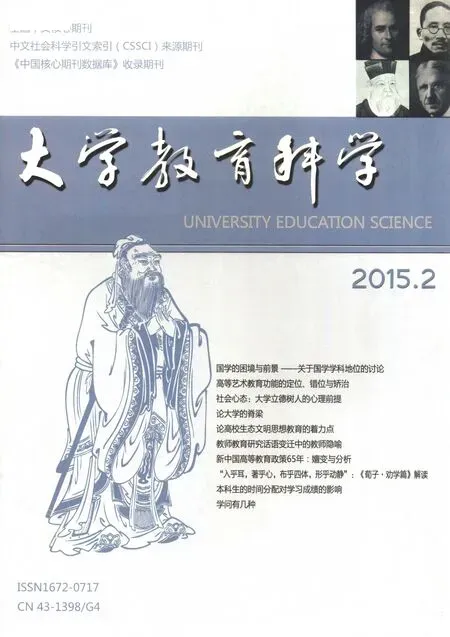论大学的脊梁
2015-03-31闫广芬
□ 李 忠 闫广芬
一
社会的延续与发展需要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培养创新人才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目前的中国大学显然难以承担这种职责。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无奈地向温家宝总理坦言: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创新人才”——“钱学森之问”不仅“很大地刺痛”[1]了温家宝总理,也成为中国大学以及大学人必须面对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只有社会上出现更多有灵魂、有眼光、有胸怀、有脊梁的大学,才能真正为创新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坚实土壤。”在2012年12月广西师范大学80周年校庆“高校与社会:高端人才培养的责任与途径”论坛上,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康宁就创新人才培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吴康宁看来,大学要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有自尊,这种自尊基于大学的脊梁。“不管你是北大、清华,还是广西师大、南京师大,我们都应当成为有胆量、有硬度的大学,并因此而成为自尊的大学。你不自尊,别人便不尊你。没有基于这一原则的脊梁,大学根本就没有培养创新人才的资格。因为创新人才的基本特征就是不依附,拒绝威权。”[2]吴康宁以师范大学教师、副校长的身份对“钱学森之问”予以回应,这种答案不仅来自对教育理论的领悟,更来自切身的教育经历、体验与体悟。
脊梁俗称脊背,为全身骨骼主干所在,引申为有意志、节操、胆识、信念和刚强不屈且能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即使无生命物质,脊梁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如山脊是维持山体的重要构成,桥梁是桥得以成形并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有生命物质,脊梁尤为珍贵,它甚至是物种进化程度的标识。对人而言,脊梁让人得以直立,是人成为人、人成为自己的标志,也是人与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组织之间的差异所在。大学脊梁由大学的精神及其支配下的理念、制度与行为铸成并从中体现。思想自由与人格独立是大学的精神。如何守护精神,不同大学有不同做法,大学的理念、制度与行为是这种做法的具体体现。作为知识精英汇聚之地与培养未来知识精英、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场所,大学需要有自己的脊梁,需要基于这种脊梁的自尊。
大学的脊梁使大学成为大学而非其他社会机构。因为,在所有人类公共机构中,只有大学能够超越当前准则,注意到未来的多种可能,并通过目前的判断注意到突发的种种机遇。大学通过自己的研究创新知识、创新价值观,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指明方向,使社会按照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而非相反;大学通过教学推广知识并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引领社会发展而非成为现存社会的被动适应者;大学通过专业技能考察知识并通过出版传播知识,校正可能出现的歧路并扩大影响,带动社会发展而不是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者。大学是人类把不可或缺的智慧世代流传的殿堂,大学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她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这需要大学有脊梁、能自主、有自尊、能担当,能够承担这种职责并扮演这种角色。没有基于这种脊梁的特质,大学将失去自我而雷同于其他社会机构。
二
大学脊梁的性质决定着大学是否在扮演或在多大程度上扮演着大学的角色。依附性的大学脊梁是扭曲的:依附于宗教的大学,扮演着教会角色;依附于政治的大学,扮演着政府机构角色;依附于利益的大学,扮演着企业角色。脊梁挺拔的大学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扮演着大学角色。她自主而不依附:大学知道,在现代社会,从自由向依附的任何倒退都是精神不健全的标志,因为这种倒退与人类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不相符合。她谦虚但拒绝权威:大学知道,与浩瀚宇宙相比,人类所知甚少,人类甚至对自身认识也极为有限,在未知面前,每个人都是小学生。她有远见且能持续努力:大学知道,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因为人类历史已经展示了无数的不确定领域,没有人能准确预测二十一世纪会发生什么事情。正如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莫兰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的报告所言:“今后人类征途的不可知的特点应该促使我们培养准备应付不测事件而处理他们的头脑。所有身负教育之责的人们应该走向迎击我们时代的不确定性的最前哨。”[3]教育是“未来的力量”,大学是改变现实与创造未来最强有力的力量之一。正因如此,大学必须有并全力守护自己的精神和脊梁:她有信念但不固执,她自尊但不自负,她谦虚但不自卑。
大学脊梁决定着大学对自己的定位及其思考与行为方式。大学有其共性,但一所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标志在于她所秉持的精神、理念以及对这种理念的坚守与践行程度,即大学的脊梁还使大学之间有了差异。大学的精神与理念以大学宪章方式体现,从大学的思想、制度与行为中呈现。为了“求是崇真”、追求“真理”而设的哈佛大学,恪守“察验真理”之旨,致力于“促进知识并使之永存后代”;为了使青年“学习艺术和科学”设立的耶鲁大学,追求真理、提倡质疑、反对迷信,永远强调责任感、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并崇尚独立人格;麻省理工学院秉持“手脑并用,创新世界”之理念,谨守学术精神、探究精神和评判精神,致力于解决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让“所有的人可以学到任何他想学的学科”而建成的康奈尔大学,持续致力于创造公平、平等的未来,反对盲从和不加辨析地接受。大学也在变,但精神不变,变化的是如何能更好地坚守并践行这种精神,使其脊梁更健壮。
大学脊梁的坚挺需要政府认识到大学特性并给大学以充分的自治,使大学能够自主,让大学先成为大学。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在著名的《学会生存》报告中指出:“一个官僚主义的、惯常脱离生活的体系会感到难于接受这样的想法,即学校是为儿童而设立的,而不是儿童为学校而生存的。上面发号施令,下面唯命是听,建筑在这样基础上的政权,不可能发展自由教育。在工作一般处于隔绝状态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要想培养学生爱好创造性的工作,这将是困难的。”[4]今日中国大学却正好处在这种困境之中。“钱学森之问”是一种现象、一个问题,吴康宁教授则给出解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约束。”政府部门通过校长任命、资源分配、等级区分等做法,“形成对大学的超强控制,我们的大学不是自己在办学,而是政府部门在办学,是政府官员在办学。”历史学家、前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先生则对“政府官员办学”的弊端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政府官员办学”的最大弊端在于把人当做物,忽视对人的有效关注:“从深层根源来剖析,主要问题仍在于主管教育者本身缺乏正确的认知。……现今教育当局主事者把各项重大措施都名之为‘工程’,实际上是忘记了人性不同于物性。”[5]
依附政治、政教合一是中国古典教育的突出特点,这种教育曾在维护统治以及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然而,它不健全。因为,依附性教育以工具或适应他人(或物)自居,以随从附和作为处事原则,无视自我的同时导致平庸,它培养出的是充满依附性、人格不健全的忠臣孝子。这种教育难以应对社会变革并引领社会发展,在面对列强军事、经济、文化侵略时举止乖张、捉襟见肘、弊端尽显,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成为众矢之的,终成被唾弃的对象。正是对单纯适应政治的依附性教育的变革,民国时期出现的一批有脊梁的大学,甚至在战时出现的著名的西南联大,不仅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与推动者,而且谱写了中国大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
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而非政府机关的延伸,是培养领袖人才的地方而非官僚养成所。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说:“大学校长的地位极其崇高,政府当局和整个社会应该把他们尊为宾师,决不可以视同一般之高级政府官吏,拘之以功令,困之以事务,使贤者裹足,不肖者滥竽,则庶几收领袖群英宏奖学术之效焉。”[6]因为,如果校长是官吏,在更高权力面前必须低头,在学校中又以长官面目示人,这种做法违背大学的基本精神。大学是有梦想的人的聚集之所,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这不仅需要大学有脊梁,同样需要大学中人有脊梁。
校长作为大学的舵手,首先要有脊梁。视“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的蔡元培,将北京大学改造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所,吸引大批学者云集,这些学者不仅使北大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成为新思想、新知识和新价值观的集散地,而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视大学为研究学问之所、实现理想之地的罗家伦,将“为学问殉道”视为人类最光荣、最高尚的事业,将“能唤起他人对于此事的觉悟”视为对社会最有实利的贡献,致力于清华建设,终使清华由留学预备机构升格为国立大学;视“大学为大师之谓而非大楼之谓”的梅贻琦,认为大学存在的价值体现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为达目的,筑巢引凤,在吸引大师的同时注重培养通才以便成就未来的大师,终使清华成为著名学府。竺可桢视大学为养成公忠坚毅、主持风会、转移国运领袖人才之所,恪守“务实求学,存是去非”之旨,为浙江大学赢得“东方剑桥”的美誉。为了抵制外来干涉,蔡元培先后五辞北大校长;为了维护校统,罗家伦毅然辞去清华校长。他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和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规化。”[7]
作为直接从事学术的研究者与创新人才的培养者,教授必须有脊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竺可桢说: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在竺可桢看来,大学的主要职责不是供给或贩卖现成知识,而是要开辟新途径、创造新知识,培养学生批判精神与反省精神,使学习者能够自动求知、持续研究与创造知识。这要求教授先有这种意识与能力,并具有将其贯彻下去的脊梁。这种脊梁,甚至重于教授拥有的专业知识。因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也未必具有独立精神和健全人格。爱因斯坦曾指出,具备了专门知识的人,“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情感,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8]脊梁扭曲的教授也会培养人,但培养不出脊梁坚挺的人。这样的人只能阻滞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正如吴康宁校长所言:如果我们的大学所生产的是一些陈旧的知识,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庸人、贪名逐利的邪人、趋炎附势的小人的话,那大学不仅不能引领社会,反而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帮凶和罪人。
大学生是大学人的绝大多数,只有他们有脊梁,我们的未来才会光明。大学生开始接触高深学问,以便获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智慧;开始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以便从容应对人生中的挑战;开始思考人生意义,以便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这不仅需要大学生自己做出持续努力,更需大学予以帮助与培养。大学首先要将学生培养成健全的人,即有自我意识——能认识自我;有德性——能成就自我;有理性——能认识他人和周围世界;有实践性——能实现自我;有创造性——能展现自我;有情感性——能与他人和周围世界发生联系。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脊梁。蒋梦麟说大学要帮助学生“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养成健全之人格”、“养成独立不易之精神”。胡适认为,独立的精神就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我们各个人思考的结果。竺可桢指出,浙江大学的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大学生本身对现实比较敏感,若大学以权力与功利加以诱导,后果堪忧。“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但我们绝不能陷死在现实的泥淖之中;若是陷落下去,必至志气消沉,正义感与是非心一道埋灭。”罗家伦曾如是告诫。
正是因为有脊梁,在短短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等一批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的大学,而战争中的西南联大更是这一时期大学的典范;正是这些大学、大学校长、大学教授致力于学生脊梁的培育,出现了一批精神丰满、脊梁健硕的学子,成为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与推动者。我们今天所谓的大师,都曾是那个时期的学生。
四
不可否认,在权力与功利双重作用下,今日中国大学的脊梁已严重扭曲,突出表现在大学对于政府部门、政府官员普遍的言听计从,亦步亦趋。“有些大学甚至像政府部门手中的机械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是落实政府部门的通知、指示、要求。”大学一旦惟命是从、脊梁扭曲,便会失去自我,成为行政命令的被动执行者。脊梁扭曲的大学在管理与培养人才方面会出现严重问题:权力之下,惟权是从;功利之下,惟利是图。在权力与功利之下,人人都得低头、弯腰,造成诸多内耗与浪费的同时,培养出人格不全、精神萎靡的人。“大学应当成为大学精神的守望者,坚守大学超凡脱俗的‘气节’。坚贞不屈地走大学自己的发展之路!”[9]因此,当大学没有脊梁、没有基于脊梁的自尊时,大学中人难有脊梁与基于脊梁的自尊,大学以及大学人将被异化而失去自己的个性、特点与特色。“只有拒绝依附,我们的大学才能成为有胆量的大学,有硬度的大学,才能算得上是一所有自尊的大学,这样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才有希望。”[2]吴康宁教授如是说。
只要大学还存在,就会发挥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有正面与负面之分。今日的痛苦,是昨日努力不够或努力方向问题造成的;今日创新人才奇缺,是昨日大学出现问题的自然结果。大学的脊梁是大学秉着自己的灵魂、精神、信念和不懈努力铸成的,不是通过赋予或怜悯赏赐给予的。有自尊的大学脊梁需要政府与环境的支持,同样需要大学以及大学人的努力。今日大学在培养未来社会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社会精英,如果这些精英灵魂失落、精神萎靡、信仰缺失、脊梁扭曲、惟权是从、唯利是图,那么,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从这个意义上看:善待大学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培育大学以及大学中人的脊梁就是在培育中国的脊梁,这需要政府、大学以及大学人共同付出努力。
[1] 温家宝.钱学森之问对我是很大刺痛[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05/c_1273985.htm.
[2] 谢洋.南师大吴康宁:不自尊的大学没资格培养创新人才[N].中国青年报,2013-01-17(03).
[3]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88.
[5] 章开沅.谁在折腾中国大学[EB/OL]. http://www.csstoday.net/Item/16964.aspx.
[6] 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胡先骕文存(上卷)[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423.
[7] 罗家伦.罗家伦史学与教育论著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8] [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74.
[9] 李震声,李斌,张蔚.论大气的大学[J].大学教育科学,2013(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