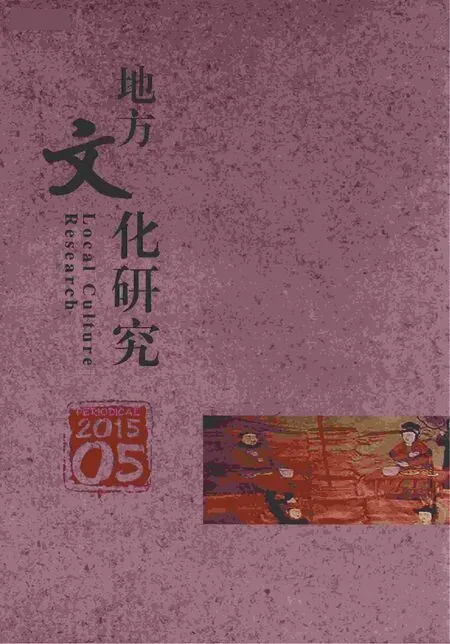潮汕海盗文化的“海丝”遗产价值研究
2015-03-30郑松辉
郑松辉
潮汕海盗文化的“海丝”遗产价值研究
郑松辉
(汕头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广东汕头,515063)
明清时期潮汕地区海盗活动十分猖獗,而且持续时间长,对海盗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的认知程度定义多种多样,对它的评价也多有争议。海盗活动带来了许多问题,对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海盗的猖獗活动业对明清两朝政府的压力。但客观上,他们刺激经济、发展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海盗的探索和开拓也扩大了世界贸易的商业空间,它们在商贸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潮汕“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演化,加速了这一地区与世界融合。笔者认为,潮汕海盗活动遗迹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有关部门应站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高度来重新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价值,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他们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海上丝绸之路;潮汕;世界遗产;海盗活动
从世界海洋发展史看,可以说自从人类学会造船,迈向海洋开始就有了海盗,海盗是海洋航运与贸易衍生的海洋社会群体。①杨国桢:《松浦章与中国海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3期。“海上丝绸之路”自古是很多人探寻的神秘所在,历史上的海盗活动也非常活跃,留下许多海盗活动的痕迹。潮汕沿海曾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节点之一,明清时期潮汕地方社会海洋文化进入发育转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海上贸易频繁,围绕着海盗问题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历史过程,
海盗活动几乎伴随着潮汕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全过程,造成了重大影响,在潮汕海洋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海盗行为在历史上一直被西方视为一种值得夸耀的海洋文明,西欧各国不但不掩饰他们祖先的海盗史,甚至将之当作一种文化加以弘扬,作为人类的一种海上行为,海盗活动几乎是海上贸易活动的衍生物,中山大学著名潮学研究学者陈春声教授认为,围绕着海盗问题所开展的种种活动,对后来的潮州社会和人们关于“潮州文化”的理解,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②陈春声:《明清之际潮州的海盗与私人海上贸易》,《文史知识》1997年第9期。所以,海盗文化是潮汕海洋文化的一个组成元素,也是构筑”海上丝绸之路”遗产完整性不可缺少,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痕迹,海盗活动及其历史遗迹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申遗的组成部分。
一、潮汕海盗活动的缘起
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私擅航行海上,以正义或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险费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海上武装集团。①刘平:《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周玄呻:《泾林续记》,《劝顺堂丛书》本。在海洋文化发展过程中,只要是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带,都有海盗活动的痕迹。西方海盗兴盛于帝国强盛时期。在西方,特别是北欧的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历史上一些“海盗国家”、“海盗民族”,都经历了他们所谓“海盗时代”。②杨国宜:《开拓创新,填补空白——喜读〈中国海盗史〉》(2007-01-10)[2011-11-21][EB/OL].http://www.huixue.org/bbs/show.asp? id=205&bd=2.(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283。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历史上,沿海地区居民很早就开始海洋谋生,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化。汉唐以来,海上交通、海上贸易、造船和航海技术、海上捕捞和鱼盐制造等等,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③杨国桢:《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283。在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发展史上,先民们在经营海洋生产和从事抢劫活动的同时,也有时反抗官府和土豪,因此被称为海贼、海盗、海寇、洋匪、岛寇、绿客等等。④陈支平:《郑成功海商集团兴衰的历史反思》,陈支平主编:《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5页(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卷134,《职方典》。学术界普遍认为潮汕是中国历史上海盗的高发区,特别是明清两朝实施“海禁”政策,使大量靠海为生的潮汕居民的生活日益艰难,他们不得不违禁下海通番,从事亦盗、亦商的活动。海盗问题伴随潮汕沿海商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频繁发生,使潮汕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的历史过程;而海盗活动和走私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带动潮汕沿海百姓也参与其中,沿海破产失业的渔民、水手下海为匪,甚至地方官员也经不住诱惑成为通盗之人。沿海社会的城乡贫民也视海岛为逋薮,航海商旅随之赀贩其上,并以不同方式移民海岛或往来于岛陆之间。⑤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5期。林大春:《井丹先生文集》卷8,《状疏表》,香港:香港潮州会馆.1980年影印。
从文献里可以找到许多有关海盗及其走私贸易的记载,潮汕地区很早就已有海盗活动,东汉永初三年(109),海盗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兵讨平之,⑥顺治:《潮州府志·卷七》,《兵事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册第590条。这是潮汕有海盗的最早记载。《宋史》卷27,“高宗纪”记载,南宋绍兴三年(1133),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毁城去。⑦《宋史》卷27《本纪·第二十七·高宗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第505页。甚至在史书上还出现海盗的首领名字,见诸文字记载的首例潮籍海寇是南宋的沈师,《宋史》称沈师为“潮贼”。南宋淳熙八年(1181),“广东安抚巩湘诱潮贼沈师出降,诛之。”⑧《宋史》卷35《孝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第675页。《东里志》对南宋沈师的海盗活动有更为详尽的记述,谓“先是海寇沈师犯南澳,万里合诸郡兵讨平之。”⑨(明)陈天资:《东里志》卷2《境事志·灾异》,汕头市方志委员会、饶平县方志委员会办公室印行,1990年,第48页。清郭春震的《潮州府志》记载,“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⑩(清)郭春震:《备经论》,乾隆《潮州府志》卷40,乾隆五十年(1785年)刊周宣帏的《泾林续记》云“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已资市物往贸,利恒百余倍。”①刘平:《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周玄呻:《泾林续记》,《劝顺堂丛书》本。“迩来漳泉等处奸民,倚结势族,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用器,收买奇货,诱博诸夷,日引月滋。”②杨国宜:《开拓创新,填补空白——喜读〈中国海盗史〉》(2007-01-10)[2011-11-21][EB/OL].http://www.huixue.org/bbs/show.asp? id=205&bd=2.(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283。“臣访得番徒海寇,往来行劫须乘风候。南风汛,则由广闽而浙,而直汪洋;北风汛,则由浙而闽而广,而或趋番国。”③杨国桢:《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283。《古今图书集成》卷134《职方典》记述,“饶(饶平)邑滨海信宁都乡民持险为恶,接济番舶,劫掠行舟。”④陈支平:《郑成功海商集团兴衰的历史反思》,陈支平主编:《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5页(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卷134,《职方典》。根据林大春《论海寇必诛状》记载,当时潮汕“舟楫往来,皆经给票,商旅货物,尽为抽分,是沿海之舟楫商旅,无一而非海寇之人也。”⑤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5期。林大春:《井丹先生文集》卷8,《状疏表》,香港:香港潮州会馆.1980年影印。海盗的出现,加剧了朝廷统治的危机,引起朝廷官员的警惕和惊慌,地方官员上奏大呼“查洋盗向为广东、福建为最,江南、浙江次之。广东洋盗又多在潮州、惠州二府。”⑥顺治:《潮州府志·卷七》,《兵事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册第590条。雍正年间柘林港进入繁盛时期,当地兴起“红头船”海运之风,商民大造“红头船”300余艘,航行于台湾、广州、上海、天津、宁波、福州、泉州等地,蓝鼎元在其著作中指出:“抑愚闻在洋之盗,十犯九广;则弭盗之法,尤宜加意于粤东。”①(清)蓝鼎元:《论海洋弭捕盗贼书》,见(清)贺长龄等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5,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第2189页。(明)何乔远:《闽书》卷40,崇祯二年刻本。
关于潮汕海盗活动的成因是人们普遍关注问题,《中国海盗史》一书的作者、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郑广南在纵观中国海盗活动的全过程后,提出自己客观、独到的见解,认为海盗兴起的具体原因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分别论定。②郑广南:《中国海盗史》,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3页。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843条。如果从海上贸易史考究,潮汕的海上贸易开始年代远在广府和福建之后,潮汕沿海居民是因为福建的影响才开始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群体较松散,贸易规模远不如广府及福建的泉州等地,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但潮汕却在明清时期兴起庞大的海盗集团,出现大规模的海盗活动,成为是中国海盗的高发区,这是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首先,潮汕沿海海盗活动频繁,与其特殊的环境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潮汕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客观上为海盗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现代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这种客观环境主要就是自然地理环境。③许平中:《中西历史进程差异的地理基础》(2009-5-27)[2011-11-21][EB/OL].http://www.zkxww.com/PAPERS/lunwen/wenhua/lsx/ 200905/114816.html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2年。美国学者穆黛安(Murray,D.H.)指出,从海盗的角度来看,一条无数水道纵横交错、可以藏身其中的海岸线及其附近大大小小的岛屿所能提供的保护,乃是最为适宜的地理形势。④(美)穆黛安(Murray,D.H.)著;刘平译:《华南海盗:1790~18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页。林济在《潮商史略》一书论述,潮汕海寇的产生,是与其海疆边陲地位密切有关。由于王朝官府统治力量的薄弱,这里的居民长期不受约束,其行为常常是在王法允许的范围之外,活动也常常脱离官府的管辖。⑤林济著:《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49页。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航海家、曾任沿海边防要职的陈伦炯认为潮汕“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粤之贼艘,不但舰海舶,此处可以伺劫,而内河桨船橹船渔舟,皆可出海,群聚剽掠。粤海之藏污纳垢者,莫此为盛。”⑥(清)陈伦炯:《天下沿海形势录》,见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28页。潮汕地区的河流连成水运网络,与内陆腹地沟通,便于内陆特种农业产品的外运,所以潮汕自古航运发达,潮汕“拓林、黄冈、南澳、樟林、东里、达壕、海门、神泉等处皆为出洋之口。”⑦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商业》,香港:龙门书店,1965,第102页。“粤东三面皆海,千樯云集,各省商民及外洋番估携资置货往来者甚多。”⑧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册410条。
显然,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优良的港口,使潮汕具备了发展海外贸易的先决条件。同时,潮汕的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又为盗寇随地藏匿和逃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得盗匪在这些海域出没无常,朝廷防不胜防。到了在嘉靖后期,潮汕的拓林港及南澳岛就成了当时西方及日本走私商人活动的场所,特别是闽、广交界的南澳,位于韩江入海口,独立于大陆之外,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亦是走私贸易的交接之地和海寇往来的必由之地。⑨廖大珂著:《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225页。南澳周边海域有许多岛屿,“少人屯聚,地甚辽阔而又有险可据。”⑩(清)邢定纶,(清)赵以谦纂修;郭沫若点校:《崖州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3页。《闽书》卷40载:“南澳在漳、潮二州海岛中,四面阻水,可三百里,潮则通柘林,漳则通玄钟,”①(清)蓝鼎元:《论海洋弭捕盗贼书》,见(清)贺长龄等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5,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第2189页。(明)何乔远:《闽书》卷40,崇祯二年刻本。这些走私贸易港或地处航海要冲.地蛰险要,或地处偏僻,统治阶级鞭长莫及,对于海上的走私和海盗活动,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打击海盗也互相推诿,“巡海官兵遇有歹船,妄执闽粤疆界之分,不肯穷追;及至失事,则互相推诿;迨委员会勘,又复转辗耽延。”②郑广南:《中国海盗史》,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3页。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843条。而洪武初年为巩固海防.将岛民内迁,不少岛屿被废为荒岛.一度弃守,岛上没有任何官方机构管理,正是防务上的漏洞造成海盗多活动于此,常为盗匪聚集的场所。③许平中:《中西历史进程差异的地理基础》(2009-5-27)[2011-11-21][EB/OL].http://www.zkxww.com/PAPERS/lunwen/wenhua/lsx/ 200905/114816.html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2年。潮汕地区的海盗集团大多以南澳岛为根据地,南澳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岛屿一直是各国商人的交易场所,也演变为海寇巢穴,成为东南沿海的最大走私据点,吴平、曾一本、杨老、林道干、诸良宝等著名的海上武装集团,都曾以该岛为根据地,以致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称南澳“内宽外险,腊屿、赤屿还处其外,一门通舟,中容千艘,番舶寇舟多泊焉。”①(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3,台北: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冷东:《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10期。海寇商人集团经常以此为基地,出没沿海一带,经营其“亦商亦盗”式的走私贸易。②李金明,廖大珂著:《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易建成:《潮汕也是“海上丝路”大港口》,《羊城晚报》,2002-07-03[B14]。以至与自明以来,“屡为寇垒。”③《潮州海防图说》,蓝鼎元:《皇朝经世文编》卷83《兵政14海防·上》,善化贺长龄耦庚辑。“番舶、海蔻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抢掠。”④(明)陈天资:《东里志》卷1《疆域志》,“澳屿·长沙尾”条,汕头市方志委员会、饶平县方志委员会办公室印行,1990年。饶宗颐在《潮州志汇编》甚至认为南澳为“倭之巢穴也。”⑤饶宗颐:《潮州志汇编·大事志》,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第655-667页。当时的番舶寇舟“广捕之急则奔闽,闽捕之急则奔广。”⑥(明)茅元仪:《武备志》卷213,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刻印本。
其次,潮汕海盗活动的与海上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性的小传统受到西方海洋人文的冲击,转而走向海上走私贸易的道路。它以与海外的海上走私贸易和海洋移民拓殖与反馈为基本形式和途径。⑦李德元著:《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宋、元两代,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促成了东南沿海海路的开通,各种商船北航东洋,南下西洋,来往频繁,潮汕沿海海域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通道,潮汕成为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潮汕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为潮汕地区的海洋文化注入了一股新的重要活力。⑧李德元著:《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明中叶以来,受海洋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沿海地区居民纷纷造船置货,违禁下海通番。很多集海盗与海商两位一体的海上走私者,不顾政府“禁海”、“迁界”的政令,私造商舶出洋通贸,从事亦商亦盗的活动。⑨唐文基主编:《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6页。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潮汕逐渐成为粤东、闽西南和赣南地区物资集散地和出入口岸,成为明代东西洋海上贸易中继站,到国外进行自由贸易,牟取利润为目的的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崛起。⑩李金明,廖大珂著:《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明政府厉行海禁.残酷打击走私贸易的情况下,有些走私商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武装起来,组织成走私集团.以对抗官军的追捕和残杀,这就是明代海外贸易史上的所谓“海寇”。①(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3,台北: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冷东:《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10期。这些走私集团采取武装手段甚至联合国外势力对抗朝廷,遂以武力对抗海禁转变为武装海盗集团,如此恶性循环,海盗之患愈演愈烈。②李金明,廖大珂著:《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易建成:《潮汕也是“海上丝路”大港口》,《羊城晚报》,2002-07-03[B14]。
二、潮汕海盗活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黄伟宗曾率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专家考察团深入汕尾白沙湖、澄海樟林港、凤岭港和潮州饶平柘林港实地考察寻古,并认为:潮汕地区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沿潮汕地区的这些古港,再到广州,及至粤西的徐闻,已经形成了一条脉络分明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贸易路径,它们在我国古代的不同时期交替兴起、繁盛,构成了古代“开放广东”的生动写照。③《潮州海防图说》,蓝鼎元:《皇朝经世文编》卷83《兵政14海防·上》,善化贺长龄耦庚辑。潮汕海商和海盗以海上贸易为舞台,打破中国闭关自守、实行自由贸易之机,开拓国内外商贸、侨批金融活动,并形成重要的红头船商帮。潮汕海盗活动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潮汕节点的形成与演进作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潮汕周边海域、海岛的开发,为“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停靠点
潮汕因为海岸线长,有许多天然的岛屿,潮汕人素有出海谋生的传统。由于明朝官府实行“海禁”,原有的航海通商贸易港口都被严查,潮汕海商只好将货物集散地、交易场所、仓储、补给基地等转移到沿海岛屿或偏僻港湾,而这些朝廷难以驾驭的港湾、岛屿更成为海盗们屯驻、接济的重要基地。沿海社会的城乡贫民也视海岛为逋薮,航海商旅随之赀贩其上,并以不同方式移民海岛或往来于岛陆之间。①吕淑梅:《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第34~35页。从史书记载可以发现,潮汕海盗和海商先后开辟南澳、牛田洋等港口作为海外贸易的基地,从事海上武装走私贸易,招引日本与西方海商到前来互市。除开发海岛外,还开拓了一些贸易基地与港口,这些地方很快成为新兴港市,交易繁盛,可以说,潮汕沿海,特别是南澳海域之所以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与海盗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吴平等海盗就以南澳为据点,使南澳发展成为一个良港。牛田洋、拓林等也都是海盗和民间海上贸易新开辟出来的港口。《潮汕志·商业》载:“大抵海运既兴,如柘林、黄冈、东里、达濠、海门、神泉等处,皆为出洋之口,巨舶往来海上,运土货至广州及闽、浙,或远达南洋、日本,转贩外货输入。至于国内贸易,则以糖为大宗,明代东里此业尤盛,遍及国内沿海各地。”②饶宗颐:《潮汕志·商业》,香港:龙门书店,1949年。所以,李德元先生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周围的海岛有很多是被海上走私贸易者开发出来的。③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第二、开辟了海洋新航线,推动造船业发展。
海上活动需要高超的造船技术,海盗活动也推动了潮汕造船业的发展。海盗在长期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中,随着潮汕沿海地区居民开始大规模进行海上商业冒险活动,特别是明代后期海盗活动的兴起和盛行,潮汕海盗长期活跃于海洋中,海盗们适应需要,“私造大船”、“下海通番”,所以,潮汕海盗非常重视造船技术的提高,他们除了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打造大量巨型舰船,也在本土建造船舶,对潮汕本土造船业的发展与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推广起了推动作用,及至清代,潮汕海盗拥有舰船连官军水师也望尘不及。雍正年间,当时港内常泊着数百艘各类船只。当时兴起了“红头船”海运之风,商民大造“红头船”300余艘,航行于台湾、广州、上海、天津、宁波、福州、泉州等地及海外吕宋、安南、暹罗等国家,遍历诸部,扬帆而去,数月后满载而归,金宝溢于衢路。④杨晓红:《古沉船富矿南澳:中国“百慕大”》,南方都市报,2010-06-23(OT08)。
造船技术的发展,使潮汕海盗在长期海上走私贸易活动中能不断开辟海上航线,为了贸易需要,他们在开辟与拓展海外航线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知识,了解和熟悉了海洋情况,经过海盗与航海者长期共同努力开辟海内外交通航线,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网,海上交通路线日益广阔拓展。所以说,海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骚扰者和破坏者;但他们又是打通“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勇猛人物,无形中促进了造船业、航海技术的发展壮大。⑤黄晶:《在三亚建座海盗博物馆》,《海南日报》,2009-2-16(6)。这对促进南北地区与沿海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推动了我国同世界各国通航和进行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⑥郑长青:《填补我国史学研究空白的专着——浅评〈中国海盗史〉》,《福建电大学报》2000年第2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潮汕节点的形成。
第三、转口贸易拓宽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
16世纪,在环中国海贸易圈内,传统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社会经济逐渐被纳入到近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环中国海贸易圈出现了激烈动荡的局面。⑦崔来廷:《16世纪东南中国海上走私贸易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4期。潮汕海盗持久、规模化的民间海上走私贸易,不仅带来了中外物流的交换,而且使潮汕经济活动能够被纳入到当时的世界海洋经济和全球性的市场之中,特别的在明清两代,潮汕地区的海商和海盗在“海上丝绸之路”有了更多的作为,其对外贸易明显体现出“中转贸易”的特点,也逐渐被纳入到刚刚兴起的世界贸易网络。
东南亚是最吸引潮汕商人和海盗的贸易和移民空间,其原因是东南亚与潮汕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最近,许多地方尚待开发,因此,东南亚不少国家对外来移民没有限制,甚至给予潮汕移民许多优惠政策,如免交一部分规礼、通事费及买办费等,这无疑吸引潮汕人,包括落魄的海盗选择移民东南亚。为逃避朝廷追捕的海盗移居海外后,也参与所在国和潮汕间的贸易往来,而且还以潮汕为中转站,积极从事所在国与广东以北各省的贸易往来,一方面从外地运来潮汕所需的手工业原材料和日用工业品,另方面向沿海城市输运西方商人从外洋进口的鸦片、洋货和潮汕本地生产的土糖、陶瓷、刺绣及其它土特产品。在更广阔的空间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为中国海商贸易网络的扩展创造了一个有效的外部经济贸易网络。为了适应与各通商口岸贸易交往的需要,他们一些与本土潮商一起先后在一些港口城市设立行号或派伙常驻其地,专事推销潮汕土货、经营转口贸易和采办外地货物来汕销售的业务,与全国中心市场以及东南亚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
三、潮汕的海盗活动史迹及申遗价值
(一)潮汕海盗活动史迹概况
历史上漳林、汕头、饶平、南澳等港口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海港,留下许多与海盗相关的历史遗迹,以南澳为例,由于南澳地处粤、闽、台三省交界海面,素有“闽粤咽喉、潮汕屏障”之称。南澳岛有悠久的人文历史,早在距今8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南澳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今天,南澳岛及周边海域留存许多海盗活动的历史遗迹,全岛已发现和修复的文物胜迹达50多处,其中有陆秀夫、戚继光、郑成功、刘永福抗侵御侮、俞大猷剿贼、郑芝龙抗荷、林则徐查禁鸦片等辉煌的海防史迹。其中不少史迹与明清潮汕的海盗活动息息相关,如南澳岛深澳湾旁有一个名为“吴平寨”的村庄,是中国唯一以海盗的名字命名的村庄。吴平明嘉隆年间(1521~1572),活跃在南澳岛的众多海盗首领之一,而位于深澳镇东北角的吴平寨,至今仍有30余户吴姓人家居住。明嘉靖年间,盗匪吴平即在此占寨聚众为王,后被戚继光一举剿灭。岛上人还多称吴平寨一带为“贼坳”,而金银岛则传为藏宝之地。同时期活跃在南澳附近海域的其他比较有名的海盗还有林国显、许栋、许朝光、林凤、林道乾、曾一本等。南澳的总兵府是明万历四年(1576年)由副总兵晏继芳建,为明、清副总兵和总兵驻地。现在原总兵府旧址建成了全国第一座海防史陈列馆,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是广东省唯一县级海防史专题博物馆。而“南澳Ⅰ号”是一艘沉没于汕头南澳“三点金”海域的明代古船,船载万余件瓷器,“南澳Ⅰ号”是一艘明代沉船,长35米、宽8米,沉没于汕头南澳“三点金”海域,“南澳Ⅰ号”的抢救性发掘,被评为2010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教授单世联认为,“南澳Ⅰ号”的水下打捞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研究明代瓷器、岭南文化及中外交通史提供了大量文物资料。①李刚:《“南澳Ⅰ号”水下考古抢救发掘启动》,《人民日报》2009-10-23(06)。
(二)潮汕海盗活动史迹的申遗价值
海盗行为在历史上一直被西方视为一种值得夸耀的海洋文明,西欧各国不但不掩饰他们祖先的海盗史,甚至将之当作一种文化加以弘扬,纵观中华区域海洋文明,潮汕的海盗史其实是潮汕人与海洋的关系史,它贯穿着潮汕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全过程。明清两朝的“海禁”与潮汕海洋文化的价值趋向完全悖逆,造成潮汕海洋文明发展的扭曲态势,出现了亦商亦盗私人海洋行为,而在官府的眼里,亦商亦盗私人海洋行为都是违法的,而且在朝廷文献里,他们被冠以“寇”或“盗”,但如果客观地分析,虽然海盗活动的表现形式是扭曲的,但是它却是最持久、最顽强反抗着封建专制与闭关自守,并与之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也正是这种冲突,使中国在世界大潮席卷而来时,打破了明清统治者企图以“海禁”把中国阻拦在世界潮流之外的治国理念,在潮汕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连锁性作用,促进潮汕社会的海洋化发展。在反海禁的斗争中,这些集海盗、海商于一身的海盗现象有其代表和争取区域社会利益的正当性。其实,明清之际潮汕沿海的海盗活动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以“非法”的身份彰显地域商业势力,并能与老欧洲殖民者进行对话的海洋力量。持久、规模化的海盗活动,不仅带来了中外物流的交换,而且使潮汕经济活动能够被纳入到当时的世界海洋经济和全球性的市场之中,表现出了早期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一些特征,造成了一股地域性海洋商业文化景象,对潮汕“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历史作用。
英国学者格温·琼斯(Gwyn Jones)在他那部被誉称为海盗史“经典之作”的《北欧海盗史》专著中,肯定了对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海盗国家历史上的海盗活动对贸易、发现、殖民和对受影响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化、习俗所做的贡献。在西方,海盗国家和民族以当海盗为荣,视海盗为海洋勇士,英国人特设“海盗节”,有以“海盗”命名的球队,航空与航天器亦有以“海盗”命名的,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可以看到海盗的“身影”。丹麦哥本哈根的《海盗报》,则以滑稽幽默而出名。此外,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市立博物馆、渥太华全国人类博物馆和芝加哥博物馆,都举办过与海盗相关的展览,吸引众多观众前往参观。西方对海盗的客观评价也影响到中国海盗史的学术研究。国内学者近年来亦逐渐重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海盗活动问题。有不少人涉足“中国海盗”这一看来颇为冷门的研究领域,试图为公众和学术界勾勒出一幅中国海盗的奋斗史、辛酸史。雪珥的《大国海盗》一书,就体现了这种努力。郑广南教授所著的《中国海盗史》一书,则应该说是国内有关海盗最早的一部通史。于是,一些沿海岛屿富裕起来的居民们,开始看中海盗文化的进一步开发。浙江台州三门湾蛇蟠岛决定利用其自然历史地理资源,开发“海盗村”风景区,供游人瞻览,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潮汕的海盗文化遗存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物遗产的一大亮点,对研究我国海上运输贸易活动乃至我国的陶瓷史、航海史意义重大,也提供了汕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宝贵历史见证资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补充,完全可以成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亮点。
四、潮汕海盗文化遗存的申遗思路
海盗活动伴随着潮汕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全过程,在汕头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节点上曾造成了重大影响,海盗们挺而走险,遁入盗蔽,是在生存环境发生变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选择。潮汕海盗由形成、兴盛至衰落的整个过程,客观上在我国海港史和航海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潮汕海盗活动的历史遗迹,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资料,完全可以成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由,确立海盗文化作为申遗的遗产元素,是申遗的一个亮点,将填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空白。遗憾的是,目前,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过程忽略了海盗文化的存在,海盗文化作为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汕头应该调查、收集和海盗相关的文献、历史遗迹,研究海盗活动对潮汕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潮汕海盗文化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是涉及历史、民俗、文化、考古、交通、生物、环保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合作,共同努力。对此我们建议:
1.客观评价海盗活动,提高全社会对海盗文化的认知度。
在宣传上提升海盗文化在潮汕海洋文化的地位和历史价值,尤其是提高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知名度,提高全社会对海盗文化的认知度,增强全社会和全民对海盗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客观、公正地对待潮汕海盗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探索海盗文化的形成,从海洋文化的视角考量海盗现象及其在潮汕海洋文化形成发展史的作用和在潮汕曾造成的影响,给潮汕海盗文化一个客观评价,期盼能更深层地理解潮汕海洋文化的各种组成元素,扩展潮汕海洋文化研究的空间,将其作为研究潮汕海洋文化必不可少的内容。
2.凸显文化亮点,着力塑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南海Ⅰ号”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凝聚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历史信息,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出水已成为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文化事件。因此,应该以“南海Ⅰ号”为契机,大力发掘海洋文化遗产,充分展示广东省作为海洋文化强省的文化标志。
3.整合海盗文化遗产资源,精心设计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潮汕遗存的海盗文化遗迹与文物极为丰富,具有多方面独有的重要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可以借鉴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以“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澳岛海盗文化”为核心,精心设计项目,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以金银岛为中心,把南澳岛建设成国内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功能的“海盗文化”主题园区,开发航海、探险、海盗、水下观光等旅游项目。
四、小结
如上所述,潮汕海盗的性质是比较模糊,难以清晰划定。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潮汕海盗活动既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也是应对西方海外扩张殖民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他们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是草根群体组合,没有西方的殖民主义性质。潮汕海盗长久以来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自始至终受到朝廷的围剿和打击;而归纳海盗行为的形成与过程可知,商业利益为最主要的,正如孟庆梓所言,明代中后期,倭寇与海商具有共同行动的表现,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本质上的不同点。从中国内部来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海商具有反海禁的进步性。而倭寇则是侵略性的。①孟庆梓:《明代的倭寇与海商》,《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认为陈春声教授对潮汕海盗活动的论断更为客观,他认为,只有真正了解当时潮汕地方社会这种民盗难分、甚至民盗“合一”的情势,才可能深刻理解自明代中期开始的乡村军事化过程,及同时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性质和意义。②陈春声:《韩江流域的社会空间与族群观念》(2011-5-12)[2011-11-21][EB/OL].http://isites.harvard.edu/fs/docs/icb.topic276877. files/Chen%20Chunsheng%20abstract.doc。
笔者没有为潮汕海盗翻案的意思,其实,不容置疑的是,潮汕海盗行为是一种无序行为,潮汕沿海的海盗活动由于历史的原因,其活动的掠食性是客观存在的,不必回避和否认。海洋文化的移动性表明它天然地与贸易相联系,海洋的变幻莫测自然使得海洋文化崇尚拼搏、冒险精神,当以世界视野和发展眼光评判潮汕的海盗活动,既可以看到其消极、野蛮一面,即海盗集团以武装走私和武装掠夺为手段,海盗的活动也确实对沿海地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烧杀、抢劫等无穷灾难,甚至寇盗勾结,导致潮汕倭患更加严重;在“亦商亦盗”过程中,其行为对朝廷威胁更大的是有些海盗和倭寇相勾结,加剧了潮汕的倭患。史载:“自是倭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从向往。而艅艎在海中者,亦无以菽粟火药通,往往食尽自遁。”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50页。“倭寇拥众而来,初以千万计而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济以水米,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响导,然后敢深入海洋。”④(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67《胡少保海防论》,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所以,频繁的海盗活动,对潮汕乃至东南沿海地区话多或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破坏了社会秩序,以至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来打击海盗,维持潮汕的治安,以巩固其统治。但潮汕的海盗活动是潮汕地域群体以一种特有的形式和方法争取区域自身利益的活动,海盗们遁入盗蔽,是在生存环境发生变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选择。
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潮汕海盗活动有诸多消极因素,如对当时社会的整体管理产生冲击,也影响了后来潮汕正常商业活动的进行,甚至危及社会安定,但海盗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催生潮汕海洋文化的内生增长因素之一。潮汕的这些海盗的活动确实也在发展贸易、开发海洋、促进各地社会进步方面,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其海上走私贸易的实践活动在客观上有助于当时潮汕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是试图用一种“非法”的手段把中国货物输出到世界市场的一次努力尝试。①孟庆梓:《明代的倭寇与海商》,《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5年第1期。海盗活动冲破明清两朝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走私海外自由贸易,同各国通商,海盗与海商走私开放海外自由贸易,同各国通商,这种现象和行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向,是有进步意义的。②郑长青:《填补我国史学研究空白的专着——浅评〈中国海盗史〉》,《福建电大学报》,2000年第2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没有必要掩饰潮汕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海盗史,而应该肯定这种海盗活动对潮汕地区社会状况、经济结构,乃至潮汕整个海洋文化的最终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肯定其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海上贸易的兴起和繁荣,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发展,推动潮汕“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正如陈春声教授在谈到明清之际潮汕海盗活动的社会意义时所言,潮汕的海盗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内容。”与海盗和反海盗的一系列活动相联系,使“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有了新的内容。”③易建成:《潮汕也是“海上丝路”大港口》,《羊城晚报》,2002-07-03[B14]。而这些所谓的新内容,当然包括潮汕地域文化的海洋化转型。从这个角度看来,海盗文化可视为潮汕地域社会整体历史脉络的一个环节,也是潮汕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页。所以,海盗文化是构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完整性不可缺少的要素,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痕迹,海盗活动及其历史遗迹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申遗的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吴树生)
Research on the Heritage's Value of the“Maritime Silk Road" of Pirate Culture of Chaoshan
Zheng Songhui
(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 Guangdong,515063)
There are pirates in the early oceans history of the world.Piracy was rampant in Chaoshan area,and last a long tim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cognition on the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irate in the history is varied,whose evaluation is controversial.Piracy,however,brought a lot of problems,for example,it affected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and rampant pirate activities gave pressure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But objectively,they stimulate the econom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de development,and the pirates’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lso expanded the business space of the world,in commercial activities,it furtherly promoted th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haoshan"Marine silk road",accelerated the fusion betwee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The author thinks that,chaoshan piracy sites are part of the"Marine silk road"as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stand at the heigh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to rediscover the heritage value of"Marine silk road",and take feasible measures to declare the"World Heritage List".
Marine silk road;Chaoshan;W orld heritage;Piracy
K928.6
A
1008-7354(2015)05-0035-09
郑松辉,男,汕头大学医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英国T he Electronic Library杂志顾问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