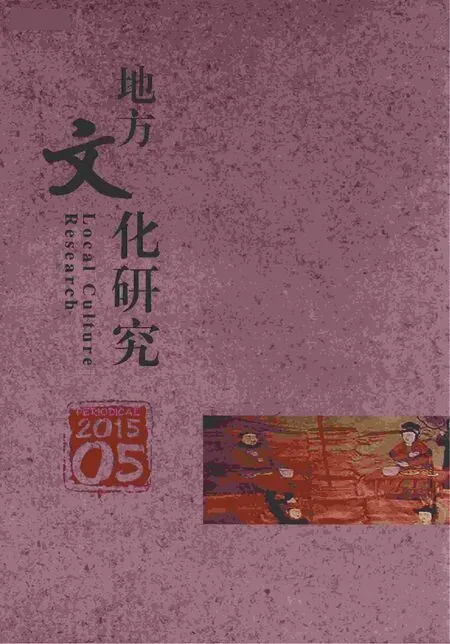民众记忆、文化身份与故事讲述传统
——以重庆走马民间故事为例
2015-03-30穆昭阳
穆昭阳
民众记忆、文化身份与故事讲述传统
——以重庆走马民间故事为例
穆昭阳
(赣南师范学院文旅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民间故事作为民众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承担了言传身教的功能。通过传统的讲与唱的故事讲述活动,向听众传授了丰富的民间知识和地方传统,也实现了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走马民间故事承载了千百年来巴渝大地广袤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为走马古镇的文化品牌,不仅凸显了古镇民众的历史记忆,也成为代表古镇特色的民俗传统。走马民间故事与它的讲述者们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成为显示地方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
走马古镇;故事讲述;民众记忆;民俗传统
走马古镇的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有故事讲述的杰出代表,即被合称为“东方格林兄弟”的“特级民间故事家”魏显德和魏显发(均已去世)。曾经的走马古镇作为驿道停留的小站,往来客商及各色人等络绎不绝,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停歇处的人们为了解除旅途疲劳和舒缓心情,将自身所携带的各种故事、段子等形式多样的叙事以口述的方式表达。于是在走马古镇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形成了浓厚的讲述氛围。客栈、地头、茶坊等场合常常成为当地村民和外界过往行人的交流地。经过不断地交流与文化融合,众多反映巴地历史文化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继承下来,成为传授当地人文礼俗和知识经验的极好素材。许多当地的人民也参与到讲故事与听故事的行列里来,慢慢形成了浓厚的讲述环境。走马古镇因此而成为故事的汇集地,当故事讲述积淀为一个地方的民俗传统之后,就会更加稳定。
在走马古镇这个半开放的特定区域内,口头交流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流行事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众多的口述信息加以完善之后,形成较为固定的故事文本,最终经由地方知识精英和其他普通讲述者共同传承下来。无数代的人们共同参与了口耳相传这一民俗传统的关键环节,在话语表达方式和传讲内容上达成了基本认同。这是集体的智慧和经验所得,并经受了历时的考验而最终成型。故事讲述带有集体性的特点,在古镇民间故事的叙述中也展现了镇民对生活地域文化的认同。这种集体的叙事行为能够成为地方历史记忆建构的必备要素。
一、故事讲述与历史记忆
传统的故事讲述活动,在传授民间知识的同时,也实现了人的情感诉求和情绪表达。讲述内容也体现了讲述者的个人思想、信念、世界观及价值观等等,并将此种知识谱系和源于生活、生产的感受和经验传播给他人。“讲故事是支持记忆、保存过去,激活以往体验乃至构建集体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①[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3页。因此,在传讲的过程中实现了一地知识体系的传播,造成了民众的适应性接受和广泛认同。民间故事的讲述内容不仅与讲述人本身的生活经历有关,还与其所生活地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事件有密切联系。民间故事的内容中一定存有人们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记忆,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民间故事,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历史记忆,有真实亦有虚构。我们并不探讨对虚构与事实的区分,而应该去思考在现实生活场域中所形成的这种故事讲述传统中所传达的民族记忆信息。“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他们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当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时候,他们必须为此创造出可以共享的资源,获得形成社会记忆的契机。”①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民间故事的叙述带有一定的人类记忆,在传递业已形成的集体的社会记忆同时,也掺杂了个人的记忆。记忆使得民间故事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命内涵,得到了应有的文化地位。
“在历史记忆里,个人并不是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所以说,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②[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走马民间故事中承载了当地人们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和体悟,还有许多地域性的知识和风俗,以及某些历史事件在民间流传的样态等等。这些都建构并丰富着走马民间故事的内涵,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故事讲述里所传达的地方民众记忆。在已出版和印行的有关走马民间故事的内容中,对于地方地名的故事与地方文化也占到一定比例。③如《重庆九龙坡》(《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牛王会》、《山王会》、《药王会》、《秧苗会》、《四月八嫁毛虫》、《八月十五天门开》、《识相不识相,难过走马岗》、《赵云过走马岗》、《居廷鸡》、《女儿丘》、《躲子山》、《转山坪》、《冬笋坝》(《魏显德民间故事集》),《龙王坝的传说》、《回龙湾的来历》(《走马镇民间故事》)等。关于走马古镇附近转山坪的来历,魏显德与陈富其都有各自的讲述。
话说叶小娃成了仙,玉皇大帝就封他为“一山大仙”,还赠了一条“赶山鞭”给他。这条鞭子厉害,河流堵塞,大山挡道,那鞭子一挥,河流畅通,大山让路。叶小娃赶山累了,就要回龙宫洗澡,虽然腾云驾雾,他也感到还是有些麻烦。于是,他就想:何不自己造一个浴池呢。
这一次,他到了重庆,一看那地势,还真是一个理想浴盆。如去赶一座山,把北碚口一堵,就是一片汪洋,成为我的浴池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本地的土地佬,土地佬不同意,但又不敢惹他。叶小娃的赶山鞭虽厉害,但只要天亮,就失去法力。于是,土地佬决定拖住叶小娃。
趁着夜黑,叶小娃抓紧时间赶山、修浴池。到了白市驿与北碚相近的地方,叶小娃坐着歇气。土地佬跑来说:“叶仙,我们来下盘棋。”叶小娃说:“我不下来,我还要忙着赶山呢。”土地佬说:“下棋好耍得很,我教你。”叶小娃想,山也赶得差不多了,剩下一点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同意下棋。土地佬有意拖延时间,慢慢教,叶小娃觉得新鲜,专心学棋。不知不觉,鸡公叫了,天亮了。叶小娃这才想起干山的事,大叫:“坏了,坏了”。土地佬说:“叶仙,你修浴池会闯下大祸,你若把北碚口堵了,要淹死好多生灵。”
土地佬把这事向玉皇大帝报告了,玉皇大帝大怒,把叶小娃打下凡间。转山坪就是叶小娃赶来的山,那一丛一丛的丘陵,就是他没有下完的棋。④《转山坪的传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走马镇民间故事》(内部出版),1997年,第96-97页。
而对于转山坪来历的讲述,魏显德所讲的故事就与上文陈富其讲的不同,他的故事主要角色并非前面提到的叶小娃和土地佬,而是变成了孽龙(割青草拾到夜明珠,最后又变成龙的穷小伙)和二郎神。但其他的如北碚、鸡鸣的情节都包含在内。据他讲,转山坪是从油溪河边搬来,是因为孽龙对人们对他不公而产生不满,想将嘉陵江堵住,使四川成为汪洋大海。
正当孽龙扛着这座山往北碚方向走来的时候,二郎神一眼看见了他。二郎神知道孽龙的心思,很不忍心让千千万万的无辜人民丧命,可一时又不知如何劝他回心转意,就问:“孽龙兄,你扛这座山要扛到啥时候才停止?”孽龙心想没多远就到北碚水口了,鸡叫时一定能搬到,就说:“我扛到金鸡叫。”二郎神一听,心里也马上有了主意,他可以学金鸡叫。
孽龙听到“哥哥咕,哥哥咕”的鸡叫声只好停下脚步。但他不明白金鸡为啥子这么快就开始叫了,想了想,突然明白是二郎神耍的花招,他连忙放下那座山,气冲冲找到二郎神,不由分说,与二郎神斗气法来。
本来,二郎神和孽龙都只有七十一变,眼看二人将战成平手,这时突然走来一个染店老板,他肩挑各种染料,二郎神急中生智,趁孽龙不注意,抓起一把靛青往脸上一抹,孽龙一看大吃一惊,“你的脸怎么又青又黑?”二郎神答道:“脸青脸黑正在变。”孽龙听了心里发慌,因为他不会这一招;二郎神看他以犹豫,趁机劝道:“孽龙兄弟,那财主只是一个人,四川却有那么多无辜百姓,你就打消原来的年头吧。”孽龙自知斗法不能赢他,又觉得他的话的确有道理,虽然还是不服,但也只好就此罢休。不过,那座山,他也懒得再搬回油溪了,所以就把它留在那里了。这就是现在巴县境内的转山坪。①魏显德讲述:《转山坪》,彭维金、李子硕主编:《魏显德民间故事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151页。
“一个社会情境,在其内外资源、社会制度、结构与权力关系达到某种稳定状态时,皆倾向于复制与延续它自己,所谓‘叙事结构’便扮演此种功能。它使得文本或表征呈现一种规律性,而由此复制与延续社会本相与情境,也造成历史本相。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情境’与‘文本’将永远在这些叙事结构中循环不息。”②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页。个人与群体所处的社会情境各有不同,在叙述与传达中自然发生变异或与其他因素结合,以此来对应各自所要应对的事象。对于转山坪的来历,两人所讲的故事内容相距甚远。但其中的主要元素和情节有相似之处,比如对于洪水情节的描述,是否印证了历史上这里的人们曾经遭遇过,或是要面临这样的危险。
“故事讲述在已经共有化的人类经验的层面上表现出其想象的技巧。情节、人物、主题因素等都是一个生命的多种形式,这生命其实是共同的生命。在这方面,自传、传记以及忏悔书都只是叙事之拱的小片断,而叙事之拱作为一个整体,在相互影响的层面上描述并且重新描述人类行动。”③[爱尔兰]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王广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走马民间故事在关照故事中文化记忆的同时,也能够适应外界环境的改变,成为象征地方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二、故事讲述与文化身份
民间故事的讲述不单单是一种特定的民俗传统,同时也是一种经过历史性的凝结而成的一种稳定存在的生活惯习。它记载着某种社会记忆,能够通过激发共同的历史认同和记忆情感,团结众多的个人形成“传承的共同体”。走马故事讲述传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和身份象征,它能够从古流传至今,必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生命体征。“民俗以许多口头和语言的形式、以习俗行为的形式、以物质的形式显示它自身,但民俗自身是永远也不能完全整理记录的思想、内容和进程的传统的复合体;它只存活于民众相互影响的表演和传播中。”④[美]布鲁范德著,《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走马民间故事是一种可赋予我们文化身份的叙事,它反映着人们的期望与价值标准,通过群体或个体的力量,以讲述的方式或其他行为传承、发展。
“民俗学并非仅仅是着眼于传统文化和集体认同的学问,民俗学也能够关注现实的社会甚至个体的生活或者个人的人生,即人自身的主体性存在价值和意义。”⑤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上)——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载朝戈金主编:《中国民俗学》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1984年启动的中国大规模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实际上在故事采录的过程中为我们推出了隐藏在讲述背后的这些“个人”。“萨姆纳认为民俗生成的起点是个人的习惯,也就是在民俗之民中引入了个人。民俗学研究普遍的东西,流行的东西,通常是注重森林,不注重树木,在重视集体共同性的时候,忽视了个体差异,如果我们循着他的启示,以个人为起点去讨论集体,民俗学有可能发展到既注重集体的共性,也留意个人的个性因素,既注重从众倾向,也留意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主体性。这样发展对研究现代民俗尤其有益,因为在现代生活中,个人的主体性已经发展得比较充分了,随着这一因素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民俗研究越来越有必要在着眼于群体,着眼于群体的一致性的同时,也顾及个体,顾及个体的选择机制。”①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而故事讲述传统越发地对于这些个人及故事家讲述群体加大了关注,加大了对于他们的宣传。在维持并延续了中国民间“讲故事”的传统活动中,故事讲述者的功劳也占了重要部分。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里面积淀了自己的生活过往和点滴记忆。故事讲述时的场合是开放的,有讲述者、听众,甚至包括后来参与采录故事的采录者(特殊听众)、各种因故事讲述之名前来采访的人等等。故事的讲述对于个人历史的塑造,对于人们记忆中历史事件的讲述,对于日常生活的记述和体验,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你会依照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来讲述自己的现状。你根据自己过去的状况和将来的发展来阐述自己现在的境遇。这样做,便给自己一个叙事的身份,而这个身份便终生粘在你身上。”②[爱尔兰]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王广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然而,历史上这些讲述人并没有作为文化传承的特殊人物记录下来,尤其是讲述人讲故事的情景和活动没有系统地记载,只是把讲述人讲的故事作为社会进步的依据和文学创作的资料予以载录,因此,我们看到的民间故事记录就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了,更谈不上民间故事流动的生活状态。当然,它还是保留了民间故事面貌的基本轮廓,保留了民间故事发展的基本线索。20世纪以后,伴随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倡导从科学立场采录民间故事的呼声越来越高,采录方法也渐趋成熟,讲述人在民间故事传承中的特殊作用日渐被人们所重视。”③林继富:《中国民间故事采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叙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387页。走马镇民间故事的发展和传承,不仅仅要依靠个人,同样也需要有强有力的讲述群体。而那些奔走于采录、保护,为走马故事思量、实干的人们同样也值得我们尊重,也是能够保证其得到很好保护和传承的重要人群。在国内几个有名的故事村,如河北藁城的耿村和湖北丹江口的伍家沟村,都是有着比较密集的故事讲述群体的。
讲故事这样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赋予了讲述者们更深意义上的文化身份,众多优秀的故事从他们口中述出,故事家群体的聚集给一个地区的地方文化传统传承增添了重要的力量。除此之外,走马民间故事不仅突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故事讲述者,同时也成为了走马古镇当之无愧的“品牌”,与它的讲述者们一起成为宝贵的文化资源,成为显示地方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走马民间故事承载了千百年来巴渝大地的广袤的历史文化信息,是能够代表古镇特色的文化传统。除了这一核心内涵,还有民间故事保有会、民间故事讲述队、山歌传唱队和川剧演唱队等文化队伍定期举办故事会、曲艺会演、川剧座唱、山歌演唱等活动。“民间文学是无形而丰厚的资源宝库,它一直处在自觉的与不自觉的应用之中。由于这一资源的开掘,静态的景物带上了历史的与幻想的动感,食品、用品等非意识的物类也注入了精神的与社会的成分,从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④陶思炎:《应用民俗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随着时代变迁,古镇趋于衰落和势弱,原来的讲述传统也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我们看到,乡土社会中重新发明出来的村落传统,实际上已经融汇到日常生活之中,与新时期乡村社会的生产合作制度、以家户为单位的经济生产模式、社会关系资源及其构成的资源网络、共同体意识的创造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传统文化的再发明或者再创造,既凸显了被民族——国家现代性话语所淹没的民间历史的集体记忆,民间也通过援引历史的记忆来证明当下生存方式的合法性,从乡民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后者可能更重要。乡土传统的重新发明,不仅仅只是使之服务于过去历史的记忆,在很多时候,传统也被赋予新的意义。”⑤刘晓春:《一个人的民间视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第98页。虽然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走马民间故事的传讲活动有着不小的变化,但乡土社会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他们身上那种带有时代命运印记的个人生活史记忆,将会拓展其讲述传统的内涵。
三、故事讲述传统的保护与传承
对于走马民间故事的保护和发展,各方人士有着不同的看法。故事传承人、讲述者、研究者、地方文化工作者等等,这些围绕着走马民间故事的讲述生命而共同形成的群体,是能够促使走马民间故事发展、为其提供保障的特殊群体。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获得创新和适应性发展,在保留基本特色基础上获得生机,是一个不小的的挑战。2011年,重庆市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考核制度,与他们签订了协议。在协议中对于传承人所带徒弟的数量,所传授的内容要定期进行问询,年终也会进行考核测评。如果在这其中,传承人敷衍了事,态度不认真,传承人的资格将被取消。反之,如果所收徒弟的技艺达标,传承人将获得额外的经济补贴。但是这并不能够完全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在对走马民间故事如何能够跟上时代,不被遗忘的问题。传承人们也做了思考:
“讲故事挣不了钱,谁愿意送孩子来学。”民间故事市级传承人陈富其说,他也曾想多收几个徒弟,但看上有潜质的孩子时,就会被对方家长一句“讲故事能挣几个钱?”挡回来。如今,陈富其也到了城里打工。他担忧地说,作为市级传承人,他每年还能得到国家一定的津贴补助,但那些“故事篓子”讲故事都是“白讲”。①张樟:《老段子听众越来越少民间故事该怎么讲?》,《重庆商报》2012年11月20日
不仅是讲故事的人变少了,就连听众也逐渐减少,这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实际情况。那么,要想让走马民间故事的发展跟上时代,它的题材选择、内容更新、讲述方法都要进行相应的变化。
民间文学研究者、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倩予认为,民间故事不仅要在内容、题材方面创新,融入新内容跟上时代,还要在表现手法和传播渠道上有创新。她建议,可建现代化故事馆,通过电子存档搜集故事。日本东京就有类似的故事库,不仅有文字,还配有图像和声音,市民点击即可观看故事。②张樟:《老段子听众越来越少民间故事该怎么讲?》,《重庆商报》2012年11月20日
对于民间故事的数字化工作,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已做了许多相关工作,有成熟的经验。他们把现存的民间文学资料县卷本及其他现有资料,按民间文学的科学分类编排、扫描、录入,并继续在全国征集留存在各地基层文化机构和个人手中的民间文学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排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库,设计科学简便的检索体系与功能。③见侯仰军:《建设中国民间文化的数字化长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综述》,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民间撷英:中国民协机关“走转改”调研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近年来,随着急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向现代化,民间文化特别是以民间故事为重的口头文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传承方式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中,显得尤为弱势。而网络传播和口头文学遗产的数字化将是我们未来工作的一个侧重点,以数字化工程的手段来传承和传播传统的民间口头文学,已然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文化共享工程重庆分中心于2010年11月制作了专题网页“走马镇民间故事”④详见网址:http://2010.cqlib.cn/story_index.asp,文化共享工程重庆分中心制作,2010年11月。,里面以不超于10分钟的短片形式,记录了重庆走马民间故事的代表作品。共录制保存了7位讲述者的五大类125则故事,可以直接点击在线观看。足不出户也能聆听到走马民间故事的魅力,给了我们另一种直观的讲述感受。
将民间故事植入媒介语境之中,并借助现代传媒的各种优势,能使其获得更好的传承和延续。著名学者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提出了传播的“文化享受,丰富精神世界,社会遗产传承”的三功能说。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大众媒介在民间文化的传承中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先进的传媒手段和传播技术,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让人们获得充分的精神享受和文化盛宴,从而发挥其在保存社会记忆和民众教育等方面的功能。故事的发展并不会简单地依赖于任何思想或是原有的传统,如果时空发生转换,故事讲述与故事讲述者也会有所应对,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们因此获得了新的讲述生命,以此赋予故事新的时代意味和新的生命色彩。
四、结语
因为民间故事,让走马镇拥有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曲艺之乡”三块“国字号”招牌。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也成就了在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中的地位,成为能与河北耿村、湖北伍家沟相提并论的“故事聚落”。走马民间故事的意义并不止于作为地方的文化符号和一种文化品牌的可能,更多地是能够在讲述中传递知识,这种知识与民众记忆和地方历史有关。故事讲述传统之于地方文化的意义也在于此,民间故事承载的民间历史信息和民众记忆,包括他们对人、事件、事物等的认识和评价,是一部值得探究的厚重的“民间史”。如何利用好这些故事讲述文本,来拓展我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在故事讲述研究里更应该得到重视的。
(责任编辑:吴启琳)
Memory,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Story is about Tradition——In Chongqing Cook's Folk Stories for Example
Mu Zhaoyang
(College of Jiangxi Normal College Text Brigade,Ganzhou Jiangxi,341000)
Folk stories as a part of people to the life world,bear the function of the precept.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peak and sing the story of activity,and taught the audience rich tradition of folk and local knowledge,also has realized the reg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ity.Cook's folk story carries one thousand to rivers,the earth's vas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as cook's old town culture brand,not only highlights the town people's historical memory,also b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olk tradition in ancient characteristics.Cook's folk stories and the narrator are all precious cultural resources,become the show an important symbol of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Cook's old town;The story is about.Public memory;Folk traditional
C958
A
1008-7354(2015)05-0012-06
穆昭阳(1986-),男,山西阳泉人,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民间故事与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