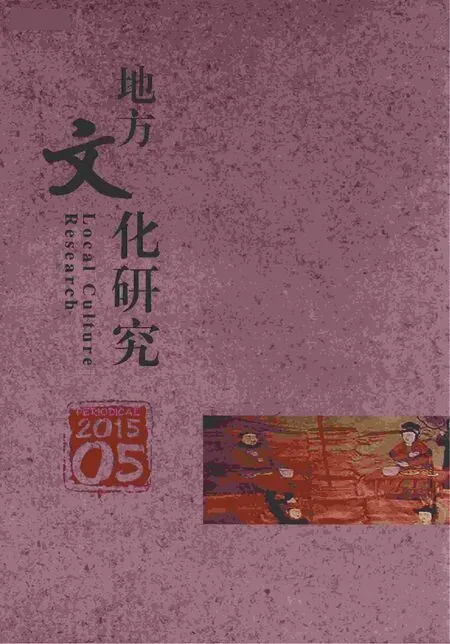贵州古代土著社会的居住形态演变及其特点探析
2015-03-30叶成勇
叶成勇
贵州古代土著社会的居住形态演变及其特点探析
叶成勇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唐代及其以前贵州土著社会的居住形态为“散在山洞间”的山地型,这是与山地乔木与灌木环境下形成的游耕兼畜牧经济相适应的居住形态。宋代,随着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内地政治经济因素的输入,土著居住形态出现分层化、等级化的发展态势,并呈现出从山地型向河谷平地型的过渡态势,但二者长期并存,各得其所、各得其宜,是一种缓慢连续性发展变迁。元明清时期,贵州不断被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管理之下,内地汉族的经济文化及其居住形态直接移入贵州,普遍出现了按照内地规制建筑的城市,在此背景下,产生了贵州土著居住最高形态——土司城。同时,各土著社会在对抗内地化农耕经济及其城镇居住形态的过程中,因长期“据阨为垒”、“据险起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适应当地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与游耕畜牧生计方式的军事化居住样态。
贵州;土著社会;居住形态
贵州在历史上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其居住形态到底经历怎样的演变,具有什么特点,是研究者一直忽视的问题。在当今贵州加快城镇化的条件下,理性地看待贵州少数民族的居住习性和相关文化心理,尊重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十分紧迫的课题。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知识,对贵州历史上土著社会居住形态的演变及其特点进行初步梳理,以期能为贵州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照。
一、唐代以前土著居住形态
汉代以前,贵州境内的土著居住形态,在今威宁中水、毕节青场、六枝老坡底等地、普安青场等地的考古发掘已有所揭示,总体特征是:房屋一般不建在平地上,而是建在坡地或山前台地。房屋规模非常小,一般不超过50平方米,比较流行栽柱式的地面建筑,出现了分间式房屋,也有半地穴式和窝棚式房屋,平面不规整,室内设施十分简陋,仅有火塘。①叶成勇:《贵州西部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格局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
汉代的情况,从《汉书·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可略知一些: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夜郎王兴被牂牁太守陈立诛杀后,“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阨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都尉万年曰:‘兵久不决,费不可共。’引兵独进,败走,趋立营。立怒,叱戏下令格之。都尉复还战,立引兵救之。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这里提及的“据阨为垒”很值得注意,即是指在险要之地建营垒,而非临时所建,而是夜郎王经营已久,有粮道和水道,设施已齐全。汉军趋战而败走,遂不得不立营作长久作战。最后汉军不能正面进攻,而是截断通往营垒上的粮道和水道取胜。这个战例,其实反映的是土著选择险要山顶建造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营垒,同时又有粮道和水道以满足日常生活之需。这种据险立营垒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山地区域很早即已出现。《史记·礼书》提及战国时期楚国为对抗秦国,“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邓林,司马贞《索隐》注引:“刘氏以为今襄州南凤林山是古邓祁侯之国,在楚之北境,故云阻以邓林也。”方城,张守节《正义》注引《括地志》:“方城,房州竹山县东南四十一里,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为方城,即此山也。”①(汉)司马迁.《史记·礼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66页。邓林与方城,一在楚国北部,一在楚国西部,都属于山地军事性防御设施。夜郎“据阨为垒”的营垒形态、功能与楚国的邓林与方城,何其相似。笔者曾提出夜郎王当出自楚地,是楚庄蹻之后,汉代的夜郎国是战国时期楚庄蹻入夜郎后,其后裔与土著濮人融合的产物。②叶成勇.《南夷社会考古学研究》,第304-308页,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而前述分析的汉代夜郎“据阨为垒”的营垒与楚地的防御设施相似性,也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三国时期,仅有一些疑似遗存及其传说,从一个侧面可略知三国时期贵州土著的居住情况。史载唐太宗贞观四年,牂牁谢氏内附,置琰州,辖七县,其中有武侯县。③《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江南道琰州》。据道光《安顺府志》,武侯县在永宁东关岭城南诸葛营,而《水经注》提及诸葛亮南征,战于漏江之南和盘东,诸葛营在关岭之南,与盘东之文相协,故唐以武侯县名之,盖诸葛之遗踪。④道光《安顺府志》卷3《地理志二》。2012年8月笔者带领学生在关岭县南部上关镇乐安村拉达组调查时,从当地老人得知:拉达组有一座孟获屯,屯修建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相传因三国时孟获在此扎营驻军而得名。只有一条险要的山路上山,三面悬崖。顶上有两个山头,中间由长20米,宽1.5米的山梁连接,山梁两边是悬崖,地势极其险要。在上面除了这两个山头有石砌围墙外,在半山腰有一台地,有屋基、瓦片、水井,还有一个碓。这些当是人们在屯上居住过的痕迹,但不知道建于何时,没于何时。山上还长满了藤竹,据说这是做藤甲的材料。而诸葛亮扎营的地方叫孔明塘,现在被水库所淹,没有被淹时孔明塘像一把宝剑,这把宝剑意为剑指敌方,这是诸葛亮能胜孟获的主要原因。从地理位置看,孔明塘与前述诸葛营很接近,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二者很吻合,推知这一带就是唐代的武侯县地。唐初至三国初期时期虽已四百余年,但唐初在牂牁大姓谢氏内附后置羁縻州县,并非向壁虚造,当是由大姓所提议并认可,其武侯县名之来历必有所据。因此,以上传说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当地关于孟获屯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孟获第二次被擒后,由于不服诸葛亮,诸葛亮放其归山让其心服口服。孟获来到屯上扎营,诸葛亮在屯下扎营。一天,孟获攻蜀营,带领藤甲兵以火为号,但来到蜀营,只见是空营,孟获方知中计了,正准备撤离,火光四起,王平一马当先,向藤甲兵杀来,但藤甲刀枪不入,诸葛亮采用火攻,藤甲由于用油寖泡过,遇火则燃。蜀军最后大胜,孟获再次被擒。
综合《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和诸葛亮传,诸葛亮于建兴三年春三月南征,秋七月南中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悉平,十二月诸葛亮还成都。其经营南中近十个月,时间很长。关于诸葛亮南征中七纵七擒孟获之说,《三国志》无载。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有所述及,但不言具体地点和擒法。据注引的《汉晋春秋》,孟获降服后,诸葛亮“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又据《三国志·李恢传》,诸葛亮南征由越嶲入,可知擒孟获之地点当在滇池之西或北。《滇云纪略》、《滇记》、《滇志》、《读史方舆纪要》诸书言七擒孟获之地在云南大理、永昌境。而《通鉴辑览》及卢弼《三国志集解》皆以七擒孟获之说不可信。⑤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10-111页。
笔者以为,诸葛亮七擒孟获之说在《汉晋春秋》中不过一笔带过,重在说明诸葛亮攻心之策,后世志书非要凑齐不可,且越加神秘,其中附注了后世战争之光影,不可全信。其实,擒纵之法在军事上乃惯用之策,诸葛亮用在孟获身上,很有可能。尽管《滇云纪略》、《滇记》、《滇志》、《读史方舆纪要》诸书关于诸葛亮擒孟获之说的具体擒法和地点不可全信,但都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孟获皆在附近有水源的险绝之崖顶安营为战,诸葛亮则驻扎在山下,采用火攻藤甲或断其水源之类的奇计擒孟获。这种双方之间的阵势及战法,与此前陈立灭夜郎翁指之法,后世宋代攻晏州夷,明代攻播州杨氏海龙囤之法,何其相似!就建城方式而言,此时期土著延续了夜郎时期的“据阨为垒”,有粮、水、房屋等基本的生存条件。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七擒孟获的战术战法,不过是好事者通览古代西南地区土著建城特点和战阵战法后有意附注其中,尤其以《三国演义》为典型。这当是明代中后期中原人士对西南土著社会认识深化的产物,是对历史的合理化想象与重构。
二、唐代贵州土著居住形态
唐代,贵州大部分地区仍被视为“化外之地”,汉文文献对当地土著的生业、居住、风俗等记载虽很简略,但较此前已为具体。《旧唐书》卷197记载:
东谢蛮:其地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南接守宫獠,西连夷子,北至白蛮。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以饮。皆自营生业,无赋税之事。……丈夫衣服,有衫袄大口裤,以绵绸及布为之。右肩上斜束皮带,装以螺壳、虎豹猿狖及犬羊之皮,以为外饰。
牂牁蛮:首领亦姓谢氏。其地北去兗州一百五十里,东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无城壁,散为部落而居。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风俗物产,略与东谢同。
以上记载的东谢蛮和牂牁蛮大致分布在今贵州中部地区,从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唐代土著无城郭,人们散在山洞间,分部落而居。二是经济生活上,虽土宜五谷,稻粟再熟,但不以牛耕,而为畲田,每岁易地而耕,此种耕作方式即西南山地长期存在的游耕和刀耕火种。同时,服饰上以绵绸及布为衫袄大口裤,右肩上斜束皮带,装以螺壳、虎、豹、猿、狖及犬羊之皮,以为外饰。这些丝织品和大型野生动物及家禽之皮饰,反映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种植业和畜牧业,并以狩猎为补充。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人们只能是“皆自营生业,无赋税之事”。这时期文献所载的居住形式和经济生活实则有内在关联性。由于经济生活上采取畲田和游耕畜牧并重,只能适合在山地展开,自然会分散地依山而居,其居住形态必然是“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以饮。”这样,不会出现内地平原土地上的大量人口聚居,更无城郭。这种经济生活和聚居形态实质上是人们适应本地生态环境的产物。众所周知,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完全,多石山少平地。平地或凹地本不多,而且这些地方植被繁茂,草木榛莽,周遍岭谷,又水土湿气甚重,所谓“土气郁热,多霖雨”,瘴疠很常见,甚至地气和水草都有毒。①清代贵州西部南部还比较常见。康熙二十九年贵州巡抚田雯撰成《黔书》,其中专辟“瘴疠”条,详细记述瘴疠分布、出现时节、情状、危害及其救治办法。道光《安顺府志》卷14《地理志十三》气候中详细记载今关岭、镇宁、紫云、六枝一带的瘴气。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不仅开垦很困难,人们还很难适应瘴疠的侵害,瘴疠起时,土居之民“亦多瘠黄”②道光《安顺府志》卷14《地理志十三·归化气候》。,“地势温湿,不宜牛马”③《盐铁论》卷3《未通》。,故不会选择居住在平地或凹地。因贵州多霖雨,山间并不缺水,而多有山涧溪流,植被较平地和凹地稀疏得多。据笔者长期观察,黔中一带平地或凹地附近土质较厚的坡地和山地一般都分布乔木林带,其有明显的分层特点,即成片高大的乔木林下面是低矮稀疏的灌木和草丛,乔木林深长通透,可架梯为层巢居住,灌木和草丛可畜牧。而且,这种坡地林带边缘土壤深厚,为砂质黄土层,适合游耕和刀耕火种。人们选择在乔木与灌木重合部位的土坡和山地耕作、放牧和居住,比在草木榛莽,“土气郁热”,瘴疠袭人的平地或凹地要容易得多。这就是“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以饮”这段话的实质涵义。近现代,贵州中部一些地区还有土著生活在洞穴中,外人往往投以惊诧的眼光,却不知这是人们在与自然环境长期磨合后形成的适应于生态的文化传统和居住习性。
笔者在这几年的调查中,搜集到相关资料也可以验证前述分析。如我们在正安县谢坝乡调查谢氏家族史时,当地《谢氏家谱》和口头传说都谈到谢氏在元顺帝时自四川迁入正安时,先住在偏僻的阳陈山地上,过了几代,人口增多后才慢慢下移到现在谢坝乡所在的河谷坝子中开垦种植。谢氏进入时,谢坝坝子上长满水蜡烛,为草莽水泽之地,也无人居住。经过长年累月才把大片沼泽之地辟为良田。又如,笔者在黔中一带的花溪、安顺调查各家族史时,很多家族谱牒和口述中都提到明代自内地入黔,一般都先在今贵阳市区一带居住,这一带原来叫“黑羊箐”或“黑羊大箐”。顾名思义,箐,就是草莽丛生的原始森林地带。现在,很多村寨及其周边田地下面,人们打地基或深耕时,经常挖出巨大的树根。1950年代,花溪区湖潮乡修筑汪官水库时,从田地下挖出周长十多米的树兜。这些资料反映的一个共同的现象:贵州历史上,平地丛林榛莽,开发很晚,这验证了前述的分析。
总之,唐代贵州土著并无城郭,也无大型定居聚落,整个生计和居住空间主要在山地及山前台地,而不是在平地,更不是在凹地。我们可将这种生计和居住形态称为“山地形态”。当然,个别地方开始出现内地汉式的城郭。如《旧唐书》卷40《地理三》“费州条”记载:“城乐:武德四年,山南道大使赵郡王孝恭招慰生獠,始筑城,人歌舞之,故曰‘城乐’。”①《旧唐书》卷40《地理三》。“人歌舞之”,说明土著的接纳态度,这应是文献中关于贵州按内地筑城的最早的明确记录。因此,我们只有跳出今人对近代以来所谓城镇化常规的思维模式,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客观解读有关唐代贵州土著的经济生活方式和居住形态的文献记载,才能避免将之目为“野蛮”、“落后”和“愚昧”,也就才能正确地认识唐代贵州土著社会居住形态的具体功能与意义。
三、宋代贵州土著居住形态
宋代,中央王朝对贵州区域的管辖基本延续了唐代的羁縻统治。这时期土著居住形态,从文献记载看,在基本延续前代形态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为:随着内地的生业和居住形式的输入,其样态开始在土著上层社会流行。
1.抚水州地区
《宋史》卷495《蛮夷三》记载:
抚水州在宜州南(按:“南”当为北),有县四:曰抚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劳。唐隶黔南。其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镇。民则有区、廖、潘、吴四姓,亦种水田、采鱼。其保聚山险者,虽有畲田,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无羊马、桑柘。地曰帚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余家,夹龙江居,种稻似湖湘。中有楼屋战棚,卫以竹栅,即其酋所居。兵器有环刀、标牌、木弩。
以上所谓“抚水州”大致在今贵州水族居住地区的荔波一带。抚水州蛮与今水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生计方式和居住形态出现了山地型和河谷平地型两大类型。山地型,即所谓“保聚山险者,虽有畲田,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无羊马、桑柘。”狩猎成分很重,畲田不足以自食,甚至无畜牧之养殖,这些与前述今贵州中部地区的唐代东谢蛮和牂牁蛮基本一致,对山地自然之产物依赖更重,这应是普遍的传统生计模式。正如《宋史》卷495《蛮夷三》“抚水州”条所谓:“诸蛮族类不一,大抵依阻山谷,并林木为居,椎髻跣足,走险如履平地。”而河谷平地型,即“地曰帚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余家,夹龙江居,种稻似湖湘。中有楼屋战棚,卫以竹栅,即其酋所居。”这部分最值得注意者有三:一是五百家夹河谷川原而居,人口集中居住,种植水稻,如内地的湖湘地区村落,这明显受到内地汉人生计和居住的影响;二是首领或上层居于村落其之中,但所居住的房屋是“楼屋战棚,卫以竹栅”,较一般民居不同,表明等级的差异;三是即使是首领,仍没有脱离本土社会的母体,在象征等级的居住建筑上也是本土化的楼屋、战棚、竹栅,这些都是取之于本地的材料和建筑形态,并没有出现内地的房屋形式。
这里有必要对河谷平地型生计居住形态出现的原因作进一步分析。据前引《宋史》卷495《蛮夷三》记载:北宋“熙宁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砦,比之内地。元祐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这是从政治角度的记载,从熙宁间“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到元祐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仅仅十余年,最后朝廷“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据此可知,“始创城砦,比之内地”的做法在本地并未被接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宋王朝按照内地筑城的做法在当地是行不通的,朝廷只好作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不符合包括居住形态和文化心理在内的土著社会经济文化模式。
宋代在荆湖南路大量驻军与经略,必然对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加之内地社会经济形态的不断输入,也对当地民族的生计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之逐渐由山地游耕转变为稻作农耕,反映在居住形态上,即出现了“始创城砦,比之内地”的趋势。但由于两宋时局不定,对西南区域无法取得长期而稳定的管辖,从而才导致贵州区域的民居形态在时局反复中并未呈现稳定的转变。而文献记载抚水州土著社会经济文化在宋代经历了从山地型向河谷平地型的过渡,且两种形态长期并存,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呈现出连续性发展的状态,总体和谐,没有明显的断裂。总体而言,宋代“抚水州”土著的河谷平地型生计和居住形态是在内地汉族深刻影响下,土著社会经济文化自觉缓慢发展的产物,其实质是由生业形态的转变所引起的居住形态的变化。
2.牂牁蛮地区
据《宋史》卷496《蛮夷四》载:
西南诸夷,汉牂牁郡地。唐置费、珍、庄、琰、播、郎、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无城郭,散居村落。土热,多霖雨,稻粟皆再熟。无徭役,将战征乃屯聚。刻木为契。至道元年,其王龙汉(王尧)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太宗召见其使,询以地里风俗,译对曰:“地去宜州陆行四十五日。土宜五谷,多种粳稻,以木弩射獐鹿充食。每三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杀人者不偿死,出家财以赎。国王居有城郭,无壁垒,官府惟短垣。”
以上所谓“西南牂牁诸蛮”,大致就是今黔中一带,其记载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依然采取唐代的“无城郭,散居村落”的居住形态,但出现了“多种粳稻,以木弩射獐鹿充食”的生业形态,即以粳稻种植为主的农耕和木弩射獐鹿充食为辅的狩猎两种生业方式并存;二是人口居住相对集中,一般三二百户聚居为一州,州有长,施行一定的社会管理,表明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三是社会分化较明显,速度加快,“国王居有城郭”,“官府惟短垣”。不仅有“国王”,还有其管辖下的官府,这个官府当是羁縻州,官府管理者应为羁縻州刺史。“国王”作为土著社会顶层居住在高级别的“城郭”建筑中,以显示其社会地位,而一般的官府只有“短垣”,类似于前述抚水州的“竹栅”,相当于房屋外的围栏。不过,“国王”虽然有城郭,但无壁垒,这又明显不同于内地的城郭的建制。无壁垒的城郭,就是不设防的城郭,说明它对于土著社会和群体是开放性的,这与内地集权政治模式下的都城和各级官府衙署,在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国王”—“羁縻州刺史”与王朝在内地派出的“官府”性质有根本之别,它们是本土社会内生出来的自我管理的政治形式,其必然是依赖土著民众,并为之开放。这样的土著社会类似于塞维斯《酋邦社会》或者斯图尔德《文化变迁论》里面提到的初民社会发展的酋邦社会阶段。
以上“西南牂牁诸蛮”社会所体现的生业居住形态的特点是农耕与定居,伴随着社会分化,居住也分化为普通民众的散居村落—直接依赖村落的短垣房屋—高于土著社会和群体而又开放的无壁垒城郭三个等级层次。前两种属于山地型,后一种属于平地型,这三种居住形态层次对应的就是土著“国王”—“羁縻州刺史”—普通民众的分级管理,这是唐宋时代的羁縻州制度的反映。“国王居有城郭”、“官府惟短垣”有面向朝廷的政治义务和角色定位,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又是一种将土著上层与土著社会民众进行分割的标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宋代贵州土著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住形态出现分层化、等级化的发展态势,总体上经历了从山地型向河谷平地型的过渡,但两种形态长期并存,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呈现出连续性发展的状态,总体和谐,没有明显的断裂。当然,各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受内地经济文化影响程度也不一致。
四、唐宋以来土著筑城技术的进步与据险起事
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土著据险反叛的事例颇为常见,史籍多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居无城郭,但“征战之时,乃相屯聚”,“战乃屯聚”,“有所攻击,则相屯聚”等。如《元和郡县志·江南道》载锦州洛浦县(今湖南保靖一带)“有石城一,甚险固,仡僚反乱,居人皆保其上。”《新唐书·南蛮传》更是载有太宗、高宗时期的十多起僚人反叛事件,其中就包括有在黔东地区的琰州僚人的反叛。又道光《遵义府志·土官》载有罗荣其人,唐大历时期(766—779)播州夜郎反叛,“命荣帅师南征,剿抚并行,蛮方永靖,朝廷遂以其地分封,命世侯播土。”宋代土著据险起事的情况更为突出,兹举例加以分析。
1.晏州夷筑城与据险反叛
《宋史》卷96《蛮夷四》载:“政和五年(1115),晏州夷卜漏叛,寨将高公老遁,招讨使赵遹讨平之。”晏州夷反叛之事,《宋史》卷348《赵遹传》和《续资治通鉴》卷92有详细记载。综合以上文献,我们把这段史实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以卜漏为首的土著据守的中心在轮缚大囤,其地林箐深密,“其山崛起数百仞,周四十余里,卜漏居之,凡诸囤之奔亡者悉归于此,共保聚拒守”,①《续资治通鉴》卷92“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条”。而且在其周边还有三十余囤。这是自然之险与人群之聚的有机结合。
第二,囤的结构和设施大致为“垒石为城,外树木栅,当道穿坑阱,仆巨枿,布渠答,夹以守障,俯瞰官军。”②《宋史》卷348《赵遹传》。城外有关卡,住所“皆茅竹为之”③《续资治通鉴》卷92“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条”。。可见经营已久,层层设防,结构完善,设施较齐全,具有非常系统的军事防御思想。
第三,官军不能直接对抗卜漏据险之众,所谓“官军以强弩射之,曾不能及半,兵陈四周凡累日,将士相顾无计。”④《续资治通鉴》卷92“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条”。只能采取谋略巧攻,尤其要利用思州土著首领田祐恭所带领的“轻趫习山险”的思、黔土丁、药箭手。这部分习地方山险的土兵从最陡绝的地方攀援而上,捕得生猱,然后“纫麻为长炬,灌以膏蜡,使群猱背负之。暮夜,先以数辈登崖颠,系绳梯数十,缒而下,众各衔枚,挈群猱次第挽绳梯而登。鸡方唱,众已悉登,及栅,乃然炬纵猱。”借用猱带着火进入,“群猱所历,火辄发,贼奔呼扑救不暇。猱益惊跳,火益炽,争前驱逐群猱。”⑤《续资治通鉴》卷92“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条”。最后,官军乘势战胜了卜漏。这次战争的胜利应该归结为官军将领能够充分利用“轻趫习山险”的思、黔土丁、药箭手,利用他们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药箭、攀援、借猱火攻),而这些正是长期的山地居住形态所积累的生存知识和技能。
第四,平定后,官军以其地之要害者建置寨堡,同时,在所控制的沃衍宜种植之地,“画其疆亩,募并边之人耕之,使习战守,如西北弓箭社之制,号曰胜兵。”从而实行军事和经济双重控制,尤其是“募并边之人耕之,使习战守”,渐渐使“并边之人”从传统的游耕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为宋所用。
2.石阡县河坝场城门山遗址、思南县杨家坳城头盖遗址与土著任氏据险反叛
城门山遗址位于石阡县西部的河坝场乡北约5公里处,处于山峦叠嶂的山峰沟谷部,三面环水(即罗回江,原名龙回江),且为悬壁,只有从城门去的一条独路可通其上。遗址主体部分大致由南北数道石城门、石围墙、十余处房屋建筑群组成,依山峰沟谷走势蜿蜒盘曲,可容纳数千人。石城门和石围墙的基本形状仍可辨识,残存的石墙长的近百米,而房屋建筑群已荡然无存,地基部分已被当地群众开辟成阶梯状的耕地。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围墙外围或内部,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似有墓群的布局,墓葬之间很密集。坟丘形态很特别,由外到内用碎石块围砌成螺旋圈状。有的坟丘很高大,圆径在10米左右,高也在2~3米,而多数坟丘则比较矮小,甚至已经与地面齐平,难以分辨出来。这种差别说明墓葬规模大小不一,可能是不同时代或不同社会等级的反映。从遗址向北有一条小路下到罗回江边,以供饮水之需。另外,在古墓群下边罗回江的悬崖上有猴子洞、月亮洞、观音洞。猴子洞在险峻的半岩上,可容纳上千人居住,洞口有堆砌的土砖块。月亮洞与猴子洞相距约300米,里面有石堆、石鼓,曾经有人在洞里见过花鞋等物品。据河坝场中学安元华老师介绍,河坝街上一带为山间坝子,罗回江横贯其中,四周高山耸立,山上有残留用毛石砌成的城墙,墙高3—4米,四方还有城门。在河坝场外围10—20公里范围内,有很多屯地,东面15公里处有宰家屯,南面15公里处有任家屯,西面12公里处有昌家屯,北面10公里处有葛商屯,屯地周围都有大片良田。①2011年6月9日~11日,受石阡县政府的邀请,笔者有机会与有关专家的考察。参见叶成勇《石阡河坝场城门山遗址的时代与性质试探》,未刊稿。
安元华提供的《安氏家谱》讲到:两宋之交,“黔南妖僧任则天猖寇作乱,肆横数百里……金头则天调铁天、打天、骂天弟兄诸将及四野屯、万胜屯、木猴、六郎、八郎、新官屯、朱家等屯蛮兵,与安崇诚部战于镇远之西。”又据民国十九年《思南县志》记载,今思南杨家坳乡城头盖上,北宋时建有城子寺,“城头盖城子寺宋时有妖僧建增,精习邪术,炼成铁身,惟胸窝略软,且善飞,一朝往返百余里,人呼为金颈和尚。有陕西安崇诚征蛮于此,首获其徒,问厥由来,乃以实告,方于万胜屯一箭穿胸死亡,余党逃窜。”当地民间盛传金颈和尚在城头盖聚众造反数十年之事,甚至还有很多神话般的故事。相传建增叫任则天,他还有四个弟弟,即打天、骂天、铁天、武天。整个城头盖突起于绿池河边群山之中,四周悬崖峭壁,有六个口通顶上,总面积约六千亩,三面较高,中部平坦,最高峰城子寺高951米,中部850米左右。高山上有一股终年不涸的大水,又有旱涝保收的1200多亩耕地和4800多亩宜林地带。其上有宋代墓葬和城子寺遗址,据汪育江先生研究,城头盖很可能是隋至北宋末年夷州下辖的都上县所在地,延续时间达500余年之久。北宋末年任则天以都上县为中心,联合三十六洞九十九寨及各屯,据险反叛。②关于城头盖为都上县及北宋金颈和尚的传说,详见思南县原文物管理所所长汪育江:《故都城头盖》,第8-12、24-37页,思南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2006年3月。又参见先生著《都上县城遗址考》一文,载《思南与乌江文化》,贵州省思南乌江博物馆编。
石阡县河坝场城门山遗址和思南县杨家坳城头盖遗址其遗址的状况与前述晏州夷筑城与据险反叛非常相似,两地都是数屯相连,形成十分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反映的是同时期西南土著据险反叛的普遍性。
元、明、清时期,土著筑城据险起事,也大量存在,仅举凯里明代香炉山遗址来说明。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21“都匀府清平县条”介绍,香炉山“壁立千仞,延袤三十余里。众山环列,若戈(金延)相向,盘亘三四重。鸟道悬崖而上,可容百万人。有瀵流一溪,沃畴千畎,聚落蜂屯,保以为奸。正统末,苗韦同烈者凭险拒于此,官军讨之,久而弗克。景泰三年乃就抚。正德十二年,苗阿向等复据旧巢作乱,列栅数十里,积粟聚兵,结都黎、都兰、大漂、大坝、龙对诸苗相形援,诏湖贵合兵讨之。环列山下,弗克攻。侦知苗俗以长至日为岁朝,至其夜,架梯悬崖,直捣其巢,焚其寨栅,遂平之。因城香炉为官戍。嘉靖十三年,增拨清平卫中左所兵戍守。”由此可见,明代贵州土著依然继承了历史上据险起事的方式,筑城方式也基本未变,而且明朝也采用了宋代的方法,在占领后,“城香炉为官戍”。
自汉代以来,各土著长时期普遍性地“据阨为垒”、据险起事或反叛,一定程度上是贵州土著社会在适应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而形成的游耕畜牧经济条件下“散在山洞间”的居住形态军事化转变,在对抗内地的农耕经济及其筑城居住形态中具有独特的优势。随着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建筑技术也有所改进,特别是石材的开凿技术和粘合材料的运用,客观上为土著据险起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明清时期,土著据险垒城反叛性活动越来越频繁,且往往能够酿成威震一时的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五、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城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20评论元代以来贵州的情况:“贵州自元以来,草昧渐辟,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苗蛮盘绕,迄今犹然。”其实,元、明、清时期,贵州不断被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管理之下,大量汉移民进入,内地汉族的经济文化及其居住形态直接移入贵州,土著的生计和居住形态发生重大转变。在贵州境内,普遍出现了内地样式建筑,大致包括各级官府治所和土司治所。这里举几个土司城事例来专门说明。
1.岑巩县木召元明时期田氏思州司城遗址
现在的木召村,包括上木召、中木召和下木召三个自然村寨,分布在约10公里的南北向狭长地带,地势平缓,土壤肥沃,汤江溪迤逦其间,向东南流入潕阳河。木召古遗址群就分布在这个狭长地带5~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遗存的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其中,位于中木召刘氏村寨的古城遗址已于1985年11月2日公布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整个古城遗址位于山前台地上,坐南朝北,被现在的刘氏居民房屋占据。地上建筑基本不存在,但石构的墙基、路基、地基保存比较完整,地面上残存有砖墙、门栏、石水缸及零星的柱础石、门砧等。青砖和瓦片随处可见。古城后面坡地是翠竹修茂,前面则有长500多米,宽2.5米的石板路,路旁有数十株苍劲古柏,还有银杏树两株,母树早年死亡,子树高约三十米,树干围长6米。从显露的遗迹看,整个古城布局比较规整,平面大致呈长方形,长约500米,宽约100米,四周有石墙。城内以7条纵向巷道间隔6列房屋,巷道和房屋地面皆以石板铺筑。每列由3~5排庭院式房屋,每排由3座独立的房屋构成,至少共有50座房屋。每座房屋大小不一,基本结构为三合院,即正房和两厢,正房正对面有照壁。前后房屋紧邻而高低错落,从山前向半山坡延伸,房屋之间以石墙相隔,有石板路、石台阶和八字大门连接。城内地面基本用凿制规整的青石板铺砌,排列有序,石板上有的刻有花纹和图案。特别是石门栏、石柱础、石门砧纹饰多阴刻和浅浮雕,风格粗犷古朴。整个城址结构完整而连贯,风格一致,当是事先规划,短时间内建成,可见工程量浩大。据初步推算,需要100万至200万个工日,如以4000个劳动力建造,需要10~15年。
我们对保存较完整的第一、二条纵向巷道和第一、二列房屋作了初步测量。第一条巷道宽3米,长113米,第二条巷道宽2.8米,长94米,第一列房屋在一二条巷道之间。这列房屋地基总长66米,共4排,每排3座房屋。第一排进深30米,第二排进深24.8米,第三排进深28米,第四排进深12米。每排房屋有石墙相隔。在第二条巷道长65米处的左边(紧邻第四排房屋后墙),有一条通往该排房屋后面长方形水池的石板路,水池也是石砌而成,东西长20米、南北宽16米、深约2米。现已填平建有房屋。在第二条巷道长90米处的右边,有一座八字大门。门宽2.8米,门前有台阶。进门后,有一条长约21米、宽3米的石板路。路外有石墙,相当于影壁,路里边有一座三合院。正房房屋面阔16.4米、进深7米,左厢宽5.7米、长10米,天井宽5.5米、长10米,右厢宽5.1米、长10米。在水池与这座房屋之间,还有三至四座房屋,但结构很不清楚。
第二列房屋地基总长77米,有3排房屋。第一二排各3座,第三排2座,这2座房屋左右并列,在这个古城中结构完整,面积最大,被当地人称为中厅堂。“中厅堂”的结构也为三合院式,左右房屋之间有过厅。整个中厅堂的入口为一座八字大门,位于第三条巷道长约50米处的右边,门口宽2.6米。右边房屋正房面阔约28米,进深约12米,屋内地面用棱形厚砖铺垫。天井南北长18.4米、东西宽12.8米,用120块刻有不同花纹图案的青石板铺砌。厢房长宽不明。天井前部有一口大石水缸,高1米、长2.4米、宽0.8米,缸一外壁上刻有一对蝙蝠,蝙蝠中间有“双喜”字(或以为“寿”字)形花纹。雕刻精细,技法娴熟。过厅长18.4米、宽6米。左边房屋与右边房屋结构一致,面积稍小,正房内用方砖铺砌。天井前部也有一口水缸,纹饰相对简略。在左右房屋正房之间有火塘和水缸底石一块。整个中厅堂外有一堵石墙,墙宽约50厘米,后面也有一堵石墙。
另外,我们还测量了第二列第一排的一座三合院房屋。其正房面阔23米,进深9.5米,天井东西长11.4米、南北宽9米,左厢长9米、宽5米,右厢长9米、宽6.8米。其他几条巷道和房屋由于保存较差,未作测量。
古城内及附近一带,经常出土各种器物。当地群众在城址上修建房屋时,不时地从基石2米以下挖出一些瓷片、陶片、瓦砾、青石料等。在城外南边坡地上,群众建房时发现有窑址、铁锅;在城前石板路外的大田坝中,犁田时发现有青石料、铜权、清代钱币以及大量陶瓷片。大田坝外有一条叫汤江溪的小河,小河冲刷出大田坝2~3米深的土壁岸上,清晰可见大量残砖、瓷片、瓦片、陶片等。①2009年10月24至26日,笔者与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郭国庆博士受岑巩县王文云副县长的邀请,在县文管所杨涛和文史馆黄透松先生的陪同下,专门考察了位于大有乡木召村的木召古遗址群。后又于2010年1月17日至24日再次前往考察。以上资料是我们两次考察亲自所获。
笔者结合文献中关于元明时期田氏思州政治变迁的记载,认为该古城约从1275年沿江安抚司设置时起至1281年成为思州田氏土司政治中心后进一步完善,并一直使用至永乐十三年左右(1415),经历约140余年的政治变迁,其真正被废弃的时间可能晚至正统末年(1449)。特别是在1281年至1413年间,古城曾是元明思州田氏土司的政治中心,可称为“元至明早期田氏思州司城”。②叶成勇:《关于贵州岑巩县木召古城的再认识——兼论思州田氏土司治所之变迁》,《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作为元明时期思州田氏土司政治中心的木召古城,是一座石城,也是目前贵州乃至西南土司城址结构保存较完整的一处,比贵州明代中期府州县石城普遍出现要早。
2.开阳县合丰乡元明时期的宋氏土司总管府遗址
这个遗址是元代底窝、纳坝、紫江等处长官司和明代宋氏土司十二码头之一的底窝码头治所,已于2006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笔者考察,其位于禾丰坝子边缘斜坡台地上,建筑风格与木召元、明时期田氏思州司城遗址十分一致,也是石基墙、石板铺砌地面和道路、排列建造庭院式房屋。
3.瓮安县珠藏镇瓮水犹氏蛮夷长官司遗址
据贵州省博物馆1989年的实地调查,遗址位于朱藏镇瓮水司村一坡地上,面向平地和河流,面积约10公顷,但破坏很严重,断壁残垣、滴水、筒瓦随处可见。整个遗址分为七重,第一重台基高于地面约2米,占地90平方米,由东西两厢和天井构成,两厢尚存石基。第二重高出第一重1米,占地约100平方米。第三至五重每重高差1~2米,第五重右侧有大石砌成的台阶,高出地面3.5米,拾级而上达于第六重。第六、七两重实属一个院落,左、右、后三面石墙残高3.5米,厚1.3米,每面有一小门,门边设置一个石哨棚,后墙外有一条石墁通道,过通道又有一道护寨围墙,残长70余米。其中,第六重房屋面阔36米、进深20米,台基四周有细石铺就的回廊,东西两面有残存的宅基石,中部用1.7×1.2米的石板镶筑的一条石道,与屋后部石阶相连,登九级石阶至第七重。此重高出第六重2.15米,面积与之相当,很可能是长官司正堂宅基。总体来看,瓮水司遗址的建筑风格和结构与木召古城也很接近。调查者根据瓮水长官司的历史记载,初步把这个遗址时代定在宋、元时期。③《贵州省志·文物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4.遵义宋明时期播州杨氏土司衙署海龙囤
海龙囤遗址位于遵义市北部30里的湘江上游龙岩山东麓群山之巅。山顶上建阁楼、兵营、仓库、水牢、绣花楼,囤前设铜柱、铁柱、飞龙、飞凤、朝天、万安等九关,各关之间有护墙相连,凭险设关,关关相联,以石块垒砌的高大城墙关隘,形成三层防御体系。据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介绍,如今周长约6公里的环囤城墙尚存,囤内面积达1.59平方公里,“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囤内两组最大的建筑群,面积均在2万平方米左右,大体为“横三纵三”的布局,是集军事屯堡、衙署与“行宫”为一体的土司遗存。2014年5月16~18日,笔者有幸参加在遵义举办的“播州土司历史与文化”会议,期间参观了明万历时期播州海龙囤“新王宫”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发掘主持人李飞先生详细介绍了遗址布局和出土情况,笔者发现海龙囤“新王宫”遗址与木召古城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差异,但木召古城时代要早得多,故木召古城在土司建城史上的建筑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亟待探讨。另外,本次考古发掘还揭示了可能是南宋末年播州杨氏在朝廷帮助下修筑的“老王宫”遗址墙体的局部,发现其砌墙的方式为天然片麻石平砌、粘合剂为一般的泥土,与明代的墙体用开凿加工成规整的石灰石和砖砌筑、以石灰作粘合剂的砌筑方法明显不同。前者是土著的砌筑方法,后者当是受到了内地的直接影响。鉴于海龙囤“老王宫”“新王宫”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未完全公布,笔者不便对此作进一步讨论。①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遵义海龙囤遗址:2012年度发掘》,《考古》2013年第7期。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初步总结元、明时期土司城的特点:第一,土司城一般依山险而建,有的坐落在台地上,面向河流和平地,明显地从山地或山巅下移到平地和河谷。海龙囤比较特殊,特别建在四周悬壁的宽阔山巅,是集军事屯堡、衙署与“行宫”为一体的土司遗存,主要是从军事上考虑。第二,城的规模比较大,结构严谨,上下前后层次分明,左右对称,土司处理政事的厅堂政治中心地位凸显,当是一次性规划的产物。第三,土司级别越高,城的规模越大,有系统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附属性设施,这是居住形态政治等级化的表现。总之,土司城在形制上大体模仿了内地汉式政治性建筑,但在选址、内部功能、具体设施上差异很大,如对山地山险的充分考虑、缺乏汉式礼制建筑、没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和办公场所等,这些都是土著性的体现。
六、结论
1.唐代及其以前,贵州土著社会的居住形态为“散在山洞间”的山地型,这是与山地乔木与灌木环境下形成的游耕兼畜牧经济相适应的居住形态。这种形态是贵州土著居住的基本模式,延续时间非常长,至近代在局部地区还常见。
2.宋代,随着土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内地政治、经济因素的输入,土著居住形态出现分层化、等级化的发展态势,并呈现出从山地型向河谷平地型的过渡态势,但二者长期并存,各得其所、各得其宜,是一种缓慢连续性发展变迁。河谷平地型生计和居住形态是在内地汉族深刻影响下,土著社会经济文化自觉缓慢发展的产物,其实质是由生业形态的转变所引起的居住形态的变化。
3.各土著社会在对抗内地化农耕经济及其城镇居住形态的过程中,依赖传统的山地型生计居住模式,长期“据阨为垒”、“据险起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设施和战争优势,这是适应当地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与游耕畜牧生计方式的军事化居住样态。
4.元、明、清时期,贵州不断被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管理之下,内地汉族的经济文化及其居住形态直接移入贵州,在此背景下,产生了贵州土著居住最高形态——土司城。土司城在形制上大体模仿了内地汉式政治性建筑,但在选址、内部功能、具体设施上差异很大,如对山地山险的依赖、缺乏汉式礼制建筑、没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和办公场所等。
5.在当今少数民族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充分考虑各民族长期惯习的山地型生计居住模式的建筑样式、具体功能和独特的生态适应价值,不宜全盘否定;要吸取宋代“始创城砦,比之内地”的“浪潮”后引起的“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吴启琳)
A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ving Form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Guizhou in Ancient Times
Ye Chengyo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aiology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550025)
The Tang Dynasty before,the living form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Guizhou is the mountain type of" spread in the cave",which is a living form that meet the needs of shifting cultivat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mountain trees and shrubs.In the Song Dynast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nputof mainlan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aboriginal living form is layering and hierarchical,and present a transition from the mountain to the valley plain model,but the two forms co-exist for a long time,which is a slow continuous change.Guizhou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under its direct management in the period of the Yuan,the Ming and the Qing,Chinese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its morphology in the mainland are directly in Guizhou,c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 construction in mainland generally appeared,in this context,the Toast city as the highest native living form in Guizhou comes into being.At the same time,the aboriginal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against the agrarian economy and urban morphology in the mainland,formed the unique military living form which is adapt to the local Karst mounta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hifting cultivat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livelihoods for long-term"guarding Ai as base","uprising guarding the risks".
Auizhou;Indigenous community;living form
K901.8
A
1008-7354(2015)05-0001-11
叶成勇(1977-),贵州思南人,历史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西南地区民族历史和民族考古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