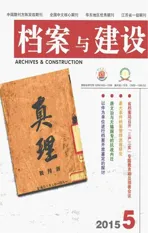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档案文化走向探析*
2015-03-30倪丽娟
李 洋 倪丽娟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受社会政治体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档案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仅具一种文化表征而是由档案管理制度、档案社会意识、档案保护技术、档案利用方式、档案职业特点、档案学术研究等因素与社会政治体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环境因素结合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凝聚。由档案文化构成的内容来看,只有对档案文化组成部分进行深入剖析,才能更好的对档案文化走向进行总结。
1 档案管理思想的人本化
奴隶社会时期,我国社会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神权政治。正如《礼记·表记》中所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即当时社会的一切政事并不是由统治者个人专断,也不是由王公贵族共同商议探讨决定,是以天或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请示神祖命定,先神事,后人事。在奴隶社会时期其实还未出现专门的档案管理,自然档案管理思想还未形成,但通过对商代甲骨档案的研究,我们对当时档案管理意识也可知晓一二。商代的甲骨档案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在进行政事和占卜活动中形成的原始记录性的系统化官府文书。在卜辞刻写上也有固定的体式,一篇完整的殷商卜辞文书主要包括前辞、问辞、占辞、验辞。第一部分就是记载卜问的时间及卜官的姓名;第二部分是记述向神祖卜问求告的事情;第三部分即对卜兆结果的记载并根据兆圻而定的吉凶之辞;第四部分是对卜问后应验情况的记载。其实无论是当时档案的内容还是形成方式或是对甲骨文书的保管,我们不难看出奴隶社会时期,对于档案的管理被卜官看成是对神物的管理。也正是由于早期社会生产力的地下,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的意志理解不清,才会有神祖就是吉凶祸兆的掌控者的观念,才会将档案当作神物一样管理。
进入到封建社会,阶级开始分化,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统治,视档案为帝王所撰写的规章典籍,他人不可侵犯。故档案管理思想的神权化逐渐被君本位管理理念所取代。档案作为维护政权统治、打压异己、宣扬传播唯我独尊专制思想的利器,被应用于律法、修史编志、文化传播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秦朝时期律法档案中的皇帝诏令(秦代最基本的法律),“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2],这表明诏令具有当时最高法律效力的同时也可以随时针对变化着的情况颁布,这就大大加强了皇权专制下的为所欲为的统治。另外,早在秦朝官府颁布的命令中还广涉农业、手工业、赋徭、官吏等方面,这些律法无疑为其推行中央集权,巩固专制政权起到的重要作用。久而久之,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档案管理日益受到重视,从文书档案管理机构及官吏的设置到文书档案的种类与体式体例再到档案的保管存贮都体现着君本位管理的强权政治色彩。如明代建立的保管全国赋役档案的专门档案库——后湖黄册库。据《后湖志》等相关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其在收藏黄册的数量、库房建设、档案管理人员机构设置上的规模在我国档案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明太祖对于库房建设上也极其重视,曾多次参与策划。对于黄册库的用纸制度及定期晾晒制度、保密制度等都有着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这种斥资聚力对专门档案库的修建并不是因为当时的财政实力,而是由于黄册直接关系着明王朝的专制集权统治和经济命脉,对于后湖黄册库的重视则是当时皇权统治不可侵犯性的直接反映。在封建社会将近2400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君本位档案管理思想时刻贯穿在统治阶级意识中,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更替与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君本位档案管理理念的伪科学性也逐渐被档案界认同。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我国档案学思想也向着科学规范的管理理论稳步迈进,人们逐渐认识到档案的管理不是以政治统治为宗旨,为社会提供利用与服务才是最终目的。例如,“我国著名档案学家吴宝康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发表的《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首次明确地提出档案的保管和社会的利用是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档案利用是档案工作诸环节中的主要环节,利用是中心,利用是目的,并说这是我国档案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3]随后,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五条规定:“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因此,是否便于社会各方面对档案的利用,成为当时对档案工作成果检验的重要衡量标准。同时我们也可从中看出,便于社会各方面对档案的利用,满足社会对档案的需求,也成为档案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4]。这种以人为本的档案管理理念在我国档案工作改革至今一直发挥着良好的社会效益。正如201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中,杨冬权同志提出2015年全国档案工作的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贯彻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继续推进“三个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宣传质量,创新宣传方式,为档案工作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为建设档案强国提供强大舆论支持[5]。
2 档案社会意识社会化
档案社会意识是指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这一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是人们对档案的性质和价值的认识,对档案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它包括社会上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6]。随着档案管理活动的开展与深入,档案逐渐从政治领域走向经济建设、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档案的社会意识也渐渐形成,人们对档案的意识已从封闭禁锢的印象中走出来,由史料慢慢演变成公务文书、信息资源、社会记忆、知识、文化等多个角色。社会对档案的需求也呈现出逐渐深层化、专业化的特点,档案的这种服务于民众与社会的价值也逐渐凸显出来。
古代社会时期,无论是当权统治者,还是那些管理文书档案的史官,都将档案视为“史料”,这时的史料主要分为官方文书和私人编纂。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档案这种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成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统治、打压异己、宣扬传播唯我独尊等专制思想的利器,而社会对档案的需求还没有出现。如两汉时期的“汉承秦制”,即汉的国家制度、官吏选拔等都是在秦朝档案基础上加以增损变通而得到建立和发展。在汉朝对档案的收集方面,司马迁在《史记》中进行了详实的记载,“汉王所以具知天下砈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7],刘邦军攻入咸阳时,萧何首先抢救和收藏了秦朝中央保存的律令、地图、户籍等档案文件。可见当时汉王朝统治者已将档案视为制定国策规定的史料依据。其实不仅仅是汉朝将其视为史料,历代统治者也皆有此意识,他们重视对档案的保管并命专人进行档案史料编纂,并教育自己的臣民以史为鉴,以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目的,从而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随着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近代社会西方思想的传入和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档案不再仅具有史料的功用,档案日益转化成“公务文书”的角色。社会对档案的需求日益增加,逐步重视其辅佐公务的功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文书档案连锁法将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两者结合为一,改变了当时文书运转迟缓和档案管理分散、垄断的状况。当时的学者也纷纷表示赞成,甘乃光认为,“文书与档案本不能分,档案原为归档之书,文书及未归档之档案,二者实一者也”。周连宽在《档案管理法》对档案也是这样定义的。“所谓档案,系指处理完毕而存贮备查之公文也”[8]。何鲁成在1938年《档案管理与整理》中提到,“档案者乃已办理完毕,归档后汇案编制留待参考之文书”[9]。这些代表性的观点反映出当时对档案性质与属性的判断以及档案工作的特点,即公务文书化。
现代社会里的档案,记载了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涉及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文学艺术、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故档案不仅是政治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经济建设、文化发展、信息资源建设、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档案载体形式的多元化,档案利用方式逐渐多样化,无论是档案管理者还是社会公众,都将档案视为可提供凭证参考的原始记录;视为生产生活的信息保障;视为历史悠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视为信息经济时代下的一种知识资产。档案的社会价值也得到社会公众更好的挖掘与利用。据有关资料统计,民生档案的利用率逐年上升,“如重庆南岸区档案馆为了积极做好档案查阅利用服务工作,2014年区档案馆在区行政中心B 区行政大厅设立了档案查阅窗口,全年档案馆共接待档案查阅利用4075 人次,调阅档案6721 卷次,复印资料13229 张,其中查阅婚姻档案3583 人次,招工42 人次,破产解体企业155 人次,编修史志203人次,其他92 人次。从2014年查阅结构上来分析,其民生档案查阅利用率达到95%以上,各种档案原始依据为广大市民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0]。”这也正是档案被视为可提供凭证参考以服务民生的的原始记录的有效体现。又如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目前总体上来说可分为“实体管理”与“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两大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占据档案管理工作半壁江山的实体管理,已无法满足现代化信息技术挖掘信息共享,围绕创造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管理模式;其次又因企业档案管理工作边缘化趋势加剧,企业纷纷进行薪酬改革,扁平化改革,精简管理人员,降低档案档案工作人员的薪酬,因此如何构建一套完备理论与管理技术的知识管理体系成为了学者们研究企业档案管理的热点和主题。无疑,这种档案社会意识也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要求。
3 档案职业追求的社会化
档案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自文字产生以来,档案工作就应运而生。档案工作将我国历史各个时期的文明与文化都进行了传承,为我国社会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档案职业特点正是通过档案工作的特点所表现出来,本文所述的档案职业追求的社会化即指档案职业特点由原来的文化传承到文化传播的过渡。
近代社会以前,尤其是封建社会,我国档案工作还未形成专业的系统的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学思想,更无所谓专职的档案管理机构及专业人员,且档案管理与文书管理没有明显的界限,档案管理人员主要由当时的史官或辅政机构人员担任。档案工作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档案文献的编纂上,档案文献编纂也主要是起居注和实录等官修史书,这种历代的编纂就对我国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传承作用,再现历史面貌的同时,也传承了社会记忆。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编订的六经填补了我国先秦时期的档案工作空白;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后汉书》的编写积累丰富了两汉时期的档案文化,并为世代的文化传承与后代学术团体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合称的“十史”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十个王朝的记载;1928年正式出版的《清史稿》《四库全书》《皇朝通志》对我国清朝时期二百九十余年历史的编写与记录。虽类如《春秋》《史记》的通史数量较少断代史数量居多,但代代相传、代代延续的档案编纂文化从未因朝代更替中断过,我国的“二十五史”就是很好的佐证。档案文献编纂一直成为档案文化传播的主要承载物。
近代社会,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职业追求更注重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我国档案工作在政治变革、学术繁盛的背景下,随着社会危机的动荡和五四运动后科学主义思潮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档案工作逐渐认识到文化的入侵在侵蚀这一个国家的灵魂。只有维固好本国的民族文化才能强国富民。如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亚考察时对尼雅及敦煌地区大量文物的盗取;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时对档案文献、国家珍宝的强行掠夺;甲骨等文物的被瓜分等,这些都激发了档案管理人员的民族文化忧患意识。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以私人力量在金石档案、甲骨档案、简牍档案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代表作有刘鹗的《铁云藏龟》,郭沫若的《卜辞通纂》《金文丛考》,郭沫若、王国维的《流沙坠简》等。除此之外,我国文书档案种类,文书档案名称和体式,档案管理制度及档案管理方法的前承后继、世代相承,也弘扬了我国博大精深的档案文化,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随着信息社会的信息量激增、信息服务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公众需求的专业化趋势,档案工作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注重档案文化传承的同时,将档案工作重心转移到文化传播,使档案意识范围社会化。因为文化具有动态性,受众的需求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但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具有稳定性,这就需要档案工作人员利用档案通过管理活动、利用服务或媒介推广对我国档案文化进行传播,使我国社会公众更好地树立档案价值认知观念。目前,我国档案界对于档案文化传播的学术研究、实践管理活动也相继开展起来。如各省市档案馆纷纷设立的档案文化教育基地,档案文化精品的专题展览与主题月活动,由多媒体终端催生而来的微博、网站、微信订阅号等新兴媒体形式等档案文化传播方式。但与美国相比,我国在新媒体背景下档案文化传播的方式与途径还相对陈旧,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注重档案与新媒体结合下核心价值的发挥,利用科技优势使社交媒体成为档案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现任总统奥巴马先生也曾大力倡导行政管理部门提高业务素质与能力,驾驭新技术,及时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业务工作与决策,让公民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互动交流。美国的这种档案文化传播理念与方式是新颖的,可以借鉴。但我国档案职业追求应从我国档案管理体制出发,注重档案文化传播中个人隐私及信息安全问题,保证我国档案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礼记·表记》.
[2]秦铜权铭文.
[3]马仁杰,张胜春.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档案学通讯,2002(9)
[4]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国家档案局办公室. 2015年全国档案宣传工作要点[EB/OL]. http://www.saac.gov.cn/news/2015-02/27/content_87860.htm.
[6]尹美京.档案意识和档案工作的关系之我见[J].档案学通讯,2008(5).
[7]《史记·萧相国世家》.
[8]周连宽.档案管理法[M].中正书局,1954.
[9]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M].档案出版社,1987.
[10]张柯. 区民生档案查阅利用率逾95%[EB/OL]. http://www.cqna.com.cn/na_content/2015-01/08/content_3611463.htm,2015-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