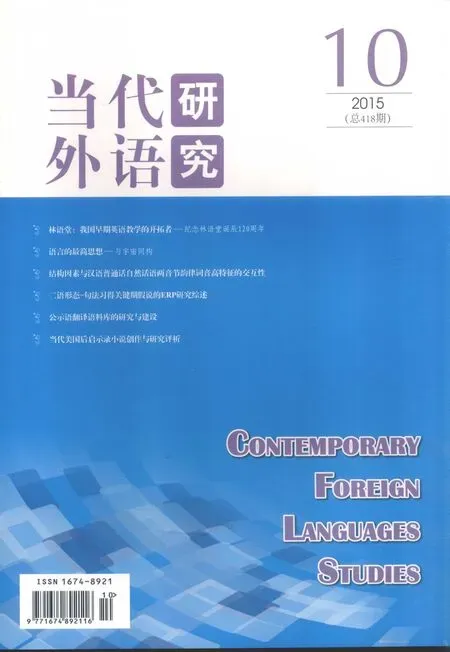戴·赫·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意象观
2015-03-29邵珊何江胜
邵珊 何江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210016)
戴·赫·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意象观
邵珊 何江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210016)
戴·赫·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有一个明显特征,即用意象创作。劳氏意象表征了贯穿短篇小说始终的主题支离人。根据两者间的对应程度,劳氏意象可分为直指主题和半指主题的意象,前者丰富了传统意象的内涵,后者扩大了传统意象的外延。同时,劳氏意象是以视觉为主,集听觉、触觉、嗅觉甚至动态因素为一体的杂糅意境,充分激发了读者的抽象感知。劳氏意象多重观感的汇聚流动形成了一动一静两个能量涡旋,对现代社会进行了一次从历时到共时的透视。劳氏能量涡旋记录了社会效应由外而内的转化过程,并揭露了支离人产生的根源,即现代化的解构性使巨大的消极物质能量变为爆发性的精神能量,无处宣泄,引发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分崩离析。
戴·赫·劳伦斯,短篇小说,意象,涡旋
戴·赫·劳伦斯一生写有七部短篇小说,并在其中成功塑造了支离人(the disintegrated individuals)形象。所谓支离人,即指处于西方现代文明重压下或饱经战争暴力摧残后被异化,以支离破碎的心理状态孤立生存的现代人。描摹形形色色的支离人是劳伦斯短篇小说最突出的主题。其中有些人物的支离破碎是直接显现的:《狐》(The Fox,1920/1922)中的“玛琪在两性关系中性别角色错乱”;《上尉的玩偶》(The Captain’s Doll,1923)中的“亚历山大在婚姻中无法履行男性角色且被操控摆布”;《瓢虫》(The Ladybird,1923)中的“迪翁尼斯因被摧毁了男性气质而疯狂无助,而戴夫妮在婚姻中压抑窒息”;《烈马莫尔》(St Mawr,1925)中的“路易莎不安于自我被压抑,桀骜焦虑”,而“莱科虽安于自我被压抑,内心却备受煎熬,焦虑不安”。另外一些人物的支离破碎在矛盾中显现:《小公主》(The Princess,1925)中的“多莉自诩为公主高高在上却为世人所厌弃,是个丑小孩般的存在,只能在无性婚姻中寻求慰藉”;《女孩与吉普赛人》(The Virgin and the Gipsy,1930)中的“伊薇特看似受宠实则为家人所憎恨厌弃”;以及《逃跑的雄鸡》(The Escaped Cock,1928/1929)中的“‘他’(即耶稣)重生后放弃了救世使命,陷入存在与生存意义虚无的泥潭,是个行尸走肉般的存在”(邵珊、何江胜2014)。支离人形象是对普通人外表平静完好而内心却创伤迷惘的概括,外表与内心间的张力既使得支离人的言行举止间渗透出异样的空洞和绝望,又是支离人形象能量与活力的源泉。
“作为意象派诗人一员的劳伦斯”(Drabble 2005:515)不仅在诗作中奉行它的创作原则,还成功地将意象融入短篇小说中。“意象可以是任何东西,它可以是一副速写、一个插画、一段评论、一句格言警句,也可以是印象主义,甚至是诗以外的其它文类(prose)”(Pound 1915:349,转引自Hakutani 1992)。劳伦斯笔下的意象并不局限于“狭义上象征文学作品的某种事物”,还包括“作用于感官上的抽象意境”(Abrams 2004:121)。劳氏意象既丰富多样又和谐统一,他在每部短篇中都创造出一个主导意象:《狐》中的狐狸、《上尉的玩偶》中的玩偶、《瓢虫》中的瓢虫、《烈马莫尔》中的烈马、《小公主》中的小公主、《女孩与吉普赛人》中的宠儿,以及《逃跑的雄鸡》中雄鸡。这些意象表征了不同情形的支离破碎,根据意象与主题支离人的对应程度,劳氏意象可分为两类:直指主题的意象,即较全面概括支离人的意象,如狐狸、玩偶、瓢虫和烈马;半指主题的意象,即仅提炼矛盾的支离破碎中矛盾一方的意象,如小公主、宠儿和雄鸡。
直指主题的意象是对直接显现的支离破碎的正面描摹,并通过类比丰富了传统意象的内涵;半指主题的意象是对在矛盾中显现的支离破碎的衬托,并通过反语扩展了传统意象的外延。同时劳氏意象还具有杂糅的意境,直指主题的意象形成的动态意境和半指主题的意象形成的静态意境充分激发了读者的抽象感知,完善了从支离人到意象的投射。劳氏杂糅意境的能量都因共性而互相吸引,形成能量涡旋。两个涡旋一动一静,从历时到共时对现代社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透视。
1.劳氏意象的内涵和外延
劳氏意象立意新颖,意蕴丰富,“摆脱了传统意象的一般性特点”(萨克文2009:129),是对传统意象内涵的丰富,也是对其外延的扩展。传统意义上,狐狸是一种弱小、狡猾、善于隐藏的动物,也可指狡诈的人;玩偶是微缩的人形玩具,是傀儡,也指被操控摆布以取乐于人的人;瓢虫(ladybird or ladybug)这个词起源于中世纪,“人们谨以这种昆虫献给圣母玛利亚,并称它们为圣母之虫,是圣母的象征”(Britanica 2010);烈马是温和驯服的动物种群中桀骜不驯的另类存在,也可指桀骜不驯的人;公主指身份尤为高贵的皇族直系女性;宠儿是某个社会单位或群体中备受宠爱和关注的人;雄鸡通常是鸡群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唯一雄性,“雄鸡啼叫在基督教文化中象征着觉醒、耶稣复生……宣告精神上的黑暗和绝望之终结……也象征勇敢”(丁光训、金鲁贤2010:719)。劳氏意象中直指作品主题的意象沿用了传统意象的能指范围,即狐狸、玩偶、瓢虫和烈马原本都可以用来指人,它们的“非一般性”在于使传统意象的内涵多样化、具体化。而半指主题的则沿用了传统意象的所指内容,即公主、宠儿和雄鸡都保持着传统的意义,它们的“非一般性”在于使传统意象的外延扩大化。无论是对传统意象内涵的丰富还是外延的扩展,劳伦斯都以新的视角引领着读者体验一场细腻而传神的文字盛宴。
直指作品主题的劳氏意象既脱胎于传统意象,又与其迥然不同。劳氏狐狸是迷幻诱人而又注定死亡的,既符合传统狐狸的弱小狡猾,又因注定死亡而不同。劳氏玩偶既是惟妙惟肖的,又是被倒置而无力的,既符合传统定义之被摆布的人形玩偶,又因被倒置而不同。劳氏瓢虫既是私密而疯狂的,又是沉重而压抑的,它符合传统圣母圣子间的亲密感,又因疯狂和毁灭而不同,同时它符合圣母被无限弱化的附属地位,又因自身的不情愿与被压抑而不同。劳氏烈马既是桀骜不驯的、会伤人的,又是顺从的、焦虑不安的,它一方面符合传统的桀骜抗争,又因对男性的厌恶而不同;另一方面它符合温顺种群的顺从压抑,又因时时爆发的焦虑而不同。
直指作品主题的劳氏意象是对直接显现的支离破碎的正面描摹,其内涵与支离人的境遇性质相同。劳氏狐狸的迷幻诱人、注定死亡与玛琪在同性、异性关系中的摇摆不定和附属地位是同质的。玩偶与亚历山大的极度相似和被倒置的无力状态,是对他在婚姻和社会生活中被妻子操控摆布的“惟妙惟肖的模仿”(939)①。瓢虫作为家徽“由家族女性亲手缝制……绣在衬衣衣领内侧,紧贴着皮肤”(1073),传达了圣母圣子间的血肉相连的私密感,表征着流淌于迪翁尼斯血液中的男性气质;而“绣在帽子内侧……类似谚语中帽子里飞进蜜蜂意指疯狂”(1073),则体现迪翁尼斯被摧毁了男性气质,内心狂乱而无助。同时瓢虫作为宝石顶针“戴在手上很重……这种沉沉的感觉,她[戴夫妮]一边缝纫,一边想着自己的丈夫”(1080),通过指向圣母在圣父与圣子间不可或缺却被无限弱化的附属地位,表现戴夫妮在婚姻中的压抑窒息。烈马的桀骜不驯、会伤人的特征与路易莎对社会礼教的抵触抗争,以及对像莱科一样被驯化男性的厌恶逃避是同质的。而被圈养的烈马终究会像其它的马一样温顺恭谦,与莱科虽然“是一匹烈马”(1061),野性却时刻被压制,永远也无法爆发,而“焦虑不安”(1113)的境遇是同质的。
类比实现了从支离人到劳氏意象的投射,透过意象可以清楚地透视支离人,而支离人的种种境遇也使得劳氏意象具体而丰富。“类比是为了显示两事物相似的一种比较,通常是为了说明(通过与人们熟知的事物间相似性的比较,来说明不为人熟知的事物)或论证(力图说明对比的两事物间,适用于其中一个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另一个)”(李正栓2006:384)。劳伦斯通过重点渲染支离人境遇和意象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使人们将后者性质自然地转嫁到支离人身上,从而产生相应的投射:玛琪像狐狸一样错乱多变;亚历山大像玩偶一样受人摆布;迪翁尼斯像谚语中的瓢虫一样疯狂无助及戴夫妮像代表圣母的瓢虫一样压抑窒息;路易莎像烈马一样桀骜不驯及莱科像被圈养的烈马一样野性被压抑而焦虑不安。类比的使用使支离人形象与日常生活经验和事物相联系,消除了支离人形象的陌生感,也赋予老生常谈的日常事物以不同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
半指主题的劳氏意象沿用传统意象的所指内容,却颠覆其能指范围,将意象所指投射在与传统能指完全相反的范畴,而新能指范畴是对支离人境遇的概括。在劳伦斯笔下,高贵美丽的公主被用来指代丑小孩(changeling),而丑小孩是民间传说中在婴儿时期被仙女偷换后留下的孩子。丑小孩具有不受欢迎、是替代品的性质,是对多莉为世人所厌弃、只能在无性婚姻中寻求慰藉的处境的概括。深受人们宠爱关注的宠儿被用来指代吉普赛人,而吉普赛人历来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是被排斥厌恶的流浪者。由于这些被排斥、游离的性质,吉普赛人是对伊薇特为家人所憎恨厌弃、被边缘化的处境的浓缩。充满活力生气、斗志昂扬的雄鸡被用来指代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肉体存活而精神死亡的代名词。由于肉体的活力和精神的无力,行尸走肉是对“他”复活后放弃了救世使命、陷入生存意义虚无的泥潭的处境的象征。
半指主题的劳氏意象的新能指与传统能指间的对立是主题矛盾的缩影。公主与丑小孩间的对立,是对多莉自诩高高在上,事实上却为世人所厌弃而只能在无性婚姻中寻求慰藉这个主题的浓缩;宠儿和吉普赛人间的对立,是对伊薇特看似是家里和主流社会的宠儿,实则为家人所憎恨厌弃,是个被边缘化的吉普赛人的主题的概括;而雄鸡和行尸走肉的对立,是对“他”复活后肉体充满旺盛生命力,却放弃了救世使命,从而陷入生存意义虚无的泥潭的主题的浓缩。
反语(irony)实现了意象和其对立事物间的投射,其通过将处于对立的两者转换为对等关系而扩大了传统意象的外延。“反语作为修辞……特征是说与真实意图完全相反的话”(Kierkegaard 1989:247)。作者利用欲说之事与所述之实之间的张力,实现一种欲盖弥彰的效果,从而建立对立双方的投射关系。所谓小公主,喻指多莉自诩的冷漠疏离的贵族姿态,而丑小孩作为替代品带有勉强和不尽如人意之感,象征多莉在两性关系中被阉割的处境。多莉身上所表现出的嫌恶世人与被世俗关系遗弃的对立,变相显示了她作为不合时宜存在的支离破碎。所谓宠儿,是伊薇特那些道貌岸然、“却彼此憎恨的家庭成员们”(1260)为了掩盖她被遗弃的真实处境而营造出的假象。同时流浪、被遗弃的处境传达了伊薇特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反映了她的挫败与压抑。雄鸡旺盛的生命力喻指“他”被动获得的生命,而行尸走肉的生存状态象征了“他”生存意义的虚无。当一个神之子否定了为人类救赎的使命,“他”的存在就成了一种悖论,存在的事实凸显了意义的虚无。反语将原本格格不入的事物和意义联系在一起,使二者相斥相生,建立了处于张力中的和谐。
2.劳氏意象的杂糅意境
劳伦斯在创造文字盛宴的同时,还以杂糅的意境为读者营造了一场华丽的感官盛宴。劳氏意象突破了传统意象单纯的视觉性,并不局限于“对某种事物或场景的视觉再现”(Abrams 2004:121),而是一种以视觉为主,集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甚至动态因素为一体的杂糅意境。透过意象的折射,读者对支离人的认知由平面直观上升到立体会意,而折射的基础是意象与支离人间直接或间接的共性。因此杂糅的意境充分激发了读者的抽象感知,完善了从支离人到意象的投射。
直指作品主题意象的意境大多是动态的,以变化交错的视觉画面为主,并伴随其它感官感受及抽象感知。劳伦斯用细节描述和典故引用构建能激发全方位感官感受的杂糅意境,影射支离人的境遇。作者笔下的狐“是魔鬼……总在她们(玛琪和女友)眼皮子底下偷家禽……让她们气恼……溜得太快,根本捉不住”,又经常“在草丛中悉索潜行,若隐若现”(1006-1007),一旦现行总会让玛琪陷入“白日梦、半催眠中”(1008,1009,1010,1013,1022)。这些关于狐的细节描写营造出迷幻效果,作用于视觉、听觉以及抽象感知的动态意境,暗指玛琪与女友间模糊暧昧,却令其不满的性别角色。夜晚的梦魇中,玛琪“顺着狐狸的歌声拼命追逐,却被狐尾扫中,被烈火灼烧”(1015),看见“女友躺在棺材里,只能以狐皮覆身”(1031),而“最终死去的狐被倒吊着……被剥去皮毛”(1031-1032),营造出作用于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动态意境。追逐灼烧的细节影射玛琪内心对两性关系的渴望,而死亡、剥皮则暗示她在两性关系中注定无法实现自身想要的性别角色的结局。玩偶“穿着紧身的苏格兰呢子裤……是苏格兰人”,和“可怜的玩偶头朝下、双臂无力的耸拉着”(939)这些描述创造的意境偏静态,主要作用于视觉。前者象征高原人坚毅、豪迈的性情,后者影射压抑亚历山大真实性情的婚姻状态,并暗示着他在两性关系中始终支离破碎的结局。“几百年来,瓢虫一直绣在[迪翁尼斯的]家族帽子内侧”,“一个正常的世界业已毁灭……让我[迪翁尼斯]像瓢虫一样疯狂吧”(1073),这些细节创造出了作用于视觉和抽象感知的动态画面,暗示着迪翁尼斯男性气质的错乱颠倒和他在疯狂的世界里做一个没有意义的存在的命运。同时戴夫妮陷入与丈夫不愿亲热和与情人迪翁尼斯不能亲热的两难处境,只能作为一个“处女般贞静的存在”(1106),和“你[戴夫妮]无论生死,都是瓢虫[迪翁尼斯]在夜间的妻子”(1105,1108)的意境是静态的,主要作用于视觉,暗示了戴夫妮作为被阉割的存在的遭遇。烈马对于路易莎来说,是个“魔鬼”(1121),散发着“黑色的、隐形的火焰”(1119),却又“像一个从黑暗中张望的神祗……散发着白色的、刀锋般的冷冽”(1121),这种黑白交错、有形与无形杂糅、魔鬼与神祗共存的矛盾修饰法创造出作用于视觉、触觉和抽象感知的动态意境,暗示着路易莎桀骜不驯的内心及对文明世界压抑人的自我的外部抗争。对莱科来说,烈马“存在于一个希腊英雄们、包括希波吕托斯在内……的时代”(1124),并“充满力量……蠢蠢欲动,伺机报复”(1121)。神话典故的运用将烈马塑造成一个破坏者,一匹摔死神之子的马,这种意境是动态的,主要作用于视觉和抽象感知,影射莱科倍受压抑自我的煎熬的内心以及焦虑不安的处境。
劳伦斯还通过明喻将杂糅意境与支离人境遇间的暗示影射变为实在指涉。“明喻是一种……对比较之物与被比之物间共性的衡量……通过使用鲜明的意象来表现两者间常识之外的联系——比较通常不能比较的事物间的相似性”(Israel et al.2004:124)。以细节描述和谚语典故引用影射支离人的关键,在于它们所创造的意境画面尽管多变甚至抽象,却紧紧围绕着意象事物的内涵这个核心,是对意象事物内涵的立体化:无论狐狸在白天时的诡诈飘忽还是夜梦中的被屠戮,都反映了玛琪在两性关系中的摇摆错乱;玩偶被扭曲倒置的画面反映了亚历山大在婚姻中被操控摆布的处境;瓢虫在疯狂的世界中飞行的画面,反映了迪翁尼斯被摧毁了的男性气质;瓢虫夜间是妻子、白天像处女的画面反映了戴夫妮在婚姻中压抑窒息和被阉割的状态;烈马无论是像魔鬼散发黑色火焰,还是像神祗充满冷冽气质的画面,都反映了路易莎桀骜不驯及对文明世界压抑人的自我的不满;烈马像破坏者般报复的画面,反映了莱科倍受自我压抑的煎熬,从而焦虑不安的内心。同时,意象事物的内涵与支离人之间是类比的,具有同质性,因而意境与支离人之间是同质而不同类的关系。这种共性确立了文字描述和视觉及其他感觉所呈现的氛围间的投射,促成了支离人和意境间前者像后者的明喻关系。
半指主题意象的意境主要是静态的,以特写画面为主,以调动读者的抽象感知为辅。作者通过静与动、具体与抽象间的张力,象征意境与支离人境遇间的矛盾冲突,以激发读者的抽象感知。在劳伦斯笔下,有的意境在和谐中隐晦地透露出矛盾之处,即主体画面是对主题中矛盾的某一方的具象化,却又在细节上隐晦地透露出矛盾的另一方:小公主多莉“像从画儿里走出来的美人”(1227)、“像无性别的仙子”(1229)和“像永不结果的花朵,装腔作势、格格不入”(1228)。作者用美人、仙子、花朵表征公主所传达的美丽优雅和高贵身份,形成了静态的华美画面,而无性别、不结果的被阉割感是渗透于画面中的抽象感知,因而意境隐晦的矛盾在于华美精致总是伴随着被阉割感。有些意境是和谐统一的,画面仅体现主题中矛盾的一方,与主题另一方的支离人境遇形成鲜明对照,而二者的矛盾冲突调动了读者的抽象感知:如伊薇特“活得有些没心没肺”(1259),“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1262),“年轻、柔美的脸上透露出丝丝刚愎任性,显得有些冷酷”(1272)。这组人物特写主要是静态的,玩世不恭、冷酷疏离是伊薇特身为一个宠儿所流露出的特质,而她作为支离人的真实处境被转化为“自负……对主流社会嘲讽质疑”(1272)的吉普赛人形象。玩世不恭、冷酷疏离的宠儿姿态和愤世嫉俗却被边缘化的吉普赛人形象间的鲜明对比是对矛盾主题的模拟,两者间的对立激发了读者的抽象感知。雄鸡“侧着头,倾听着来自陌生世界里未知同类的挑战声”、“并以响亮的啼鸣应战”和“它上下扑腾、全力挣扎”(1320)。这组特写是动态的,意在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而“他”作为支离人“对重生感到厌恶”“充满幻灭”(1324),行尸走肉式的处境反映了精神和肉体上的静灭状态。斗志昂扬、不屈不挠的形象将雄鸡宗教意义上的特质动态化、具象化,与支离人内心肉体的静灭间的对立形成了对矛盾主题的立体化。
劳伦斯通过暗喻实现意境与支离人境遇间相斥相生的对应关系,将由反语实现的文字上的对立对等转化为抽象感知的对立对等。“暗喻源于两者(即比较之物和被比之物)间相通的日常体验……选择性地将一个领域的观念投射在另一个领域上……即创造两个领域间的共性”(Israel et al.2004:124)。作者或是利用意境中隐晦的不协调感与支离人境遇的矛盾感间的同质性,或是直接利用意境与支离人境遇间的矛盾冲突间蕴含的同质性,创造性地将静态或动态的感官感受转化为抽象感知,完善从意象到支离人的投射,而矛盾冲突始终是这种投射不变的核心。美人、仙子和花朵是无性别和不结果的,华美画面与被阉割感间的矛盾,与反语所实现的多莉看似是小公主实则为丑小孩的矛盾是同质的,暗喻利用这种同质性将文字领域的体验投射在感官领域上。而对于单纯的意境,暗喻则实现了由内在世界至外部画面的投射:如伊薇特外表玩世不恭、冷酷疏离而内心却自信自负的意境,体现了表里不一的对立,与伊薇特看似是宠儿实则被嫌恶、是被排斥的吉普赛人的处境间的对立是同质的。又如,斗志昂扬、不屈不挠的外在画面和被动幻灭的内心间的对立,与“他”肉体充满生气而内心却死气沉沉间的对立是同质的,暗喻正是藉由这种同质性,将文字上的矛盾统一转化为抽象感知的对立统一,完善了由支离人到意象的投射。
3.劳氏意象的能量涡旋
无论是直指主题的意象,还是半指主题的意象,杂糅意境对读者感官和抽象感受的调动都是意象能量与活力的体现。“意象是一个(观感)汇聚的节点或集合;它(意象)必然会成为涡旋——一个各种观感因不断产生、凝练、回归而生生不息的循环”(Pound 1914:469-70),而且“形成涡旋的意象充满了能量”(Hakutani 1992:47)。每个劳氏意象都是汇聚多重观感的集合,充满了能量与活力,而每组意象的意境都因拥有相似的性质而互相吸引,产生流动。同时能量因流动而融合凝练,释放出新的涡旋。直指主题的意象间的共同能量体现在视觉上色调的变化和感官上动静间的过渡,意境在这两方面的融合凝练释放出的涡旋是一段记录现代文明历时演变的动态短片。半指主题的意象间的共同能量体现在视觉层面和抽象感知层面始终奉行的矛盾感上,即两极间的相斥使涡旋充满了爆发性的力量,而其相生是种限制爆发的力量,给涡旋蒙上了一层平静的外表。这个看似平静实则汹涌的涡旋是对现代社会解构性的共时记录。
直指主题意象间的共同能量体现在视觉上色调的变化和感官上动静间的过渡。这组意象像黑白胶片,有的意境画面黑白分明,是动态的。如白日梦中狐狸迷离而疏远,时隐时现,夜梦中狐狸被追逐、灼烧、剥皮、死亡。有的意境画面黑白相间、时动时静。如瓢虫在白天贞静如处女,黑夜时却疯狂而毁灭,以及烈马是黑色的魔鬼,却像神祗散发着白色的光芒,像英雄充满力量却又躁动不安、伺机报复。还有的意境是空濛且静止的,如玩偶是被倒置的,四肢无力地耸拉着。这组画面有从黑白分明到黑白相间再到空濛的灰色的变化特点,和从动到时动时静再到完全静止的特点。意境在相似的色调和动静两方面拼贴融合,生成了由黑白分明到空濛灰色、由动而静的能量涡旋。
直指主题意象间所形成的由黑白分明到空濛灰色、由动而静的能量涡旋,是一段记录现代文明历时演变的动态短片。其色调变化力图体现现代化由启蒙时的艰难求存到繁荣壮大再到疲软的轨迹。白与黑、动与静都是好和坏的代名字。黑白分明的色调形成记录了现代化作为历史必然在发展初期的先锋性和进步性,与其在封建势力的统治下艰难求存形成鲜明对照。黑白相间则记录了在迅速发展的中期,现代化全面改造社会生产力的好和对人性逐渐产生异化作用的坏糅合共存。空濛灰色则记录了后期现代化在推动生产力飞跃方面的迟滞疲软和将现代人彻底变成支离人的弊端。同时,涡旋的动静转换记录了现代化效应由积极向消极的演变。“动”记录了现代化从萌芽到巅峰的上升过程,以及伴随生产力的飞跃而来的物质财富激增。“静”记录了现代化发展进入平稳期后,生产力失去激增魔力所导致的迟滞疲软,以及伴随现代化对人生存意义的解构而来的支离破碎。
半指主题意象间的共同能量体现在视觉层面和抽象感知层面始终奉行的矛盾感上。劳伦斯所描摹的现代社会似乎是“善”的体现:从视觉来看,现代人像公主、像宠儿、像雄鸡;从抽象感知来看,伴随公主身份的崇高地位和美丽精致,伴随宠儿身份的玩世不恭和万众瞩目,以及雄鸡所传达的旺盛斗志和生气勃勃是主体。然而相反的“恶”才是作者真正想传达的社会现实:从视觉来说,现代人其实是丑小孩、是吉普赛人、是行尸走肉;从抽象感知来说,被阉割感、被边缘化和死气沉沉才是隐晦却又真实的感受。无论是视觉还是抽象感知,作者都在差异最大化的两级间建立对等关系,这使涡旋充满了爆发性的力量,而对等给爆发性的力量掩上了一层平静的外表,因而形成一个看似平静实则汹涌的涡旋。
半指主题意象间所形成的看似平静实则汹涌的涡旋是对现代社会解构性的共时记录。现代社会的解构性是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人的生存意义的消解造成了人的客观实在与意义虚无间的悖论。传统观念上人的存在是先验宗教价值的体现,而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人被物化的过程。当赋予人一切行为以意义的上帝被证伪了,人的存在就不再具有了先验的价值,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行为也不再具有高于行为本身的意义,而仅仅是为了行为而行为,即人从一种价值自在体沦为纯工具性的存在,陷入了存在与意义虚无的泥潭。无论是意象的视觉效应还是抽象感知方面,美好外在和残酷内在间的强烈反差是对现代人陷入了存在与意义虚无的概括。因而,这个能量涡旋象征着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加剧的存在与虚无的悖论,涡旋平静的外表象征了现代人的客观实在,而汹涌内在象征了生存意义的不断被消解。现代人是一群顶着光鲜靓丽的外表而内心荒芜残缺的支离人。
4.结语
劳伦斯通过直指主题意象和半指主题意象所形成的两个能量涡旋一动一静,截然相反,并从历时到共时对现代社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透视。直指主题意象的能量涡旋是对现代社会外部世界演变的概括,无论其色调变化还是动静转换,都按时间轴的推移,记录了现代化进程中消极效应打破积极效应的垄断不断显现自身的过程。而半指主题意象的能量涡旋则是对现代人内在世界的描摹,是悬置了时间概念后,对身处同一社会的整个人群的透视,并透过静态的表象挖掘现代人分崩离析的意识形态。
同时,从历时涡旋能量的由动到静,到共时能量涡旋的由静到动,记录了社会效应由外而内的、动—静—动的转化过程。静态是能量对接的中间环节,也是社会效应由外而内的关键。当直指主题意象的涡旋的社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了外部扩张的积极效应后,其破坏性的力量不再被压制,由外而内作用于人身上,即能量从外部世界流入现代人的体内,转化成一种使人支离破碎的精神能量。巨大的消极物质能量变为爆发性的精神能量,无处宣泄,引发精神世界分崩离析,是现代社会解构性的根源。
劳氏意象是一种揭露现代文明解构性的创作实践。意象手法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丰富的感官效应,更在于对当下社会的审视和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探究,是通过世界来看人,也是透过人来看世界的尝试。这种努力使得劳伦斯的短篇超越了小说抒情、叙事的功能,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质。
附注
①文中劳伦斯作品的引文均选自Lawrence(2005)。所引中译文均为笔者自译,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Abrams,M.H.2004.A Glossary of Literature Term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ritannica.2010.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Z].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Drabble,M.2005.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kutani,Yoshinobu.1992.Ezra,Pound,Yone Noguchi,and imagism[J].Modern Philology1:46-69.
Israel,M.,R.H.Jennifer,&T.Vera.2004.On simile[A].In A.Michel &K.Suzanne(ed.).Language,Culture,Mind[C].Stanford:CSLI.123-35.
Kierkegaard,S.1989.The Concept of Irony,with Continual Reference of Socrates(Hong V.Howard &Edna H.Hong ed.&tran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wrence,D.H.2005.The Selected Works of D.H.Lawrence[M].Hertfordshire:Wordsworth.
Pound,Ezra.1914.Vorticism[J].Fortnightly Review573:469-70.
丁光训、金鲁贤.2010.基督教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正栓.2006.英国文学学习指南[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萨克文·伯克维奇.2009.剑桥美国文学史(第5卷)(马睿等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邵珊、何江胜.2014.戴·赫·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支离人”研究[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8-72.
(责任编辑 玄 琰)
I106.4
A
1674-8921-(2015)10-0067-05
10.3969/j.issn.1674-8921.2015.10.012
邵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现代文学。电子邮箱:nuaashaoshan@126.com
何江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现代文学。
*本文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科创基金资助项目(编号NR2014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