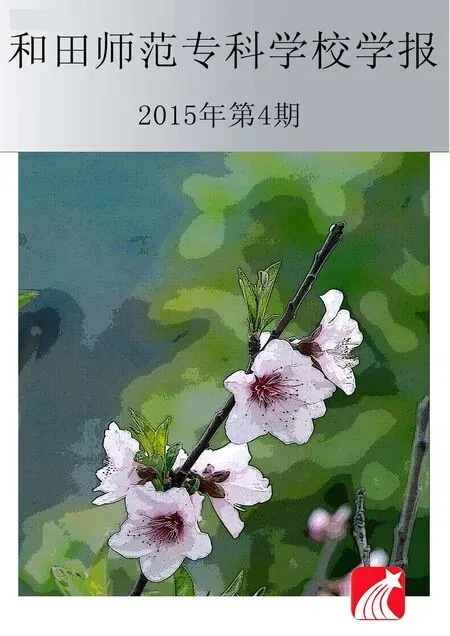王国维与红楼梦评论之悲剧
2015-03-29安之乐
安之乐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王国维与红楼梦评论之悲剧
安之乐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阐述了独特的美学精神、哲学思想、伦理价值、人生体悟,理性的分析了人类悲剧的因由,并且提出了解脱悲剧之道。然而,在其完备的哲学阐释下自己却又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一生,终究难以达到自己所构设的哲学境界,这种自身思想与现实相悖的解脱方式,说明王国维始终处于既可理性分析人生却无法超越人生的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
《红楼梦评论》;悲剧 ;解脱之道 ;美学;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是 1904年连载于《教育世界》的长篇论文,是王国维受外来思想 (主要是叔本华和康德的思想 )影响的激发而完成的 ,或者说是王国维在接受了外来的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独特的哲学、 美学观,并且通过解读《红楼梦》来阐述其一系列对于人生、欲望、死亡等思想。在当时所谓考证派、索隐派盛行的红学研究中,这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索《红楼梦》哲学、 美学价值的文章 ,既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以革新小说来革新国民的精神,用近代启蒙思想改造国民精神出发,发动了一场“小说界革命”后应运而生。王国维自己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 吾人持此标准以观美术。而美术中以诗歌、 戏曲、小说为其顶点 ,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 ,曰《红楼梦》 。”[1]由此可见,王国维对红楼梦如实描写人生,并对其如何解脱生之欲望与苦痛的阐释是相当推崇的。
一、《红楼梦评论》之悲剧思想与王国维之悲剧意识
《红楼梦》作为我国最优秀古典小说,其丰富杂糅的思想内容,高深的哲学境界决定了其内涵的开放性,对其解读从古至今堪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单是就其思想内容,就因读者眼光而有种种的不同见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鲁迅先生此话足见其思想内容方面的深度和广度。那么,王国维何以在正值青春年华的时期,带着一种人生悲剧的情愫去以这种别样的方式解读《红楼梦》完成《红楼梦评论》的长篇大论,这与王国维所处时代,少年时缺少父母之爱不善现实营生以及对艺术哲学的汲汲追求的经历相关,并且在种种的现实下导致对叔本华从本体论出发,揭示出生命存在的本身悲剧和虚无的哲学精神的接受。同时,《红楼梦评论》中所含的悲剧意识也似乎贯穿了王国维悲剧的一生,也是王国维一生的影射。
(一)生命情感之悲苦历程
首先,从王国维的人生、情感经历说起。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这个时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风云变换、屈辱难熬的时代,清代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时期,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也刺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民。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脊梁最早接受新思想而觉醒。王国维籍贯浙江海宁人,是近代哲学家思想家的集中分布区,蔡元培、鲁迅、龚自珍等都是浙江人,因其傍海而居,大海的惊涛澎湃、奔流不羁,孕育了这些学者更具有锋芒的思想,故地域文化本身对王国维作为接受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者身份奠定了文化因子。从王国维自身来说,王国维3岁时母亲不幸病故,父亲一直在外谋生,可见,王国维童年时是缺少孩童所需求的正常的父母之爱,是颇为孤独的。于是,童年的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寡言笑”[2]这样的童年经历奠定了王国维悲剧意识的性格基础。
王国维自从1896年与莫氏成婚之后,生活平静,1907年莫夫人病逝,要说童年时期人间生死离别带给王国维的仅仅是无以言说的情绪,莫夫人病逝给青年王国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失落。其诗《蝶恋花落日千山》:“中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这种细数往事的滋味又何尝不及“小轩窗,正梳妆”,“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谁复挑灯夜补衣”中国传统诗文中的悼亡经典之作。于此不久,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支撑他的父亲也去世了,这无疑对王国维来说是雪上加霜。1927年王国维不到50岁,长子王潜明在上海不幸病逝,丧子之痛于王国维这样一个外表沉静寡言、内心情感热烈的人来说又是一次强烈的打击,这一系列的情感冲击使王国维认识到了人生无常,世事变幻莫测的苍凉。
自古以来国人有人生三大不幸: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说法,我们纵观王国维的一生,人生的不幸他几乎全部经历了。而《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以及文章本身所延伸出来的人生存在的普世悲剧,阐述了王国维对悲剧的认识,同时,也隐含和预设了王国维的悲剧一生。
(二)精神追求与现实人事之两相矛盾
人事之累,即就是钱的问题,是每个人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同样,也成为成年后王国维为之困惑的问题,王国维自己也不善赚钱,从他结婚后仍然受父亲帮衬可见。他1899年去上海编辑《教育世界》的杂志,后来受罗振玉的资助,以及与其因为罗孝纯的生活费问题而决裂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经济之事。王国维自己也说是“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对于这样一个由祖宗光耀到逐渐衰落,经济拮据,由盛而衰的过程使得王国维对人情世故有了别样的认识。这种现实的经济问题与王国维的精神追求形成了一个极不协调的矛盾。王国维是一个对形而上的艺术哲学问题有深刻理解的人,如其所言“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这种绝对超乎功利主义的思想,与此前的经济问题格格不入,也成为王国维复杂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1900年他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很快对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与他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体验是吻合的。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王国维开首就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庄子和老子都认为人生存在最大的灾难就是人有了肉体本身,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无论是追求生活之欲的或是满足生活之欲的都会陷入一种无缘由的痛苦之中,一种欲望得到满足,一种欲望就会接踵而至,所以人生永远都得不到满足。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犹如西西佛斯、钟摆这样无休止的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故而人生即痛苦。随后作者又通过《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吾国人之作品构设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的心里自慰现象。批判吾国人这种乐天期己的生活愿望,这和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习惯于以大团圆结局,瞒和骗的精神实质相契合。得出“欲”即生活痛苦之本源。
王国维所说之欲包括了人生存所依赖的衣食住行物质方面需求和七情六欲等精神上的追求。而从王国维童年对于情感缺失的情形和青年时期为生活奔波的状况、对叔本华哲学的接受、以及一系列思考人生的现实体验,可见,人生即痛苦不仅是王国维理论上的一种见解阐释,更多的是其在生命中的真实体验。基于此,王国维对悲剧的定义不同于一贯从社会、阶级、环境议论善恶的看法,他把悲剧限定在人类本身的命运上,认为这是人类最终的结局,所以他能写出《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
二、《红楼梦评论》之美学价值与王国维之美学精神
王国维认识到精神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所以指出人生之解脱只能依靠于情感精神的暂时解脱,人生要暂时摆脱这种痛苦只能寄托于哲学、艺术。哲学艺术之根本便是美,通过美来净化外物之欲带给人的生命苦痛。1903年、1904年王国维发表过《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义》阐述了美所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美所指为人在艺术美中所体现的情感,人之所以有情感的起伏,是因为自己心系于某一个关于自己切身利害之事,独独有美的事物能够使人忘记现实之中的烦恼,从而达到一种心灵完全超脱纯净的境界,在这种境遇之中人才能得到一种纯粹的快乐。基于此,王国维又开始对美进行探索,并且对美的形式,以及不同形式的美对人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做了相关的阐释。
在《红楼梦评论》中将美又分为优美、壮美两种,优美是“由一对象之形式,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 ”壮美则是“越乎吾人知力所能奴之范围,或其形式大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 ”在这里,优美是一种平和宁静、小家碧玉之美,壮美是一种“悲壮”的形式,它更加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的思想超出于利害之外而又陷于意志分裂。与此相对应,在《人间词话》中,他说:“无我之境,人惟由静中得知;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3]优美在“无我之境”的“静”中使“人心平和” ,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相忘,便如庄子所书蝴蝶是庄子,还是庄子是蝴蝶,达到自我与本体合一的境界。壮美在“有我之境”的“由动之境”中“起人钦仰” ,一种追求而不得,得之而又苦苦追求的痛苦,一种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孤独隔绝的情感体验,无法回归的痛苦对本体的呼唤,从而实现它们的审美价值或人生价值。但不管怎样,作为美的形式,优美和壮美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让人摆脱生活的苦痛,沉醉于艺术的纯粹中。在红楼梦中,王国维所举的例子便是九十六回中泄机关颦儿迷本性中宝黛最后见面的情状:那样疯疯傻傻恍恍惚惚的对话、神态、情形、本就点点相印的两颗心在现实中却又是如此相隔相离的两个人,这种对读者的冲击真有种感天地,泣鬼神的震慑力,读者读之也有种排山倒海的情感起伏,五味杂陈欲说还休的难言,王国维将此归于壮美,而且王国维对壮美更加情有独钟,正是这种悲剧性的美感,在王国维看来是最能触动人心灵魂的,他认为《 红楼梦 》的价值正是在于以无限的悲壮而展现其伟大之处。王国维对于艺术,尤其是文学在情感美育中的功能之大,通过宝黛的最后决绝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红楼梦评论》之解脱之道与王国维之自杀
既然人生如此之苦痛,作为于痛苦之中挣扎的人,不得不去探求于此中痛苦的解脱之道,而以王国维来看红楼梦之根本精神则在于解脱。王国维自己提出:然则解脱者,果足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否乎?叔本华在其《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说个人意志的解脱不能脱离整个人类意志的解脱,因而解脱便成为可望不可即的理想。王国维对此观点提出了明显的怀疑态度,王国维自己所说的西方之哲学大多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1905年在其《静庵文集》序文中对叔本华哲学:“渐觉其有矛盾之处,去夏作《红楼梦评论》其理论全在于叔氏之立脚点。然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4]王国维科学客观的评判了自己文章立论的漏洞,又指出叔本华哲学中的种种缺陷问题。带着此种阙疑之精神分析出《红楼梦》伦理上之价值便在于解脱,作者否定了因生活之痛苦而自杀轻生之人,譬如尤三姐、金钏等人。指出解脱中的真正之解脱在出世、在宗教、在艺术。通过对王国维先生的生命情感历程的考察和文学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王国维先生曾也在不断的探索宗教的、艺术的解脱,但是最终却又以自杀的方式展现了其哲学思想的不可实现性,构成了现实和理想的某种悖论。
(一)皈依宗教之释道思想
王国维先生的出世思想,我们可以说从他早年的诗词中就隐伏了厌世弃俗的迹象。“生平颇忆挚卢敖,东过蓬莱浴海涛。何处云中闻犬吠,至今湖畔尚乌号。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王国维在引自己的这首《平生》是中通过卢敖、蓬莱、地狱、人间、众生、世尊等诗歌的意象,显示了强烈的黄老和佛学思想。在其早年的另外一首诗中王国维写到“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此诗对于人间是是非非的淡漠也浸透着强烈的出世心态。此外,王国维发表《人间词》时1906年,这部分诗也是作于其30岁左右,然而《人间词》中却透露出了强烈的人间悲苦体验,有股饱经风霜的沧桑感。如《蝶恋花辛苦钱塘》:“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到海……潮生潮落,几换人世间”。这首诗颇如苏轼的大江东去有种厚重的宇宙感。而宇就是天地四方的空间意识,宙则指往来古今的时间意识,宇宙意识实际上就是个体人所处在亘古流长的时间中有一种昙花一现般的瞬息感,在浩渺无垠的空间中有种沧海一粟般的渺小感。王国维在这首词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思想,与《红楼梦》中宝玉看着春去秋来、花红凋谢,鸟雀惊飞时的情感是相通的。所以贾宝玉不仅因为情爱失落而弃世,更加因为其对人世、对宇宙的一种绝妙的体悟而出家。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5]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最后之归宿也是随癞头和尚、破足道人而去 ,贾宝玉本是由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经一番世俗的悲欢离合的顽石,正是从来处来,往去处去,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本源“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 由此可见,王国维这种宗教的出世精神也与曹雪芹思想很契合。因此,王国维的这种思想因子与其《红楼梦评论》中所推崇的出世的解脱之道是相关的。
(二)悖于自我理想之最终自杀
《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将出世的解脱又分为两种:观他人之苦痛、觉自己之苦痛,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也。显然,王国维最推崇的解脱之道为实实在在经历了真真实实的生活,感到生活之痛苦而出世的方式,这也正是红楼梦这部书的伟大之处。同时,王国维自己在文中说到:“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满于现在之生活而求主张之于异日,则死于此者固不得不复生于彼,而苦海之流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这里王国维指出了自杀与生活之欲的关系。在《教育小言》中:“自杀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这是王国维自己对于解脱方式的思辨阐述。然而,王国维自己却于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仅仅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关于王国维自杀之因学术界有多重说法,罗振玉利用此次机会上演了王国维“殉清”“尸谏”的闹剧。也有根据王国维生前与罗振玉的书信关涉经济问题的指出所谓的罗振玉“逼债说”。同时,也有“殉学术”之说。陈寅恪在《王观堂挽词并序》一文中:“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6]即有名的殉文化之说。然而,这种种的解释如同贾宝玉因林黛玉魂归离恨天而“殉情”一样,红楼梦如若这样也决然没有了价值。我们以此来看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的生命解脱之道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王国维对叔本华的阙疑最终又用自己证实了其阙疑的错误性。
通过窥探王国维其人以及读其《红楼梦评论》一文可见其所阐发的悲剧思想、美学精神、解脱之道与其个人的生命经历和体验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有与其思想的相契的人生痛苦的观点,又有与其自身相悖的解脱方式,从而得出王国维始终处于既可理性分析人生却无法超越人生的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
[1] 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红楼梦评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文中关于《红楼梦评论》之引文皆出于此)
[2]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3] 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 陈寅恪.观堂集林[M]. 中华书局出版,1934.
[7]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 王国维评传[M].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9]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014-11-11
安之乐(198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