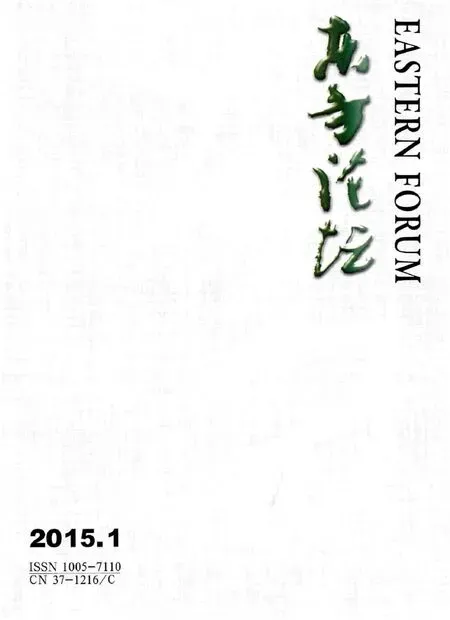再探“韦伯命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基于《中国的宗教: 儒教与道教》的一种解释
2015-03-29孙晨光
孙晨光
(香港城市大学 亚洲及国际学系, 香港 九龙 999077)
再探“韦伯命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基于《中国的宗教: 儒教与道教》的一种解释
孙晨光
(香港城市大学 亚洲及国际学系, 香港 九龙 999077)
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区,虽然其内部也存在宗教,但整个文化区的凝结宗旨是儒家式的伦理文化,即一种以家庭、宗族为基础的文化类型。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儒家伦理为讨论焦点,从社会生活的诸层面去论证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与西方的新教传统相比较。他着眼于官僚制的阻碍、卡里斯玛的巫术取向以及城市共同体的被压制、救赎宗教的缺失这四个关键特征,去探寻中国在各种社会条件都优于西方的情形下,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
韦伯命题;儒教;官僚制;卡里斯玛;城市共同体
一、“韦伯命题”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马克斯·韦伯虽以“宗教”为大命题,然实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思想诸层面的问题汇于一炉中而冶炼,称之为一部涵盖中国古今大势的“整体史”之类的著作似亦不为过。更有甚者,在本书的前四章中竟罕见“宗教”的踪迹,因此,韦伯在构筑此书框架与行文回转间的微妙用意常为各路行家、学人所揣测和争论。譬如,王容芬认为这源于韦伯并非“文化决定论者”,而是结合了纵向历史分析和横向文化比较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因此势必需要呈现一种全面和立体感的阐释过程[1]。但她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论”批判韦伯忽视了中国古代的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结构,实略有苛责之嫌。再者如郭宏斌的“社会物质性结构”说法,指出韦伯以一种“社会”的视角来佐证其提出的“中国古代的客观物质环境相似于(甚至优于)西方社会同时期”的假设前提[2]。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推论,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书中一些看似游离于“宗教”概念的数据、史实及阐释,皆可被纳入“大宗教”视野的理论预设,即“中国的宗教”这一概念要放置于更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历史环境中去探究,因此对第四章中的宗教得以发展的经济、政治与伦理基础发挥了起承转合的作用,儒教与道教的身影始终若隐若现、贯穿全书。
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相对照,本书的主旨似乎更趋隐晦,也许韦伯不愿重蹈《新教伦理》出版后即招致激烈讨论的覆辙;抑或庞杂的文献搜集工作(从十三经、《史记》《文献通考》《御批通鉴纲目》,再到《京报》和外交官的报告、传教士的书札,等等)分散了思想分析的连贯性。但我们仍可以从包罗万象的内容中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即中国为何没有出现如西方一样健全且富于理性的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所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生成关系?——此亦即“韦伯命题”的一部分,该命题认为“儒家伦理阻碍东方资本主义发展”。不过,《中国的宗教》实际上只是韦伯对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研究的开篇之作,欲获得对于“韦伯命题”乃至其宗教社会学内涵深意的全面体会,非通读整部“经济伦理”著作不可。韦伯借这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宗教大观”,通过对世界诸大宗教(文明)及催生它们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探讨,用以彰显基督教文明的独特性。若以某些学人思虑欠妥的断言,将韦伯标签化为“民族优越论者”[3](P5-10),则此话未免偏颇。在凸显西欧近代文明特色的同时,韦伯亦向西方人描绘出了一幅彰显各异文明风格的镶嵌画来;更何况,韦伯个人对近代西方“理性化”的全面发展,即世界的彻底“除魅”后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抱着颇为悲愤的态度,正如其在《新教伦理》一书结尾时的感慨,“依Baxter之见解,对外物的顾虑‘该像一件单薄的外套那样轻轻地披在圣徒的肩膀上,随时可以脱下’。但命运却使这件外套变成像钢一般坚硬的牢笼”[4](P151)。
由此可见,韦伯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以儒教和道教为概化标志的宗教传统为何与清教伦理大相径庭,即它没有如后者那样孕育出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这种反思也为帕森斯所接受,帕氏认为,近代资本主义虽首先出现于西欧,然而证诸史实,西欧的物质环境并不比中国、印度等地更适合资本主义之蕴生——西方之所以产生出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西方拥有其经济伦理可与资本主义相配合的基督新教[5](P603-608)。
二、政治领域内的阻碍——官僚制的无处不在
韦伯在本书中针对中国有关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因素的探究无疑是深刻且宏大的。虽然这种研究仍未超出历史范畴,其途径却与一般史学者热衷选用的指标颇有差异,韦伯对于那些贯穿于整个文明中的趋于稳定的现象抱以极大热忱——王朝屡屡更迭,官制亦代代有差,但在他看来,中国的“家产官僚制”治理结构基本稳定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确立的“家产制”支配格局[6](P81-87)。此外,中国的氏族及家庭组织也同样根深蒂固,氏族血缘纽带历经数千年甚至延及当代,此种关系恒如一道无法斩断的锁链支配着中国的基层社会运行结构。
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并建立中央官僚制度比之西方要先行了数个世纪,此即意味着中国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从土地的分配转移至官职的分配,官僚们的贪污所得与税收成为了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国家有50%的岁入流向了官僚的口袋[6](P98-100)。因此,基础性的在政治领域内的阻碍因素或许正在于此:帝国政府依赖于官僚的服务,而并非如中世纪西欧那样仰仗于骑士的军事服务,与专制集权需要相适应的官僚体系日臻壮大,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内的突破口逐渐趋于封闭。
文官制度的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着资本主义理性与现代教育的诞生,韦伯亦形象地称中国为“文人治理下的国家”。此处,文人较之文官也不尽相同,多有舞文弄墨之贬义。作为官僚制基石以实现“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之意的科举制,在其背后维系制度稳态的教育方式对整个帝国的文化调节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的社会等级自隋唐以降,便与受教育水平尤其是经由考试选拔的“出仕”资格紧密捆绑,财产或家族名望等因素皆相形见绌[6](P168-170)。因此,中国古代的官僚制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被“文学教育至上”的选拔标准烙上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痕迹,深受此环境熏陶的历代文人虽然满腹经纶、礼乐通达,但除了具备基本的行政管理之术外,并无较为系统化的专业知识——国家的统治阶层以唤起卡里斯玛为终极目的,而终日徜徉于琴棋书画、填词作赋的氛围里。依韦伯的归纳法,所谓“典型的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如下两个特征:(一)非军事化的纯粹文学教育,它亦具备了祭司式教育的大部分内涵;(二)以极强的舞文弄墨的文字性为根本形式①这种“文字性”据韦伯的考察是源于汉字的独特性以及文学艺术的氛围——“文字过分拘泥于象形而没有理性化为抽象的字母形式,目睹比耳闻更重要,由此发展出中国古代对书法艺术的强调。同时,由于读音的四声多样性促使文字在听说方面比较复杂,不能为系统的思维效劳,遑论为演说艺术的盛行助益一臂之力”[5](P158)。。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方社会经由专门化的业务教育来实现人才的管理和培养,理性官僚的统治结构因而建立,这种职业官僚制(有别于文人治理)的成型促使西方转向了同样具备理性化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
三、卡里斯玛与巫术的盘根错节
除此之外,当韦伯探讨传统中国各种与发展理性的资本主义所需条件背道而驰的机制时,亦将蕴含于此等结构之中的信仰伦理体系,诸如巫术性卡里斯玛信仰(祖先神灵的卡里斯玛、皇权的卡里斯玛、鬼神的卡里斯玛)、巫术的世界图像(包括将巫术泛灵论调和到“天人合一观”体系里的“巫术的系统性理性化”)、主导阶层即士人的身份性伦理与生活取向(知命与知礼),以及传统主义的人伦规范与二元道德经济伦理等等,一一扣合起来,它们一方面支撑着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与形塑,另一方面亦受此社会结构的制约而更趋根深蒂固。值得注意的是,“卡里斯玛”(Charisma)一词在韦伯的有关政治权力学说与城市起源阐释中出现频率极高,占据着重要地位,更是其论述与追溯国家统治合法性时最喜欢运用的一个概念。
巫术在中国皇权的强化进程中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特征在早期的历史运作中尤为明显,因为政权发展伊始时魅力型的统治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当社会运行渐趋稳态时,传统主义取代卡里斯玛的权威是一种必然——此时的卡里斯玛维系以血缘为主导因素,而遵循传统才是继承统治合法性的最佳途径。巫术在伦理方面的功能已渐趋式微,强调“忠孝”伦理的儒教之勃兴恰好迎合了巩固皇权的需求,其崛起之势亦理所当然。我国古代社会正是过多地纠缠和追寻卡里斯玛,使得巫术的浓雾一直若隐若现,二者的盘根错节逐渐使传统主义太过厚重而无法如西方社会那般通过“祛魅”(disenchantment)之路径来完成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法理型的统治一直都未在这块古老又坚固的冰层中破土而出。
四、城市类型学视野下的古代中国——没有城邦的宗族国家
“公民社会”可称现代社会重要特征之一,所谓“公民”的内涵,西方史学界往往不将其与“市民”作严格区隔。韦伯认为,西方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转折事件当为“城市共同体”的出现。他的另一部著作《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①本书原为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书第2卷第9章“支配社会学”的第7节,由于本节篇幅比之前6节明显不成比例,国内学界在编著成书时往往将第7节单独处理。不同版本的译名略有不同,比如江苏教育出版社的2014年新版本译为《城市:非正当性支配》。,可以视作解读“韦伯命题”尤其是城邦视角的关键互文范本,但历来未受到应有重视,笔者以为它绝非仅是一个“东西方城市产生不同制度的比较研究”[7](P17-18)。依韦伯的观点,此一共同体得以勃兴,正是“奠基在与传统束缚——包括氏族的羁绊、外来政治支配等——的决裂上”[8](P161)。之所以将西方的城市归为“非正当性的支配”一列,正是为了凸现出这些城市共同体支配权力的自主性,以及其权力来源之挣脱传统的“篡夺性”。此书中的一些观点亦可佐证《儒教与道教》中的结论,只不过变换了一个视角——城市的起源——来探讨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独特性,即“共同体的起源温床仅见于西方”。城市的团体性格,以及(相对于乡野人的)“城市人”的概念,鲜见于亚洲各民族之史实,微弱的存在亦近乎于萌芽状态。整体而言,“亚洲的城市居民并没有具备类似西方古代与中古的城市市民权,亚洲的城市也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法人性格”[8](P24)。
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亦断言中国各地的城市都是巨大围墙的代名词——城市并不等同于城邦,古希腊的城市本质而言是一种拥有独立政治特权的城邦共同体——城市最初是“王室督牧之住所”,在经济上由于欠缺“垄断的城市市场”,从而困囿于君王专制而无法染指政治上的自治状态。因而,韦伯的一个重要结论呼之欲出:中国式的城市并非市民之家。在中国,由于不存在“由武装市民组建的、以盟誓为纽带的政治联合体”,导致“血缘亲族关系的束缚枷锁从未被彻底斩断”,事实上,“中国的城市缺少自我管理的形式化保障体制”[6](P145-155)。
“经济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而阶级的分裂却提前完成”[9],换言之,一个国家里的自治城市未能出现、亦未经历氏族瓦解而直接完成封建化,称为政治上的早熟状态。克斯勒亦认为:中国的封建化过程其实只存在于政治的意义上,因为“政治性的封建制”理应在最初与土地所有制相关,而我国古代却是从“氏族式的国家组织”中脱颖而出[10]。由氏族维系的门阀望族在上述过程中掌握了权力,因此,一种世袭式的卡里斯玛由此形成,它依靠世袭的土地财产及政治方面的收入来维持地位。此外,城市的自由权利屡遭钳制,行会也无法充分地发展,这导致在同时期西方发达的经济贸易未能在中国出现,遑论行会共同体与君主权力的分庭抗礼。韦伯对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探寻得鞭辟入里:第一,大一统的国家不会面临国别争斗的危机(如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邦国的纷争)以及对外长年累月的征战,海外殖民的经历便显得不那么重要;第二,中国的财富积累不是凭商业贸易而是仰仗政治特权,如上文所述,官僚直接行使了收税的职能,他们也因此有着积累财富的理想与机会。可见,中国始终都没有生长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只有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等政治资本主义的盛行。这种史实所导致的荼毒遗患无穷,官本位、权钱勾结等观念至今仍根深蒂固。
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所谓城市组织都没有城市应具备的政治特点,这被形象地刻画为“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8](P27)。绝大部分的乡村都是由宗族势力来统治的,正式的皇家行政只限于市区(或市辖区)的范围,因此将中国称为一个宗族的国家是毫不为过的。通过垄断祖先崇拜的精神权,宗族逐渐演变为一种可与统治者分庭抗礼的组织,乡规民约实际凌驾于法律之上,并拥有一定的族内司法权,乡村在此意义上确实是自治的。不过,此联合体由于与外界往来甚少而保持了一定的封闭性,在经济意义上奉行对家计的自给自足,这对市场发展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在自治程度较高的乡村共同体中亦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此外,由于宗族分散在乡间山野,祖先崇拜各异,“各自为政”的状况并不能如联盟力量(德意志汉萨同盟的强势持续了数个世纪)一般形成对国家政权的强大抗衡。同理,在城市中没有诸如西方中古时期那种发达的手工业者、商业行会甚至盟誓共同体在经济领域构成对统治政权的约束,只得任凭庞大、体系健全的官僚阶层如阴云一般笼罩于帝国的广袤疆域。韦伯进而论述,“根据法律,世袭官僚制的国家机器直接凌驾于小市民和小农之上。无论从法律还是主要就事实而言,都没有中世纪(西方)封建社会的中间层”[8](P35)。在世袭制国家中,法律常常被专制主义所践踏,中间层的制约缺失使得法律被皇权干涉的现象更加肆无忌惮,加之最求实质公正而反对形式主义的家长制作风、法律适用的内在性质等因素,都导致了法律的难以理性化。综上所述,一方面不存在拥有政治地位的城市法人自治体,另一方面不能够从保障特权并使之固定化的角度创设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一直未能步入城邦时代,城邦的政治特权性质以及自治形态迟迟无法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只能接受一个“没有城邦的宗族国家”的史实。
五、救赎宗教的付之阙如
具体至宗教形态层面而言,韦伯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比之西方、中东乃至印度宗教的发展轨迹,我国古代从未涌现出社会凝聚力超强的先知,抑或掌控话语权的神职人员阶层,更极少提供与本土化的拯救学说、济世理论或民间的宗教力量密切相关的教育形式。所以,除非以驯服大众之目的为诉求,官僚阶层的知识从内在而言皆轻视宗教,理性能够自由地依需要得到自我阐释。纵然与西方的经典宗教类型尚有出入,但儒教毕竟是国家指定的、被祖先崇拜之精神及其信奉者规定的“宗教”。“适应于官本位的自我保护之利益”堪称该宗教的卡里斯玛魅力特征,若以教义论之,其主要倾向应是指出当下世界(此岸性的)之主要兴趣为健康长寿、多子多福及财富适度,罕见诸如末世思想、勤俭致富或拯救济世之类的踪迹。针对其它民间宗教的态度上,官僚世袭制的理性主义大体上秉承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与亨德里克·房龙描绘的“宽容”迥然有异),并非像西方宗教那样以屠杀与迫害之手段打击异教徒[11]。之所以为人民保留宗教,其意图在于忌惮民众因缺乏信仰而导致社会失序。与此同时,皇权全然不必担忧权威的旁落,因为这种权力基于卡里斯玛而本身地位亦凌驾于民间诸神之上。再者,儒教自身的生活方式是讲究等级有序的,而非西方典型的“市民式”——儒教的世界观中不存在“神”(或“自然”)同“成文法”“惯例”乃至任何其它约束力量之间的对立,亦罕见以宗教为基础的自然法及其形式的法律逻辑,再加之缺乏自然科学的思维(而非简单的实用主义式的“技术”),一切都未能推动中国踏上法律理性化的道路。
道教在长久以来何以未被正统宗教所铲除,却能够与之和平共处?儒教内化的对其它宗教的包容性固然是一方面。此外,“道”本身亦是正统儒教的一个概念:由于巫术信仰一直是中国统治权力分配的传统基础,但儒教对巫术的世界观长期一筹莫展。尽管两大宗教彼此对立与排斥,但经过斗争取得胜利的儒教并未提出灭绝巫术以正视听,因为这将危及整个儒教的统治合法性,而其仅以垄断官职俸禄为目的追求。尚有一点,儒教无法独揽道教所附带的巫术性功能——历代统治者所沉迷的养身经和长生术亦是道教收获器重的重要因素。由此观之,儒教的统治理性主义丝毫不能推动法律的理性化过程,此重任亦更不可能由神秘主义取向的道教来担负。
六、小结
韦伯对于中国宗教所得出的结论正可印证(毋宁说“补充”)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观点。儒教(也包括道教)与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即使二者皆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来设计人类生活。然而,儒教的目标在于获取并保有“一种文化的地位”,再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世界,其强调教育、自我完善以及家庭伦理;相反,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适应一个“上帝的工具”,其强烈的信仰与热情的“善功”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韦伯在结论中写道:“帝国的和平化,至少直接说明了古代西方、近东与中世纪所共同的那种政治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并不存在的缘故”,但他也表达了一丝困惑,即“可是却没能说明为何纯粹经济取向的资本主义也付之阙如”[6](P326),这一点的确值得深入探讨,毕竟中国人面对世界的实际态度,其各种基本特征在发展过程中深受政治与经济的命运所共同影响,也许韦伯还得另完成一部巨著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总而言之,限于东西方宗教在精神上的差异与社会理性化的背道而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终究未能在中国复制。然而,类似“儒家伦理当为东方资本主义发展之桎梏”的韦伯命题又是否成立呢?如果将研究视野扩展至现代阶段,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命题遭受了极大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由于日本的经济崛起以及随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儒教伦理似乎在向世界证明:该伦理促进了东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亦促进了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有学者由此对韦伯命题提出了挑战:儒家伦理未必就缺乏甚至无法达成自我现代转型的内在能力。纯知识论的方法并不能单一论证某个伦理学议题,而传统伦理的转化方式也并非以现代知识化为惟一取向[12](P36)。不知若韦伯仍在世,他将作出何种社会学意义的回应?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作为一部社会学领域内的巨著,其描绘的广阔历史图景与探索的深邃理论观点,无疑使我们读罢叹为观止。韦伯在书中作出的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之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必将对国人的思考产生极大的启发。
[1] 王容芬.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兼评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J].天津社会科学,1988,(6).
[2] 郭宏斌.基督新教与中国儒教、道教伦理观之比较——解读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J].甘肃社会科学,2006,(2).
[3] 麦克尔 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M].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简惠美,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 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 于振勇. 韦伯的城市类型学与非西方社会的城市发展——读《韦伯作品集Ⅵ: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EB/ O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5If5h70d1L-K03GcknL5O_ Etx13HLNUY-CwRcUdBx1BXItwUrO8xAsgZicPdJR6qJ_TuwpWf pauLbXsuOxoYcdSjtrrOGs2iYZ9zL4WGygC, 2008.
[8] 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 马小红.礼与法[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10] 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1] 亨德里克·房龙.宽容[M]. 上海:三联书店,2008.
[12] 万俊人.回应韦伯:儒家伦理的一个方法论问题[J].开放时代,1998,(3).
责任编辑:侯德彤
Why Capitalism Has Not Occurred in China: a Revisit of the "Weber's Proposition" Based on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SUN Chen-guang
( Dept of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owloon 999077, HK )
Within the China-based Confucian culture community, the ethic culture of the Confucian style is prevalent: a type of culture based on family and clan. Max Weber's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focuses on Confucian ethics, discussing the influences of Confucian ethics on Chinese society from all the aspects of society and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it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Protestantism. Max tries to explore why capitalism fails to develop in China where conditions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West by concentrating on four key characteristics: impediment to bureaucracy, witchcraft orientation of charisma, the suppression of urban community, and the loss of redemption religion.
Weber Proposition; Confucianism; bureaucracy; charisma; urban community
D033
A
1005-7110(2015)01-0110-05
2014-11-02
孙晨光(1988-),男,辽宁大连人,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博士研究生、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