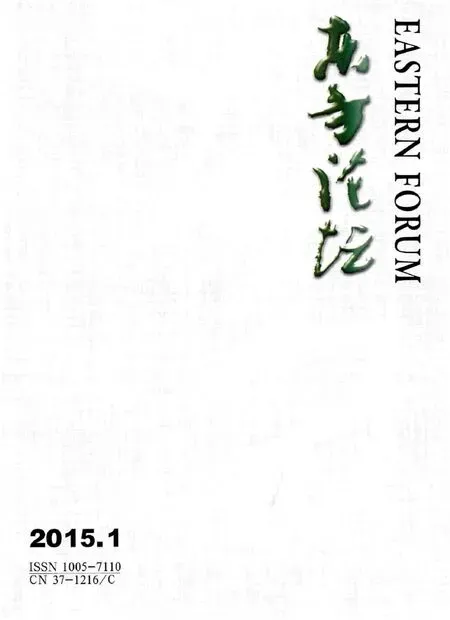创伤记忆与现代想象——重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伤痕电影”
2015-03-29韩琛
韩琛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创伤记忆与现代想象——重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伤痕电影”
韩琛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在1979-1983年间,无论是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理论争论,还是第三代、第四代的“伤痕电影”创作,抑或是学院时代的第五代导演的创伤叙事,都试图通过重构创伤记忆来释放被延迟的现代性渴望,当代中国电影则藉此而形成了新的现代想象与文化认同。“伤痕电影”是一个过渡时代的文化镜像,其与同一时期出现的其他“伤痕文艺”一样,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客观追溯与还原,不如说是试图在记忆历史中遗忘历史,进而与以发展进步为核心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达成暧昧的妥协。
现代化;伤痕电影;创伤记忆;遗忘;意识形态
通过否定之前时代,“文革”成就了自己合法性叙事,而后革命中国的历史合法性论述,也建立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新时期伊始,对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中国电影界来说,立足于辞旧迎新的历史批判,是需要首先完成的政治表达:“电影工作的当务之急有二:一是继续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二是总结过去电影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1]对“文革”的批判与否定,在1976-1979年间促成一批反“四人帮”电影的出现,《十月的风云》《蓝色的海湾》《希望》《严峻的历程》《失去记忆的人》《风雨里程》《并非一个人的故事》等“反映人民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影片,在整个电影生产中占有一个很大的比重。”[2]在完成历史批判与重建现代性项目的同时,主流意识形态也需要通过整合记忆的历史书写,来重构集体和个人的思想谱系,从而弥合“文革”造成的合法性危机。这就使得各种追溯历史、控诉压抑、感时伤怀的“伤痕文艺”风行一时,趁势而起的“伤痕电影”,亦藉此而蔚为大观,被不同世代的中国导演落实于电影创作实践中,成为1979-1983年间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之一。然而,弥合创伤、重塑记忆的历史生产和文艺创造,并不能完全消除被延迟的现代化焦虑,当下还必须拥有事关未来世界的理论蓝图,才能真正确立其文化领导权。“现代化”因此成为此一时期的主流话语。中国电影也不例外,电影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渴望,成为其理论探讨的主要诉求,并与“伤痕电影”的创作实践相伴而生。
一、现代性渴望与电影语言现代化
1979年,张暖忻和李陀发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这篇文章暗示了新中国前30年电影的“非/反现代”的本质,显示了十分激进的理论姿态。虽然作者认为论文“完全从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着眼的”,[3]但是,对所谓现代化电影语言的推崇与重视,显然使形式本身具有了优先于内容的本体论意味,电影语言的电影化、现代化,其实就是突出电影语言的自足性和本体性,以使之脱离意识形态的束缚。围绕这这篇文章,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界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不仅事关理论本身,而且更在于清算革命时代的基本电影认识,弥合“文革”给中国电影带来的伤害。辩证理论问题是为正本清源、重构合法性。这场讨论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关于电影的主题问题。其主要内容是关于人性的讨论,其与此一时期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的议题是一致的,围绕着人性的抽象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阶级性展开的论争,是对阶级斗争叙事的反拨。但是,讨论仅仅停留在表征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历史潜意识的层面。二是是关于电影体制改革的问题。电影生产的政企分离是其主要内容,袁小平认为“影片是商品,制片厂是企业”,[4]因此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关系,一个市场化的文化生产体系初见端倪。三是关于电影本体论的问题。这是一个核心议题,因为所谓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即是重构“电影是什么”的问题,前述两个问题必须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建立“现代”的电影话语体系并不仅仅意味着技术革新,它同样表明了知识精英对于现代的新认识,进步和发展的现代观念从民族主义角度得到了知识精英的认同:我们“只想从一个角度做一点探索,这就是如何使我国电影跟上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实现电影语言现代化的问题”。[3]电影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性想象的一部分,知识话语的现代性建构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表意机制重建的关键环节。即便在今天看来,关于电影本体论的争论是极为尖锐的,因为这涉及到了根本的认识论的问题,并与整个社会的历史转向联系在一起。
首先是电影与戏剧的关系问题。以白景晟,张暖忻、李陀,钟惦棐,陆建华,青竺,何仁为代表的一方主张“丢掉戏剧的拐杖”[5],“电影和戏剧离婚”[6],通过对于影戏传统的摒弃与否认,进而强调电影的本体论地位,“在银幕上以电影表现生活的逼真性代替戏剧反映生活的假定性,这才是将银幕从舞台框里解放出来的坦途。”[7]而以邵牧君,张骏祥,余倩等为代表的另外一方则主张:“只要电影还是一种叙事艺术,而且还是一种需要演员的叙事艺术,那么,戏剧矛盾和戏剧情节,就不但不是违反它的本性,而恰恰相反,却正是它的本性所要求的。”[8]辩论双方都没有否认电影的戏剧性因素,只不过持激进立场的一派致力于“纯电影”的理论建构,是一种现代主义电影观的表述,而反对一方则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电影观,并指责激进派的非戏剧化主张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原则格格不入的……从而不自觉地向现代派的非戏剧化靠拢,这可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错误道路”[9]。最终,争论双方陷入了意识形态对峙之中,并没有从艺术本体性的角度思考戏剧与电影的异同。不过,邵牧君认为“电影语言现代化”就是现代派的判断十分准确,其实践者便是数年之后出现的第五代导演。
其次是电影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张骏祥在1980年的一个会议上提出“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10],引发了有关电影与文学、电影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讨论。王愿坚,舒晓明、文伦,陈荒煤,艾明之、李天济、孟森辉,王炼,叶丹,汪流等人认为:“文学性是电影艺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种属性。或者可以说,电影,就是看得见的文学”。不过张卫,钟惦棐则坚持“电影既然作为一门独立艺术,也就必然有独立的表现思想、创造典型的功能,有观察、提炼、表现生活的直接性,不需要其他的艺术做它的中介和桥梁”[11]。余倩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电影和文学是这样矛盾,又是这样统一。电影和文学的矛盾统一,也可以说是电影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12]。围绕电影性与文学性争论其实就是关于电影的领导权的争夺。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界,主导电影话语权的主要是文学界人士,坚持电影的文学本质其实就是坚持文学对于电影的领导。而另一方则通过对于电影性的强调或者与文学的对比,突出并分离出电影的本体性特征,“电影形象本质上未必低于出自笔端的形象,甚至完全可能胜过它,是一个新的美学实体”[13](P127)。
无论是探讨电影与戏剧还是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其目的最终还是关于电影本体论的分歧,于是就出现了关于电影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是“纯电影”和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之争。邵牧君,张骏祥,李少白,张柔桑,郑雪莱,孟森辉,于敏各自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但出发点皆是针对《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表明了一种影像本体论的电影观,其基本诉求在于确立“作者电影”的观念。虽然邵牧君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中批判了前者的现代派倾向,但他本人在1980年发表了《略论西方电影中的现代主义》一文,批判性的论述亦隐含着别样的意义。到1983年,随着第五代电影的出现,有关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告一段落,郑雪莱在《现代电影观念探讨》中梳理现代电影的概念及历史,将现代电影看作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是一个生发于传统的电影模式但又与之断裂的前驱的电影观,而中国电影的现代化突破则“表明我国电影正努力赶上当代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趋势”[14]。“电影语言现代化”最终被具体“落实”于现实的电影实践中。
有关现代电影的讨论意义重大,其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电影源于担心自身被排除于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创伤体验,另一方面则表征了意识形态领域关于如何定义“现代”的分歧。所谓现代,意味着持续地断裂、分离,而现代化与其说是追逐未来,不如说是不停地告别过去。实际上,这个现代意识已经充分体现在了此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中,《沙鸥》《小花》《小街》等电影在探索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同时,又试图完成一种断裂式的历史叙事,“伤痕电影”于是成为中国电影银幕上的主流,后革命中国籍此完成了对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镜像重塑。
二、重塑记忆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伤痕电影”
从1979年到1983年,各大电影厂每年生产的剧情片从65部增加到127部。 《啊,摇篮》 《小花》《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沙鸥》《小街》《城南旧事》《逆光》等影片是这一时期比较出色的作品。影片体现了比较强烈的时代性和写实性,与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还可能受到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张暖忻和李陀谈及的现代电影语言,即指巴赞的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巴赞认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是在“拯救着一种革命人道主义”[13](P270),同样也可以作为对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的评价。不过,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不同,此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却致力于重塑历史,电影中真实的“现实”其实是关于集体记忆的虚构性重构。就像1979年发表的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一样,亦真亦幻的“伤痕电影”所塑造的创伤记忆,不过显示了一种急于告别过去的仓皇,在记忆与失忆的交织中,将个体的现代想象与国家的现代化项目统筹在一起。
“绝大部分改编自‘伤痕’文学的电影都是在1983年以前摄制的,它们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爱情关系的破裂以及忠诚于国家的个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非法迫害而带来的失望情绪。”[15]这一时期的“伤痕电影”主要有:《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 《泪痕》 《如意》 《元帅之死》 《苦难的心》《第十二个弹孔》《巴山夜雨》《带手铐的旅客》《天云山传奇》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枫》 《丹心谱》《于无声处》等。这些电影通过构造“文革”时期的创伤记忆,表达了人道主义的立场和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热烈关注”[16](P39),并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于革命历史进行反思。在一些“伤痕电影”获得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认可的同时,另外一些“伤痕电影”以及电影剧本却受到了批判,如《太阳和人》,《女贼》,《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 等。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后,“伤痕电影”基本上退出了中国大陆银幕。在1980年前后,虽然精英知识者与国家权力在中国现代性问题上可以达成基本共识,但是知识者和主流政治则是带着不同历史性和价值观来定位他们在现代性项目中位置和关系,不同政治群体对社会信仰主题的话语建构必然产生分歧,精英知识者在集体信仰话语建构过程中往往隐含了对这些话语的批判,而国家权力则通过政治惩戒、意识形态询唤,介入了对于“文革”记忆的塑造过程。“伤痕电影”的荣与衰,除了电影主题本身的局限外,主流政治对“文革题材”的限制也是它不能为继的重要原因。在对电影《太阳和人》的批判中,当时的广电局局长就认为剧本:
……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儿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样表现是不好的……”
“这个剧本大写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17]
随后的批判则被上升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18]的政治高度,并酿成了一场涉及文化界以及中共内部分歧的“苦恋风波”。实际上,就《太阳和人》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其社会批判和历史反思主要基于一种古典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带来超越性的精神反思与历史批判。这其实也是所有“伤痕电影”的共同缺陷,记忆编织与精神重建局限在狭窄的领域内进行,创伤记忆被归罪于一些偶然性事件——“反右”或“文革”,以及个别性群体——“林彪”或“四人帮”。当然,“伤痕电影”作为新时期电影发展过程中的起始一环,为电影领域的现代化奠定了生发的基点。可以说,新时期电影的现代想象是建立在遗忘基础上的,只有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才能充满激情地生活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
毫无疑问,“伤痕电影”创作中最突出的导演是谢晋。他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其实构成了1980年代中前期关于“文革”历史叙事的代表性文本。谢晋电影的几个特点,如“无深度的反思”,“温婉的人道主义”,“歌德的主流形象”,“苦尽甘来、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中庸的政治倾向”等等,被认为是“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神话”。[19]非独谢晋,此一时期的“伤痕电影”都可以看作是通过重新塑造“文革记忆”而获得自我救赎和社会救赎的神话,而通过记忆重塑的意识形态编织,社会政治主题和社会话语主体得以重新确立。
“伤痕电影”的记忆编织中也隐含着质疑。在电影《小街》的结尾,创作人员设置了三个各不相同的结局,结局的不确定性使电影生发别样的意味,表达了作者对自己所编织的叙事的怀疑,显示了一个时代在遗忘与铭记的间徘徊的惶惑。虽然限制很多,但并未妨碍创新的出现。特别是第四代电影人,其视听语言具有了一种特别的诗意,虽然不及之后的第五代那样狂飚突进,但也代表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别样路径。在1979-1983年的电影生态中,第四代即是那先锋的一环,他们“登场于新时期大幕将启的时代,他们的艺术是挣脱时代纷繁而痛楚的现实/政治,朝向电影艺术的纯正、朝向艺术永恒的梦幻母题的一次‘突围’”[20]。
三、第四代导演的感伤主义美学
在中国电影的“代际论”中,第四代是指成长于新中国,在1979年前后开始独立电影创作的一些电影主创人员,以吴贻弓、谢飞、杨延晋、黄蜀芹、吴天明、郑洞天、滕文骥、黄健中、张暖忻等为主要代表。这一代电影人是共和国一代,在1950-1960年代社会氛围中奠定了个人的价值观和艺术观,其艺术创作往往因为个体意识与主流意识的同构性而缺乏先锋精神。在1979-1983年间,第四代电影人是主要的创新群体,其理论和实践往往处于同步的状态。张暖忻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中所推崇的巴赞的“纪实美学”和“长镜头”,几乎是所有第四代电影人共同的电影美学主张,当然也不乏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电影手法的借鉴。《沙鸥》,《小花》,《苦恼人的笑》《小街》,《生活的颤音》,《邻居》,《城南旧事》等,是第四代导演在此一时期代表性作品。这些电影的人道诉求和感伤美学,成就了这个阶段中国电影的最高艺术成就,郑洞天将这个成就总结为“人的解放和电影的解放”[21]。
人的解放不仅涉及电影主题,也是第四代的自我期许,他们总是强调个人在电影创作过程的主动性。张暖忻认为电影应当“成为一种创作者个人气质的流露和情感的抒发”[22]。滕文骥“强调创作者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主观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23]。黄健中则表示导演应当成为“自己‘画面的上帝’”[24]。强烈的个人意识使第四代的影像表现出了一种比较独特的个人风格。此一阶段的电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风格趋向和艺术创新:一是对绝对纪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的追求,郑洞天、徐谷明导演的《邻居》是“纪实美学”的代表性作品,电影“在美工、道具上刻意求真。不用插曲,不采用无声源音乐”,“把摄影机作为观众的眼睛,去观察现实生活,捕捉真实而生动的现实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也能够构成独特的风格”[25]。《邻居》真正实践了巴赞的“纪实美学”。二是在电影叙事上采用了“时空交错式”的意识流结构,通过运用闪回等艺术手段突破时空的限制,使心理时间的逻辑代替了客观的时间流程,造成了电影叙事结构的解放。1979年的《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都使用了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在《沙鸥》和《小街》中,一种注重心理时空转换的“复合时空”得到了表现,主创人员将这种电影手法看作是“现代电影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使电影语言不再停留在对事物(时间、环境)的客观叙述上,而是力图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展示人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状态”[26]。三是注重了电影造型的个性化。张暖忻认为“现代电影语言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努力探索新的电影造型手段。”[3]《沙鸥》《小街》等都试图通过环境造型,光影、色调、视听手段的综合运用获得独特的电影氛围。《沙鸥》里“圆明园独白”的镜头段落以及《小街》里对于“小街”场景的主观性营造,是第四代导演在造型艺术上突破的典范。虽然写实主义的追求使这种造型缺乏如第五代电影一样的视觉冲击力,但是却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时空经验和审美趣味,从而具有一种传统的诗意。
写意和抒情本就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特征,而“意境”的营造则是电影民族化的出路。[27]在1979-1983年的电影创作中,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就是电影民族化的代表,堪称为具有民族美学精髓的“散文电影”或者“诗电影”。电影“以精巧的艺术构思把我国二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影表现的意境深邃、富于韵味,具有和谐的美,在探索电影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美学传统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果”[28]。整部电影中所弥漫的那种“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的诗意气氛正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传统感伤美学风格的体现,化繁为简的白描手法寥寥几笔便将人生的况味、怀乡的哀愁尽皆道出,是所谓“黯然销魂,唯别而已,清梦如风,乡音渐远”。《城南旧事》应该代表了此一时期中国电影的最高成就,就中国电影史来说,它继承的是《小城之春》所创造的感伤诗意的美学风格。《城南旧事》是吴贻弓的代表作,他并没有再创作出一部可与《城南旧事》相媲美的电影,而民族化的电影美学探索在大陆似乎也就终至于《城南旧事》。但与此同时,在海峡另一侧出现的“台湾新电影”,则出现了诸多电影美学中国化的典范性作品,特别是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 《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等等,真正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传统美学意蕴。如果将两岸的电影史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台湾新电影”或者才是中国民族电影的真正高峰。
如果不是第五代的出现,那么第四代的感伤美学的电影探索将会继续下去。不过,第五代横空出世,让一切因此而改变。第四代导演似乎很快就放弃了他们的写实主义电影旅程,而更多了表现主义的形式感。在第五代导演中间,田壮壮是最接近第四代电影风格的导演,其作品风格内敛低调,气度淡泊从容,奠定了田壮壮导演独特的先锋性。第四代导演营造的感伤美学风格在1990年代电影中或有所见,贾樟柯的《站台》,顾长卫的《孔雀》以及王小帅的《青红》还有个中滋味一二。在第四代导演成为这个时段的电影现代化的前驱时,第五代导演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完成他们的学业,张暖忻、郑洞天等第四代电影人作为导师,影响了他们最初的创作,使他们学院时代的作品,呈现出别样的风格特征。
四、 创伤记忆与学院期的第五代
谈及第五代电影,人们通常会认为其发端是1980年代初期《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实际上,在这两部标志性的作品出现之前,第五代电影人已经独立或者合作创作了几部电影。这些作品既包括在校学习期间的实习作业,也包括毕业之后的几部电影实践,这几部电影主要以田壮壮为创作中心。与一般所公认的第五代风格并不相同,这些电影更多记录意味与写实精神,是以田壮壮为代表的另一种第五代风格的显示。这些作品主要包括:田壮壮、谢小晶、崔小芹导演的电视短片《我们的角落》,田壮壮、谢小晶、崔小芹导演短片《小院》,潘渊亮、潘华、白宏导演的短片《目标》,田壮壮、谢小晶、张建亚导演的儿童故事片《红象》。除了《红象》,其余的短片都是他们在北京电影学院期间的实习作品。
之所以将这些实习作品作为第五代“前史”加以论述,是因为这些电影短片在题材选择,画面处理等方面,虽然已经具备了第五代后来的一些影像特征,但是也具有与其后来的总体风格不同的地方。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这些电影对于历史创伤重构,因为其涉及到的是这个“电影世代”真实的历史经验和创伤体验,这与他们日后从个人经验之外组织民族寓言的手法区别极大。这几部影片一方面与那个时期社会整体的历史反思氛围的相契合;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第五代电影在这个整体性的记忆塑造过程中的另类思考。另外,这些电影也是解读第五代导演的历史基点,因为电影的主要人物多是第五代的同龄人,表达的几乎就是他们自己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错位与无奈。应当注意的是,从未在这些电影中出场的“文革”,其实是隐而未发的历史背景与创伤之源,因为作为“共和国之子”的这一代人,在“后文革”文化场域中,被指认为处在“没有太阳的角落”里的“残疾人”。
第五代的最早作品不是《一个和八个》,而是《我们的角落》。其是根据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角落》改编的电视短片。这个短片有意识地尝试了纪实风格,质朴、沉蕴的影像构成了田壮壮后来电影的美学雏形,原生态的生活和情感是他最感兴趣的电影内容。《我们的角落》有三个特点令人瞩目。第一、纪实风格。演员全部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业余演员,保持了生命的原初状态,而充满自抑趋向的镜头,则显示了对于生活和人的尊重,整部电影“极力追求纪录片的客观态度,片子拍得哀而不伤、恬淡节制”[29](P126)。第二、庶民立场。普通市民是电影主要表现对象,与第五代后来的电影主题截然不同,对现实的关注似乎更多的与第四代电影相契合,郑洞天在同一时期拍摄的电影《邻居》具有类似倾向。第三、伤痕书写。电影是对于“共和国一代”的内在化的创伤记忆的显影,在1980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创作者没有将主人公的身体残疾和精神压抑进行简单解释,而是从个人存在层面揭示了人生残疾的本源性,人生荒诞的存在仿佛是太阳永远不能照进的角落,短暂的温暖和光明不过衬托出了永恒的缺失,人永无超越的可能,而只有沉沦的宿命。主人公的身体残疾隐喻了一代人的精神创伤,现实中国并不能提供治疗的途径,个体只有在晦暗的生命耗尽之后才能获得解脱。
第五代导演的毕业短片《小院》《目标》等,则延续了《我们的角落》的立意和风格。这两部作品分别改编自王安忆的小说《小院琐记》和《本次列车终点》,都是反映了个体在社会现代化、世俗化的过程中的困惑、无奈和不安。《小院》依然是以田壮壮为中心创作的电影,电影反映的人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挣扎,其实就是乌托邦幻灭后的一代人的生活写真。虽然电影给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女主人公桑桑通过和丈夫一起通过对于往昔生活的回忆而达成和解,美好的未来在理想主义的光芒中熠熠闪光,但是,对于“创伤记忆”的美学修正却正暴露了这一代人不能忘却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精神,第五代虽然崛起于后革命时代,但他们终究还是“革命之子”,并宿命般地留有革命的乌托邦烙印。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精神取向在田壮壮后来的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甚至《茶马古道——德拉姆》都有体现。
短片《目标》的立意则更为明显,返城知青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只好在回忆中获得精神安慰。影片在现实与过去的交叉叙事中描述着个人精神困惑,“知青世代”在返城后发现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被流放的知青生涯成为他们获得现实精神支撑的唯一来源,革命时代的“创伤记忆”成为个体的精神家园。通过这几部短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文革经历”和“知青生涯”是他们电影创作最重要的精神来源,经历“革命——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一代在世俗化的世界中,依然追寻着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然而,这个革命家园——“精神之父”曾经许诺的乌托邦——已经幻灭,“后文革”时代的个体不得不告别革命梦幻,重返世俗世界。但是革命时代的成长经历、理想主义的历史抱负,使他们力图赋予世俗化的现代性追求以乌托邦主义色彩。《目标》等电影对于精神生活、艺术人生以及知识价值的推重,将世俗化的现代化趋向转换成告别传统中国和前现代社会的理想主义景观,其与1980年代中国自我想象相得益彰——这是一个世俗现代化过程中的乌托邦阶段,其以一种吊诡的理想主义姿态迎接着一个即将到来的消费主义时代。
在1983年拍摄的《九月》中,田壮壮延续了之前的艺术追求,艺术乌托邦和人性理想国代替了革命乌托邦的拯救功能,人生在象征苦难的《小白菜》的吟唱中获得升华,“创伤记忆”成为个体获得存在感的唯一体验。以田壮壮为代表的第五代早期电影“已经形成了一条贯穿始终的探索道路,这条线索的发源处,本来是第五代电影之河最早的起点。但是,《一个和八个》这条水势汹涌的支流,突如其来,势不可挡,改变了原来主流的河道和流向。”[29](P127)实际上,《一个和八个》并没有改变这个时代的电影主流,这部电影所展示的表现主义风格是对略显阴柔、感伤的最初源流的补充,而对于“创伤记忆”的影像塑造,则从一个具象、现实和个体意识的层面深入到抽象、历史和集体无意识的层面。
结语
在1979-1983年间,无论是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争论,还是第三代、第四代的“伤痕电影”创作,抑或学院时代的第五代导演的创伤叙事,都反映出对于现代化未来的无限期冀,以及对于过去创伤经验的记忆编织,当代中国电影藉此而获得了新的现代性认同。与那些在创伤记忆中营造乐观未来的“伤痕电影”不同,作为第五代最早的电影《我们的角落》,或者才真正将历史创伤在新时期的无奈延续给充分表达出来。电影中的残疾主人公既是“知青一代”的自我想象,也象征了被这个致力于“遗忘”的时代所有意忽略的“沉默多数”,现代化的阳光并不能照进他们生存的角落,即便照入,也是不知所往的“残梦”,而非浴火重生的“新篇”。这个诡异的现代化状况及其后果,在1990年代出现第六代电影中有着更多批判性再现,而1980年代第五代更钟情于一个“现代化神话”的塑造。即便存在着各样异议之声,1980年代中国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的现代化进程中,包括“伤痕电影”在内的各种“伤痕文艺”的大量出现,与其说是对于过往革命历史的追溯、控诉与批判,不如说其更倾向于在“历史记忆中遗忘历史”,并试图与新意识形态达成暧昧的妥协。作为过渡时代之文化镜像的1980年代“伤痕电影”,尚未将创伤记忆完全曝光就潦草终结,成为一个新电影时代拉开帷幕前的无关紧要的注脚。
[1] 夏衍.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祝《电影艺术》复刊并从中国电影的过去展望未来[J].电影艺术,1979,(1).
[2] 艺军.揭示心灵的战斗历程——反映与“四人帮”斗争的电影创作的一个问题[J].电影艺术,1979,(1).
[3] 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J].电影艺术,1979,(3).
[4] 袁小平.关于改革电影事业管理体制的我见[J].电影艺术,1980,(12).
[5] 白景晟.丢掉戏剧的拐杖[J].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79,(1).
[6] 钟惦斐.电影和戏剧离婚[J].电影通讯,1980,(10).
[7] 青竺.也谈电影与戏剧的“离婚”[J].电影创作,1980,(11).
[8] 余倩.电影应当反映社会矛盾——关于戏剧冲突与电影语言[J].电影艺术,1980,(12).
[9] 邵牧君.现代化与现代派[J].电影艺术,1979,(5).
[10] 张骏祥.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根据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片第二次导演总结会上的发言整理)[J].电影通讯,1980,(11).
[11] 张卫.电影的“文学价值”的质疑[J].电影文学,1982,(6).
[12] 余倩.电影的文学性和文学的电影性[J].电影新作,1983,(2).
[13] [法]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4] 郑雪莱.现代电影观念探讨[J].电影艺术,1983,(10).
[15] [美]威廉·吕尔.中国大陆电影:1949~1985[J].杨彬译.当代电影,1987,(8).
[16] 梅朵.历史与现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
[17] 徐庆全:《苦恋》风波前后[J].南方文坛,2005,(5).
[18] 本报特约评论员.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N].解放军报,1981-04-20.
[19] 朱大可.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N].文汇报,1986-07-18.
[20] 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1] 郑洞天.仅仅七年——1979~1986中青年导演探索回顾[J].当代电影,1987,(1).
[22] 张暖忻.我们怎样拍沙鸥[J].电影通讯,1981,(8).
[23] 滕文骥.尝试和探索[J].大众电影,1981,(8).
[24] 黄健中.人·美学·电影[J].文艺研究,1983,(3).
[25] 张明堂.群星灿烂又一春——中国电影金鸡奖第二届评选活动侧记[J].电影艺术,1982,(2).
[26] 吴天忍.环境节奏时空——由影片《小街》所想到的[J].电影艺术,1982,(8).
[27] 艺军.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J].电影艺术,1981,(11),(12).
[28] 中国电影金鸡奖第三届评选委员会对各获奖项目的评语[J].电影艺术,1983,(5).
[29] 倪震.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冯济平
Traumatic Memory and Modern Imagination: Revaluing the Scar Films of the 1980s
HAN Che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Between 1979 and 1983, all the theoretic disputes about modernizing film language, all the works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directors' films telling the trauma from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fifth generation directors' traumatic narratives, tried to reconstruct the traumatic narratives to release the delayed desire for modernity. From then on, the new modern im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s. As a mirror of the transitional era, the scar films or others arts telling about trauma, was a recall or reduction of history rather than an action to forget it, then reached a compromise with the modernist ideology whose core i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scar film; traumatic memory; forgetting; ideology
J951.1
A
1005-7110(2015)01-0049-07
2014-10-26
韩琛(1973-),男,山东黄县人,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华语电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