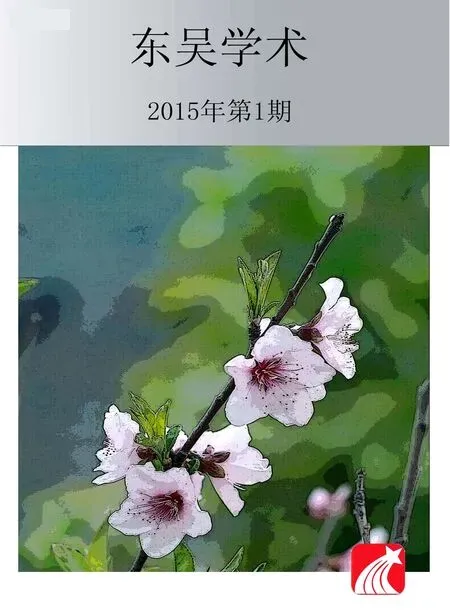从迷茫暗夜里引出的记忆
——解读二○一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
2015-03-29瑞典
〔瑞典〕万 之
世界文学
从迷茫暗夜里引出的记忆
——解读二○一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
〔瑞典〕万 之
本文通过对瑞典学院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的详细解读,说明本年度得主莫迪亚诺的成就在于将文学的“记忆”功能发挥到极致,其本质不在于“怀旧”,其技巧不在于回到“记忆”,而是利用“记忆”把历史逐步显影,引入读者眼前。这也是用“记忆”对抗“失忆”,完全符合诺贝尔文学奖重要评委埃斯普马克等人的文学趣味。因此,本年度文学奖授予莫迪亚诺这样对抗“失忆”的作家,褒奖他的“记忆艺术”,其实不出人意外。
记忆;失忆
瑞典学院给莫迪亚诺的授奖词是:“因为他用记忆艺术引出最不可把握的人类命运,揭示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
“记忆”无疑是理解今年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的关键词。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学功能一直有不同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可以“宣泄”或“净化”人的悲悯情感,而另有人说文学可以作为“时代的镜子”反映现实,或声称文学可以“表现自我”;文学当然还可以载道,可以寓教于乐娱乐大众,可以为政治服务改天换地,也可以作历史的“见证”,但瑞典学院这次的授奖词是说,优秀的文学可以是“记忆艺术”,可以承担“记忆”的功能。莫迪亚诺通过文学的“记忆”,如搭起一座文字艺术的桥梁,沟通过去与现在,让个人往昔的命运呼之欲出,让过去的“生活世界”重新呈现在读者眼前。
“记忆”当然属于过去,人只能记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确实,莫迪亚诺的笔尖很少指向当下,指向现实和未来,而总是指向过去,指向历史。他此生已经创作了近四十部作品,但正如一个瑞典评论家所说“莫迪亚诺其实是将同一个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他的一本书接一本书都像是特朗斯特罗默诗中描写的燕子,每年都要“返回同一教区同一牛棚同一屋檐下去年的巢穴”。因此有人认为莫迪亚诺只是在重复自己,甚至有瑞典作家说,虽然自年轻时代起就是个莫迪亚诺的书迷,但是读了几十年还是一种风格一种味道,不免有点审美疲劳或者是腻味了。但是对于这种批评,瑞典学院的评委有不同看法,五院士组成的评委会主席韦斯特拜利耶认为莫迪亚诺的作品就如音乐,主题似乎不变,但总是在不断变奏中流露新的逸韵。评委恩格道尔则说莫迪亚诺的作品如孪生姐妹,看起来长得像,其实性格可能完全不同。
和普鲁斯特有所不同
毫不奇怪,因为莫迪亚诺偏爱“记忆”,人们常常将他和法国现代小说大师普鲁斯特联系起来讨论,说他具有普鲁斯特风格,这当然是因为普鲁斯特的代表作《追忆逝水年华》也正是这样的“记忆”之作。但是,如果说莫迪亚诺好像不过是普鲁斯特的学生和追随者而已,瑞典学院大概又不会同意,我也不太同意。因为莫迪亚诺的小说语言风格和普鲁斯特展示内心活动的意识流语言风格不同。莫迪亚诺的文学语言不是普鲁斯特那种心理性的绵绵不绝的语言流,而是描述性的,也比较简洁易读。而且在结构上不是普鲁斯特那样内向的,把读者推向人的心理意识层面,或在时间上是后向的,把读者推向过去。他的结构是外向的,非常注重环境的细节描述,可以让巴黎的街道都栩栩如生,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而在时间上他又是向前的,他是把过去的人物又往前拉,展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所以是“引出”,以连接“现在”。授奖辞里的“引出”这个词,瑞典语原文“frammanat”就有“往前来”的意思。如果借用过去的冲洗照片方式来说明,莫迪亚诺的小说艺术就像是把一张用底片曝光的白色相纸放在显影液里,让一个个人物在显影液的作用下慢慢地显示出来。他的文学世界就像是个冲洗照片的暗房,似乎总是很昏暗不明朗,总是模糊而晦暗,总是暮色苍茫或梦境一般的夜色,常常是巴黎街头的夜色,只有昏暗的街灯。但是,不要错认为他在引导读者进入暗夜里寻找失去的记忆。不,他是把记忆从暗夜中招引出来,让你能看清楚那些人物为了生存下去如何挣扎甚至抗争,这就是授奖辞说的“引出”人的命运,“揭示”那个纳粹占领法国时期的人世。
所以,虽然前面说“记忆”属于过去,但是莫迪亚诺的文学属于现在属于将来。一张没有显影的相纸可能存有过去的记忆,但是最初你看不见,要等待作家施展技艺显影出来。这真是需要艺术手段的。所以,与其说“过去”总是莫迪亚诺写作的对象和目标,不如说是他的出发点。与其说他总是在“记忆”,其精神基调看似怀旧,甚至有些悲哀、多愁善感,其实是他在展示“记忆”。他的内心其实相当平和,正像是暗房里洗相片的一个摄影师,默默操作有条不紊,因为他自己的思路非常清晰,他知道显影不能差错,时间不能差错,如果相纸在显影液里放置太久,就会变成一团漆黑,所以他必须立即定影,才能放到光天化日之下也不变色。而这个作家用的定影液体,其实就是他的艺术文字。
不仅是个人的记忆
莫迪亚诺生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其时欧战已结束,一个婴儿也不可能对占领时期有自己直接的记忆。所以,这里说的“记忆”,其实不仅是个人的记忆,往往也是他个人不可能有的记忆,但是对过去的记忆就如现在的电脑记忆一样,可以储存在一些硬件里,一个优盘里,比如说一张旧报纸里,一张旧照片里,甚至一件旧衣服和旧皮箱里,当然还可以存在一个街道的门牌号码里,图书馆的档案里。所以这不是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个城市的记忆,更是民族的记忆、国家的记忆。所以,莫迪亚诺的作品不是普鲁斯特式的追忆个人的流逝年华,而是对纳粹占领法国时期的“生活世界”作一点一点的“揭示”。
《杜拉·布鲁德》被认为是莫迪亚诺的代表作,可以拿来作为分析介绍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科状元“记忆艺术”的范例。在这部小说的开端,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文字:
八年前,我偶然看到一张旧报纸第三版上的一个栏目,这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法国晚报》,栏目名是“从昨天到今天”。在最下面我读到:
巴黎 我们寻找一个小女孩。杜拉·布鲁德,十五岁,身高一米五五,蛋形脸,灰褐色眼睛,穿灰色上衣,酒红色毛衣,深绿色裙子和帽子,棕色系带的鞋子。有消息的话请留给布鲁德先生和太太,地址巴黎奥纳诺大街四十一号。
奥纳诺大街的这一段我很久前就熟悉。我小时候,可以跟我母亲去圣维恩区那边的跳蚤市场。我们在克利南考特门车站下公共汽车,或是有几次在市政厅外的车站下车……
小说是从一九六五年起开始叙述,叙述者“我”(这是莫迪亚诺作品常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经常可视为作者本人,因此很多评论也认为他的作品多有自传性)从“记忆”八年前读到的一张旧报纸开始,引导读者回到纳粹占领时期的一九四一年,找出旧报纸储存的“记忆”;然后继续“记忆”自己很久前(小时候)就熟悉的一段街道。“我”从容、细致地介绍那段街道,包括街道上兜售照相的马路摄影师,街道上的咖啡馆,街道上冬天时早早降临的夜色。因为观看这条街道冬景的角度依然没有改变,所以“一九六五年的冬天和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就混杂”起来。这就是作者和普鲁斯特叙述风格的不同之处。“我可能就走在杜拉·布鲁德和她父母留下的脚印上,而我自己都没有清醒意识到。那些脚印其实早就在那里,在背景里。”因为街道也有它的记忆。于是“我寻找线索,沿着时间的最远端寻找”。
八年之后,一九七三年,“我”开始了自己的寻找。这种查找工作有点像是作侦探,所以读莫迪亚诺小说有时也有读侦探小说的味道。在他的有些作品里,侦探也是主要人物之一(如《暗店街》的主角)。这里就创造了悬疑小说的那种“悬疑”,好奇的读者不由跟随着作者去发现还没有完全显影的“记忆”,当然也是把“记忆”引到现在的过程。“我”从查阅市政部门的户口登记开始,查到杜拉·布鲁德出生的医院的出生记录,也就是回到了更久远的一九二六年。直到揭示出犹太小女孩杜拉·布鲁德被纳粹分子无情“绑架”,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后死于毒气室的历史真相。
“失忆”这个关键词
类似这样“悬疑”结构的小说,还有《蜜月旅行》,写一个游客在意大利米兰的酒店里突然听到他认识的一个女人两天前在这里自杀,于是他回到巴黎之后就开始去调查她的死因和生活,《杜拉·布鲁德》其实是其续篇;《暗店街》则本身就是写一个私家侦探因故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记忆,得了失忆症,而他为找回自己的身份去寻找的一个重要人物线索又失踪了。莫迪亚诺作品很多,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分析,笔者也根本没有这样的阅读量,只知皮毛。我只愿意介绍,对莫迪亚诺的创作,瑞典学院新闻公报已经作了这样概括的总结:
莫迪亚诺作品的焦点在于记忆、失忆、身份认同和负疚感。巴黎这个城市经常在文本里出现,几乎可以被当作这些作品里的一个创作参与者。他的故事经常建构在自传性的基础上,或是建立在二战德国占领法国时期发生的事件上。他有时候从采访、报刊文章或者他自己多年来收集的笔记里抽取创作的资料。他的一部部小说相互之间都有亲和性,会出现早期的片段后来扩展为小说的情况,或者同样的人物在不同的故事里出现。作者的故里及其历史经常起到把这些故事链接起来的作用。
引起我注意的是这段话里“失忆”这个字眼。在小说《杜拉·布鲁德》里,这个字眼确实也不断出现。比如叙述者“我”把市政厅不愿意让他查阅杜拉档案的工作人员称为“失忆”的保安员。我们也许可以问,一个作家,能对平常人视而不见的一张旧报纸上的一条寻人启事发生兴趣,而且不惜花费精力时间去努力发现这一点文字之后的历史真相,去把逝去的“记忆”重新召唤到现在,这是为了什么?也许你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但对我来说只有一条,就是作家要对抗我们这个时代的“失忆”。近两年我曾将瑞典学院院士埃斯普马克的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翻译成中文出版。埃斯普马克一直是瑞典学院内五个院士组成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成员,并曾经担任过这个评委会的主席十七年(一九八七至二○○四年)。每年交给整个瑞典学院讨论决定的诺贝尔文学奖入选作家的名单都是这个评委会提交的,所以这个评委会对于每年的评选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埃斯普马克认为,“失忆”已经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而重大的问题,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朱特指出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失忆症合众国”中。埃斯普马克还用夸张和讽刺的笔法描绘当代人的这种“失忆症”——“记忆现在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还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和谁在一起度过的。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心里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是我的太太?而站在她后面的那些孩子,会不会是我的孩子?”
用“记忆”对抗“失忆”,这当然符合埃斯普马克这样的重要评委的文学趣味,他钟情于莫迪亚诺这些对抗“失忆”的作家,褒奖他的“记忆艺术”的文学,就一点都不会让我感到意外了。我甚至觉得,上面引的这段新闻公报,可能就是出自埃斯普马克交给学院讨论的读书报告。所以,虽然今年的评选结果让很多人出乎意料,因为很多人看好的作家又一次和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而在媒体猜测的名单上几乎没有莫迪亚诺的名字出现,他是一匹黑马。但以埃斯普马克在评委里的影响力,把绣球抛给莫迪亚诺这位对抗“失忆”的作家,其实是顺理成章的。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修订于斯特哥尔摩
万之,本名陈迈平,为长期居住在瑞典的中文作家、文学编辑和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