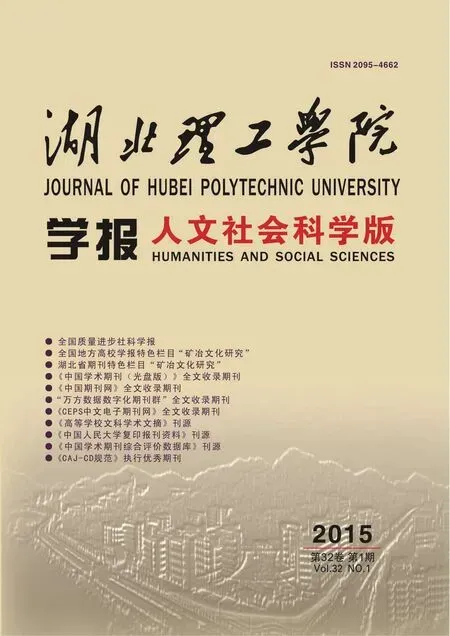论宋词中日常生活的休闲与审美境界
2015-03-28孙敏明
孙敏明
(浙江万里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论宋词中日常生活的休闲与审美境界
孙敏明
(浙江万里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文章从日常生活的休闲和审美角度来分析宋词,从人的感官的精致化,即内在自然的进一步人化为起点,通过审美观照使日常生活内容无一不可以入词,而情感的深化和理智的哲思最终又让宋词达到了对生命的旷达和超越境界。宋词主题内蕴的发展深化正契合了休闲境界的提升过程,从日常生活的享乐和愉快走向审美的自由与超越。
宋词;感官精致化;日常生活艺术化;旷达的人生体验;休闲;审美
宋词作为有宋一代最为杰出的文学体裁,精巧、婉丽、蕴藉,集中体现了宋代的文学品格和审美趣味。词本是“曲子词”、“诗余”,这让它从一开始就不必承载“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重大责任,远离了正统儒家文学,如《诗大序》中所倡导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而以“要眇宜修”的姿态来描摹日常生活、娱乐情性、抒写人生。在绚丽多彩的宋词世界里,我们选取日常休闲和审美的角度对其做出分析。
一、感官的精致化
感官的精致化是“内在自然的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在自然的人化,即人的感官、感知和情感、欲望的人化”[1]417。马克思在《手稿》中说,人的五官是世界历史的成果,是由人的社会实践造就的,因为动物的感官只为了自己生理性而存在,是完全功利性的,而人是自由自觉的行动者,虽然人的感官也具有生理性的一面,但经过长期的历史的“人化”,人的感官超越了生理性和功利性,而具有了社会性和超功利性,这也正是美感产生的根源。宋词作为宋代审美趣味的代表艺术之一,对人的感官知觉向着更精细化的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翻开宋词(文中也包括了宋之前西蜀、南唐的词,为了方便,以宋词统称)就如开启一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的全方位感官活动的盛宴,正如欧阳炯《花间集·序》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展现声色娱乐的生活是词所表现的主要内容,这个传统在宋代继续得以发展。
虽然有着内忧外患,但宋代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日益繁荣,城市化模式不断扩张,娱乐休闲活动蔚然成风。如《东京梦华录》自序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笔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可见声色大张,娱乐享乐之风盛行。而词对于纵情声色的表现,经过了审美化的艺术加工处理,过滤了大部分的粗俗的美艳,显得精工、婉媚、巧细,极大地刺激和丰富了我们的感官感受能力。
下面以李煜的《玉楼春》为例,来看一看穷奢极欲的感官沉溺和享乐: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①。
词人目之所见的是一群化了浓丽的晚妆、有着雪一样白皙的肌肤且光彩照人的宫女;耳之所闻的是如飘浮于天上的游云、流淌于地面的流水一样的凤箫声,还有那一遍遍演奏的《霓裳羽衣曲》;当一阵微风吹过,又嗅到了香味;口里喝着美酒,微微有些醉意,拍着雕栏玉砌的栏杆,和着歌舞的节拍,体会着心中深切动人的滋味。然而这些还不够,当词人从欣赏歌舞的宫殿回到起居睡眠的宫殿路上,他不让侍从点亮红烛,因为他还要欣赏大自然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在洒满月光的路上,就连马蹄的得得声都不曾遗漏。
这般莺歌燕舞的享乐不止帝王,文人士大夫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如晏殊一生富贵闲适,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宾必留,留亦必以歌乐相佐。”其子晏几道《小山词序》中亦云:“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在《玉楼春·琼酥酒面风吹醒》、《木兰花·小莲未解论心素》、《破阵子·柳下笙歌庭院》、《玉楼春·红绡学舞腰肢软》、《临江仙·淡水三年欢意》等词作中,晏几道描写了这几位歌女的美貌、风韵、舞姿、歌喉和琴声。又如欧阳修在十首《采桑子》的“念语”中说:“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宋代士大夫们较之前朝官俸厚、休假多,到处可见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即使仕途不得意的文人,如“白衣卿相”柳永,混迹于烟花柳巷,在词中也自称是“平生自负,风流才调。……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沽取百十年,只恁厮好”(《传花枝》)。
感官的精细化除了表现在对美色醇酒丝簧的感受,多情的文人更是以多情的目光看待自然万物。“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文心雕龙·物色》)惜春悲秋、庭院伫立、渡头别离、凭栏凝望成了词中最常见的内容。李泽厚说:“词则常一首(或一闺)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含意微妙,它经常是通过对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不是盛唐那种气象万千的景色事物)的白描来表现,从而也就使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有更浓厚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宽大的‘诗境’。”[1]145
我们仅举描摹自然的几个例子。如写梅,欧阳修说:“北枝梅蕊犯寒开”(《玉楼春》),花有南枝北枝,南枝朝阳,北枝背阳,所以总是南枝的花先开,而欧阳修说北枝的梅蕊也要冒着寒风开放,这是一种多么细心的观察,说的是梅更是人生的一种努力。姜夔说:“苔枝缀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疏影》)梅中有一种苔梅,枝干上都长着绿色的青苔,就好像是点点的碧玉点缀其上,且梅枝上还栖息着一对翠色的小鸟。这里用了一个赵师雄偶遇美人欢饮又有一绿衣童子歌舞助兴的典故,而历来的解释者大多指出这是姜夔在暗指那段终其一生刻骨铭心的合肥恋情。辛弃疾一句“倚东风,一笑嫣然,转盼万花羞落”(《瑞鹤仙·雁霜寒透幕》)可谓写尽梅花的姿态,梅花的开放犹如那美丽的女子一笑嫣然,她目光流动、转盼之间,所有的花大概都要因为羞愧而飘落下来。
又如,写柳:“柳荫直,烟里丝丝弄碧。”(周邦彦《兰陵王·柳》)写雨荷:“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杨万里《昭君怨·咏荷上雨》)写春色:“山泼黛,水捋兰,翠相搀。”(黄庭坚《诉衷情·小桃灼灼柳鬖鬖》)写惜花:“绿肥红瘦。”(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写夜色:“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写江南山水:“玉簪螺髻”(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等,不再一一列举。生活中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感都可以入词。词不仅丰富了我们感官的感知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已经融入日常生活,是对日常的甚至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做出的一种优雅的观省。
二、日常生活的艺术化
日常生活是日复一日所过的日子,主要内容即是人的具体感官感受、身体经验、情感体验等,而艺术化就意味着用审美的眼光来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用审美的因素来装点生活。正如《墨子》所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对于宋代的文人士子而言,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把握,首先是要有较为富足的物质生活基础;其次要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更重要的是要有悠闲的心态。
词在开始的时候固然是抒写于觥筹交错之间以助兴致的歌词,但随着词的发展盛行,文人士大夫们在词中有意或无意地透露出他们的个性、才情,词的内容也从主要描写美色艳情而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宴饮游乐、羁旅行役、节庆活动、赏花品茗,以至于打情骂俏、洗漱妆扮、懒睡醉酒都通过词一一展现。对于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浩繁内容,我们仅选取了日常生活中表现闺房浓情蜜意和慵懒无聊两个方面的几首词来做分析,希望能由此窥豹一斑。
先看爱人或恋人之间活泼的生活细节描写。例如李清照的《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以女词人的笔调来写女子与春花,两者既是对比又是衬托,更可见女子那微妙的心理变化。女主人公买了一支含春欲放的鲜花,花上还闪着晶莹的露珠,仿佛披着红彤彤的朝霞,如此明艳、鲜亮,这是花的形象也是人的形象。然而花的美艳似乎又让女主人公生起几分妒忌,她想知道自己的郎君到底有多爱她,她在他心里到底有多美。于是她俏皮的把花斜簪在云鬓上,一定要郎君看一看、评一评究竟是花美还是人美。多么天真的女子,多么爱美的情态,这般的闺房之乐让人忍俊不禁。
又如周邦彦的《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有解释者以为这里写的女主人公就是李师师,我们以为如此坐实倒没有了词本来的韵味。这里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秋夜相会的情人,先写他们双双共进时令水果,刀是并州特别锋利的刀,盐是吴地质量特别好的盐,加之以女主人公的纤纤玉指来破开橙子,场面温馨而快乐;然后交代了闺房的环境,有锦缎制成的华美的幔帐,香炉里升腾着沁人的烟气,室内的温度也慢慢变暖,她和他相对坐着,她准备为他吹笙。先是品橙,品的是味外之味;这时赏乐,大概是“未成曲调先有情”,乐在音乐之外。接下来是留给人想象的空间,直到时间指向三更,指向那个该离别的时刻,她希望他今夜能留下,却又不便明言,于是有了低声问:“向谁行宿?”问完了又连忙帮他找可以留下来的借口,什么天寒霜浓、路滑难行、人少不安全,它们都指向那“不如休去”的挽留。在这里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女子悸动、羞涩、期待等纠结的心理活动和神情变化,将男女之情写得意态缠绵,却又恰到好处,真是“风情如活”。
对闺房中快乐生活的描写或率真或泼辣或含蓄,还有“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欧阳修《南歌子》)的新嫁娘,“针线闲拈伴伊坐”(柳永《定风波》)的俏佳人,也有“嚼烂红茸,笑向檀郎唾”(李煜《一斛珠》)的撒娇,“日曈昽,娇柔懒起,帘押残花影”的甜蜜,“连鬟并暖,同心共结”(吴文英《宴请都》)的恩爱,此处从略。
再来看闺阁中的慵懒、无聊与怅然。绣楼闺阁是一个暧昧的空间,置身于此百无聊赖之际,更容易触动种种幽思。有着强烈个体生命意识的文人士子,他们多借助曾经经历的回忆或角色的偷换,通过想象,以审美的眼光去描写日常生活中具体的情态,把他们心里对生活的无助和无奈,以一种美丽的、具体的、感性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秦观的《画堂春》: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栏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眼前是春归的景致,但词人以轻细纤柔的笔致去写,没有韦庄《谒金门》“满院落花春寂寂,肠断芳草碧”的决绝浓烈;也没有李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奔放沉痛;这景是铺满小径的落花、平池的水面、霏霏的细雨,显露出憔悴模样的杏院回荡着杜鹃的啼鸣。下阙写人,这个人可以是男子也可以是女子,他/她独自登上画楼,倚着栏杆,手捻一花枝。世人多爱花,于是有了种种赏花、折花、插花、簪花甚至是葬花。他/她也爱花,却用了一种特别的爱惜方式——放开它,在对春花的凝视中,心里会涌过多少幽微的感受,放眼望去只是静静的斜阳落晖。此恨是什么,此恨又有谁会知道,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词境所展现的幽深的遗恨或怅惘,这可能是每个人心中都曾有过的感受。
闺中女子被拘束于“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生活空间,如何来安放每一天的生活?可想而知,大概只有她们无尽的相思与等待。这类闺怨写得出彩的如温庭筠的《望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寥寥27个字,却情韵兼胜的写出了思妇的闺怨:她精心梳妆修饰之后,独自倚楼眺望,望江面过往的船只是不是有载着他归来,可过尽千帆都不是,只有悠悠的流水、脉脉的斜晖,只有水边一片芳草离离、蘋花摇曳的白蘋州。这真可谓是一幅可视可感的闺怨凭栏图。后来柳永的《八声甘州》里也描摹了闺中人如此的等待:“想佳人妆楼顒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再看冯延巳的《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春风吹皱一池的春水,更搅动了女主人公不平静的内心世界。她是这样的闲散、百无聊赖,无精打采地逗着成双成对的鸳鸯,漫不经心地捻着迎春绽放的杏花;她形影孤单地倚靠着栏杆,看着水中的鸭子嬉戏争斗,以致插在松散的发髻上的碧玉簪子仿佛摇摇欲坠,如此的懒散愁闷,只因日日夜夜盼望着他的归来;抬头间突然听到了喜鹊的报喜声,这难道是在预示着他真的要回来了吗?词末带给了人希望和惊喜,然而生活的常态却更多的是无休止的思念和等待。
宋词中随处可见痴情佳人:“朱栏倚遍黄昏后”(张耒《秋蕊香》)、“坠髻慵妆来日暮”(张先《菊花新》)、“想得两眉颦,停针忆远人”(陈师道《菩萨蛮》)、“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亦随处可见风流才俊:“醉里簪花倒著冠”(黄庭坚《鹧鸪天》)、“只图烂醉花前倒”(杨万里《忆秦娥》)、“睡起流莺语”(叶梦得《贺新郎》)、“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贺铸《薄幸》),就不再一一细说。
三、闲情的深化与升华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大体上可谓是有钱又有闲的阶层,他们及时行乐,纵情欢愉,享受着耳目声色的快乐,普通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笔下也显得情趣盎然,然而他们毕竟没有沉溺于感官的欲望,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红楼之内,他们心灵沉浸的深度和精神超迈的高度才真正显示了他们思想的力量,宋词也从艳情的抒写转向闲情的抒写。闲情是什么?闲情是一种在工作中、忙碌中被忽略,而闲暇时、安静时或独处时就无端涌上心头、难以排遣甚至难以明言的一种情绪或情感。闲情又常常被称为闲愁,构成闲情闲愁的内容,有的是较为具体的相思怀人,有的是并没有具体内容的伤春伤逝人生感喟,还有的是对宇宙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追索思考。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李清照把相思闲愁写得如此率直真切。离别相思是宋词中一大主要内容,在上文中也有所涉及,因为有欢会便会有离别,而离别又远多于欢会,因为这才是人生的真相。词中如果以思妇或游子等人物或情节为主体,那么所表现的艺术形象更加定型,情感内容也较为坐实;而如果以自然景物为主体,那么意象的表现力更为丰富,更具有从特殊走向一般的艺术概括力,从而具有更为广泛的象征意义。我们认为,这是词的表现功能的扩大,意象的象征性和多义性使闲情的内蕴更具包蕴性也更深刻。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虽然我们没有历经李煜那样的亡国之痛,但面对着“逝者如斯夫”的流水,对于时光的流逝、人生的变迁也会引起忧愁的情思。或许李煜的愁还太过浓烈,那么来看冯延巳的《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本以为抛却的闲情其实并没有抛却过,内心仿佛有所失落又仿佛有所追求的惆怅无法消除,它不再是一种具体的闲愁,而似乎又和伤春伤逝联系着。日子一天天在花前醉酒中度过,虽然镜子里的容颜渐渐消瘦,可是宁愿沉浸在这无法超拔的闲愁里。年年春来、年年柳绿、年年新愁,长久地独自站在小桥之上,萦绕的是满袖的寒风。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深刻的孤寂。
如果还嫌冯延巳的闲情太缠绵太孤寂,那么秦观《浣溪沙》中的闲愁就显得轻灵、巧细: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薄薄的春寒弥漫着也浸润了小楼,这是一个阴雨的清晨,主人公坐在房中举目四望,唯见画屏上迷蒙淡远的淡烟流水图。不堪久坐的寂寞,眺望窗外,轻盈的飞花如心中轻柔飞扬的闲梦,无边的细雨如心中轻柔纤细的愁怨,而室内精巧的小银钩正悠闲地把宝帘挂起。
面对无法消解的闲愁,词人们又是如何排遣的呢?秦观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给人以一种启示和心灵的慰藉。晏殊说:“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美好的人事总是太容易消逝,那就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欧阳修说:“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玉楼春》)洛阳的花是美丽的,在它们盛开之时,付出最大的精神、情感和力量去欣赏,到花落之时就容易离别了,因为自己已经尽力,没有白白辜负这段美好的光阴。对待闲愁理性认识和珍惜是一般人所采取的方法。
宋词中对闲情的体验,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对于人生圆融的观照和精神的超越。我们先看晏殊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淡淡引出对于人生无常的悲哀,一曲新词一杯酒,春去春又回,依然是去年的天气、旧日的亭台,仿佛一切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夕阳西下,今天的斜阳落下去了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时间的流逝是每个人生命中必然面对的难题。虽然无可奈何于春花的零落,可是每年又有燕子飞回来,而且是似曾相识的燕子,这就是自然生命的循环。宇宙生命都是一个无尽的循环,如果认识到这点,那么就不必再有太多的哀怨。主人公在落英缤纷的小路上独自徘徊,带着淡淡的哀伤,也带着对春天的欣赏,还有对宇宙生命绵延循环的思索。
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达到彻悟境界的典型代表莫过于苏轼。“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满庭芳》)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写这首词时,词人在黄州谪居五年后又被委派前往汝州,他还没有到汝州就想象汝州的洛水清波也一定是美丽的。由此可见,苏轼从容面对人生的苦难,总能找到生活的乐趣,放达而超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既然很多人事是自己无法把握的,那么就忘却形体,忘却形体的欲望而引发的种种名利算计,放眼江上静谧美好的景致,把心灵引向超然物外的世界,驾一叶扁舟,任意东西,把有限的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中。然而社会现实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人是无处可以遁逃的,于是苏轼就做了一场这样超旷的神游。 “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简简单单轻装上阵,各种风雨只是人生的不同时段所遭受的外在变化,当回头看所走过的路,虽然经历了风雨的萧瑟,可是内心却依然从容坦荡平和,这便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也是一种了悟的人生境界。
宋词以优雅的姿态呈现了生命中幽微、细腻、柔软的内心世界,把难以言说的情感和体悟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传达出来,化为可视可感的对象。这里有着精巧绝伦的对感官欲望的满足,但又没有沉溺在欲望之中,放眼看去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心之所感都可以一一化为风姿摇曳的艺术形象,凝成风流蕴藉的艺术境界。一场从娱乐开始的感官盛宴,经过审美的观省、情感的深化、理智的哲思,最终达到了对有限人生的圆融观照和精神的自由超越。宋词主题内蕴的这一发展深化过程也正契合了休闲境界的提升过程,从感官的欢愉走向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并最终达到美的自由境界和人生的超越境界。
注 释
① 本文所引词作均出自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词典》(上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后面不再一一标示。
[1]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陈咏梅)
On Leisure and Aesthetic Realm of Daily Life in Song Ci
SUNMinming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Ningbo Zhejiang 31510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of leisure and aesthe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Song Ci from the sensory refinement, which further humanizes nature as a starting point, thus takes everything into aesthetic daily life account. The emotional depth and rational thinking let the Song Ci of life beyond the realm of life.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me deepens Song Ci's content and fits it into the leisure realm of ascension process from the enjoyment of daily life and happy towards aesthetic freedom and surpass.
Songci;refined senses;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board life experience;leisure realm;aesthetic realm
2014-11-03
孙敏明(1977— ),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美学、休闲学。
10.3969/j.ISSN.2095-4662.2015.01.006
G112
A
2095-4662(2015)01-0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