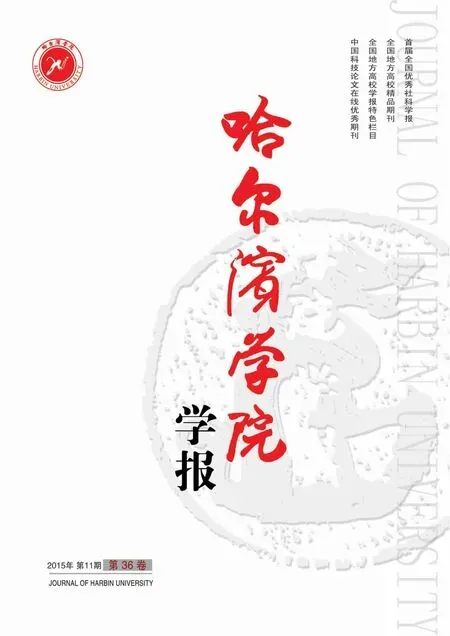人格结构理论视阈下《在切瑟尔海滩上》中爱德华的心理解读
2015-03-28吴晓群
吴晓群,戴 琳
(1.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合肥 230088;2.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伊恩·麦克尤恩(1948-)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1975)出版次年就获得了毛姆文学奖。他的创作生涯从此与各类奖项的入围名单相互交织。197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床笫之间》之后开始长篇小说创作。迄今为止完成长篇小说12部,分别是《水泥花园》(1978)、《陌生人的慰藉》(1981)、《时间里的孩子》(1987)、《无辜者》(1990)、《黑狗》(1992)、《爱无可忍》(1997)、《阿姆斯特丹》(1998)、《赎罪》(2001)、《星期六》(2005)、《在切瑟尔海滩上》(2007)、《日光》(2010)、《甜牙》(2012);儿童小说《梦想家彼得》(1994);电视剧《模仿游戏》(1981)、《杰克·弗里的生日庆祝会》以及《立体几何学》;清唱剧《我们或将死亡》(1983);歌剧《为你》(2008);电影剧本《庄稼汉的午餐》(1983)、《夏季的最后一天》(1984)以及《酸甜》(1988)。其中,《时间里的孩子》(1987)获惠特布雷德奖,《阿姆斯特丹》(1998)获得布克奖,《赎罪》(2001)获得2002年史密斯文学奖,2003年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奖文学奖和洛杉矶时报小说奖,2004年获得圣地亚哥欧洲小说奖。麦克尤恩在主流文学圈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被公认为英国的“国民作家”。2007年对于伊恩·麦克尤恩来说是极为不普通的一年。这一年,《在切瑟尔海滩上》一出版就在英国卖到十多万册,同时由其代表作《赎罪》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荣获该年度全球最佳影片奖,如此佳绩将麦克尤恩的声誉推至沸点,2007年成为了“麦克尤恩”年。
一、作品简介
《在切瑟尔海滩上》故事背景定格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英国,讲述的是弗洛伦斯和爱德华这对新婚夫妇本该新婚燕尔、洞房花烛,但是由于两人对性的无知和焦虑导致圆房未果最终分道扬镳。“他们年纪轻,有教养,在这个属于他们的新婚夜,都是处子身,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对性事困扰说长道短的年代。话说回来,这个坎儿向来都不好过。”[2](P5)纵使作品开头已经阐明结局注定是悲剧,但读者禁不住受“年代”和“坎儿”的唆使一步步走进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爱德华出生在切尔顿山的一个贫穷农舍,父亲莱昂奈尔是小学校长,性情温和,所有精力都放在学校和家庭,是好父亲的“标杆”。母亲玛约蕾在爱德华五岁时由于意外而脑部受伤造成神经失常,时常沉溺于自己的各种“爱好”中。爱德华还有一对小自己五岁的双胞胎妹妹安妮和哈丽特。爱德华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他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爱德华不同的是,弗洛伦斯出生在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母亲维奥莱特是大学老师,父亲杰弗里是事业有为的企业家。虽然母亲很有学识,但弗洛伦斯与爱德华一样未曾感受过母爱。弗洛伦斯对音乐有强烈的喜爱。他们邂逅于“禁止核武器运动”集会上,算得上一见钟情。一年后,爱德华向弗洛伦斯求婚,这对才子佳人结为连理,但新婚之夜的不和谐却颠覆了一切,两人最终没能相守,人生从此再没有任何交集。回顾两人“浪漫”的交往历程,两人的感觉(外部知觉)和情感(内部知觉)一直经历着微妙的复杂变化。他们相识、相恋,受制于时代,却没有真正相知,没能将内心深处的感知彼此坦诚。弗洛伦斯的“腼腆”让爱德华一次又一次地沦陷在种种错觉中,导致爱德华的“本我”“超我”与“自我”之间冲突不断,不可否认,这也是两人婚姻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三部分组成。本我是本能冲动的根源,是一种被压抑的、完全无意识的精神现象;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起着平衡和协调作用。一方面能使个体意识到其认识能力;另一方面使个体为了适应现实而对本我加以约束和压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是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组成,起着指导自我、限制本我的作用;遵循“理想原则”。本我是人格的生物面,为最求“快乐”而不顾一切;自我是人格的心理面。“有着一种把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的倾向,并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本我中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自我代表我们所谓的理性和常识的东西,它和含有热情的本我形成对照。”[1](P8)超我是人格的社会面,监督和控制自我接受社会道德准则行事,以保证正常的人际关系。
三、爱德华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矛盾冲突
1.“自我”压抑“本我”
爱德华自幼没体会过父母的疼爱,童年的他内心是孤独的。十四岁时当父亲将母亲精神失常的真相——“脑部受伤,她的脑子有问题”[2](P82)——告诉他的时候,他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其实,爱德华难以接受的不是母亲失常的事实,而是长久以来他对于母亲疯癫行为早已习以为常,难以接受由父亲口中说出“她的脑子坏了(Brain-damaged)”此类话语。此时爱德华的“本我”恨不得跳出来拼上一架,觉得这是一种侮辱的话语,是“诽谤”,然而爱德华的“自我”却压抑了“本我”的冲动,面对并接受现实,“开始说服自己,这事儿他向来都知道”,[2](P82)默默地将震惊化为认知。
弗洛伊德认为,作为人格的生物面“本我”永远是冲动的,是追求快乐的。爱德华从小到大会时不时由着性子打上一架,在他看来,“打架有一种激动人心的不可预知性”,但凡遇到羞辱或对方蛮不讲理时便难以隐忍不发。直到有一天替朋友玛瑟出头却失去这个朋友之后,爱德华就再没打过架。此时爱德华的“自我”意识到这种“豪放的美德,到头来却是一种粗野行径”。[2](P111)打架,只能彰显自己的强悍。爱德华的“自我”压抑“本我”的冲动在与弗洛伦斯交往过程中尤其突出。与弗洛伦斯交往后,爱德华很渴望能与她有亲密的身体接触。相处时总会按捺不住“本我”的冲动,试探性地与弗洛伦斯有着肌肤的接触。但是面对弗洛伦斯的“腼腆”时,爱德华的“自我”为了不破坏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选择一次次地压抑住“本我”的冲动。
2.“本我”不顾“超我”
弗洛伊德认为,唯“快乐原则”的“本我”是性冲动和欲望的储存库,它行动的准则是为了个体满足和快感而不顾一切,这种快乐特别指“性、生理和情感快乐”。在被父亲告知母亲脑部受伤的事实时,爱德华的“自我”不断协调着“本我”适应现实,告诉“本我”母亲脑部受伤与自己无关,“终有一天他会离开,再回来时就只是一个客人”,[2](P85)想到此处,爱德华觉得内心有点内疚,但是这种勇往无前让爱德华的“本我”觉得“兴奋不已”。[2](P86)“本我”的兴奋不顾母亲脑部顽疾,这点与“超我”相悖,是违背道义的。
每个个体的成长都是初始的“本我”逐渐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同时受时代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形成了“超我”。三者之间是个相互影响的,有时“自我”为了满足“本我”的需求和快乐而将“超我”置身事外。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相对保守的那个年代,爱德华对“‘自我消遣’(self-pleasuring)的事情总是乐此不疲”。[2](P24)虽然他似乎有种夹杂失败、颓废和孤独的耻辱感,但是这可以让他释放从而感到身体上的快感。
3.“超我”战胜“自我”
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个体的一切行为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人普遍保守,杜绝婚前性行为,认为这是一种耻辱的行为。爱德华和弗洛伦斯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在这方面的知识是匮乏无知的。爱德华与弗洛伦斯的交往中,“本我”渴望与她有亲密的身体接触,但是在“超我”的监督和规范下,“本我”未曾与弗洛伦斯有过“鱼水之欢”。
新婚之夜,爱德华原本以为可以让“本我”欲望得以满足,谁料事与愿违,两人几经周折却还是将新婚之夜弄得一片狼藉。弗洛伦斯最终满怀厌恶地丢下爱德华独自跑到海滩上,爱德华随即追至海滩,两人在海滩上进行了一番刻骨铭心的对话。一方面,弗洛伦斯承认了自己的“性冷淡(frigid)”,但她声称这不妨碍她爱他。另一方面,她建议两人结为夫妻但不同房,并且同意爱德华因生理需要可以找别的女人。此时,爱德华的“超我”觉得蒙受了巨大的侮辱。“超我”觉得弗洛伦斯欺骗了自己,觉得她的建议恶心至极,觉得她结婚却不能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妻子是不道德的,是“超我”难以忍受和接受的。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爱德华心中怒火过了一年才渐消,但是“超我”一直监督“自我”禁止打听有关弗洛伦斯的任何消息。转眼,旧的时代逐渐被新时代所代替,中年的爱德华在物质上小有成就,生活安逸,却膝下无儿女。每每想起弗洛伦斯的时候,想起她当初的建议时,再没觉得恶心或羞辱。即便年过六旬,也时常会回忆着他们之间的点滴,承认着自己爱她最深。想着如果“爱情加上耐心,就一定能让他们俩跨过这个坎儿”。[2](P189)如果爱德华的“自我”当初能让“超我”有点耐心,没准两人已修成正果了,如果那样,小说所呈现的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但是“自我”终究没有协调好“超我”和“本我”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婚姻失败的结局;随着暮年爱德华“自我”“本我”和“超我”达到平衡时,爱德华对弗洛伦斯的怨恨已云消雾散而爱意不减当年。
四、结语
与麦克尤恩早期的充斥着乱伦、性虐、谋杀等恐怖因素的“惊悚文学”相比,这部作品的腔调柔和许多。作品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历的各种变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尤其是性革命给人们的性观念和婚姻观带来的巨大冲击,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麦克尤恩用“白描”的手法对男女主人公新婚之夜的心理活动进行了鲜明生动的描述,叙述之中穿插着对两人的家庭背景及成长经历的闪回,字里行间还流露着诸如反文化运动、反战游行、摇滚乐、电影等时代的烙印。从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可以找出两人婚姻失败的主要原因。爱德华的人生一直经历着“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挣扎运动,暮年的爱德华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才真正找到了“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平衡。
[1]弗洛伊德.石磊.弗洛伊德谈自我意识[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
[2]麦克尤恩.黄昱宁.在切瑟尔海滩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