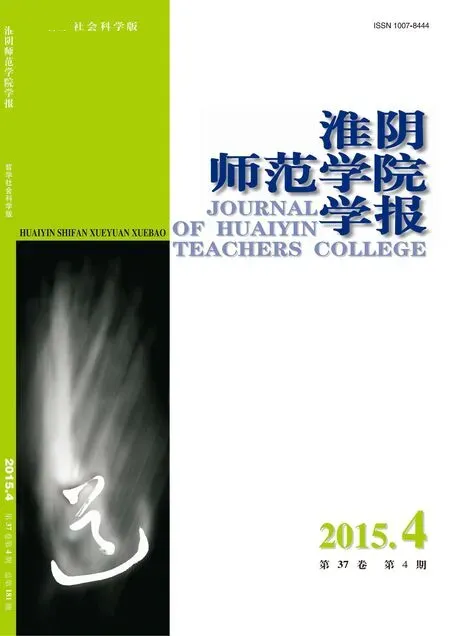梅洛·庞蒂的眼睛
——《知觉现象学》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图像
2015-03-28张晓东
张晓东
(阜阳师院 文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41)
【文艺学】
梅洛·庞蒂的眼睛
——《知觉现象学》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图像
张晓东
(阜阳师院 文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41)
现象学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回到事物本身”的认知理念,它理路清晰地引领我们来到思维的原点处。在梅洛·庞蒂的视域中,顺随着他的目光可以看见旧风景中的新色彩:关于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生命以及艺术。本文选择了几个视点——倾听与描述,呈现与判断,身体与存在,观念与欲望——结合现当代以及古典文本的解释,表达了对当代文学的观察与思考。
倾听;呈现;过程;身体;知觉现象学
一、《知觉现象学》:哲学始于“描述”,然后才是“思想”
现象学最基本的理念是其老祖胡塞尔表述的“回到事物本身”。如何回归,后继者各有路径。梅洛·庞蒂著作《知觉现象学》即是要对现象学继续追问。与所有的哲学追求一样,现象学也是试图在人与存在之间勾画出清晰的图画:存在如何“在”;我们又怎样在其中“在”。哲人说“我思故我在”,那么如何思则是“我”怎样“在”了。“回到事物本身”,是回到“存在”,也包括回到存在中的“我”,“存在”不言,所以,希腊神庙的廊柱上刻着“认识你自己”,认识了“我”,就打开了认识世界的通道。世界与我共在。
梅洛·庞蒂说自己的现象学的策略,是“试图直接描述我们的体验之所是,不考虑体验的心理起源,不考虑学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给出的关于体验的因果解释”[1]1。这与胡塞尔晚年提出的“发生现象学”或“构造现象学”相左。梅洛认为,对体验的直接描述,不应是因果性、溯源性的。而所谓发生和构造,则势必涉及起源和因果问题,奠基被奠基的关系问题。梅洛以对“描述”的重新阐释标明他的现象学关注的特别领域:“问题在于描述,而不在于解释和分析。”[1]2也即纯描述,它寻求的意味是和体验保持一致。认为“回到事物本身”即是回到“体验之所是”。“体验”是领会诸如“理解”“合理性”“本质”“世界”等的地基。但回到“体验”,不是为了解释和分析它,而是对它进行纯描述。据此,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可称为“体验现象学”。
体验追踪此时此地此身此意,但并不就只是直觉。梅洛·庞蒂借助对反省分析的剖析,呈现了“知觉”的优先地位:“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1]5通过对感觉、联想、回忆、注意与判断等的具体阐释,梅洛进一步揭示了知觉的源初性:知觉才是感觉、联想、回忆、注意、判断等的奠基者。而我们日常所谓的感觉从来就不是源初意义的,它是源初意义的知觉的遮蔽。“如果我们想理解感知,我们就要在我们身上探索这个前客观(préobgectif)领域。”[1]34体验是与知觉涵融一体的。对知觉的描述,可以使得体验被澄明化。由此得以呈现的体验境域就是哲学:“哲学只不过是一种被澄清了的体验。”[1]95所以,梅洛的体验现象学又可称作知觉现象学。
梅洛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知觉则是描述此境域的核心;路径呢?他找到了“身体”。理由直接简明:体验、知觉总和身体在一起。他的现象学其实又是“身体现象学”。“回归身体”成为梅洛《知觉现象学》最有价值、最具核心意义的论说。身体和世界共在,它们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成为《知觉现象学》要呈现的核心理念。
身体是一个世界,这是理解梅洛其他思想的一条道路。他关于时间、空间、他人、自然世界、自由、主体间性等问题的论述和思想,都是通过对身体的讨论展开的。
比如时空问题。时空是身体的时空。它有自我的表现力。“身体完全是一个有表现力的空间。但是,我们的身体不只是所有其它空间中的一个有表现力的空间。被构成的身体就在那里。这个空间是所有其它空间的起源,表达运动本身,是它把一个地点给予意义并把意义投射到外面,是它使意义作为物体在我们的手下、在我们的眼睛下开始存在。”[1]193可见,客观空间正是奠基于这种身体的原始空间才成为可能。时间也是如此,他说:我的身体本身就包涵着原始的时间,“我的身体占有时间,它使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为一个现在存在,它不是一个物体,它产生时间而不是接受时间”[1]306。原始时间使得客观时间成为可能。
关于世界问题。梅洛认为:物体、世界呈现给我,是和我的身体的各部分同时的,并且是在与身体各部分相同的一种活生生的联系中,呈现给我的。“物体的综合是通过身体本身的综合实现的,物体的综合是与身体本身的综合的相似物和关联物。”[1]264对世界的理解同样可以从对身体的理解开始。
尤其重要的是梅洛认为,身体始终是不确定的、模棱两可的。“身体本身的体验向我们显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存在方式。”[1]268如果我们要认识身体,也必须在“我只能在我的内在于时间和世界的特性中,也就是在模棱两可中认识自己”[1]435。另一方面看,世界与时间的特性就是模棱两可,于是,“世界已经被构成,但没有完全被构成”[1]567。
这一思想启示了我们该怎样理解世界。世界不是一个对象性存在,不可能被理性认识所穷尽,因为世界没有完全被构成。通达世界的道路,是通过身体,去体验、去知觉。对身体的描述,同时也就是对体验、对知觉的描述。因为体验和知觉与身体是一个融合体。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既不唯物,也不唯心,他用“涵融”一词弥合了唯物唯心的人为界限。而他对“体验”的“纯描述”也即“呈现”则突出了“过程”的价值,借助“身体”这个桥梁,梅洛连接起了世界的此岸彼岸。“世界已经被构成,但没有完全被构成。”世界需要继续构成。回到事物本身也是回到世界继续构成的过程中。
二、顺随着梅洛·庞蒂的目光看文学风景
人类的任何表述其实均可看做认识论,不过是哲学、历史与文学表达方式不同罢了,果然是文史哲不分家呢!一切同在,一切互文。用《知觉现象学》的眼睛来看看文学呢?“知觉现象学”对文学最富启发意义处,在:“纯描述”拒绝“分析与解释”,正是对人自大、其实狭小的纠正;注目第一性征的“体验”将引领我们重新探究“真实”;而“回归身体”成为文学宣言似乎比哲学更有理由。由“身体”“知觉”着“体验”的过程,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综合”了的整体世界。
(一)倾听与描述。
作为一种话语方式的文学,看起来如自言自语,其实是潜在对话。要做一个好的对话者,先要懂得倾听。倾听不只是一个动作,尤其是一种信仰。维柯《新科学》曾写道:“《日耳曼尼亚志》说,他们听到太阳在夜里从西到东穿过海的声音,而且听到过天神。”这描述中有着静默庄严的神圣,让人的心灵震撼。这不是仪式化了的宗教,而是先民真实生活的描述。在古人的天地人神四维时空中,时间、过程、声音本就是一种同构关系,“倾听”则是人连接天地神间的纽带,或者说就是先民存在的重要形式。“倾”听,从它的外在姿态就可看到其间含着的谦卑与敬畏。人是自然(存在)之子,他自然应该像子女回应母亲的召唤那样去倾听自然(存在)。可是,曾几何时,我们早已不再“倾听”,在人定胜天的信念下,我们“倾诉”“控诉”,甚至“征服”。人,好像巍然屹立在天地之间,其实,天地远人而去,神也逃遁无踪。人丢失了谦卑,只剩下浅薄的骄横。我们自称是孔子的徒孙,却不记得祖宗说过的“述而不作”,更不用奢谈领会其中的奥义了。“述”定是倾听之后的描述,正与梅洛·庞蒂的“纯描述”殊途同归。面对俗世的浅薄,孔子激动地反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
天地不言,大象希象,大音希音。沈从文说,在天地之间我唯有“喑哑”才是诚恳。斯是诚言啊!唯有倾听,才能引领我们走上归家的旅途。如果人只满足于自己在各个领域慷慨激昂的激情,陶醉于自己曼妙动听的声音,结果只能是让自己陷入一个空洞虚无的世界。
如何倾听?倾听的过程也是体验的过程。是让“存在”从我们的身体“穿过”。打开我们的身体,与天地神——存在交融。这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体验之所是”,就是“回到事物本身”。所以,他又说“体验”是领会诸如“理解”“合理性”“本质”“世界”等的地基。可是,我们常常是拒绝倾听、拒绝体验、拒绝身体。有论者说:“看看我们当下的文学,那种轻薄、轻狂、无知、狂妄、低级趣味,真是到了让人无法呼吸的地步。文学,在他们的手里早就成了死尸,虽然挂满了‘勋章’,也是死尸而已。”[3]话虽很情绪化,叙述却很真实。中国文学失却了应有的信仰:不再敬畏天地神,甚至人自身,目光如此短视,实乃庸俗欲望缠身所致。中国的文学现实已不是教科书里简单的“文学反映生活”,而是文学与生活正在进行“互文运动”,以至你已分不清是文学在模仿生活,还是生活在学习文学,真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嘉年华狂欢。比如,新时期初期的“伤痕”、反思文学的倾诉与控诉,面对曾经的大灾难是多么地浅薄、做作。“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越战之中美国阵亡士兵不到六万,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个电影反映出那些苦难?面对十年动乱的‘文革’,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我们的《晚安,好运》《战争的迷雾》《佛罗斯特·尼克松》在哪里?在《上海宝贝》里?在《大话西游》里?在《无极》和《满城尽带黄金甲》里?”“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4]这样的疑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再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新写实”:零度情感后的严肃冷峻,平民视角后的人道温情,充满生活实感、质感的描绘,固然比过去的假大空是大大的进步,可是,另一些问题就被欣喜湮没了,“新写实”里种种“烦恼人生”的逼真写实,获得读者极大面积的认同,掩藏在种种生存智慧、技巧、阴谋、无耻后面的挫败感、疲乏感、无奈感以及由这些感觉所导致的玩世不恭、坑蒙拐骗、曲迎谄媚甚至丧尽天良等种种心态,人们似乎已视为当然甚至在现实中模仿。这是文学之幸抑或不幸?作为当年新写实的重镇池莉,不用读其文本,就看她的作品名称,其写作的心路历程就已一目了然:《太阳出世》《烦恼人生》还能看见她的温暖、担当、坚持、希望,可是后来就是《来来往往》《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离婚了就别来找我》《小姐,你早!》了。今天的电视电影荧屏更不用说了,不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就是戏说、穿越。在嘈嘈切切叽叽喳喳中,我们自己明白,中国人已没有心灵生活。可是,就是在现当代,我们也经历了太多的大苦难,为何至今我们却几乎没有对得起这大苦难的大作家大作品,我们整个民族包括作家在内缺乏大的精神境界恐怕是根本原因。我们听不见天地神,看不见大宇宙,也不追求那个在我们的理念中应该趋向完美的“人”,我们只会在墙角、窗下窃听。
(二)呈现与判断。
如果是打比方,可以说“呈现”与“判断”这两个词具有不同的德性;如果把它们与生命相接,也可以说对应着不同的生命习性。喜欢呈现的人的生命习性可能更近于谦卑、仁慈、自然、朴素、诚恳;喜欢判断的人的生命习性可能更近于骄傲、蛮横、作秀、粉饰、谄媚。当然不绝对,只是可能。
从思维逻辑说,人们应该更尊敬呈现,即便要判断,也应在更加充分的呈现之后。道理早被人简单说明,呈现总是和事实相伴,判断则取决于判断者的自主选择;判断可能会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事物的判断不同,往往不是因为价值观或者智力的差异,而仅仅是因为对事实的掌握不同。”[5]这样就可以理解梅洛·庞蒂在他的现象学里为何要特别强调“纯描述”,反对解释和分析(判断就隐含其中),因为如果要“回到事物本身”,我们就先要找到回到事物本身的路径,此即倾听、描述抑或呈现。而且,需要强调的还有另一面,呈现与判断的思维方式不同,呈现是“过程”思维,判断是“结果”思维。过程是与时空共在,判断是时间的静止、空间的凝固。这里有绝对、大大的不同。再打个比方,呈现仿佛展开一幅画卷,判断则如一锤定音。基于这样两幅不同景观,米兰·昆德拉也有他的评述,喜欢判断的人多是一些既骄傲、专制、自大,又僵硬、懒惰、具有偏见的人物,因为骄傲自大,他们看不见人的渺小,因为懒惰狭隘,他们不承认世界的相对性模糊性中所蕴含的复杂与深邃。他们只期待世界如他们判断的那样存在。最好善恶标准泾渭分明,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理解之前即进行判断。米兰·昆德拉说,就是在这种欲望之上,他们“建立了宗教和意识形态”[6]。
中国文学成绩不佳,缘由多多,作家的创作理念认知上的浅薄当属一条。把判断凌驾于呈现之上,就是很多作家的通病。这样的作家往往习惯性地扮演“智者”的形象,不自觉地就把自己“端起来”写作。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曾得到很高评价的张炜的《古船》,实在是一部从语言到立意都很做作的作品,载道意识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结合,使得《古船》里的那一份凝重极不自然,小说的一号主人公隋抱朴,连名字都充满了一种古典凝重的气象,作家隐喻的意图昭然若揭。小说确实也着意刻画主人公的凝重,表情凝重,身体凝重,心理凝重,连他的爱情也被作家写得无比凝重。作品反复写他的厚重的脊背,和磨坊及磨坊里厚重的石磨这样的背景贴合在一起,这个几乎足不出户整日坐在磨坊里凝眉思索,外形高大又冷峻的男人形象,一定让作家觉得气韵生动韵味十足,深得象征之三味。但作品缺乏汁液饱满的生活、生命细节,作家虽然想把隋抱朴塑造得如一尊神,但结果连一个鲜活的人的形象也没能刻在读者心里。而《古船》里的那个“古船龙骨”被作家画龙点睛般地特写推出,更是画蛇添足。隐喻和象征如果浓墨重彩如油画一般地被画出,他就不是隐喻象征,而成蹩脚的比喻了。
和汪洋恣肆的存在相比,即使高明的观念也不值一提,中国作家的那一点小聪明耍起来只会更加难看。歌德的话虽已被引得太滥,毕竟是一句真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何从生命这株大树中汲取营养才是中国作家应走的正道。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拷问吧,然后,细致、舒缓、毫无保留地呈现吧。莫言先生是懂得的。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答谢致辞的题目就很精彩:《讲故事的人》。这是一个优秀作家对自己身份的准确定位。作家是靠“讲”故事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而莫言的“讲”,恰恰就是描述、呈现,而不是解释分析判断。莫言的可贵是在于他信任读者的智力。读莫言的作品,你脑袋里不大会出现精致的概念,而只觉得汪洋恣肆美丑交融的生活生命世界扑面而来,意象鲜明,蕴含富足。莫言的小说把你带进时空的历史长河,把存在的世界真的像一幅色彩斑斓的长长画卷在你眼前缓缓展开。他充满肉感的文字把你引进亦幻亦真有形有质有色有香的世界时,恍惚间你也许真会有庄生梦蝶之感:是莫言的小说唤醒了我们对生命世界丰富而难言的记忆,还是我们丰富难言的生命记忆让我们趋向认同莫言?莫言的小说从《透明的红萝卜》始就专注于人物的内心体验。体验的特点一是它的“过程性”,一是它的“弥散性”,由此而言,可以说莫言的小说是和他的人物同步诞生的。这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阐发的思想简直就是异质同构:世界没有完全被构成,世界正在被构成。通达世界的道路,是通过身体,去体验、去知觉。对身体的描述,同时也就是对体验、对知觉的描述。因为体验和知觉与身体是一个融合体。
文学的呈现靠细节,描述细节的能力是区分作家高下的标志之一。莫言是写细节的高手。比如《檀香刑》[7]259-261中的县令钱丁,他一直想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德国人滥杀无辜,拳民孙丙造反,朝廷下令捉拿,钱丁出于正义,也因自爱孙丙之女孙眉娘,书中写钱丁满怀激情夜奔莱州府陈情请愿,可是,经历了严寒、荒野、野狼、伤痛的折腾,“知县心中的激情,渐渐地消退,身体上的热度,也慢慢地降低。没有风,潮湿的霜气,如锋利的刀片,切割着裸露的肌肤”。“在辽阔原野的深处,马的喘息声和枯草摩擦衣服的嚓啦声大得惊人。从遥远的村庄那里,间或传来几声模糊的狗叫,更加深了夜的神秘和莫测。知县的心中,泛起了一阵悲苦的感情。”知县想起“那时候我们意气风发,青春年华,胸中怀着天大的抱负,想为国家建功立业,可如今……”因为逃避狼的攻击,丢盔弃甲,官帽散落荒草深处。“他突然想起了那顶象征着身份和地位的官帽子,急忙下令:‘春生,先别忙着搂草啦,我的帽子丢了。’‘等点上火,借着火光好找。’春生说。春生竟然敢违抗命令,并且公然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不寻常的发现让知县感叹不已。在这深夜的荒原里,无论什么样子的准则,其实都是可以修正的。”后来的钱丁终于没有成为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只是那个制度下很难说好坏的千百个官员中的一个。莫言写人,从不硬性拔高或贬低,他是把人放在“场”里如工笔画一般地精雕细刻,或者如他所言,他只是个“讲故事的人”。但他讲得细腻、具体、深入,此时、此地、此身、此意,宏观写意,微观工笔,有纵深,有前景,神形兼备,纹理清晰。还要画蛇添足地判断么?
同样的,那些只会玩弄名词,挥舞理论大棒,心灵枯槁、笔下生涩的批评家们不也该反省反省么?少一点居高临下,多一些对存在、生命的敬畏,让文字从灵府的深处自然流出吧。
(三)身体与存在。
回归身体,身体是一个世界,而且,只有身体才标示出了我们与世界共在,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现象学最核心最富有创造性的论说。梅洛·庞蒂的“身体”指的不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即通常所谓作为对象存在的客观身体(肉体)。恰恰相反,只有当身体不再是客观身体之际,才是梅洛·庞蒂所要说的身体,才是“身体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身体的意义也才开始呈现。“由于客观身体的起源只不过是物体的构成中的一个因素,所以身体在退出客观世界时,拉动了把身体和它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意向之线,并最终将向我们揭示有感觉能力的主体和被感知的世界。”[1]105
有一个听起来很俗套的说法,作家一定要多体验生活。有道理。可是,很长时间里,我们对此理解却很庸俗,体验生活被理解成离开自己生活去经历陌生生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扩大自己的生活面。难怪王小波有一回阴阳怪气地嘲讽道:“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啊,你没有生活!”王小波说自己听糊涂了。没有生活?难道我活着是“死人在乍尸?”后来明白是要他放下自己的生活去体验别人的。[8]可是,王小波们一定还是糊涂:我自己的生活比别人的没有意义?更关键的问题是:别人的生活我怎么去体验?所谓人的孤独,最基本义就因人的身体的独自造成,不可替代、叠加的一个个身体让人成为一个个孤岛。身体就是一个人世界的边界线,你无法越出自己的领地。当初,陶渊明远远看着农人的生活时,实际是他的心灵——精神、心理、性格、情趣等在看,身体被悬置着。它更多看到的其实是田园风光,是有距离的审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在他生命晚期,他真的归耕农野之后,才真实“体”“验”到了农人生活的苦况,《田园归居(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外狭木长,夕露沾我衣。”可是,这已是诗人陶渊明更是农人陶渊明的生活体验了。体验生活绝不是走马观花,绝不只是暂时抽离自己的角色让肉体去旅行,体验要的是你的身体在场,一个人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其实就是你身体经由体验而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此即梅洛·庞蒂强调的身体是一个界域的意思。他说,回归身体,意思也是说,从你的身体出发,走向你所能达到的世界。身体是储藏室,能源库,是出发地,也是归宿处,身体就是我们的一切。探索我们存在的边界,就是探索我们身体的边界;反过来说同样成立。身体与存在共在。
我们的文学在探索存在时,却常常讳言身体。《金瓶梅》这部神奇之书就因它太过大胆放肆的身体书写,人们似乎找不到面对它的自然姿态,几个世纪以来,对它的理解总不得要领,不是道学家的虚伪,就是肉欲者的下流。其实,《金瓶梅》是探讨人的内面宇宙的一部奇书。它描述了一个没有信仰唯有欲望的世界。
《金瓶梅》里没有人在乎什么生命的意义,大家追求的就是吃吃喝喝、性爱玩乐、发财赚钱、争宠斗妍这些世俗欲望。《金瓶梅》提出了一个很简单、根本,却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确定了生命的本质“只是一团欲望的集合”(斯宾洛莎语),生命还能寻求什么?“兰陵笑笑生先带我们进入一个理性热闹的表象世界,再用人心深处的钱欲、权欲以及性欲,把那个看似秩序井然世界里的所有意义与价值——不管是伦理、道德、义气、友情、爱情都一一解体,让我们看穿:原来‘价值’只是表层的假象,欲望才是底层的真实。正因为在乎真实,过去那些被视为粗鄙、贪婪、淫秽的一切于是有了值得被凝视的理由。《金瓶梅》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一个世俗世界,他用‘粗鄙’来颠覆‘价值’的虚伪。”[9]所以,与其说《金瓶梅》描述了世间的丑恶,还不如说更是在呈现着人面对欲望时的贪婪与软弱。明白了这些——而不是更多的道德教训,人才有可能稍稍远离对人性的无知,懂得一点点的悲悯。《金瓶梅》是一本愈读愈虚无、荒凉的书。
而作为一个风情万种的挑逗者,《金瓶梅》里的潘金莲也成千古绝唱。我们的文化遗产里,不喜欢潘金莲这样的角色。她凭着对人性极端精妙的拿捏与理解的丰富,示范出绝佳、动人的风情万种。我们有太多的忠孝节义,却很少潘金莲这样的千娇百媚。我们渴望着,却不敢表达。
三、必要的反思:在存在与理念之间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唯一使命就是勘探存在。而“克尔凯郭尔不仅告诉我们存在先于思想,或者,所有思想都是某种具有存在的表现;他还通过向我们揭示思想就是一种没有伪装的存在,即其本人的有血有肉的存在,而告诉我们这一真理”[10]。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理解,实际的情形是,存在与理念的关系问题不仅纠缠着一代代的哲人们,其实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如果存在之前就有理念,那这理念也只能是上帝的,不是人的;如果真有上帝,当然也可以说人是上帝的理念之一。那么至少在人自己的世界里,存在先于理念。理念最基本的功用是认知,因此,呈现存在本就是一切理念的第一理念。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着意“身体”“体验”基础上的“知觉”理解,反对先验的解释与分析,显然是反对把理念凌驾于存在之上的理路。而中国文学常有的一个尴尬在于:我们太多的充斥着先验观念的文学在面对着欲望的生活、生命存在时,要么失语,要么顾左右而言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不敢直面”、到处充满着“瞒和骗”。《金瓶梅》是中国小说里的一个异数。小说里的人们不用观念来指导生活,人物的内心生活只是随机而起,生命的时态永远是正在进行时,不回望过去,也不遥看未来,所有的激情都交付给现在。生命的历史就是欲望的追逐过程;欲望耗尽之日,就是生命终结之时。这是没有前程的往前奔,却为何还这样地摇撼人心?《金瓶梅》展示了生命本体执着而荒谬的力量,在自我审视的讽刺中满怀着苍凉的况味。
文学是人学。和哲学、历史、政治等人文学科一样,文学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解读人类命运,有两个基本路径:如何认识自己及与身外世界的关系。哲人说:“多少世纪以来,人类就不断设法超越自己,超越物质世界的幸福,向往所谓的真理、上帝或实相那种无限的境界,或不受外境、思想及人类的堕落所影响的存在。”[11]3人类早期的宗教、哲学诞生于人还是大自然奴仆之困境时代,人无意识地匍匐在神、理念、上帝的脚下,身处在此岸的苦难之中,没有突围之策,心中就幻化出了彼岸天堂或仙境那般的世界。如此这般理解存在的传统诞生当然很慢,可是一旦生成,消失也难。而我们却因此有了自己的一份命运,这命运始自我们的出生:我们只能依据自己所在的传统,订下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也许是佛教的,也许是基督教的,也许是儒教的,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传统为我们划定是非善恶的标准,我们只需恪守力遵,久而久之,我们的言行思想便有了惯性,不假思索就会自动反应。我们从不思想。在宗教的历史中,我们总是看见差不多的景观:总有被称为圣贤、圣徒之类的人向人们宣示:只需要一些仪式、祷词或咒语,压制欲念、控制思想、升华热情、限制口腹之欲、疏导性欲,等等,经受这些磨砺之后,就能在这渺小的生命之后,获得终极拯救。于是我们看见有人退隐于沙漠或山洞之中苦修,有人托着钵一村一镇地乞食流浪,还有人群居一处组成修道院,强迫自己的心智臣服于某种既定的模式。没有人问为什么。更没有人像尼采那样喊出“上帝死了!”在中国,只有鲁迅的狂人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那么到了今天,在人已具有了非凡的反思能力之后,是否该向自己发问:这个身为人的我们究竟是什么?人首先期待的难道不是活在真实的存在中么?
人与个人不同。“个人”只是部分的存在;“人”却是普世性的。“个人”是个受限、残缺而又饱经挫折的渺小生命,但是身为一个“人”,他关怀的却应是整体人类的福祉、不幸和困惑。我们能否撇开理论,不谈理想,而只是实事求是地活着?就如弗洛姆在《自我的追寻》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要获得自己的幸福,一厢情愿地瞎浪漫是没用的,首要的是心平气和地弄明白我们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的。不要把观念凌驾于我们的生命之上吧。让真正的理性归于我们的灵府吧。“真理是活的,互动的,不驻留的,既不在佛寺、教堂里,也没有任何人能领你到那儿去,这活生生的东西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你的愤怒、你的残忍、你的凶暴、绝望、痛苦和悲伤。能认清这些就是真理。只有学会如何去观察生活中的这些真相,你才可能了解真理。你是无法透过空想、文字障、期望或恐惧而得到它的。”[11]22
这就是真相。有时真相很残酷。在真相面前,有不同选择:可能因绝望而生出玩世不恭的犬儒心态;在它的对面则是勇敢地面对且承担,没有任何人,只有我们自己为自己负起全责,然后所有的自怜才会消失。不要怪罪别人,这只是另一种自怜罢了。在独立的寂静中,人能不能从自己的本质和内心里产生自我的发展,获得自己的喜悦、快乐、幸福?人能否改变自己的残暴、好强、焦躁、恐惧、贪婪、嫉妒以及构成今日人类现状的种种劣根性?撇开愚蠢的观念,直视我们自身。这就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要“直接描述我们的体验之所是,不考虑体验的心理起源,不考虑学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给出的关于体验的因果解释”的缘由所在。重要的是如何观察日常生活中确实在发生的事,不论是内在的或外在的。我们必须承认眼前的事实:我们总是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理念置于存在之上,而理念并不能涵盖整个存在的领域,不论我们如何机巧地把它们缝在一起,也不论多么古老、多么传统,它们仍然只是存在的一小部分,而我们必须面对的却是生活的整个领域。如果我们再深入观察,就会明白,其实过程从没有内外之分,只有一个过程,那就是整体性的发展过程。内心的活动表现于外,而外在的反应又源自内心。如果我们懂得观察、倾听、体验,所有的事都能一目了然,而观察、体验并不需要哲学的指导,我们只要像沈从文那样用心通过自己的眼睛去注视就好了。“而我欢喜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像别的书净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书中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它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12]沈从文说的不仅是文学的立场,更是生命应该秉承的信仰。
[1]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孔子.论语·阳货第十七[M].
[3] 杨光祖.技术时代的当代文学庸俗化倾向[M]//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6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2010:51.
[4] 刘瑜.民主的细节·至少还有记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58.
[5] 刘瑜.民主的细节·后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291.
[6]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5.
[7] 莫言.檀香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8]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164.
[9] 侯文咏.私房阅读《金瓶梅》[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2.
[10]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杨照明,艾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51.
[11] 克里希那穆提.重新认识你自己[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
[12]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77.
责任编辑:刘海宁
I022
A
1007-8444(2015)04-0530-07
2015-02-07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现代文学‘情色’书写研究”(12YJA751082)。
张晓东(1966-),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