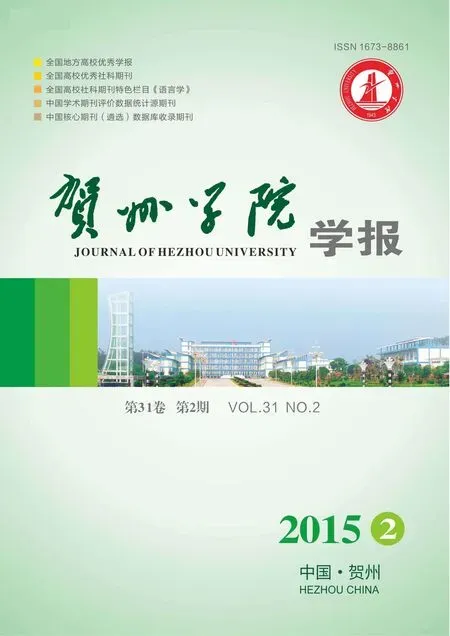端木蕻良在桂小说解读
2015-03-27臧晓彤
臧晓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端木蕻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处于被冷落的地位,翻阅民国时期三四十年代的报刊,端木蕻良作为著名作家已被大家所熟知。端木蕻良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与我们当今对他的评论、重视程度是不对等的。这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遗憾。端木蕻良的小说,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到达了一个高度。进入20世纪,对端木蕻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端木蕻良文集》得以出版,相关的研究专著也开始出现。在小说方面,端木蕻良的创作,在20世纪40年代有着明显的转变。端木蕻良1941年3月来到桂林,1944年年底离开,在这3年半的时间,他一共创作了15篇小说,按照创作时间先后,分别是《初吻》 《早春》 《雕鹗堡》 《步飞烟》 《海港》 《蝴蝶梦》 《红灯》 《科尔沁旗草原》 (第二部)、《女神》 《饥饿》 《海上》 《前夜》 《琴》 《红夜》 《几号门版》 (长篇小说),由于创作心境事过境迁,《科尔沁旗草原》 (第二部)草草收笔,而《几号门版》并未写完,因此这两篇长篇小说在本文中将不予解析。
爱妻的逝世、个人的愁苦都在桂林这个城市发酵,独特的人生经历也催发了端木蕻良不同的创作手法。通过对其小说的取材、结构的角度对这13篇小说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在桂林这个城市契机下端木蕻良在桂小说的特色。由于端木蕻良在桂的文学创作有着明显的转变,因此在具体的文章中,也会涉及到端木蕻良来桂之前的作品分析及前后对比。
一、小说取材由“实景”到“虚处”
端木蕻良前期的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小说的内容多是由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的人、事中取材,人物生动、取材丰富。但是端木蕻良在桂期间的小说取材却有着明显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小说取材由现实性的人、事转向了民间传说和西方神话。从民间传说取材改编的作品有《雕鹗堡》《步飞烟》 《红夜》,从西方神话中取材的作品有《蝴蝶梦》 《女神》 《琴》。不管是民间故事的取材还是西方神话故事的改编,都富于象征意味地表现端木蕻良的情感剧痛,同时也使得这些小说内化特征更加明显。
《雕鹗堡》虽取自民间传说,但又颇像是寓言故事,作者有意模糊时间地点,但却突出了主题的超时空性。文章开头“主宰这小村子的命运的,就是那雕鹗。”“雕鹗不知传了多少代了,人们不注意这些,就好象人们也不大注意这村子过了多少代一样”“什么都是没有变的。”主人公的名字“代代”也暗含着不变。但是石龙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个变。石龙的形象设定中牵扯到第三人称叙事与第一人称叙事的真实。文中说“石龙是这村子里最惫懒的孩子了。”但是在代代与石龙的对话中,有这样的表述“石龙说:‘这不算重的,我帮着他们扛石头那才重呢!’”与其说是“运用象征主义方法针砭国民性的小说。”[1]16不如说是针对自己遭遇,端木蕻良所写下的一份批判书。
《红夜》这篇小说充满了神秘、异域的色彩,洞口石人的传说与姐姐“玛璇”和龙宝的爱情交相呼应,而远古的传说又与巫师“汉爷”成为了两种对抗的力量,原始情爱“在祭神的晨光就是犯罪。”这篇文章歌颂了原始的情爱,否定了所谓的人间理规,这无疑也是对当时人反对端木蕻良和萧红婚姻的一种无声的抗议。不过这篇小说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还在于故事背景是西南地区,这在以往端木蕻良的创作中是没有的,在桂林一年的时间,西南地域的文化已经逐渐渗透到端木蕻良的心理构成了,成为了端木蕻良创作中的构成要素。
端木蕻良所改编的希腊神话的3篇小说《蝴蝶梦》 《女神》 《琴》所依据的是汪倜然的《希腊神话ABC》。《蝴蝶梦》重写了人间公主菠茜珂与阿弗洛谛德的儿子伊洛丝的爱情故事。《女神》全文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倾诉了我对只有夜间才能来临的月神一般的“女神”的爱情。《琴》重写了山林女神达芬妮惧于太阳神爱普罗狂热的追求而让父亲将自己变为月桂树的故事。对于这3篇改编的小说,端木蕻良曾在文中附记说明:“完全按照汪倜然先生的《希腊神话ABC》一段重述出来”“没有十分改动”,那改编后这3篇小说的意义何在?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重写型”的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仅是改编这么简单,考察“重写型”的小说就要考虑到重写文本、前文本、作者、写作语境等多个方面。对于端木蕻良这3篇“重写型”的小说而言,重写文本与前文本所要表现的主题也没有什么差异,都是为了突出希腊神话灵肉一致、强健活泼的一面。但是在作者对前文本进行“重写”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也就是认知模式,“所谓认知模式指的是人们观察事物的立场,看待事物的方法。质言之,‘重写型’小说文本都体现着重写者看待前文本的认知方式。”[2]8因此,重写文本与前文本的无差别反而表明了端木蕻良对希腊神话中灵肉一致的爱情的认知与认同,同时也进一步凸显了这两种文本共同的精神指向。
对灵肉一致的爱情的认同,这一点在小说《步飞烟》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步飞烟》副标题为“故事新编之一”,这篇小说改编自唐人皇甫枚的传奇《飞烟传》。通过和前文本《飞烟传》的比较,尽管故事内容是相同的,但是在故事的安排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在人物的设定上,前文本中负责传信的门媪改为了晴云和小香两个年轻活泼的小丫鬟。其次叙事的具体安排上,删除了前文本中步飞烟约见赵象和女奴向武公业私告步飞烟以及结尾后人对步飞烟的评说的几个情节,增加了步飞烟与晴云的对话并有意在文中突出了玉碗这一意象。通过男主人公的淡化和女主人公的突出,文章的主旨是很明显的,正如文中所说“她用着一种生命来爱一个人,她不是非爱赵象不可,而是那青年公子,是属于她的理想那一面的。”文章所主张的是女性对个人需求的满足的追求。但在解读这篇小说是,有些学者将其描述为塑造了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女性步飞烟的形象,“个性解放”这个帽子不得不说扣得实在太大了。文中有一段对步飞烟私会赵象的行为的原因作了如下的解释:“赵象的影子出现在她的眼前,正像在她的情感的河湾上,开了一个闸口,她那被压抑的情感就一齐的向这方向奔流……向这一边跑去,正是给那可厌的、可憎的、肮脏发锈生活的一种报复……”以“报复”作为理由,恰恰说明了“解放一说”的虚妄。
端木蕻良的《红灯》,在端木蕻良作品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过多的提及,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端木蕻良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实验意味,笔者以为,这篇小说是端木蕻良最具实验特征的作品。在这篇发表于《新中华》1943年1月出版的复刊号上的小说中,端木蕻良似乎恢复到了以往的“宏大叙事”,即鞭挞日本帝国主义和本国政府的残暴无情:“这儿和山地已经是两个国度,已经是两国的人民”,政务次官禁止山东工人登岸,“刮风来了,便把他们刮翻了,这儿等不了陆,山东老家回不去,只好死在海里……”,但如果对这篇小说的解读仅限于思想内容的概括,那这篇小说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创作于1942年12月份的这篇小说已经突破了当时小说创作的常规。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态度模棱两可。一般地说,对于贫困的人物,作者的态度多是同情、怜悯,可这篇小说却不是那么简单。文中出现的主人公只有五个:爷爷、婆婆、醉鬼、黎老爹和莲花。爷爷,瘫痪在床已一年,往常他都会载海边挂起红灯,好让出海的渔民找到回家的方向,但“今晚”,爷爷挣扎着在礁岩上坐起了红灯,却只有“好些尸身,刮光了毛的猪群似的向那灯光爬去”;奶奶,只是在搓绳子,“我的手指头正好和麻绳捻在一起了”,“今晚”她一直在找不知道是还没有捻还是捻过却丢掉的绳子;醉鬼,从海边死尸身上剥下的衣服,一直在恳求着老妈妈买点;黎老爹,来爷爷家找旧铧铁,好救海边还有活气的人;莲花,在海边白茫茫的死尸中想分辨出她那已死去的爸爸。小说就围绕着这五个主人公不断的重复。对于爷爷海边挂红灯的行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所有人都明白“灯也不中用了”。而奶奶反复的搓麻绳,可是“搓了半天还是五根”,作者在否定这些行为的同时却又彰显了这些人的一种“西西佛斯的精神”,即使是那些尸身,也会向那灯光爬去,“那红郁郁的灯光,仿佛重新又在那些尸身上涂了一层血色……”这篇小说颇有些西方叙事的特色,模糊故事的时间、地点,甚至小说的内涵也远不是小说中的人物所能承载的。
《饥饿》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改编”之作。小说的体例模仿了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思想主旨模仿了林淡秋所翻译的挪威作家包以尔的《大饥饿》。小说通过“我”的心理活动和言语交代了我这一生饱受了“饥饿”的折磨。从小说的创作及发表的背景看,这篇小说也算是应时之作。1943年,被当时的文艺界视为胜利之年,如1943年1月《新中华》复刊号的发刊辞中所言“是此一九四三年,固不惟为盟国反攻之年,抑亦将为盟国胜利之年。吾人之胜利已在望矣!”“要当以此两者(作者加: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之建设为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饥饿》完全可以属于致力于国民精神建设的范畴。
小说是一种关于时间、空间与人的艺术,联系到端木蕻良当时的创作语境,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改编的作品,超越时空,淡化人事,但这样的有意虚化却赋予了这些小说主题以永恒的意义。这些作品的指向已经不再是讲故事那么简单,而是上升到了自我与人类的悲剧命运,而这些也都是端木蕻良人生经验的一种外显。
二、小说结尾由“外放”到“内收”
端木蕻良前期小说作品的结尾往往是模糊的,主人公最终的去向往往没有得到作者明确的说明。如《门房》中的“我”——一个卖梨膏糖的小孩儿,在经历了生活的辛苦与荒唐后,决定把手风琴卖了做“去张家口”的车费,但最终“我”去没去,作者并没有交代。《海港复仇记》中渔夫“大有”杀人逃走后再次偷偷回家时,儿子问他几时回家,他却只回答“快了”,至于以后回没回家,文章没有再叙述。再如《乡愁》中,“金先生”在提到大学生被捕询问星星奶奶他儿子姓名后狡猾的对奶奶一笑,但文章结尾到底是不是奶奶的儿子被捕也没有具体的说明。
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多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扮演着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角色,文中自有一种罪与罚的审判立场,尽管作者设定的结尾是模糊的,但这个模糊是相对于文章中的主人公而言的,作为读者,却是明白的,如《乡愁》,我们读者明白被捕的大学生就是奶奶的儿子邓铁珊,如《海港复仇记》,读者也知道“大有”肯定会回来报仇。这样的叙述自然形成了一种张力,文章主人公的等待期盼转化成了读者的明确的焦灼,在这样的阅读感受下,读者更能体会到恶势力的残酷,从而也追随着文章主人公有了抗争的力量。这也体现了端木蕻良早期的文学创作观念:“我最初接受的文艺理论,是‘为人生而艺术’的理论,这几乎影响我的一生。”[3]74来桂之前的端木蕻良的小说结尾是外放辐射的。
与此相对,端木蕻良来到桂林后的创作的作品往往都有明确的结尾,但这明确的结尾中却让读者感觉非常的困惑。这自然与作者的创作心态有着很大的关系。端木蕻良来桂后的创作视角转向了自我,不管是直接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故事,还是以第三人称来讲述他人的故事,其目的都在于反映我此时的心境。可是,失去萧红的端木蕻良此时的心情是痛苦复杂的,这反映在文章的创作上就是文章明确的结尾后面却包含着大量模糊的心绪。最明显的莫过于《初吻》和《早春》这两篇文章,《初吻》虽然是写我对灵姨的感情以及感情的失落,但中间却夹杂着作者的逃避的心态,《早春》表面上是写我丢失了伙伴金枝,但深层中却是忏悔。再如《雕鹗堡》,这篇近似于寓言的文章表面上写了石龙和代代的微妙的儿童感情,却因为夹杂着村里人的看法以及石龙的死而变得特别的复杂。再如根据希腊神话而改编的《蝴蝶梦》 《琴》等,简单的神话改编却赋予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剧命运观。来桂之后的端木蕻良的小说结尾是内收的。
从端木蕻良前后期小说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端木蕻良小说的结构的变化,前期小说结尾看似模糊实则明确,而后期的小说则是看似明确实则模糊。小说文本的话语方式尽管不能完全与作家当时的精神状况相等同,但是两者的确具有内在同构性。小说结尾的变化内在的反映了端木蕻良此时的心境。前期小说结尾模糊中的明确更像是一种小说叙事手段,而后期小说结尾明确中的模糊则反映出端木蕻良此时对人生的一种感悟。
三、创作风格转变的契机
端木蕻良开始文学创作之后,他到过很多地方,天津、北平、上海、青岛、武汉、西安、重庆、香港、桂林、遵义等城市都留下了他的创作身影,但是,唯独桂林,是与端木蕻良个人气质及故乡地域文化最相契合的城市。
端木蕻良的个人气质有其矛盾之处。从家族传统而言,端木蕻良的父辈自有尚武的传统,且性情暴躁,曾祖父曹泰被家乡人称为“曹日老虎”,因为他打过“黄带子”(即清皇族),祖父曹履安因考试失败而气愤地踢翻了“赵大爷的供桌”,父亲曹仲元一生想做武官,独特的父系传统让端木蕻良的性格中有其豪爽不羁的一面。端木蕻良的母亲原是农家之女,被掳成妾,到了曹家经常受到欺凌,常常无缘无故地落泪,也多次把自己的苦痛讲给孩子们听,母亲独特的情感教育又赋予了端木蕻良敏感、忏悔的性情。从居住环境而言,端木蕻良的家乡虽处北国,却又有着南方的秀丽风光。“我家住的街叫‘杏花园胡同’,要在四月光景,向外望去,满眼都是杏花、梨花、樱桃花”[4]10而这样的故乡风情更是加强了端木蕻良性情的两面性,正如“性格的本质上有一种繁华的热情。这种繁华的热情对荒凉和空旷抗议起来,这样形成一种心灵的重压和性情的奔流。”[3]378如果说端木蕻良来桂之前的作品像北国的雪一样刚强暴烈扑打在人脸上,那端木蕻良在桂期间的创作更像是南方的雨,湿黏的浸在灵魂的深处。桂林,呼应着端木蕻良故乡的柔情的一面,将他的敏感、细腻铺展开来,使他的创作由外到内,开启了端木蕻良新的创作历程。
而桂林与端木蕻良家乡的文化内质相似,又进一步推动了端木蕻良创作风格的转变。地域文化一直是东北作家群的一个突出特色,但端木蕻良来到桂林之后,地域文化在端木蕻良的创作中有了明显的变化,地域文化不仅仅局限在了东北地域文化的表述上,他的着力点已经放在地域文化的深层意味上。粗旷的塞外东北与秀丽旖旎的桂林似乎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但是从文化的深层意味看,两者却有着共同的指向,即原始、异域及生命的张力。端木蕻良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鴜鹭树,这里除了主要的汉民外,还有蒙古人、少数的哥萨克和俄国的浪人等。昌图县是个多宗教的地区,满族人多信奉萨满教,而且端木蕻良的大舅就是萨满教的巫师,也就是跳大神的。受这种环境的影响,端木蕻良的小说也总是带几分不安与诡异。昌图地处塞外,较少的受到正统文化的影响。广西,自古就被称为蛮夷之地,而桂林独特的秀中带险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民间传说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野性与神秘这些都对端木蕻良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荒蛮的背后往往凸显着人的本质,人,这个复杂的动物在本真的自然中也有了本真的表现。东北与桂林,南北巨大差异背后的文化的同质,使得端木蕻良开始挖掘文化的底蕴与人的内心深层的东西。
[1]严家炎,范志红.小说艺术的多样开拓与探索——1937-1949年中短篇小说阅读琐记[J].文学评论,2001(1).
[2]祝宇红.“故”事如何“新”编[J].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3]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4]端木蕻良.化为桃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