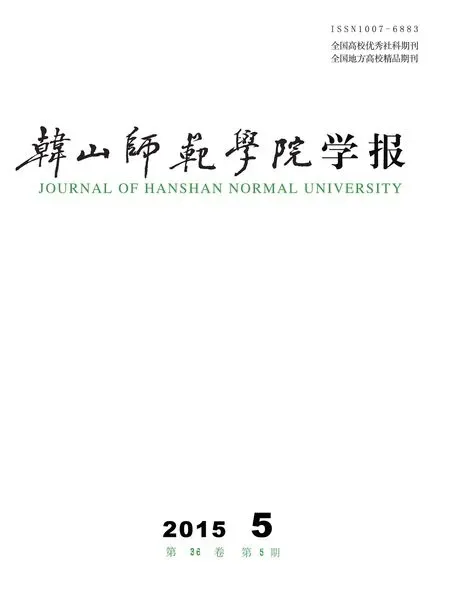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人的海上贸易
2015-03-27吴二持
吴二持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潮州 521041)
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人的海上贸易
吴二持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潮州 521041)
清以前潮商的海上贸易就有一定的基础。清初禁海时期,潮商的海上贸易活动也从未停止过。开放海禁后,起初官商先于民商而动,随后潮汕民间的海上贸易便迅速发展起来。清代潮商海上贸易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红头船,他们运用红头船在东南亚与国内各口岸间交叉穿梭进行循环贸易。清代潮商海上贸易的重头戏是中暹贸易。清代潮汕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埠市是庵埠与樟林。清代潮商的海上贸易有其独特的特点,他们敢于冒险,善于经营,多有神祇崇拜,并利用遍布各地的会馆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清代潮人的海上贸易形成潮汕商人独特的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汕由于有了这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兴盛,港口口岸经济崛起,成为潮汕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带动地域性的各行各业,尤其是各类手工业的发展,较大程度地扩展了潮人的生存空间。
清代;潮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贸易;循环贸易
一、清以前潮商的海上贸易基础
潮汕地区的海外商业贸易,早在唐宋已有肇端,至明代已颇为兴盛,相关的记载和研究也颇多。只是明王朝比较保守,实行海禁政策,故多以各国贡舶为名或走私而实施贸易。由于潮汕沿海地理位置的方便和优势,潮汕的南澳和柘林湾较早就曾以接济通番的形式与各国商船进行贸易往来。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因海禁渐弛,勾引番船,纷然往来海上,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或五十艘或百余艘,或群各党分泊各地。”①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接济,谓黠民窥其向导,载鱼米互相贸易,以赡彼日用。”[1]也就是说,因有各国番舶(商舶或贡舶)往来或停泊于潮汕的南澳或柘林湾等地,潮汕商人便抓住此时机,运载鱼米、蔬菜、淡水等食物与之相通,接济其生活日用之需,换取等值的洋货,顺便与之作货物贸易,这是潮汕商人与海外贸易较早的一种形式。外国商、贡舶在南澳等地能够得到较好的接济补给,乃至贸易,也多愿意停泊于此,或于此作逗留,因而南澳、柘林等地便逐渐成为明代潮汕海外贸易的重要地点。
潮汕沿海地区多以渔盐为业,善于驾舟是沿海人民的特点,且接济外国商船是个能获厚利的营生,于是便有更多沿海地区之民趋之,渐渐也就形成了一些较成型的商贸集团。这些集团实际上亦商亦寇,其首领大多为海上贸易者,亦是海寇的首领,如许栋、许朝光嘉靖三十四年(1555)经商日本,张琏、萧雪峰嘉靖三十九年(1560)经商闽粤、三佛齐,罗袍嘉靖年间经商闽粤沿海,林国显嘉靖四十二年(1563)经商厦门、南澳,林道乾嘉靖四十五年(1566)经商厦门、柬埔寨,杨四嘉靖四十五年(1566)经商海外,林凤隆庆二年(1568)经商台、澎,杨志隆庆五年(1571)经商海外,诸良宝万历元年(1573)经商南洋。[2]虽然朝廷对于海上贸易的禁令从没有停止过,但禁令颁久,渐渐便会执行不力,或官员利用以腐败谋私,便自然较为松弛;到情况恶化,重申禁令,加以整顿,又会较为紧束。如此循环往复。在海禁被严格执行的时候,一些习惯海商贸易的人,尤其是一些海上商贸集团,因处境艰难,便多流为寇盗,劫掠地方;还有一些外国海商集团,如日本的倭,流劫地方,成为当地人民之患。唐枢在《筹海图编》中曾说过:“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①唐枢:《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叙寇原》。“朝廷既视寇祸与互市而俱至,遂厉其禁,寇祸愈烈。”[3]谢杰在《虔台倭纂》中也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倭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越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满载而去。”②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也就是说,海禁越严厉,寇祸就越严重。终明一代,基本上都实行海禁政策,但基本上都禁而不绝。大多时候,海上贸易活动,贡舶贸易也好,走私贸易也好,都是相当活跃的。而海寇之祸,却也未曾断绝过。直到明末清初,一些海上寇盗集团(也是海商集团)在官府的强大军事剿捕和严控之下无法立足,则转而流动到东南亚各国,各自找寻落脚点建立其商贸经营和生活之据点,落籍东南亚各国。
上文这段关于潮汕明代商贸的概述,只是想说明几点:(1)潮人在明代已有许多与海外各国商人贸易的经历和实践,潮人的善经商已在此一时期表现得比较充分。(2)当国家贸易政策稍宽(弛海禁)之时,各国商舶纷至,贸易活跃,潮地商人也能得利,海寇(海商)多从商得利,沿海居民便少遭劫掠,则潮地人民也沾好处;海禁严厉,则事与愿违,刚好相反。(3)潮汕的海寇商人集团在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港和一些移民的落籍地点,都是清代及尔后潮商方便贸易之处,由此建立的贸易基点,是清代潮汕海外贸易的较好基础。
二、清代禁海与海禁初开时期潮人的海上贸易
清初为封锁海上的明郑集团,清廷实行极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凡官员民兵私自出海贸易,又迁移海岛居住耕作者,但以通贼论斩。”③《大清律例全纂》卷二十《兵律·关津节》。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潮汕商人也仍有往日本、东南亚等地贸易者。虽然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之下,潮汕商人的海上贸易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据日本的《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等相关文献记载,由于遇风漂流和受地方官员派遣,从康熙二年(1663)起,仍陆续有潮汕商船不断前往日本贸易。[4]以此推论,潮汕商船到潮人更熟悉更有基础的东南亚各国从事贸易,当也应该是有的。可见,潮汕商船的海上贸易活动,是从未停止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占据台湾的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清王朝完成全国统一的态势,海上已消除了反清力量,寇盗也基本上在此之前被剿灭或被迫留居海外,于是清廷便在次年(1684)宣布开放海禁“令广东、福建沿海民人,许用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④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二。虽然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实施了一定的控制和管理,规定“除夹带违禁货物照例治罪外,商民人等有愿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准其出入贸易”。⑤《大清会典》,引自饶宗颐总纂:《潮州志》第一册《大事志》,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出版,第328页。翌年(1685)清廷在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设置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及征收关税事务,潮州的庵埠总口为粤海关七大总口之一。⑥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二。
开放海禁政策的颁布给潮汕商贸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潮汕沿海商贸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澄海一带的港口,差不多形成潮汕对外贸易的中枢。潮汕“濒海居民,所恃以资生而为常业者,非商贩外洋,即渔盐本港”。⑦金廷烈:乾隆《澄海县志》卷十九《风俗》。开海对沿海善于经商的潮人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澄海县志》载:“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卒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①李之吉:嘉庆《澄海县志》卷八《埠市》。
在海禁严厉时期,如上文所说,仍有一些官员派出船只,前往日本、东南亚等地贸易。在开海初期,许多官员的船只便捷足先登,纷纷出洋贸易。屈大均《广东新语》曾有记载:“今之官于东粤者……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垄断网利。于是民之贾十三,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②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事语·贪吏》。这是当时的一个事实。海禁初开,民间创痍未复,民间商人一时尚须恢复元气、积聚力量,而官员则自有资本,可指使其“亲串”网罗商民,为之谋利,故在开禁之初,则官商多于民商。
三、红头船与清代潮人的海上循环贸易
随着开海后海上贸易的发展,潮汕民间的海上贸易也比较快速地发展起来,他们的海外商贸发展依靠的主要工具是木帆船,也即后来闻名遐迩的红头船。红头船原是清廷出于对出海民船进行统一管理而来的。雍正元年曾有令:“着将出海边船按次编号,船头桅杆油饰标记。”广东在东南,南方属火,为红色,故广东民船油红色,福建偏东,东方属木,故油绿色,各省不同,易于辨认。到后来因出海船只太多,这一管理手段实际上也难实施。而潮汕商人大约觉得这种颜色顺当吉祥,喜欢这种油饰,也就一直沿用,成为潮汕商船的一种标识。
这种潮汕商人赖以作为贸易工具的红头船,在清初开海之后迅速增加,其造船的木料多是从东南亚,尤其是暹罗(泰国)进口的楠木、柚木,在潮汕本地大量制造,稍后也有潮人在暹罗等地制造。由于暹罗大量出产造船所需的木材,其木材质量好,价格低,而暹罗又有较多的潮人移居,于是,红头船的造船基地逐渐转移至暹罗。相关资料显示,在暹罗曼谷,一艘重470吨的木船造价仅7400西班牙币,而在潮汕的樟林,造价则需16000西班牙币,价格要翻倍还多。[5]因此,到乾隆年间,不少潮汕人转移到暹罗去造船,潮商在当地购船后,同时办好货物,满载而归。③《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二八五。相关研究资料显示,清代潮州很大一部分红头船是在暹罗制造的。
潮汕商人利用木帆船这一交通工具,非常灵活地利用各地货物的特点和地域性差价,又利用海洋季风,行南走北,大量贩运南洋商品,同时运载本土出产的蔗糖、烟叶、葛布等货物,北上苏杭、上海、天津等地;又从京、津、苏、杭等地贩运北方的杂货、苏杭的丝绸返回;乘季风又装载诸如瓷器、石雕、丝织品、葛布、纸张及其他手工艺品经海南往暹罗、安南等东南亚各国,销售之后,又满载东南亚的蔗糖、大米、木材、香料、胡椒、象牙、檀香、苏木、沉香、药材等货物运回销往国内,形成循环贸易。而本地的手工艺品的带销,也是其中的重要项目,这也有力地促进了潮汕地方手工工艺行业的发展,如地方官蓝鼎元曾有过这样的描述:“闽广地少人稠,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者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银钱货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④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
潮汕商船海上贸易的突出特点,就是循环贸易。他们并不是单一的双向海外贸易,而是东南亚与国内各口岸交叉穿梭的循环贸易形式。每年春季,潮州商船装满潮糖、烟叶等潮地及梅汀赣等南方特产,乘季风经台、厦、闽、浙、宁、沪,至山东、天津等,沿途贩卖。到秋季又借助季风满载津门、山东的北方特色的杂货、农产品如色布、棉花、花生、大枣、大豆、药材等,返航经苏、淞、宁、沪,到处贩卖,又购进苏、淞等处的特产如丝织品、生丝、布帛等类,或回潮州或直接往海南等地,直到暹罗等东南亚港口,贸易之后再装载大米、药材、香料、木材、蔗糖等东南亚特产运回潮州。“一往一来,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①金廷烈:乾隆《澄海县志》卷十九《风俗》。海禁初开之时,还主要是在国内各港口贸易,所谓“止及苏、淞、乍浦、汀、赣、广、惠之间,到稍后则海邦遍历,而新加波、暹罗尤多,列肆而居”。②吴道镕:光绪《海阳县志》卷七。善驶木帆船的潮商,能够按季节借助季风,顺风行驶,省时省力。曾为潮地官员的蓝鼎元有过记载:“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弋)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6]53一次循环,或三几月,或一年半载不等,获利颇丰。著名的红头船故乡樟林,民间流传有民谣说:“洋船到,猪母生,鸟仔豆,带上棚;洋船沉,猪母晕,鸟仔豆,生枯蝇。”这是说,运气好,生意顺利,洋船平安返回,连家里的家畜、植物也一片生机。
四、中暹贸易:清代潮商海上贸易的重头戏
在潮商的贸易圈中,最为频繁、最为大量的是与暹罗贸易,进口的主要货物是大米、蔗糖、木材、象牙、香料和药材,出口的主要是瓷器、丝织品、生丝、葛布、纸张、铁器制品和各种工艺品。潮人早期移居东南亚,以暹罗为多,而且潮人在暹罗王朝也比较有地位,吞武里王朝的郑信王为潮人混血后裔,潮人也多与暹罗当地人有婚姻关系(多为女婿),因而潮商与暹罗贸易的优势也是有其历史机缘和人文背景的。况且,中暹贸易的互补性很强,暹罗向为大米出口国,而清代中国南方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粮食严重不足,米谷供不应求,在暹罗等东南亚国家进口大米,实为清代与东南亚贸易之大宗。康熙末年,闽粤两省米荒,朝廷甚为紧张,适有暹罗贡使说:“其地米甚饶裕,价钱也贱,二三钱即可买稻米一石。”③《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九八。朝廷当即要求暹罗官运30万石大米到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贩卖,同意给予免税优待。④《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九八。自此以后,也鼓励民间商人的中暹米谷贸易,并且特别地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在往后的岁月,这种优惠政策还不断加码。如雍正二年(1724),暹米运到,清廷特别令地方官按时价收买,不准行户任意压价,其船随带其他货物,也概免征税银。⑤《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二十五,卷六十六。雍正六年(1728)又重申:“米谷不必上税,著为例。”⑥《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二十五,卷六十六。乾隆六年(1741)广东巡抚王安国密谕海关监督“劝谕各商贩籴米谷发卖”,后奉旨免征税银,于是商民积极参与贩运米谷。[7]乾隆八年(1743)规定每船“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⑦《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二○○,卷二七五,卷二八五。十一年(1746)又规定载米不足五千石的,也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二。⑧《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二○○,卷二七五,卷二八五。当然,贩运大米,“向来获得甚微”⑨《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二○○,卷二七五,卷二八五。,而商人都是逐利的,潮汕商人尤其精明,他们以贩运大米作为合法途径,也同时运载其他货物,所谓“米不满五千,货可达数十万”,既从事朝廷鼓励的米谷贸易,又能使往返贸易有厚利可图,同时还可享受其他货物的免税或部分免税的待遇。这样,就使得潮商与暹罗贸易成为最频繁的热门线路。
潮汕与暹罗间的贸易繁荣,也不只是潮州的红头船在往来,暹罗方面也有不少的船只在进行着中暹贸易。暹罗是清代与中国通商最早的国家,顺治九年(1652),暹罗就已前来朝贡;康熙四年(1665),定下暹罗贡期三年一次;六年(1667)规定暹罗“贡道由广东”。[8]贡舶其实也就连带有商贸交易的成分。清初,借助中暹贸易的方便移居暹罗的潮人已经不少。暹罗那莱王朝时,已经有不少王族和高级官员拥有自己的贸易商船,从事中暹之间的帆船贸易,但多是委托或雇用潮汕商人进行实际操作,包括驾驶和水手等。潮州人实际上很大程度地参与了暹罗的航海贸易事业。据相关研究,那莱王曾建立一支拥有400艘商船以上的贸易船队,其所有船只差不多由华侨(多是广东潮州人)驾驶。[9]后来随着商贸活动的进一步扩展,暹罗民间参与中暹贸易的商船也不断增多,但仍然多是潮侨在经营。在中暹贸易的整个过程中,清廷对暹罗进口大米给予了非常优惠的待遇,暹罗方面对中国商人也从税收等方面加以优待。这就使其贸易发展有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潮商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除上述重点的与暹罗贸易之外,与其他各国家各港口的贸易也都比较频繁,如与安南(越南)、新加波、马来亚、吕宋等(这些国家同样居住有不少潮籍移民),像安南的商业贸易,几乎是潮汕人主导的,尤其是海舶贸易。
五、清代潮汕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埠市
清代潮汕对外贸易的港口,主要集中在韩江的出海口一带,最繁华的港口当数庵埠与樟林。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设立粤海关,庵埠成为粤海关七大总口之一,庵埠总口下设16个支口,为粤海关总共50个支口之冠。[10]可见潮汕当年海外贸易之兴盛。尤其是澄海一带,粤海关就设有五处税馆,计有南关口、南洋口、卡路口、东陇口、樟林口,清廷每年从此五处税馆所收税银,占全省总税收的近五分之一。[11]52于此可见,潮汕清代口岸经济的繁盛。庵埠港毗邻潮汕韩江、练江、榕江三江出海口之交汇处,又与四通八达的内河水路交通网络相通,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成为潮汕地区联结出海港口与内河各埠市码头之间的中转站,处于海外交通与潮汕内河交通的枢纽地位,粤海关的潮汕地区总口设于此地正是因为其地理位置与货物汇聚转输的原因。清代康乾盛世为庵埠港最繁华的时期,“地当海、澄交界,实海(阳)、潮(阳)、揭(阳)、澄(海)四县之通市,商贾辐辏”[12]834。潮汕沿海港口货物于此汇聚,潮汕各内河交通帆船也汇集于此贸易,梅、汀、赣地区的货物也总汇于此,通过沿海各港口输往南北各地与东南亚各国,故其成为内外交通之要港。在港内停泊上税的商船有往南北各地泛海的商船,也有各内河贸易货运的帆船。
樟林港原是一个渔业港,清初开海之后,就开始有商船从事海上贸易,康熙末年清廷决定从暹罗进口大米之后,商民纷纷扬帆出海,从事大米贩运,兼带其他货物贩卖,樟林港开始繁荣起来,并且迅速崛起。樟林港位于韩江与大海的汇合口,水深港阔,且与埠市连为一体,既有优越的港口条件,也有优良的口岸经济条件;既是中暹贸易的主要港口,也是潮人及客家人移民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始发港。在清代,樟林港成为潮汕海内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其于康熙后期兴起之后,繁荣时间跨越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个朝代,历百年有余,[11]105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港口。
海上贸易所带动的潮汕本地内河贸易也非常繁荣,乾隆《潮州府志》所记载潮汕各县沿江的埠市墟市,大县有近二十个,小县也有近十个,总共超过百个。[12]174-178这些埠市墟市当然多以附近乡村聚落居民赶集交易为主,但也都有商贾贸易和帆船转运贸易等,多数墟市也与沿海港口如庵埠、樟林等大港口埠市相通,货船往来,运载一些进口或出口商品。
六、清代潮商海上贸易的经营特点
清代潮商的海上贸易经营活动,总体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或者说体现出一定的文化精神,这些明显的特点或文化精神也许正是清代潮商海上贸易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一是敢于冒险。商船航行于海上,或则载有重货,或则携有重赀,时时处处都有两个方面的风险:人为的风险和自然的风险。前者为海上寇盗之行劫,后者为海上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各不同海域地理风貌隐藏之风险。尽管清代海盗较之明代已是大为减少,但终未完全灭绝;地理与自然气候之风险更是无时无之。即使是在海上贸易已经合法化的清代,清廷已经实施了对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域的控制,海盗的活动仍是官府之海防所难以完全控制的,或者说仍有些鞭长莫及,海上贸易仍有很大的被劫风险。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南澳外的海面上,就有三个小岛,常为海盗出没之地,“称为三澎,南风贼艘经由暂寄之所;内自黄岗、大澳而至澄海、放鸡、广澳、钱澳、靖海、赤澳,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潮郡贼艘出没之区。晨远飏于外洋以伺掠,夜西向于岛澳以偷泊,故海贼之尤甚者多潮产也。”①陈伦炯:《沿海形势录》,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这些海盗,规模不大,潜伏于汪洋,三五成群,或潜至港口附近,窥伺小艇,露刃行劫。在康熙年间,潮地海域海盗仍然猖獗,每年当“三四月东南风盛,粤中奸民哨聚驾驶,从南澳入闽,纵横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浯屿、料罗……而入于浙。八九月西北风起,则卷帆顺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粤……来岁二三月土婆涌起,南方不能容,则仍驾驶北上……”[6]197对此,敢于冒险的潮汕商人,或于航行中携带器械,与海盗相从事,或与海盗相联络,给以好处,求得相安无事。面对自然,更是惊心动魄,一艘商船,连同货物,所值是上万两至数万两白银,加上数十人至数百人的生命,航行于波涛险恶的茫茫大海之中,时刻都要面对狂风巨浪与海域不确定因素之风险,“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随时都有葬身鱼腹之危险。其冒险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而潮汕商人却能视之如常,安之若素,“冒险射利,视之如陆”,而且从业人数不断增加,可见其勇于冒险的精神品质。当然,其前提是利润丰厚,有利可图。
二是神祇崇拜。潮人的神祇崇拜历来是相当重视也比较广泛的,也不分什么儒释道,几乎是逢神便拜,各地区也还都有各自崇拜的神。潮汕商人的神祇崇拜,除了有同其他行业潮人一样的崇拜之外,这个群体尤以崇拜妈祖与关帝为甚。妈祖是传说中的海上保护神,水上操舟的人多得其庇佑,潮汕、闽南及台湾等地都有非常明显的妈祖崇拜风俗。实际上,这与上面所说的经商海上的各种风涛险恶的自然环境有关,大海的不确定因素和行舟海上的各种风险,促使人们须要寻求一定的心理安慰,乞求神祇庇佑的心理也尤为强烈,妈祖崇拜也就成为必然之首选。在潮汕各地,尤其是濒海地区,妈祖(天后)庙几乎无处不有,从地方志记载的一些建庙修庙碑记可看出潮人崇拜妈祖是出于乞求庇护的心理,如乾隆《揭阳县志》所载的《天后庙重建碑记》云:“揭地濒海,其土沮洳,近达漳泉,远通吴越,商舻贩舶,出入于巨浸中,每遇铁飓银涛,……则有颠覆之患。榜人睹帆樯欹仄,魂惊魄悸,辄呼号求于天,神必示灵,夜则火光烛天,冉冉而至,昼则江鸥先集,异香徐来,即安澜有庆,舟保无恙……”①刘业勤:乾隆《揭阳县志》卷八《艺文》。嘉庆《澄海县志》所载的《建南门外天后庙记》云:“粤于职方为南,澄又居粤之南……地滨大海,烟涛浩淼,水天弥茫。生斯土者,群以海为命,自富贾大商,以暨龙户渔人,咸于是托业焉。当风利潮高,扬帆飞渡,瞬息千里。操奇赢者,贸易数省,上溯津门,下通琼趾,布帛菽粟,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所恃以无恐,则天后实默佑之,故我乡之虔事天后也。”②李之吉:嘉庆《澄海县志》卷二十五《艺文》。潮汕商人正是从妈祖崇拜中吸取勇敢无畏的精神力量,同时也于虔祀妈祖能够获得庇佑的心理暗示之下,获得战胜海上狂涛、化险为夷的自信与自慰,从而勇于冒险海上,以海商为业。
潮商的关帝崇拜仅次于妈祖崇拜,关帝在潮州商人心目中不仅为财神,也是忠义、信义的化身。唐宋以降,潮人受儒家文化浸淫日深,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体现在潮商的道德价值观中,就是以忠义和信义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不仅仅是商人,潮人普遍都敬祀关帝,“潮汕地区从城市到农村到山区,关帝庙随处可见,数量甚多,前往关帝庙进香求平安赐福的海内外潮人,人数之多与崇拜妈祖不相上下”[13]。商业发达与商人聚居的地方更是如此,甚至各地的潮商集中活动的潮州会馆也多供有关帝神位,上香祭拜,甚是虔敬。这与潮商重信义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潮州商人所从事的海贩业,规模大,距离远,风险大,往往采取借贷经营或合伙经营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商业信用关系在潮州商人商业活动中具有关键地位,对于支持商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以‘信义’道德价值观强化商业信用关系。”[14]这样看来,潮商普遍的关帝崇拜就是其来有自、深具基础、势所必然的了。
三是善于经营。潮商的善于经营,表现在多个方面。善于驾舟,具有海上贸易的经验,这是基础;能够抓住异地贸易的差价,尽量利用各地往来的互补性进行兴贩贸易;能够灵活多变地抓住贸易的各种机遇,与很好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这也是其能够较大程度成功的条件。比如,海上贸易须借助季风,一旦错过季风时节,那就意味着须较长时间在异地逗留,这样不但增加成本、消耗时间,而且也许就错过另一次顺风行驶的方便和可能带来的利润。因而潮汕商人在贸易过程中时间观念极强,货到目的地,商人们便会抓紧时间,各自寻找买主,尽快出货,以利快速返航,赶上季风。有时为了迅速销售,往往需要灵活地运用低价批发甚至廉价抛售等手法,以快速销售来避免货物压冬所增加的成本利息,这样便形成“货如轮转”的经营效果。再如潮商所赖以海上贸易的红头船,在本地建造购买价钱太高,便有造船商人转移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建造,因其地盛产造船木材,成本相对低得多。而购船也会利用诸如泰国进口大米之类的优惠政策,在该地购船并备办货物(其中连带购运大米),满载货物以合法途径运回,以减少成本。
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潮汕商人多取合伙经营的模式,风险均担,经营的成功程度与船上每个人都有关联,从业人员之间不像西方国家的大公司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是富商巨贾与中小商人广泛合作的关系,构成了功能互补的商人群体。“富商巨贾,卒操奇赢”能够“握算持筹,居奇囤积”,①李书吉:嘉庆《澄海县志》卷八《都图·埠市附》。他们资本雄厚,既挟有巨资,又拥有大量巨舶,因而拥有出海贸易之主动权。但海上贸易带有巨大的风险,这类巨商往往不愿亲身历险,“危身以博阿堵之物”,便多取与中小商人合作,提供船只与放贷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而坐收巨额海商贸易利润;而中小商人,则会亲身历险,从事长途兴贩贸易,“其资本多仰给于富室,而为之四出经营,以分其息”。[15]在具体的各条商船中,船主、中小商人与水手形成利益相关的伙伴关系,船主从商业利润中按相应比例抽取商贩利润,水手的报酬则根据抽取利润的多寡进行分配,而且商船上的船长、司事、伙计和水手,都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本地特产或其他货物沿途销售,如商船载货7~8万担,“船长得200担,总管事100担,伙计2名各50担,其他人员每人7担”。[16]这就使整条商船的贸易与船上每个人的利益形成直接关系。这样,如果货物办得适销对路,中小商人甚至包括伙计、水手随船赚取丰厚利润,乃至发家致富,也都完全有可能,这样的例子甚多。这也就成为潮汕社会平民追求发家致富的梦想,由此也就激励着一代代的潮人加入海商贸易乃至水手之类海上生涯的行列。于是潮州的商人群体也就不断发展壮大。有学者曾作这样的描述:中国商人“没有正式的组织,完全是零细的个人照顾自己的小买卖。他们在中国各自向船东租借货轮,亲自押货到海外贸易。每一艘帆船就这样常运载了数以百计的小商人,仿佛是个百货公司一样,各人照顾自己的柜台。帆船一抵达港埠,这些商人就各自散开去寻找自己的主顾,化整为零。回船时商人们又各自找人办货,定期聚合搭船,化零为整。当时人形容中国海商的贸易是‘萍聚雾散’,莫可踪迹。”[17]
四是各地会馆纷立。潮商的经营特点虽是分散的,但潮商整体上是颇有凝聚力的,这从潮商遍布南北乃至东南亚各地的林立的会馆就可看出来。会馆为中国传统商人旅外的组织,多以地缘文化相连结,其功能除了同一地域商人互相聚会联络乡谊及接待、服务、救济等之外,主要是维护商人利益,争取商人权益。清代潮州的同乡会馆文化相当发达,大港口(如天津、上海、苏州)、省内各地及东南亚各地的潮州会馆(或者称闽粤会馆)均颇为发达成熟,在当地都是名声显赫的行会组织。“同乡会馆的建立纯粹是为了发展他们自己的贸易。在外地的同乡商人结成具有共同利益的会员关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免遭外地商人的竞争和官府的勒索。”[18]这是美国学者马士在《中国行会考》中对同乡会馆组织性质的描述,潮州会馆文化还远不止这些,潮州会馆还包括对内的仲裁、解决纠纷、救济等等的功能。有些会馆甚至还购有墓地,以备会员万一遭遇意外客死他乡之安息。总之,清代潮商的会馆文化已经相当成熟,表现出强烈的乡土文化意识和团体精神。
清代的潮汕,由于有了上述的海上贸易,港口口岸经济迅速崛起,形成了独特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商贾辐辏”的局面,这是潮汕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海内外贸易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地域性的各行各业,像渔盐业、各类手工业、农业乃至服务行业等。各行业依赖发达的海内外商贸,依赖海上丝绸之路,使其产品销路畅通,销量不断增大,其发展壮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手工业的带动发展就更直接,当时出口或外销较多的商品:黄糖、白糖、瓷器、铁锅、烟叶、葛布、潮绣及其他各种手工艺品等等,每一个品类都是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的结果,手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种种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从业人员,包括一些技艺人员,缓解了潮汕地区人口太过稠密、人多地少的逼仄的生存环境,较大程度地扩展了潮人的生存空间。
[1]郭春震.潮州府志:卷一·地理志[M].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3:20.
[2]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146,153.
[3]饶宗颐.潮州志(第三册):实业志(六)·商业[M].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1165.
[4]焦鹏.清初潮州的海上贸易[C]//黄挺.潮学研究:13.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67-97.
[5][泰]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泰国潮州人及其故乡潮汕地区研究报告[C]//汕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头船的故乡——樟林古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33.
[6]蓝鼎元.蓝鼎元论潮文集[M].郑焕隆,选注.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J].历史档案,1985(3):17-27.
[8]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古代下册[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815.
[9]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帆船在东南亚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J].历史研究,1956(8):1-21.
[10]叶显恩.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209.
[11]张映秋.潮汕澄海人移殖泰国的历史发展[M]//汕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头船的故乡——樟林古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
[12]周硕勋.潮州府志[M].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7.
[13]谢惠如.试论潮汕人之崇拜关羽[J].广东史志,1995(1/2):94-95.
[14]林济.潮商史略[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119.
[15]萧麟趾.普宁县志[M].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7:357.
[16]菲普斯.中国与东方贸易论述[C]//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54.
[17]张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纪华人在东南亚水域的贸易优势[C]//张炎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台北:中研院三研所,1988:345-368.
[18]马士.中国行会考[C]//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79.
Maritime Silk Road:Seaborne Trade of Chaoshan Merchants in Qing Dynasty
WU Er-chi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Seaborne trade of Chaoshan merchants had acquired something of a foundation before Qing Dynasty and had not come to a stop even during the“maritime-forbidden”period.After the ban was lifted,ma⁃rine trade developed rapidly.The main shipping vessels were Redtop Boats,going in trade cycles on the run of ports of Southeastern Asia and domestic ports,with the China-to-Thailand route as the leading trade.In Cha⁃oshan area,the major ports of that time were Anbu and Zhanglin.The features of Chaoshan merchants were dar⁃ing and adventurous,adept at economic operation,believing in gods-worship,making use of guilds in different places to protect their self-interest,thus forming the uniqu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ir own.Also,because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maritime trade,seaport economy emerged and developed to be the major impetu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putting in motion various trades,handicraft of all types in particular,expanding the living existence of Chaoshan inhabitants to a great extent.
Qing Dynasty;Chaoshan merchants;Maritime Silk Road;seaborne trade;trade cycles
F 752.9
:A
:1007-6883(2015)05-0047-08
责任编辑 黄部兵
2015-02-06
吴二持(1955-),男,广东揭西人,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