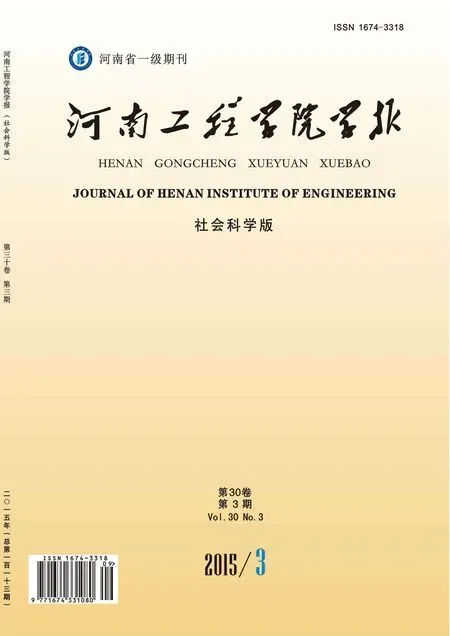狄奥尼索斯的主题学阐释
2015-03-27陶艳柯
陶艳柯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狄奥尼索斯的主题学阐释
陶艳柯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狄奥尼索斯是一个古老的神话原型。它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已有生命自由、迷狂、暴力等多方面的含义。现代文化视域中,德国早期浪漫派正式呼吁狄奥尼索斯的回归,关注其迷狂的一面;随后尼采将酒神精神发扬光大,为狄奥尼索斯在20世纪的复兴埋下了伏笔。尼采关注的更多的是狄奥尼索斯形象中受难、迷狂和生命自由等方面。尼采以降,众多理论家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着重凸显狄奥尼索斯形象中的迷狂、生命自由和暴力等方面。
狄奥尼索斯;生命自由;迷狂;暴力
酒神,又称狂欢或放荡之神,是人类在童年时代塑造的一个虚幻的神话形象,在很多古老文明中都存在。希腊人称其为狄奥尼索斯(Dionysos),罗马人称之为巴克斯(Bacchus),埃及也有类似的神祗,名为俄塞里斯(Osiris),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狄奥尼索斯。在西方漫长的文化进程中,狄奥尼索斯自古典时代起就一直备受青睐。不管是其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姿态的活跃,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在绘画和雕塑中独特魅力的呈现;无论是浪漫主义诗人们对之深切的呼唤,尼采对“酒神精神”的高扬,还是20世纪以来诸如戏剧、绘画、文学等诸多艺术领域对之的青睐有加,似乎都在印证着这样的逻辑:我们的时代离开生命的本原越远,艺术和诗歌就越坚决地渴求回到那里去,向往原始模型、榜样,向往藏在深处的不变的东西,[1]同时也充分彰显了其独一无二的魅力。
一
有关狄奥尼索斯的起源,众说纷纭,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根据历史学及考古学现有的研究,大致有“色雷斯—弗利亚说”“希腊本土说”等几种说法。由此可知其起源问题的复杂性。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亦保存了众多狄奥尼索斯出身的有关神话和其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就其出身问题,主要流行着两种相关的神话:一种是根据俄耳甫斯神话,狄奥尼索斯名为扎格列欧斯(Zagreus),是宙斯和珀耳塞福涅的儿子,因赫拉嫉妒被泰坦神撕成碎片并吞食,后被宙斯借塞墨勒将其复活。另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则认为,狄奥尼索斯是天神宙斯和凡人塞墨勒(底比斯国王卡德摩斯之女)所生的高于人的神,其具有人和神的双重血统。《荷马史诗》中记载 “塞墨勒生了人类的欢乐狄奥尼索斯”①引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56.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荷马史诗》中只是偶尔提到狄奥尼索斯。。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的《神谱》(Theogony)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卡德摩斯之女塞墨拉与宙斯恋爱结合,生下了一个出色的儿子,快乐的狄俄尼索斯。”[2]此外,狄奥尼索斯的诸多传奇经历也成为后世文艺创造的素材,古希腊罗马时期众多的文艺创作对此也都有反映。如希腊诗人诺努斯(Nonnus)的叙事史诗《狄奥尼西卡》(Dionysiaca)中载有狄奥尼索斯远征印度的故事,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刻画了狄奥尼索斯感谢弥达斯并赐予其点金术的故事,卡图卢斯(Catullus)的《歌集》64首中提及狄奥尼索斯拯救阿里阿德涅的故事,而最著名的莫过于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剧作《酒神巴克斯》(Bacchus)中记述的狄奥尼索斯惩罚彭透斯的故事。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狄奥尼索斯主要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作为树木、谷物等的丰收之神,生殖崇拜和欲望之神。与狄奥尼索斯作为生殖崇拜之神身份密切相关的即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其大约在公元前10至公元前9世纪时传入希腊并对古希腊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希腊人为祈祷和庆祝丰收,每年在播种和收获季节举行祭奠酒神的仪式。祭祀时,白天人们摆成行列举行浩大的游行,合唱颂歌;夜晚在荒野间饮酒沉醉,纵情狂欢。酒神祭典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所有参与者皆可打破禁忌,解除束缚,纵情狂欢。希腊人对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热情主要与他们对生命的挚爱有关。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狄奥尼索斯是感性的象征,代表着生命力、自由和放纵。早期的狄奥尼索斯作为一个神话原型蕴含着人类文化开始之初的集体无意识——生命力和自由,经过长时间的浸染形成人们对酒神的广泛认知,并在西方文化中得以显性传承。另一种是作为神秘崇拜的仪式之神。根据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古希腊罗马时期,除了在城邦中举行的大规模的狄奥尼索斯崇拜,在远离城邦的偏远地区,还盛行着狄奥尼索斯的神秘崇拜,主要有巴克斯秘仪、俄耳甫斯教和厄琉西斯秘仪。关于狄奥尼索斯的出生、死亡和在冥府中的传说,狄奥尼索斯祭祀中的迷狂状态,都在秘仪中得到借用和发挥。狄奥尼索斯崇拜从最初的表达生命自由逐渐发展为许诺未来幸福的宗教,狄奥尼索斯也逐渐含有更多的意义:灵魂不死,生命轮回。此后,狄奥尼索斯更成为一个集“生—死”“光明—黑暗”“欢乐—残暴”等矛盾对立于一体的极其复杂的双面之神。
狄奥尼索斯出现在秘仪中,与古希腊罗马人关注灵魂和来世、追求生命的动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狄奥尼索斯的神秘崇拜,对后世的宗教、哲学和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罗素就曾指出:“由于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便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神秘主义,它大大影响了许多哲学家,甚至对于基督教神学的形成也起了一部分的作用。”[3]然而恰恰是两者的这种关联,后来伴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对异教信仰之间的排斥和迫害,导致基督教与狄奥尼索斯秘密崇拜之间的争斗。在基督教兴起之初,狄奥尼索斯在秘教中常以反基督教的异教首领身份出现,是基督的强劲竞争对手。《马加比书》(Maccabees)中记载了狄奥尼索斯和基督的矛盾和对立:在塞硫古王安提阿古三世的迫害下,在庆祝狄奥尼索斯的节日里,犹太基督徒们被迫戴上用常春藤编的冠冕,在街上游行,并把荣耀归给狄奥尼索斯。*《马加比书》6.7.参见http://www.xiaodelan.com/BookInfo.asp?ID=10629,(2015.4.1)。基督教在历史进程中取得统治后很长的一段时期,狄奥尼索斯在秘教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后来随着基督教的深入发展并最终在社会文化各领域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与狄奥尼索斯有关的神话和秘仪开始消隐。在中世纪漫长的历史中,狄奥尼索斯一直处于隐匿的状态,且在这期间更多地成为酒的隐喻。
14世纪自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艺术家们摆脱了精神枷锁,重新重视并力图复兴被禁锢了一千多年的古典文化艺术。长期隐匿的狄奥尼索斯逃过了中世纪的漫漫黑夜,重现在人们的视域之中。这一时期狄奥尼索斯数量众多且形态各异,以泛滥之势出现在绘画和雕塑艺术中,表达着人们放纵享乐的激情,折射着人们对生命诗意的赞美和对彼岸世界无拘无束生活方式的憧憬。文艺复兴时期狄奥尼索斯虽延续了古典时代的特征,主要作为酒和生命力的象征,却也流露出朝世俗化方向嬗变的端倪。*这一时期酒神题材的作品关涉更多的是其形象而非其内涵,狄奥尼索斯显得既真实又轻浮。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画家达·芬奇(Da Vinci)的《巴克斯》和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的《众神的欢宴》,提香(Tiziano Vecellio)的《巴克斯和阿里阿德涅的见面》和《酒神节》,丁托列托(Tintoretto)富有抒情色彩的《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的婚礼》和德国画家亚琛(Hans von Aachen)的《巴克斯、刻瑞斯和爱情》等。此外,众多的雕塑作品也纷纷把酒神列为创作题材,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巴克科斯》和桑索维诺(Sansovino)的《巴克科斯像》等。雕塑中酒神形象的塑造主要是用来表达对人的力量、形体和人的身体美的赞扬,再现人的情貌风范。随后的巴洛克艺术中,酒神及其神话仍更多地出现在绘画中。与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的是,酒神特征进一步世俗化,更像一个普通人而不是神。到了启蒙时代,整个西方世界从思想精神到宗教信仰,无一不服从于理性。“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4]理性主义至上使感性和个体自由受到压制,西方文明整体进入“祛神话”的阶段,神话走向衰落,狄奥尼索斯也随之失去了立足之地。
二
启蒙之后,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重新重视狄奥尼索斯,发掘其迷狂的精神气质并正式呼吁其回归。但在早期浪漫派之前,德国已有着悠久的狄奥尼索斯传统,如温克尔曼(Winckelmann)第一个以美学的形式定义了狄奥尼索斯精神,他在《古代艺术史》中尝试回到古希腊以发掘艺术及其内部精神,把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同时并立为“理想美”的两种最高类型。之后,赫尔德把狄奥尼索斯看作一种新的诗性灵感的象征,并以之为名提出诗歌创作的非理性迷狂观,在德国文学史上首次对文学的创作动机做了情感心理学的阐释。新古典主义诗人席勒也对狄奥尼索斯倾注了非凡的热情。他热衷于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题材进行创作,他反对近代基督教一神论,崇仰古希腊多神论的杰出诗篇《希腊的群神》(1788年)和《酒神颂歌》(1796年)中都提及狄奥尼索斯。席勒返回希腊找到狄奥尼索斯神,热烈讴歌和缅怀古希腊的艺术和文化,主要是为了展现对美和艺术的执着追求,表达自己对艺术美和功用的看法:只有古希腊的艺术才是真正美的艺术,只有美和艺术才能使大自然和人保持生气和完整,使世上的一切永垂不朽。浪漫派哲学代言人谢林也对狄奥尼索斯深深迷恋,这与他对神话的重视有关。谢林认为,“整个神话历程无非是要以感官化的图像来为狄奥尼索斯的降生这一宗教性事件做准备”[5]379。在后期谈论狄奥尼索斯神话的关键文本《天启神学》和《神话哲学》中,他将狄奥尼索斯精神与基督精神浪漫合一,将狄奥尼索斯当作“将来的”能带来解放的神。早期浪漫派诗歌先驱荷尔德林(Holderlin)也对狄奥尼索斯神情有独钟,他同样将狄奥尼索斯看作一位将来的共同体之神。在荷尔德林看来,狄奥尼索斯的到来是一个事件,并且这一事件定会在未来的现实中发生。
深受谢林和荷尔德林的影响,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对狄奥尼索斯推崇备至。浪漫派先驱热烈赞颂狄奥尼索斯,主要与他们对现代危机的思考有关,具体来说,与他们对诗歌的重视和新神话的祈盼有关。基督教的式微造成人们信仰的缺失,神话的消隐和诸神的逃逸给现代人精神带来了危机。浪漫派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神话,向人们提供精神超越的力量。他们返回希腊找到了狄奥尼索斯,将其视为一个基督一样的将在未来归来之神。诺瓦利斯不仅在《基督教或欧洲》中引入狄奥尼索斯的寓言,让救世主“像人类中间的一位真正的守护神变为本乡的……像作为面饼面和葡萄酒给人吃喝,作为爱人被人拥抱,作为空气被人呼吸,作为言语和歌曲被人倾听……”[6]以此来阐述他“迷狂、爱—死”的概念和“与自然合一”的观点,还在《夜颂》中以诗性灵感的形式将狄奥尼索斯与基督教因素结合起来。把狄奥尼索斯看作和基督一样的将归来之神。总体来看,浪漫派对狄奥尼索斯情有独钟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狄奥尼索斯从其诞生之初就象征着生命力、迷狂和丰盈。浪漫派返回希腊寻得狄奥尼索斯体现了浪漫派诗人们最强烈的感情:他们渴望实现自身内在的无穷的创造力。在施莱格尔看来,狄奥尼索斯神即是“不死的快乐”“神奇的充盈”和“自然的丰沛”。另一方面,狄奥尼索斯神是一个著名的“两面之神”。他调和了“生—死”“光明—黑暗”“欢乐—暴力”等方面的对立,兼具双面的特征。在浪漫派的经验中,生与死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恰是狄奥尼索斯可将这种对立性保持悬置,统一在自身之中。在思想史中,德国早期浪漫派消解了狄奥尼索斯作为酒神的传统的身份,使其变成一种抽象的精神、一个迷狂的隐喻,并将其作为一个将来之神在20世纪正式登场。总之,早期浪漫派重视诗歌和神话,他们试图用浪漫的诗来克服人性异化,建立已失落的人与精神之间的关联,重新寻回如古希腊人与自然和神灵间那样无拘无束的关系。狄奥尼索斯神体现着浪漫派对现实的否定、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祈盼。
在晚期浪漫派传统中,酒神形象则更多具有否定性的意蕴,其功能主要是消解神话,摧毁道德和社会秩序,这与其在早期浪漫派那里使世界浪漫地新生或诗化的作用截然不同。[7]在海涅的作品中这一点尤其明显。与早期浪漫派用狄奥尼索斯的寓言描述基督,以表达宗教和诗歌、古希腊诸神和基督的联合不同,海涅将基督和狄奥尼索斯分为敌对的两方。海涅在诗歌《流亡中的众神》中描绘了基督教一统天下后希腊罗马众神遭受的巨变。酒神巴库斯和自己的随从西勒诺斯隐匿了真实的身份,分别化身为修道院的院长和教士,隐姓埋名悄悄地生活在人间,只在每年的秋分时节才到湖边隐秘的山林中参加狂欢聚会。海涅笔下,酒神主要是以“感官逸乐的救世主”和“神圣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的。
受浪漫派的启发,哲学狂人尼采也关注并思考了狄奥尼索斯。与早期浪漫派异曲同工,尼采对狄奥尼索斯的关注亦与其对现代性的思考相关。与早期浪漫派创立新神话的目标和关注狄奥尼索斯的迷狂本性不同的是,尼采的思考更加深入。费尔曼在《生命哲学》中曾指出,尼采超越于浪漫主义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单纯的艺术角度而是从更为原本的生命角度来透视科学的。在尼采这里,狄奥尼索斯是被借用来说明艺术的起源、本质作用及人生关系的一个象征,形象复杂,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具有受难,迷狂、生命自由等多面的含义。一方面,在其早期作品《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狄奥尼索斯看作受苦受难的象征,但又没有简单地将狄奥尼索斯及其崇拜视为一种原始的神话和仪式,而是将之提升到一种哲学和精神的高度给予心理学的分析,赋予其形而上的意义。尼采认为,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是发生于梦中和迷狂状态的心理—生理现象,是艺术冲动的二元对立。在尼采看来,狄奥尼索斯是一种原始的迷狂体验:“……我们就瞥见了酒神的本质,把它比拟为醉乃是最贴切的……或者由于在春日熠熠照临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酒神的激情就苏醒了,随着这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8]91狄奥尼索斯的本质在于个体化界限的消除,“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自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8]92尼采以古希腊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艺术的起源、本质和作用,并赞颂以酒神精神为根基的审美悲剧,与他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及对理性的批判相关。尼采谴责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性哲学扼杀了希腊人的艺术本能——包括酒神冲动和日神冲动,批判整个理性主义文明,谴责科学精神和理性知识对悲剧的戕害,冀图在现代理性的包围中复苏酒神精神,重振悲剧艺术,呼唤新的富有创造力的德意志精神的新生。另一方面,尼采将狄奥尼索斯及其精神的颂扬看作对生命的颂扬。尼采认为,狄奥尼索斯崇拜是一种肯定生命的形式,“酒神祭之作为一种满溢的生命感和力感,在其中连痛苦也起着兴奋剂的作用,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9]。狄奥尼索斯是“对生命的宗教肯定,对整个未被否定和拆半的生命的宗教肯定”[10]373。尼采将象征着永恒的创造和破坏、万古长流的生命意志看作世界的本质和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本能,把对生命的肯定当成人生的根本意义。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基督教批判之上,自然也就有了狄奥尼索斯和基督的对立。实际上,两者的对立在晚期浪漫派那里已经初露端倪,但尼采将狄奥尼索斯的“叛逆”精神演绎到极致,将之彻底转变为“反对十字架上的人”:“狄奥尼索斯反对‘受难的基督’,于是你们就有了对立。这不是殉道方面的差别——这只是说明同种事物有不同的含义。生命本身,它永恒的富蕴和生命轮回,决定了苦痛、破坏和毁灭意志……十字架上的上帝乃是对生命的诅咒,他指点人们要从生命中拯救自身——剁成碎块的狄奥尼索斯乃是对生命的许诺:他永远新生:由毁灭中再生。”[10]374尼采认为,基督教文化是一种与狄奥尼索斯精神敌对的颓废文化,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及道德观是新时代人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总之,狄奥尼索斯在尼采这里处于彻底的狂欢状态,他不仅反理性,还反基督教,彻底成为生命自由的呐喊者和代言人。在此意义上,西方文化史中可以说正是尼采使狄奥尼索斯得以不折不扣地重新回归,不仅将其形象中的叛逆因素演绎得淋漓尽致,还将狄奥尼索斯精神发扬光大,成为审美生存的一种象征。*值得一提的是,从早期浪漫派到尼采,关于狄奥尼索斯的演绎值得注意的有两点:首先,和基督的关联。透过现代视域中众多哲人对神话和宗教关注的表象,他们更深层思考的落脚点是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关注。其次,狄奥尼索斯的回归凸显着这样一个转向:他已不再仅仅预示着是一个酒神、仪式崇拜之神,而且其形象中所蕴含的深层的抽象的隐喻意义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三
经过尼采的努力,狄奥尼索斯声名鹊起,之后的整个20世纪,狄奥尼索斯都受到极大的关注。在创作领域,和狄奥尼索斯相关的创作题材得到广泛的运用。*第一,歌剧方面,德国创作者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采用“戏中串戏”的序幕形式创作了传奇小歌剧《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Ariadne auf Naxos, 1912),法国米约创作了独幕五场微型法国歌剧《阿里阿德涅被弃》(The Desertion of Ariadne,1928),意大利先锋歌剧家盖迪尼创作了歌剧《酒神》,德国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策(Hans Werner Henze)创作了歌剧《巴萨里茨》(The Bassarids,1965),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创作了影响巨大的歌剧《69年的狄奥尼索斯》。第二,绘画方面,西班牙印象派大师毕加索创作了《酒神祭》(Bacchanale,195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画作《捕金枪鱼》主要以狄奥尼索斯为背景,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吕佩兹(Markus Lupertz)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了《酒神颂歌》等系列作品。第三,文学方面,法国文学及哲学家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enne)创作了《致死的狄奥尼索斯》(Dionysos slain,1977)。在研究领域,20世纪初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罗德(Erwin Rohde)、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道兹(Eric R.Dodds)、奥托(Walter F.Otto)等,主要是从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和神学等方面来研究狄奥尼索斯和希腊文明之间的关系,狄奥尼索斯和古希腊悲剧的关系,狄奥尼索斯和其他神之间的关系。[11]20世纪中期以后,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J-P.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在《众神飞扬——古希腊诸神的起源》《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和《神话与政治之间》等一系列著作中,都有提到狄奥尼索斯。“法国结构主义学派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加深了对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研究,认为在整个古希腊宗教体系中,狄奥尼索斯崇拜是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中心因素而存在的,它在许多方面都构成了对奥林匹斯宗教的反面,但正是这种反面凸现了古希腊宗教多维度的思想体系。韦尔南强调狄奥尼索斯的‘面对面’的特点,认为人们通过‘面对面’的魔力,通过他诱人的目光,进入到他的掌握之中,凭借‘最大范围的支配性在场,模糊了种种界线’。 ”[12]也对狄奥尼索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一学派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加深了对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研究。尼采以降在各个不同的地域和文化氛围中,学者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对狄奥尼索斯主题的每一阐释都呈现出独特意义。总的来看,尼采以降对狄奥尼索斯的研究大体上呈现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迷狂的狄奥尼索斯。迷狂曾被作为狄奥尼索斯神一种肯定性的气质在通往浪漫派新神话的路途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狄奥尼索斯仍是作为一个将来之神出现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笔下的。布洛赫对狄奥尼索斯的钟情,与其对文明的忧虑和构建乌托邦的理想密不可分。在《乌托邦的精神》一书题为《社会主义的概念》一节中,布洛赫强调:欧洲文明即将永远死去,是因为欧洲资产阶级没有很好地继承西方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根据布洛赫的观点,正是浪漫主义不切实际,摈弃了基督,麻木不仁,没有热情,失去普世精神并丧失了灵魂才招致西方的没落和文明的萎缩。对于如何才能拯救欧洲、拯救人类,布洛赫提出,唯一方式是唤醒我们内在的乌托邦精神。在何处寻得“乌托邦精神”?布洛赫认为,“乌托邦精神”存在于人类的文化之中。“他几乎翻遍人类历史文化的各个角落——从犹太神秘主义派别卡巴拉到佛罗利斯的约阿西姆(Joach in diFiore,12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从基督教到诺斯替教,从康德、黑格尔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找其中隐藏的‘乌托邦精神’。”[12]他认为,这里才是“文化遗产”概念的本源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依靠希望和乌托邦精神,乌托邦是有待实现的希望,是推动自然和历史的永恒动力,希望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人类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不该丢弃它,否则人类将会灭亡。恰在此意义上,布洛赫强调了宗教对于人类的不可或缺性和弥赛亚的重要性,提出“对于救世主弥赛亚必将降临的信念是关乎人间和天堂的思想精华,借助于他,不仅人间,而且天堂也不会糟了”[13]。尽管布洛赫实际上并不认同“有神论”,但他努力继承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内容,勾画了未来“宗教无神论”的图景:上帝并不存在,但上帝将存在。对于布洛赫来说,无神论是宗教乌托邦的前提,宗教乌托邦是乌托邦的一种,宗教乌托邦是一种希望。而狄奥尼索斯之于布洛赫,如弥赛亚一样,是一个将来之神,是未来的希望。“这一希望首先将狄奥尼索斯神引入心中,不论这希望在过去200年里以新神话的方式在哪里表达自身。在所有的古典神灵中只有狄奥尼索斯,因为他是‘将来之神’,最容易与犹太——基督教文化中的弥赛亚期望相和解、类比。布洛赫的整部著作也都寄托在这样一种文化上。”[5]45
第二,生命自由的狄奥尼索斯。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这一时期的狄奥尼索斯沾染并流露出浓郁的时代气息。狄奥尼索斯及其精神的风靡和当时各种此起彼伏运动的盛行、自由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彰显了人类追逐自由的努力。*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狄奥尼索斯被先锋艺术家们演变成一个反抗者,获得了更多世俗的含义,用以表达当代人的思绪和情感。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作是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69年的狄奥尼索斯》。这部剧作是根据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巴克斯》改编而成,于1968年第一次演出, 随后《69年的狄奥尼索斯》一书出版,并在1970年被著名导演布莱恩·德·帕尔玛(Brian De Palma)改编为电影《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在剧中表现为试图为自己建立崇拜的嬉皮士,是一个自由、无序、混乱的化身和代表。为让彭透斯认可自己的神性和建立自己的崇拜,狄奥尼索斯宣传性解放、性自由、同性恋的理念。谢克纳将《酒神巴克斯》改编成为闹剧并对之做了一种与社会和政治相关的极端激进的诠释。 这部具有激进色彩的戏剧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中非理性情绪的盛行,将性与灵魂自由从传统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倾向,同时也表达了对人们具有的过度的宗教般狂热的激情蔓延的忧虑。谢克纳对狄奥尼索斯持一种指责的态度,他认为,狄奥尼索斯的原则和脾性对公共道德、城市和国家的秩序是一种危险和灾难。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狄奥尼索斯及其相关的神话在美国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狄奥尼索斯及其精神更多地成为一种隐喻和概念化的象征。诺曼·布朗(Norman O.Brown)和马尔库塞是狄奥尼索斯及其精神的坚决支持者。布朗将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视作希腊遗赠给人们的超自然能力的隐喻,是肉体欢乐、性和狂欢本能的象征。狄奥尼索斯“不是梦,而是酒醉的;不是远处的带着面纱的生命而是完整的现世的生命”[14]。狄奥尼索斯象征着生命自由,可以废除压抑,使人的身体从压抑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布朗对狄奥尼索斯及其精神的关注和赞扬与其对文明及个体生存现状的忧思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20世纪重要的精神分析学者,布朗对人类的文明及其主要成果持否定的态度,对现代社会充满着失望与不满。他认为,人是一种受压抑的动物,受压抑的爱欲是人类据以创造历史的动力。布朗努力探索未来的出路,呼唤一种自由的、无压抑的生活,呼唤爱欲的解放。和布朗不约而同,同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马尔库塞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思索之后,也同样提出了爱欲解放论和“非压抑性生存”的概念。在马尔库塞看来,爱欲是“使生命体进入更大的统一体,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努力”[15],是人的本质。但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展开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当代工业社会的集权统治和工具理性泛滥,导致当代社会的单向度性。个体也在社会中遭遇异化并失去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单向度的人”。在马尔库塞看来,在单向度的社会中,阿波罗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而狄奥尼索斯精神正在慢慢消逝,人的本质——爱欲受到压抑,肉体的解放与感性的胜利成为永远的梦幻,人们完全丧失了区分梦幻与现实的能力。因此,他认为,解放爱欲、消除异化,实现向人本质的复归是必要的。他将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爱欲解放论和“非压抑性文明”的构想,作为医治西方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痼疾和病态文明的良方。诺曼·布朗和马尔库塞对爱欲的呼唤,既是对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呼唤,亦是对自由生命价值的高扬。
第三,死亡和暴力的化身。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对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巴克斯》进行了重新解读,他更多关注的是狄奥尼索斯崇拜中的暴力和谋杀,将其蕴含的消极意义演绎到极致,狄奥尼索斯最终成了死亡和暴力的代言人:“暴力是酒神最合适的本性。他的所有属性都与暴力相关。如果他和预言启示(如阿波罗在俄狄浦斯神话中扮演的角色一样)的天赋有关,这是因为先知的灵感是祭祀危机的一部分……在《酒神巴克斯》中,祭祀危机带来灾难性后果之后,这个神显现了,这一象征的出现是由彭透斯破毁的宫殿来印证的。”[16]基拉尔把欧里庇得斯的文本视为“迫害”文本,将酒神神话的主题解读为“暴力”,与其对文明和文化的重大假设相关:模仿欲望和替罪羊机制。具体说来,人类相互模仿竞争消除了差异,趋向追求统一的欲望,共同希望得到同一物体。这必然使相互之间产生激烈的竞争和冲突,进而导致暴力的产生,威胁团体和社会的团结,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所有人团结起来找出一个所谓的“罪犯”(一个人或一个部落)即“替罪羊”,来承担这场冲突的责任。基拉尔试图发掘的是原始社会创建的神圣的暴力起源。根据基拉尔的观点,各个社会保留的仪式性质的节日中都存在着僭越、违反和亵渎,这种违背常规的种种行为和表现只是为了消除差异,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暴力和冲突,而酒神崇拜仪式恰是一个重要的典型。
[1]〔苏〕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扎通斯基.论现代派文学[M].杨宗建,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0.
[2]〔古希腊〕赫西俄德.神谱[M].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9.
[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7.
[4]〔德〕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
[5]〔德〕弗兰克.浪漫派的将来之神——新神话讲稿[M].李双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德〕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M].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13-214.
[7]刘小枫.尼采与古典传统[M].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89.
[8]〔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101.
[10]〔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11]魏凤莲.狄奥尼索斯崇拜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4.
[12]夏凡.从文化遗产到文化生产:布洛赫文化哲学刍议[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1):141-146.
[13]梦海.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J].哲学动态,2005(12):13-18.
[14]〔美〕诺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M].冯川,伍厚恺,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54.
[15]〔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63.
[16] GIRARD R.Violence and the sacred[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133.
The Thematology Interpretation of Dionysus
TAO Yanke
(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Dionysus is the prototype of ancient myth. It often has the meaning of liberty, ecstasy, violence and others. In modern cultural horizon, German romantic poets called for the regression of Dionysus and payed attention to the ecstasy character of dionysus; Then Nietzsche carried forward the dionysian spirit, preparing for the revival of Dionysus in the 20th century, Nietzsche concerned more about Dionysus′ suffering, ecstasy, Liberty, etc. After Nietzsche, though the starting points of many theorists were different, the characters of ecstasy, liberty and violence were highlighted.
Dionysus; liberty; ecstasy; violence
2015-04-21
陶艳柯(1985-),女,河南漯河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3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
I545.077
A
1674-3318(2015)03-005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