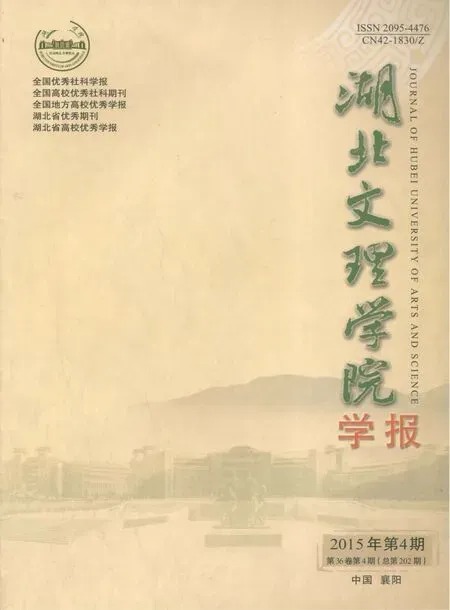米芾“集古字”与“二王”摹本的关系及意义
2015-03-27
米芾“集古字”与“二王”摹本的关系及意义

杨豪良
(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摘要:虽然米芾在“集古字”的过程中转益多师,但总的来说,米芾“集古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32岁之前是“广泛集古”阶段,其后进入“定向集古”阶段,并开辟了一种新的“临古—集古—通变”的学习方式,即“以我为主学古人”。米芾“集古字”有三个层次的意义,其一是集“字”,其二是集“方法”,其三是集“文化”。而“定向集古”阶段的主要取法对象是“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在此过程中,米芾“集古字”不仅促进了“二王”法帖的鉴藏、摹刻与传播,也保证了“二王”法脉的传承,对其后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米芾;集古字;王羲之;王献之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1]米芾自言“集古字”,表明其学书在传统上下了很大功夫,这是其独步书坛的基础。并且,他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史称“二王”)作品的喜爱和深入研究的方法与结果,也深深影响了其后书法史的发展,试述之。
一、米芾“集古字”的本质
细观米芾的学书过程,可以寻绎其转益多师的依据:“余初学颜,七八岁也……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锺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2]米芾在这段自叙文中,共提到向十一位书法家学习,用了三个“久之”,说明其临习时间之长,这和米芾自称“集古字”的学习方式是相吻合的,再加上米芾学“二王”等书法家,可以说他取法的对象远不止十一人。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1)临帖需持久不懈;(2)临帖要不断上追古人,追根溯源;(3)临帖应转益多师。
米芾为什么会不断改换门庭,其主要原因是书法审美的模糊性与个性化特征,即审美倾向、个性特征、心理品质,而这三方面又是统一在一处的。米芾最初的“集古”是出于对书法的一种“懵懂”之爱,而唐代书法作品是他最容易得到的范本,所以他勤学唐代碑帖顺理成章,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广泛集古”阶段。米芾三十二岁那年在黄州见到苏轼之后,真正进入到“二王”世界,进入“定向集古”阶段,并开辟了一种新的“临古—集古—通变”的学习方式,即“以我为主学古人”。“以我为主学古人”是“集古字”的高级阶段,它不是米芾的发明,但在米芾这里得到了强化。“米元章临右军《玉润帖》后米友仁跋云:‘此帖先臣芾手临,盖中年写也。笔笔取似,无少异。’”[3]由此可见,米芾从中年后开始“刻意求似”地临摹古帖,而“中年以后”当指米芾三十二岁之后。这种“笔笔取似”表明了米芾“几可乱真”的临写手法,也道出了“二王”书法对米芾产生非常深刻和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并且,米芾对“二王”的取法不仅在于“形”似,更求其“神”似。
米芾学习古人书法,善于在“发现或批评古人不足的同时取诸长处,从而将颜书的开张、柳书的紧结与骨力、欧书的奇崛、褚书用笔的自然多变了然于心、形之于手,以丰富自己的艺术创造”[4],同时对“二王”父子的內擫与外拓之法拿为己用,这些也成为米芾刷字的技法基础。梁敏认为:“对于米芾来说,双钩勾勒是一个强化对前人作品细节处的精熟理解和准确记忆的过程……创作时可以将头脑中储存的前人作品、摹本的细节加以运用,达到将古人书法之细节集中在一起自由组合、自由发挥的目的。所谓‘集古字’,其真意即在于此。”[5]此说法有其道理,我们可以想见,米芾通过双钩法进行复印式地“摹”学古人法而求点画细节之精准,获取对古人书法、技法、技巧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将多种技法烂熟于心而化为己用,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是集“方法”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米芾的“八面出锋”实际上是米芾善用侧锋和喜爱书写过程中的丰富变化,正如《翰林粹言》所讲“侧锋取妍,此钟、王不传之秘。”[6]这也是米芾“刷字”和“八面出锋”的核心所在。
很显然,米芾“集古字”在追求“不知以何为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自身的书法审美特征。归结起来有四:(1)唯美——强调空间造型;(2)多变——追求用笔的过程之变;(3)意趣——由唐入晋而显现振迅天真意趣;(4)求异——“刷字”之法明显地体现出米字区别于其他书法家的独特性。反过来讲,这些审美特征又成为其集古字的选择依归。“刷字”是米芾书法的典型特征,但并不是说在其书写过程中每一笔都是“刷”出来的,很多时候他还是守着许多传统的技法完成其书法创作的,惟其如此,才能够映衬出其“刷字”的独特性。米芾的“集古”与“出古”其实是“以古为新”的一种理念和身体力行,“不知以何为祖”恰恰表现出熔铸百家后自我面貌的确立,其笔下字既有出处又有己意。
米芾“集古字”告诉我们,学书法而能有大成者,需有天赋、韧性、学养,此三者少其一则不行。而“集古字”的文化学意义则在于其集古“法”以及“法与意”的辩证统一。所以,米芾的集古字有三个层次的意义,其一是集“字”,其二是集“方法”,其三是集“文化”。集“字”是对取法对象的基本认知和字形结构等的接受、吸收等;集“方法”是与古人、与同时代人的技法砥砺,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技法和方法论,比如米芾的“刷字”;集“文化”就是将书法文化梳理提炼而形成自己的认知和理论观点,比如米芾的《书史》、《海岳名言》等,而米芾在传统书法文化中接受信息最多的对象当是褚遂良和“二王”父子,并且其书法得力于“二王”的经典作品,其书法鉴定得力于他对褚遂良的认同和学习。一定意义上讲,只有用批评的眼光去选择传统才是对传统的真正继承,这也是米氏“集古字”的精神实质。
二、米芾“集古字”与“二王”摹本的关系及意义
“集古字”选准取法对象非常重要,米芾三十二岁后由唐入晋,主要学习了“二王”,尤其是取法了王献之,便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1.米芾对“二王”法帖的鉴藏、临摹与传播
米芾1082年在黄州见到苏东坡之后,才把学习的目光集中到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也正是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了有意识地“集古字”,《方圆庵记》是其窥魏晋门径的最初见证。米芾书写《方圆庵记》的时间是1083年,也只是他见到苏东坡之后用心于“二王”法帖的一年之后,很显然,米芾曾在《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中折射出米芾的悟性与天赋。米芾一生极喜《兰亭序》唐临摹本,经他记录、题跋过的《兰亭序》临摹本有多本。米芾曾有《褚临黄绢本兰亭序跋赞》称,他对“右唐中书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临晋右将军王羲之兰亭宴集序”曾“审定真迹秘玩”[7]30。米芾对不同摹本的《兰亭序》用功之勤勉与精准,由此也略见一斑。
十卷本《宝晋斋法帖》中收录了大量王羲之作品,只是第六、七卷所收录的均是王献之的作品,但并不影响米芾对王献之的追慕,“诚然,米芾不怀疑“二王”父子在书法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二王”相较,他更偏爱王献之。他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可‘神助留为万世法’,而更认为王献之的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因而他对王献之法书的临学,也花了更多的功夫。”[4]米芾之所以更加偏爱王献之的作品,还因为羲献父子书法的不同之处:(1)王献之书法骨力不及其父,而媚趣过之;(2)王献之书法用笔多为外拓法,王羲之的书法用笔多为内擫法;(3)王献之创行草,弥补了王羲之书法在这方面的缺憾。明代丰坊《书诀》云:“右军用笔内擫,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子敬用笔外拓,侧锋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8]在宋四家中,对于米芾而言,书法是排在第一位的,既是他的寄托,也是成就其“颠”名的法宝,米芾的“书”名与其“颠”名相关联,米芾“颠”的原因基本上有三个方面:(1)“出身冗浊”的心理隐痛;(2)“标新立异”的个性追求;(3)“以书立身”的文化表现。这些使得米芾“颠——书”成为一种同构,也表现在他对取法对象的选择上,他在中年以后更多地钟情王献之书法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王献之有冲出其父旧规的勇气和书法中的超逸奔放之姿,这些合乎米芾的“脾胃”。米芾书法追求得趣,这也与王献之的“媚趣”相一致。虽说“在东晋末年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里,在实用书写便利和形态流美方面,王献之书法要比王羲之的影响大得多”[9],但实际上是,米芾之后才有了王献之的真正书名,“米芾率意自然的审美,使他在“二王”之间更倾向于王献之,他以为:‘子敬真超逸,岂父可比也!’实践中,他对“二王”尤其是王献之的作品用功精勤,持之以恒……米芾对于王献之的书法继承,绝不是照本临摹,他的临书作品很少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而是有所取舍,朝着自己的审美方向去努力,通过临摹‘寄兴’、‘取其意气’,表现自己的真实面目。米芾的行草造诣尤高,淋漓痛快,隽雅奇变,得王献之笔意最多。”[10]“尤其值得称道的《张季明帖》、《李太师帖》、《临沂使君帖》等又更进一步,化用了王献之的很多笔法……充分展现其‘八面出锋’的用笔技巧。”[10]米芾“更倾向于王献之”与“有所取舍”恰恰是他“以我为主学古人”选择性集古字的表现。米芾的“一笔书”具有新意,蘸上一笔墨后连续书写数字而保持笔锋不散,笔力不败,墨色层次丰富多变,《虹县诗帖》把这一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这种“一笔书”是米芾对王献之书法的创造性吸收。米芾对王献之书风的继承与发扬,保证了王献之的书法史地位。实际上,作为被真正鉴定后的“二王”作品的大规模流传始于米芾。从此,书法史上的米芾与羲献父子便融在了一起。
2.“二王”刻帖与摹本保证了“二王”法脉的传承
当失去了“二王”作品真迹的时候,摹本就成为研究的最好范本,当然“摹本”也有高下之分,越是接近真迹的摹本则越有价值。而从流传下来的这些刻帖或者摹本来看,米芾的贡献是无人替代的。因为过去印刷技术的局限,复制书画的途径就是临写或摹拓。
米芾曾称王羲之两件作品为“天下第一法书”,一件是《兰亭序》,另一件是《王略帖》。米芾尤其推重《王略帖》,并说“吾阅书一世,老矣,信天下第一帖也。”[7]31《王略帖》堪称米芾“宝晋斋”中珍贵秘玩宝物之一,米芾在得到《王略帖》之后曾作《王略帖跋》,紧接着又作《王略帖跋赞》,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整个《宝晋斋法帖》中共有四个《王略帖》,第一卷有两个,第三卷有一个,第九卷有一个,并且这四个《王略帖》是四个不同的版本,“所以,不管至今流传的版本是否是米芾的临本,可以肯定的说,从米芾所临摹过的作品表格中也可以看出,米芾肯定学过而且临过《王略帖》,并且临摹水平非常高,几欲与原帖真假难辨。”[11]实际上,在《宝晋斋法帖》中,所收录的王羲之作品,除了第一卷的《王略帖》之外,还有第二卷的《兰亭序》、定武本《兰亭序》、《乐毅论》、《黄庭经》;第三卷中的《范新妇帖》等二十二件法帖;第四卷中的《十七帖》;第五卷中的《得告帖》;以及米芾所临写的王羲之作品,米芾所临王羲之的作品保留最多的就是在《宝晋斋法帖》中,这些对王羲之书法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流传至今的“二王”法帖几乎没有墨迹本,即便是《快雪时晴帖》仍然有人怀疑是唐代摹本,其他基本上是刻帖或摹刻。米芾在《海岳名言》中云:“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12]按照米芾说法,只有学习真迹,才能领略书家真正的精髓,而米芾却将所藏晋帖刻石,“《宝晋斋法帖》为崇宁三年(1104年),米芾任无为军时将平生所藏晋帖刻石于官廨中。南宋时,刻石已残,当时的无为太守葛祜之根据拓本重刻;后曹之格通判无为,复加摹刻,并增入家藏晋帖与米帖多种,汇为十卷。米芾所临摹王羲之《王略帖》就是曹之格后来增补的。”[5]
正因为米芾长于收藏和精于临摹,素有“善于伪作”之名,并且米芾的“伪作”与原帖相差无几,足以乱真,“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皱纸,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13]974“余临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废帖装背,以与沈括。一日林希会章惇、张询及余于甘露寺净名斋,各处书画,至此帖,余大惊曰:‘此芾书也。’沈悖然曰:‘某家所收久矣,岂是君书?’芾笑曰:‘岂有变主不得认物耶!’”[13]971米芾并非刻意作伪者,但他对古人法帖的精准临摹的确为其“作伪”提供了技法保证,从而在他的“集古”之路上留下了不少被疑为“二王”作品的“伪作”。而实际上这些“伪作”却对我们研究“二王”书法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也为后人学习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因为米芾在集古的过程中“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14]“米元章有嗜古书画之癖,每见他人所藏,临写逼真。”[15]这些均表明了米芾临写水平之高和对古书画佳品的钟爱,当然米芾的收藏目的并不是为了“作伪”和通过收藏挣钱,而是为了学习,正如米友仁所言:“先臣芾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笔临学之。”[16]
由上述可知,米芾“集古字”的态度与方式已成为后人学习书法的一种有益参照。并且,米芾“集古字”不仅促进了“二王”法帖的鉴藏、摹刻与传播,也保证了“二王”法脉的传承,对其后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宗霍.书林藻鉴:第9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35.
[2]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172.
[3]岳珂.宝真斋法书赞[G]//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1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303.
[4]傅合远.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米芾书法美学思想略论[J].山东社会科学,2012(10):30-35.
[5]梁敏.米芾“集古字”辨析[J].中国书法,2012(7):183.
[6]漆剑影,潘晓晨.中国历代书法名句简明辞典[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6:280.
[7]水赉佑.米芾书法史料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8]丰坊.书诀[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08.
[9]王世国.“二王”书法比较[N].书法导报,2013-08-07(23).
[10]丁二留.略谈米芾对王献之书风的继承[N].书法报,2014-02-12(25).
[11]刘艺铭.米芾集古论[D].济南:山东大学,2008.
[12]米芾.海岳名言[G]//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4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976.
[13]米芾.书史[G]//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4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14]中央文史研究馆.谈艺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169.
[15]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一)[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2:29.
[16]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米元章临右军四帖[G]//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2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303.
(责任编辑:刘应竹)
Significanc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Mi Fu’s
“Jiguzi” and Wang Xizhi and Wang Xianzhi’s Facsimile
YANG Haoliang
(Fine arts College,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441053, China)
Abstract:Mi Fu learned from other masters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Jiguzi”, which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wo periods: broad sucking before he was 32 years old, then “directional Jigu”, opening a new learning style of “copy -accumulation-transformation”, that is, learning from the ancients based on self-centered style. Mi Fu’s “Jiguzi” conveyed three meanings: first, the character itself; second, the method; third, the culture. The object for the “directional Jigu” is the calligraphy in Wei-Jin Dynasty, represented by Wang Xizhi and Wang Xianzhi. Mi Fu’s “Jiguzi” promoted the collection, carving and the wide spread of writing scripts of “Two Wangs”, and ensured the inheritance of Two Wangs’ calligraphy styles, which produc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Key words:Mi Fu; Jiguzi; Wang Xizhi; Wang Xianzhi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5)04-0015-04
作者简介:杨豪良(1968— ),男,湖北宜城人,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书法学。
收稿日期:2015-01-15;
修订日期:2015-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