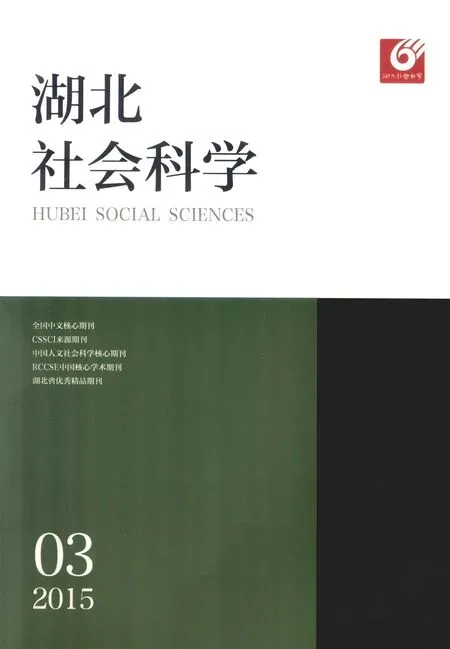从关联期待看拒绝言语行为的解译
2015-03-26芦丽婷
芦丽婷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一、引言
关联理论是由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一书中系统地提出来的,用来阐述人类交际的“内在机制”(Sperber&Wilson,1986/95:32)。[2]从此,关联理论在西方语言学和语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持续的关注。Sperber和Wilson认为,语言交际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负责接受语言刺激信号的单位首先接收了语言信号,然后把它们传递到中心系统,再由中心系统进行运算和破译。所以,语言交际并非简单的“编码—解码”过程,而是一个寻找关联的“明示—推理”过程。意义的理解也不仅仅是对语言符号的解码,而是对发话人的明示意图和交际意图进行辨认。[3]
本文所观察和描写的客体是拒绝言语行为(Refusal Speech Act),是一种强语境下的言语行为。它是指说话者对交际对象的邀请、请求、建议、给予等表达拒绝意图的言语行为。它是交际中威胁面子的一种言语行为,为了使拒绝达到让双方都满意的效果,除了语言的交涉,还可以恰当使用缓和气氛和调节拒绝行为的各种辅助策略。人们使用的拒绝策略往往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策略的综合,“拒绝”这种威胁面子的行为由于其表达的复杂性,使得受话人在解译这些迂回曲折的“拒绝”时必然要下一番功夫。本文试从关联理论中“关联期待”的始发、改变、取消、重生以至最终“期待”得到满足或被放弃的整个过程,结合汉英语料,来描写“拒绝”话语如何得解,语用推理如何完结,拒绝策略为何多样。
本研究所采集到的语料分为两组,第一组来自汉英两个版本“语篇补全测试”的问卷调查,第二组则来源于汉英各5部职场剧目,其出品年份均为2010年以后,这样的选择既保证了语料的新鲜度,也保证了某些语用习惯和社会习惯符合现代人特点。收集到的样本,根据统计学“分组比例抽样”的原则进行抽样。最后两组数据合计,本研究中“职业交往中的拒绝”语料,汉语共780份,英文共780份。
二、关联期待在拒绝语用推理中的作用
交际关联理论中最关键的概念就是最佳关联性,听话人所有的推理都在假设话语具有最佳关联性的基础上展开,它是听话人推理的主要依据,对它展开的一系列的理解过程是关联运作机制的关键。[2](p607-632)认为在话语解读过程中,需要按可及性的顺序检验解读假设,且当“关联期待”得到满足时,停止推理。
关联期待是关联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明示意图与交际意图在关联期待的制约下相互调节。[3](p719-22)关联期待产生于所有话语处理的最初阶段,它包括对于说话人有信息传递的意图的期待、对说话人意图传递的信息与某话题相关的期待和对说话人意图传递信息的具体内容的期待。[4]
其中,最宏观的是第一种期待,它不涉及任何方向性,仅仅是对接下来的话语的一种不具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期待;比如,在办公室里,老板突然叫了一声小张的名字“张百胜!”,此时小张便会对其老板接下来的话语产生关联期待,但此时的期待仅仅是小张对老板接下来有意图传递的一种期待,不涉及内容。
第二种期待比第一种具体一些,听话人对说话人的话题有预先的信息期待,所以听话人的大脑中已经激活了某些关于这个话题的相关语境信息,这些语境信息会使话语的推理变得省力;如,最近部门为了接下一个大单子,一直忙于各种公关工作,此时员工A对员工B说:“对了,那个单子的负责人是谁?”这里,A说的“那个单子”,B能够在不费努力的前提下很轻松地从高可及的语境范围内找出“那个单子”的指称。
最后一种期待是最具体的一种关联期待,它不但对说话人的语境信息有所期待,而且对具体的话题也有预先期待,此处的关联期待已经满足了量的需求,融入了关联内容和关联方向的期待。本研究中的拒绝语料,如果未使用迂回手段而是直接拒绝的话,大多数是这种关联期待的体现。比如,老板要员工加班、同事请求帮忙或员工要求加工资等等,在听话人回答之前,提出要求的一方就已经将语用推理的方向锁定在“同意还是拒绝”的选择上了。
其实,关联期待并非仅仅产生在语用解读之前,也不是在整个话语释义过程中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产生期待到满足期待,它在整个过程中都可能产生变化,且这些变化相互关联,上述三种类型的期待可能出现在话语释义过程的任何阶段,并且可以互相转化。这些期待内部的内容调整或类型转化都能影响到认知效果和对话语的处理、理解。如:
[1]总编:只要你从现在起,决定不要孩子了,……,我调你去法国总部工作一年,行不行?(《辣妈正传》)
李木子:可我还是更想要孩子。
[2]李木子:我得赶紧回家一趟,那个选题策划会,你先帮我管一下,我,我一个小时就回来。(《辣妈正传》)
夏冰:策划会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3]李斯特:装修方案和报价,搬家时间表和流程,这些东西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啊?(《杜拉拉升职记》)
玫瑰:其实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要动个小手术。
首先,最初的关联期待应该产生于拒绝者说话之前,被拒绝者在以上三例中,都期待“同意或不同意”的答案,这会使得被拒绝者提前为话语推理预设一定的认知语境范围,当接受到对方的信息之后,预设范围内的语境假设具有较高的语境可及度,接着便会在预设的认知语境内进行一系列的充实命题、分配指称、消解歧义等显义生成过程及推导隐含结论所需的隐含前提的确定,从而指向对方是否同意的方向。
在例[1]中,“我”和“孩子”这两个词的指称在预先设定的认知语境范围内很容易得解,“还是更想要孩子”也很容易被“决定不要孩子了……调你去法国……”的语境补足,其命题充实后,得出的话语显义是“选择孩子,放弃法国工作”,这直接满足了被拒绝者对拒绝者所传递信息的具体内容的期待,期待得到满足后,语用推理结束,且在这个答语中,关联期待单纯而未经改变。
例[2]很好的阐明了关联期待的动态性。这一例中答语里“策划会”“我”等的指称分配也依然很明确,其命题上的充实也可以在预知的语境范围内得以进行,然而,预先设定的“同不同意”的推导方向却无法获得明示,于是最初的关联期待被搁浅,推理由最初的具体内容期待转换成对说话人意图传递的信息与另一个话题相关联的期待。话语的显义激活了如下的语境假设:
“第一天上班,不可能熟悉新会议的流程和内容”
“不熟悉就会需要时间学习和了解”+“离会议开始还有半个小时”
结论:“时间不够,无法学习”
最后根据推导,得出认知效果“夏冰无法担此大任”,满足了对话题相关性期待的解读,并且上述推理直接否定了“夏冰是否同意”的先决条件,成为初始关联期待被取消的原因,也满足了被调整以后的期待,推理结束。
例[3]的解读更为复杂,李斯特在听到玫瑰的答语之后将话语放在预设语境范围内,准备生成显义的过程中就遇到了麻烦,在“装修工作”的语境中,并不存在“身体”和“手术”的指称,要理解玫瑰的话语,初始期待必须被暂时搁置,需要在话题相关期待的预设语境中找到关联,然而,玫瑰的答案里没有跟“装修工作”相关的任何信息,该重期待再次被搁置,此时对说话人意图或传达信息的大致方向都必须进行调整,这时只剩下对最宽泛的交际意图的期待。其实,剧中玫瑰在话语表述的同时,递上了一份体检报告,此时环境起到了作用,该信息在“递报告”“面色蜡黄”等非言语交际的语境中更具有优先权,玫瑰的意图是传达这个新信息而非讨论上述旧信息,所以无法对李斯特的话题给出反馈,这就是两重上级期待被取消的原因,此时,推理也终止了。玫瑰更为关注的是个人健康,而非工作,从而也表达了委婉的拒绝。
以上三例可以表明,解译拒绝时,大多数情况下,关联期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满足,满足调整后的期待是关联期待动态性的体现,拒绝话语无论间接与否,信息传递和对方在理解的过程中,随着被满足的关联期待与初始期待间的差距越大,推理方向和初始期待方向的偏差也会越大,听话人所付出的努力也就越大。如果产生于语言处理前的关联期待较为具体,语用解读就只限于对该具体期待的满足;在推理的过程中受到解码顺序和受话人显性认知语境交互的影响,当最初的关联期待产生的显义或被解码出来的显义能满足该期待时,拒绝话语得解,推理结束;当关联期待在其生成的语境中无法被满足时,为了使得推理正常进行,原期待只能被暂时搁置,等待后续话语中来带的新语境和新信息,或者是通过对期待的调整引起受话人显性认知语境的改变,经过调整以后的期待需要在重新调整后的语境中去寻求满足的契机,若在此处能生成满足该期待的显义,又能解释上级期待为何取消,则话语得到了解读,推理工作完毕,若仍无法满足,则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满足。
三、语用解读的终止与关联期待
在表达“拒绝”的初始阶段,被拒绝一方的语用推理就开始进行了。随着语用推理的继续,关联期待的性质会转换或发生内容增生,最终,关联期待被满足或是被放弃,推理结束。
(一)语用推理终止于关联期待的满足。
改变受话人的认知语境是交际的目的之一,人的大脑中储存的语境假设数量庞大、结构复杂,如果不加限制,通过话语本身与语境假设结合产生的认知效果有可能会过于膨胀和无法控制,在实际话语解码的过程中,关联理论认为语用推理的目标是用最小的认知努力来获取最足够的认知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要关联期待获得了满足,语用推理就必须终止。然而,理想的模式不是总有发生,在表达拒绝的话语中,如果拒绝的直接性高,比如说话人直接说出“不行”“不可以”“No”这样带有否定含义的词汇或相应的表达,期待的满足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很多情况下,语用推理结束时所得的认知效果都并没有完全满足或根本不满足最初的期待。关注语用推理在拒绝言语行为中的应用,必须以关联期待的动态变化为理论基础。要获得这种动态性的期待满足,受话人必然要下一番功夫。
[4]Gaby:up?
Job agency lady:No,…(《绝望的主妇》)
[5]Job agency lady:You have experience with children.I have a job at a day care center.
Gaby:And deal with other people’s kids?I don’t even like my own.(《绝望的主妇》)
[6](调查问卷第十题“接替工作Taking over other’s job”)
Your reply:I have been working for like 14 days without any break at all!
以上三例,是关联期待被满足导致推理结束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静态满足。例[4]中,Gaby提出自己的薪酬应该上涨,在工作人员给出回答之前,Gaby已然已经预设好了关联期待,而且该期待固定而明确,在整个话语理解过程中也并未出现性质和层级上的改变,由于工作人员的正面直接拒绝正符合其期待,所以该例子体现的是最简单的语用推理过程。
第二种,单向动态满足。例[5]中,Gaby的拒绝话语无法通过直接的语用推理得出解答。这是由于受话人在提出建议以后,最初的期待是Gaby的答语限定在“做或不做这份工作,或者至少给出与“这份工作”相关的信息。然而当Gaby一开口,受话人就不得不将关联期待沿着某单一方向做调整,此处,关联期待被调整为跟“deal with other people’s kids”这样的具体信息相关,具体化的期待叠加到原有期待之上,称之为期待的内容增生,这种额外的期待随着强语境的植入“I don’t even like my own”,让受话者的认知语境控制在关于孩子的解读上,了解到Gaby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喜欢,“even”在这里是一个有标的用词,可以推导“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人,更不会爱其他人的孩子”这一结论,从而丰富了受话者对于Gaby给出的关于孩子的新信息的认知,最终得出的话语解读是“不希望从事和孩子有关的工作”,这个解读既满足了最初的期待,也满足了被具体化以后的期待,推理终止。
第三种,曲折动态满足。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话语解读过程。职业交往中,无论是汉语还是英文,人们往往对上下级的敏感程度都略高于日常生活,在发生拒绝这样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时会分外小心而采取更为曲折的方式,这对于解读话语的人而言,语用推理的过程会变得比较复杂,此时在语用推理过程中期待会发生层级调整,推理结束时得出的认知效果是一种满足综合变化后的关联期待。如例[6]中的受试,当被要求接手他人工作时,受试表明自己已连续工作多日。当受话人接收到这个信息时,发现该信息并不满足他最初的具体期待,即回答与“工作”、“生病员工”和“是否同意”有关。然而,受试的回答生成的显义无法与语境匹配,也就是说受试“连续工作”和预设的推理方向“生病员工”等无法产生联系,受到语境的限制,原期待不得不取消,连带其推理方向也被阻止继续。进而,受话人根据省力原则,在话语产生的场合、非言语交际行为(如对方表情和手势等)和个人认知体系中寻找足够相关的解释,发现当“连续工作14天”和“忙、累”这一语境假设的可及度比较高,作为隐含前提被临时调用,所以该受试的话语能够找到具有关联的解释。其实,推理并未终止,因为,想要满足该关联期待,受试本可以说“不”来表达拒绝,既然舍易取难,必然有其原因,于是,受话人的期待又动态演变到下一层级,并使得其期待增加了新的内容:找出不直接拒绝的原因。即,用表述自己对公司的贡献作为理由,削弱了拒绝本身的直接度和不礼貌程度,也表达了加班的辛苦和些许不满情绪。自此,语用解读满足了语境和话语内容下的动态关联期待,各层期待均被满足,从而初始期待也不言自明,推理完成。
(二)语用推理终止于关联期待的放弃。
关联期待的放弃,常常被认为是话语理解失败的结果。然而我们发现,在释义拒绝的过程中,预设语境范围内或与语境相关联的推理方向上体验不到相关的语境效果是常态,这种情况下,推理经常会被取消,但这并不是推理失败的标志,而是为了实现对拒绝的解译而扩大语境范围和泛化推理方向,来生成新的期待。关联理论本身是承认语境有大有小的,熊学亮[5](p1-6)认为在小语境内(如语句提供的信息)不相关的信息在大语境内(如百科知识介入)可以相关,在原有语境中不相关联的信息在扩展了的语境中可以关联。也就是说,语境的延伸和扩展是随需要可以实现的。
在对拒绝语料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当受话人对于对方的信息传递意图有了关联期待,而话语的实际内容却无法和受话人脑中的任何可及语境假设产生关联从而达到足够的认知效果时,受话人有两种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被迫放弃推理,二是可以通过将对该话语的解读留在短期记忆内,等待接下来的交际提供合适的语境假设时,再来进行二次解读。如:
[7]Bree:…Some Salmon en croute or perhaps some cog au vin?(《绝望的主妇》)
Vitale:Got anything I can pronounce?
[8](调查问卷第4题“送礼”)
您的回答:我的妻子是位非常严厉的母亲,上次儿子成绩没考好,闹着要去动物园,我偷偷给带去了,回家就挨了批评。这东西带回去,老婆还不把我给剐了。我有时太宠小孩了,应该检讨,老婆是对的。所以我从不会送孩子这么贵的礼物。
在例[7]中,Bree提供关于宴会餐点的建议,客户Vitale是受话人,他对于Bree的餐点安排是有宏观期待的,然而,出身上层社会的Bree脱口而出的法语菜名让Vitale无所适从,他无法将该信息与脑中的旧有知识和语境假设做出关联,虽然语境明确,上下文清楚,但该信息无法达到足够使受话人顺利推理的认知效果,Vitale只有被迫放弃推理,通过打断Bree的话来拒绝并重新发问,要求获取足够关联的新信息,寄希望于新信息能够产生恰当的认知效果,挽救放弃推理带来的交际失败。
例[8]问卷中的受试,为了拒绝下属的送礼,可谓并不轻松。首先讲了一个略显得没头没尾的故事,无法为现有语境产出相关的认知效果,听者的关联期待仅仅在最宏观的一个节点上等候“接受或不接受礼物”。所以,此故事一出,必然会让受话人的期待落空,从而只能停止该期待。由于在可及性高的语境中无法产生与“妻子”“动物园”等所指相匹配的认知效果,该受话人也无法改变期待和推理方向。此时唯一能做的,便是静候接下来的话述是否能扩大语境的可及度。接着,受试用到了“这东西带回去,老婆还不把我给剐了”这样半开玩笑的语用策略,使得听者的初始期待重新得以显现:
“带孩子去动物园就会挨批评”
“替孩子接受贵重礼物更会挨批评”
“接受了礼物等于宠坏了孩子”
“所以,拒绝收礼”
其实,一般情况下,受话人发现期待需要被迫放弃时,往往会尽量延缓这个过程,为的是将交际损失减到最少,而在这个拖延的时间内语境可及范围会变大,在新范围内如果能找到与话语结合产生足够量的认知语境假设,话语依然能得解。这里的受试并未用到明确的“不”字,而用了一则小故事,委婉地表达了拒绝的含义,对方在释话的过程中,随着关联期待的产生,停顿,重新获得,推理结束,也渐渐能明白拒绝者的良苦用心。这样的拒绝,既不太伤害对方颜面,也给自己留下台阶和树立了形象,是职业交往中常用的一种拒绝模式。而解读这个拒绝的过程,看似是期待的放弃,其实只不过是期待的暂停。
四、关联理论下的拒绝言语行为的多样化
在不同场合下,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是使用语言还是保持沉默,又或是使用非语言,如肢体语言来达到交际的目的。实际上,语言的使用是一种交际的选择,这种选择包括语音、语义、句法、词法和句子结构等、。而做出相应的语言选择并不是随机的,为了使得交际顺利进行,语言选择背后有着许多的因素如语境、对象、文化制约等。
根据关联原则,话语的理解过程是在一系列的语境假设中做出选择,语境有大有小,既能指通识和百科知识,也包括长时记忆、短时记忆、文化背景、词汇形式等等。解译话语的关键是在可及度较高的语境假设中寻找关联信息,可及度越高,解译所需要的努力就越小,话语就更容易理解,反之,可及度低的语境,解译所需要的花费就更大,理解可能更费周折。
当拒绝者听到一个请求、邀请等时,他/她将自己要表达的信息进行“明示化”给受话人,分别明示其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由于受话人是发语者,所以自然会在初始阶段生成关联期待,并使用其逻辑思维、百科知识和词汇语法解码知识来创造一个语境假设,或是当一个语境假设不够足量认知效果时,创造一个系列的语境假设,接着从这一个系列的语境假设中寻找具有最佳关联的假设,来解译该“明示话语”,得出被拒绝的结论。其实,拒绝者的话语表达过程和受话者的语用推理过程是同时进行的,拒绝者表达拒绝含义时也受到语境假设和诸多其它因素的影响,反应出来的拒绝策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策略的综合使用。想要理解这个拒绝的真实含义,需要从一系列的语境假设中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在双方的认知环境中既省力又是最佳关联。在一种文化里,人们对于最佳关联的选择可能在另一种文化里是根本说不通的,或者说在一种文化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行语用推理在另一种文化里需要更加费力才能搭建起关联桥梁。
语境假设本身是多样的,是具有个体差异的,对于个体而言,随着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性特征和所处环境的不同,其认知能力和语境假设的范围体系也有所不同,特别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生、成长、受教育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对于最佳关联的选择必然是不同的,思维推理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相同场景下表达拒绝,他们的言语选择和策略选择也是不同的。例如:
[9](问卷调查第6题“邀请做讲座”)
您的回应:我这何德何能啊,还为你们部门的人做培训,况且你那个部门的一些业务我也不是特别的懂,当然没有你那么专业了。
[10] (问卷调查第6题“邀请做讲座Inviting you to do a lecture”)
Your reply: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packed at the moment.It sounds very interesting,though.Have you asked…?She may be available.
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样的拒绝场景中,语言的选择不仅仅限于词汇、语法、句法等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由于认知背景和语境假设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策略。因而,在解译拒绝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不同的语用推理过程。
就本研究中的语料样本来看,职业交往中的拒绝往往采取更为委婉的间接语用策略来实施,这也要求听者付出额外的努力才能顺利释话。“只要言者以最佳关联性为交际目标,就有理由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是为了驱使听者去寻求更多的语境效果,以此来补偿为这类话语所付出的代价。”[8](p9-16)
例[9]中,受试的回答使用了“自我嘲讽”的语用策略,该策略使得听者无法从当下情景中寻找关联来满足自己的原始关联期待“是否同意”,于是促使听者调用上层语境里中国人传统的“自谦”实则表示“推脱”的认知概念,从而拒绝得解。美国文化崇尚独立和个性,例[10]中的受试希望自己的时间和自由不被束缚,因而用完全关乎自身的理由来拒绝对方,是可及性很高的强语境,受话人只要听到这句,便可以顺利推导出拒绝的含义。而接下来这位受试还使用了另一条语用策略“提供它法”来降低自己起初拒绝时的强势语气。试想,若是美国人听到例[9]中的拒绝,由于无法适应“自谦”这样的东方高权势文化,没有相应的认知背景和语境假设,必然会在语用推理过程中不断推翻之前的关联期待,关联期待则得不到满足,从而给理解造成困难,即使反复生成关联之后最后拒绝得解,也由于不理解该策略使用的目的而危害了其面子,引起交际不愉快甚至是交际失败。同样,若是中国人听到例[10]这样的拒绝,虽然下一番功夫也能理解其明示的拒绝意图,然而必定会危害交际本身的意图,即人际关系的维护。
五、结语
拒绝,特别是职场中的拒绝,是一种极具面子侵害的言语行为,为了保证交际顺利达成,拒绝者会采用各种形式的间接语用策略来完成拒绝。而对于被拒绝者来说,解译这些纷繁复杂的间接策略,是需要预设期待、关联期待、并随着期待的取消重置和认知语境的改变来调整期待,动态性地过渡到另一个层次或另一个性质的期待,最终使得各层次上的期待被满足或是为取消的期待找到相应的理据,从而完成语用推理过程。我们发现,在拒绝言语行为的解读中,关联期待的放弃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语用推理的失败和交际本身的失败。因为,对于拒绝话语而言,其关联期待的具体程度是很高的,对于推理结果的期待是很明确的,由于预设的语境是强语境,所以即使关联期待被迫放弃,听者也可以继续发问来寻找建立联系的办法,或是暂停期待,继续在接下来的话述中寻找隐含的前提和调用更为广泛的预设语境,直到期待被再次激活,寻找推理继续的理据。
正是因为话语的理解过程是在一系列的语境假设中做出选择,语境的大小区别、记忆的长短、文化背景等都可以造成对于语境选择的不同。所以,在一种文化里人们对于最佳关联的选择可能在另一种文化里是“不可理喻”的,这也给跨文化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关于这部分的汉英语料对比研究,我们会另行文论述。
[1]Sperber,D&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86.
[2]Wilson,D.&D.Sperber.Relevance theory.Entry in G.Ward and L.Horn(eds.)Handbook of Pragmatics[Z].Oxford:Blackwell,2004.
[3]Wilson,D.Relevance and relevance theory.Entry in R.Wilson&F.Keil(eds.)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 [Z].MIT Press,Cambridge MA1999.
[4]杨子.言语交际的关联优选模式及其应用[D].博士学位论文,2008.
[7]熊学亮.试论关联期待的放弃[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3).
[8]张亚飞.关联理论评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