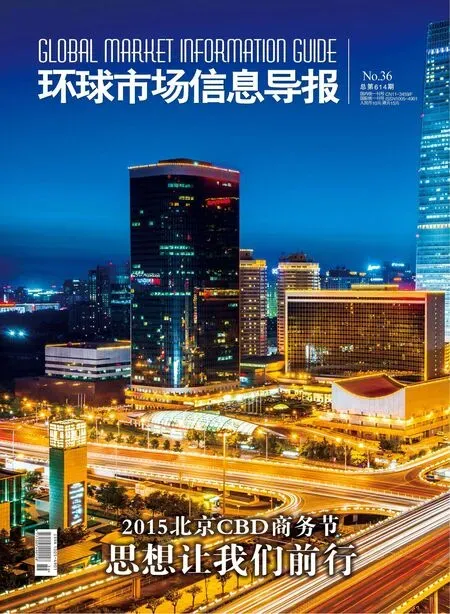借一双慧眼
2015-03-25哲人二
(文/哲人二)
许多人的青春年少时候多会有两个梦想,一是天涯明月唱策马江湖谣,二是遇淑良人谱琴瑟和鸣曲。

许多人的青春年少时候多会有两个梦想,一是天涯明月唱策马江湖谣,二是遇淑良人谱琴瑟和鸣曲。只是,实现前者的难度系数远超畅想,于是此事就渐成心口上的朱砂痣,擦也擦不掉挪也挪不去。而后者,有些时候哪怕是全力以赴地去经营,对方也不一准就是自己想遇的那个淑良人。一些已身在江湖的,鲜花和掌声也并不就是生活的全部,日子或许还没寻常人来得那么快意与温润。比如阮玲玉。生前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卑微身世的秘密,就连前夫这个纨绔到混账的人也在后来为之出身缄言。可是,她生前以为最可依赖最为懂她的那个人,在其死后撰文纪念,却在一开篇就撕裂她一直紧裹着的自卑。
并非每个女性都能够做得了“爱情教母”式的乔治·桑。男人之于女人,某些时候的“不懂”表现,也许是不愿或者不敢懂。所谓女人的脸不能细看,男人的心从来就不堪细读大概就是这个道理。200多年前的袁枚认为男女相悦大欲所存乃天地之本心如此,“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袁乡亲有如此腔调也只是建立在女性“尚悦”的基础上,与懂无关。后人张爱玲有更通俗直白的说法:“一个男人选择一个女人,绝对不是因为她内在有多美,而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外在形象带给他美好的感觉。”前者的“尚悦”说到底就是一种把玩,而后者是有所经历已经把人世看透。
男女之悦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这是有前人潜心研究出的理论成果支持的。早在1905年,弗洛伊德就提出了一系列儿童性心理理论,在文艺复兴、工业大革命后的20世纪初,学术界竟认为弗洛伊德的性学论述太过惊世骇俗,其人也被斥为是“践踏知识花园的野猪”。在弗洛伊德之前有两位牛人,叔本华和康德,如果得见弗洛伊德的这些理论的话一定会脸色阴沉。这二位虽不是经天纬地之将才,可却写有能够诱使人们掩卷沉思并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惊世著作。按理说,此等人应该“找一个开满鲜花的日光小镇,和相爱的人文艺到老”,这才符合人们对才子佳人完美结局的美好期许。问题是这两个人终身未娶。
没结婚的那么多,月老不在乎多这两个,可是一个终身未娶的人竟然也好意思对婚姻指手画脚。叔本华说:“只有哲学家的婚姻才可能幸福,而真正的哲学家是不需要结婚的。”好吧,姑且认为这是打小的生活与成长环境对心态的影响所致。而康德这个一辈子都不曾走出柯尼斯堡的人凭啥说女性不应该学几何地理历史,真难道是所谓看热闹不嫌事大?被路易十六视为其文化教唆毁了法国的卢梭,更有让知识女性恨得牙根痒痒的说辞,认为会做女红的远比身边堆满各种小册子、乱写诗歌的女天才更得男人欢喜。卢梭与一位目不识丁、双眼从未被文字污染过的女佣生了几个孩子,以实际行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想来,男人的不敢懂,缘因不好掌控的女人就是太聪慧。有思想的女人会成为一种需要小心面对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