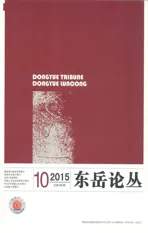鲁迅的“文脉”与《故事新编》的读法
2015-03-23刘春勇
刘春勇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文学研究
鲁迅的“文脉”与《故事新编》的读法
刘春勇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鲁迅的“文脉”其实就是由现代性的“文学”而向前近代的“文”退变,从而“超克”现代性的一种写作走向:《狂人日记》之前的留日时期,鲁迅信奉着笛卡尔意义上的具有“主观内面之精神”的主体形而上学的虚无世界像,践行“纯文学”的观念。《狂人日记》之后,一直到《写在〈坟〉后面》这“之间”,其基于主体形而上学之上的“纯文学”观念渐次崩毁,先前的虚无世界像逐渐退场,虚妄世界像得以建立。这个“之间”的时期,正是鲁迅经由从《呐喊》、“随感录”到《野草》《彷徨》再到《朝花夕拾》的写作时期,《写在〈坟〉后面》是为这一替换的终点。其后,鲁迅的“杂文时代”开启。鲁迅的杂文其实质是文章的写作,也就是“文”。《故事新编》也正是这样一种“文”的写作,它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写作,而是以“类小说”形式写成的“文”。
鲁迅;《故事新编》;虚无世界;虚妄;留白
1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①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对此,尾崎文昭是这样解释的,“其意思应该理解为:这个小说不是已有的‘文学概论’范畴里的小说,而是很新颖的,请读者不要以过去的概念来看。”基于此,尾崎认为《故事新编》既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讽刺小说,“只能认为两个都不是。应该说,这种一定要归纳到历史小说或者讽刺小说的观点本身有问题。《故事新编》应该认为是超越近代文学范畴的新文体”②引文均转引自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讲演稿:《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高远东也有类似的看法,“像20世纪50年代关于《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还是‘讽刺小说’的讨论,我以为就是囿于教科书成见的交锋,两派主张虽尖锐对立,但提问的出发点却都错了,学术上收获不多是难免的。记得唐弢先生把这比喻为在教科书的概念里‘推磨’,‘转来转去仍然没有跳出原来的圈子’。”③高远东:《〈故事新编〉的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对现有的关于《故事新编》的解读,高认为,“……或用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或用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或用‘表现主义’,或借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等等,来理解《故事新编》的特性。这样的读法,兼及《故事新编》的特殊性和其文学意义的普遍性,或对照、或联想,视野宽广,联系广泛,可以揭示《故事新编》的特质及贡献,也出现一些重要的成果(其中最优秀的著作,当属郑家建《〈故事新编〉的诗学》),我以为是不错的。”“然而还是有遗憾。最大的遗憾,在于这种读法对鲁迅文学产生的‘小宇宙’关注不够,对鲁迅之思想和艺术追求之‘文脉’把握不足,在于对已有的文学成规还是太当回事。”进而,高提出了关于《故事新编》的“好的读法”:“我以为不仅要把《故事新编》视为一部有独特形式和趣味的小说,把它和古今中外有关作家的相关作品对照来看,建立它与古今中外文学之‘大宇宙’的联系,而且也应该进入作家创作的深处,把握作家思想和艺术之创造血脉的精微流动,建立与综合体现着作家思想和艺术追求的文学生产的‘小宇宙’的联系。这样才能面面俱到,既‘串联’,又‘并联’,所建立的阅读坐标才是完整的科学的,其对小说之‘杂文化’、‘寓言性’等特质的揭示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但,高也意识到,“这样好的读法,说来容易做来难”①以上四处引文皆出自高远东:《〈故事新编〉的读法》一文。。关于《故事新编》,高有几篇非常了不起的文字,对解读这部奇怪的小说集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②高远东:《歌吟中的复仇哲学——〈铸剑〉与〈哈哈爱兮歌〉的相互关系解读》,《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高远东:《论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他上面所提出的在鲁迅的“思想和艺术之创造血脉的精微流动”之“文脉”中整体把握《故事新编》这一观点对我也有不小的启发。本文正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做一点不自量力的尝试。
2
关于鲁迅的“文脉”,我之前也有过论述③,鲁迅这一“文脉”简单地讲就是:《狂人日记》之前的留日时期,鲁迅信奉着笛卡尔意义上的具有“主观内面之精神”的主体形而上学的虚无世界像,践行“纯文学”的观念。《狂人日记》之后,一直到《写在〈坟〉后面》,这“之间”,鲁迅此前树立起来的建基于主体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纯文学”观念渐次崩毁,竹内好所谓“我也吃过人”的罪的自觉获得的那一刹那,即“回心”,是这崩毁的开始。“虚无世界像乃是对世界终极的那个消失点的僭越的结果,而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我思之人的绝对精神的自信亦是这一僭越的产儿,同时这也就是鲁迅留日时期所向往的‘主观内面之精神’的人。但是,于日本建立起来的这一信仰在《狂人日记》诞生的前后开始崩毁。所谓‘我也吃过人’的觉醒一方面是绝望的对象及于自身的表现,但同时亦是对绝对精神之自信或者对世界终极的那个消失点僭越之结果的反思之始,而虚妄就此闪现”④刘春勇:《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竹内好、木山英雄以及汪卫东关于鲁迅分期的论述及其问题》,《东岳论丛》,2014年第9期。。此后,鲁迅的虚无世界像逐渐退场,虚妄世界像⑤刘春勇:《鲁迅的世界像:虚妄》,《华夏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慢慢在他的世界中清晰起来。这两种世界像以潮退潮起的方式缓慢更替的时期,也正是鲁迅经由从《呐喊》、“随感录”到《野草》《彷徨》再到《朝花夕拾》写作的时期。《写在〈坟〉后面》是成为这一替换的终点。“鲁迅虚妄的世界像最终在1926年《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得以定型,就是那个著名的表达:中间物。如果没有虚妄世界像的建立,中间物概念的提出是难以想象的”⑥刘春勇:《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竹内好、木山英雄以及汪卫东关于鲁迅分期的论述及其问题》,《东岳论丛》,2014年第9期。。虚妄世界像的建立,伴随着鲁迅“杂文时代”的开启,即我之所谓“文章的时代”,不过,现在我更愿意说“杂文时代”是鲁迅“文”的写作的时代。“文”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概念,为章太炎所强调。章太炎认为,“把文字记载于竹帛之上谓之‘文’,论其法式者为‘文学’。”①转引自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但,留日时期的鲁迅并不心服这个概念。
……与此相关,在有别于最初演讲章的文学论的“国学讲习会”的另一个特为数位关系密切的留学生所开设的讲习会上,有这样的小插曲:根据当时与鲁迅和周作人一道前去参加的许寿裳回忆说,在讲习会席间,鲁迅回答章先生的文学定义问题时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受到先生的反驳,鲁迅并不心服,过后对许说:先生诠释文学过于宽泛。②
说“不心服”或者有为圣者讳的嫌疑,我倒是更倾向于另外一种揣测,即以留日时期鲁迅的学历和经历,并不足以全然领会其师太炎先生的小学文辞保种③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说,“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语见章炳麟:《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1906,《民报》第6号。转引自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211页)章太炎这种由文学的复古抵达文学革命的语文观念同尼采关于古希腊的语文观念似乎有某种相似之处。的本意(所谓借文学的复古以造成的文学革命④关于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之关联的话题,详见木山英雄的宏文——《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而到了1926年,鲁迅经过了种种经历之后,他慢慢生发出了一种“大回心”,即向当初其“不心服”的太炎先生的教诲回归,其“文脉”的走向渐次由“文学”而退回到“文”的理路上来。同竹内好著名的以《狂人日记》所定义的“回心”比较起来,1926年以《写在〈坟〉后面》为中心所发生的这个“大回心”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所谓的“由‘文学’而退回到‘文’的理路上来”,这里的“退回”并没有“退步”或“倒退”的意思,而且非但没有这样的一些意思,甚至还含有日本学者所谓的“用前近代的东西作为否定性媒介超越近代性的方法”⑤花田清辉语,他虽然是在用这句话讲述《故事新编》,但在我看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鲁迅后期的杂文。见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讲演稿《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
3
尾崎文昭说,“按张梦阳先生的整理,争论集中在三个问题。其一,体裁性质以及‘油滑’的评价,其二,创作方法,其三,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⑥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讲演稿:《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体裁定性的问题,这是个根基性的问题,也是后面所有问题得以回答的基础。这或许也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故事新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一问题上的原因。“建国后的主要讨论在第一问题上进行,就是到底它是历史小说还是讽刺小说。可是讨论没有达到大家能共同承认的结论”⑦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讲演稿:《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如前所论,无论对《故事新编》定性为历史小说还是讽刺小说,都还是局限在“文学概论”“教科书”的范畴内,从一开始就已经背离了鲁迅所设想和践行的《故事新编》写作。但在当时众多的争论中,伊凡的《故事新编》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⑧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依然存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延续了这一认识,认为虽然《故事新编》在整体上‘保持着小说的基本特质’,但其中‘穿插’的‘喜剧人物’以及‘大量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体现的是‘杂文的功能和特色’,因此,这部小说集可以说是‘杂文化的小说’。”⑨“杂文化的小说”这一提法虽然较历史小说或讽刺小说的定性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依然还是在“文学概论”的范畴当中。2011年出版的陈方竞的研究著作《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基础上又往前跨进了一步。“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故事新编》与他的杂文之间有更紧密的联系,这更是表现方式上的,在古代神话传说题材中置入现实生活题材的‘油滑’之笔,即‘古今杂糅’,与杂文的‘拉扯牵连,若及若离’,特别是‘挖祖坟’、‘翻老账’等古今联系、比较的运用一样,都可以追溯到绍兴民众戏剧目连戏的启示。但在我看来,《故事新编》的这种艺术表现方式,更是在杂文对此的成熟运用基础上依照‘小说方式’发展起来的,与鲁迅后期杂文有更直接的联系”①陈方竞:《鲁迅杂文及其文体考辨》,载陈方竞:《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7页,第415页,第415页。。收入该书的一篇长文《鲁迅杂文及其文体考辨》虽然主要在讨论鲁迅的杂文,但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同样适用于《故事新编》。“在他看来鲁迅后来的杂文观念同其1925年前后倾注全力翻译的厨川白村的‘余裕’的文学观有很大的关联,并且在他另外一篇长文《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陈方竞对此做了详细的考证,梳理了从夏目漱石到厨川白村的‘有余裕’的文学观对鲁迅的影响和启发,并阐述了‘有余裕’的文学观在鲁迅杂文成立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②刘春勇:《虚妄与留白:鲁迅杂文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他认为,“这是有助于我们感受和认识鲁迅‘杂文’的,同时亦可见鲁迅的‘杂文’与‘杂感’的差异:如前所述,后者更为敛抑、集中、紧张,有十分具体的针对,……前者如《说胡须》《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题目就可见,并没有具体的针对,……将一切‘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而颇显‘余裕’的写法,……”③陈方竞:《鲁迅杂文及其文体考辨》,载陈方竞:《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7页,第415页,第415页。“‘杂文’较之‘杂感’更近于‘魏晋文章’。”④陈方竞:《鲁迅杂文及其文体考辨》,载陈方竞:《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7页,第415页,第415页。陈方所论述的“杂文”的写法其实正是《故事新编》“油滑”手法的精髓。总体来看,陈方虽然没有对《故事新编》的性质做出决定性的论断,但他对其表现方法的论述,关于“有余裕”的写作手法同杂文和《故事新编》写作之内在逻辑的关联所做的精彩论述,尽管有继承王瑶、刘柏青⑤较早论述鲁迅后期“有余裕”的创作方法的是刘柏青先生。参见其著作《鲁迅与日本文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钱理群等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不得不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更大的创见。2014年1月拙文《留白与虚妄:鲁迅杂文的发生》则是沿着陈方的思路继续的探索,与陈方不同的是,该文径直把20世纪50年代伊凡的问题重新拎了出来,“在我看来,后期的《故事新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杂文,是以某种类小说形式写作的杂文”⑥刘春勇:《虚妄与留白:鲁迅杂文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在陈方的论述基础上,我将“有余裕”的创作手法概括为“留白”⑦刘春勇:《虚妄与留白:鲁迅杂文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留白”不仅是鲁迅后期杂文(包括《故事新编》)的创作手法,它甚至是鲁迅的美学原则乃至生活伦理法则,其建立的基础是鲁迅“虚妄”世界像的确立⑧刘春勇:《虚妄与留白:鲁迅杂文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在此基础上,2014年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则干脆将杂文(这里面自然也包括《故事新编》)称之为与现代装置性的“文学”相对的“文章”,“它开启了属于鲁迅个人的一个辉煌的未来时代:杂文时代——而我更愿意用我个人的术语‘文章时代’来替换‘杂文时代’。过去,我们对‘杂文’这样的概念始终摸不着头脑,以为一定是鲁迅的全新创造,然而,鲁迅其实讲得很明白,杂文,其实古已有之,即古代的文章写作”⑨刘春勇:《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竹内好、木山英雄以及汪卫东关于鲁迅分期的论述及其问题》,《东岳论丛》,2014年第9期。。如前所述,所谓回到“文章”(即“文”)的写作并不是倒退,而是“鲁迅要写故事结束以后的事情,此事意味着从混沌中出现而向混沌里消失,此种叙述结构就是近代以前的小说形式,或者说,如要克服近代绝对的观念,也许需要在第三世界里反照到这样的世界”瑏瑠竹内好语,引自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讲演稿:《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瑏瑠。
4
《故事新编》当中的“油滑”问题其实也应该放在这样的一个“文脉”当中才能理解。“油滑”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法问题,而是使用这一手法的作者同世界的深刻交流当中的一种游刃“有余”的态度,甚至是作者同世界和解的产物。当一个人身处虚无世界像当中时,他同世界的关系一定是紧张的、不和解的,虚无世界像是主体形而上学的产物,是将自我主体化和世界客体化之后所产生的“世界图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图像”当中,人成为一切的中心和唯一的实体,用昆德拉的话说,“现代将人变成‘唯一真正的主体’,变成一切的基础(套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而小说,是与现代一同诞生的。人作为个体立足于欧洲的舞台,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小说。”“只有小说将个体隔离,阐明个体的生平、想法、感觉,将之变成无可替代:将之变成一切的中心。”然而,“个体作为‘一切的基础’是一种幻象,一种赌注,是欧洲几个世纪的梦”①米兰·昆德拉:《小说及其生殖》,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47-50页。。在虚无世界像当中,作为“一切的基础”的个体的人成为世界的唯一中心,即唯一的焦点(聚焦),同时也是世界唯一的“消失点”与“透视点”。作为同现代人一同诞生的小说,或文学,自然也在这一框架中,也因此,文学创作不会溢出焦点叙事的范畴,文学一定会围绕着“主题”展开。既然一切围绕着中心和主题展开,那么,同主题不相关的一切细枝末节都是不必要的,是被删除的对象。在这样一种紧张的、不留白的模式当中,“油滑”显然无处藏身。在1925年的《华盖集·忽然想到》中,鲁迅有这样一段话: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②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5-16页。
中间的一句“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其实放到前期的鲁迅身上也同样适用。我们个人的阅读鲁迅的经验都会告诉我们,鲁迅前期的《呐喊》、“随感录”大部分文字阅读起来其精神是逼狭的,没有什么余裕可言,自然就不会有“油滑”的产生。只有当鲁迅的世界像从虚无渐次转向虚妄之后,其精神才慢慢显现出同世界和解,这个时候,他的文字才开始逐渐通透明亮起来,“油滑”才成为可能。因此看来,“油滑”不可能产生在聚焦叙事的文本当中,也即不可能同聚焦叙事的“文学”相容,“油滑”的产生只能在非聚焦(或非主题)叙事的非文学的“文”之中,并且它只能诞生于面对世界时的一种和解的“余裕”心当中。
批评史上对“油滑”的认识同样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陆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一直裹足不前,80年代打破这格局的是王瑶、陈平原师徒二人。对此,木山英雄是这样评价的:
这种争论好容易在最近才似乎有了新的变化。一种观点是,认为对成为问题焦点的“油滑”应该从中国的传统戏剧、特别是作者故乡的绍剧或称作绍兴乱弹的地方戏明显的丑角演技中寻根求源(王瑶)。这种丑角,就像作者本人在《二丑艺术》(《准风月谈》)杂文中介绍的例子那样,是在演剧时抛开情节,将剧中人物的缺点作为笑料直接向观众披露或事先明告其穷途末路。另一种观点是,更加积极地援引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说来解释,即认为《故事新编》的作者将现代性的异物纳入到历史之中,是与布莱希特对以感情同化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Arlstoteles)以来的欧洲传统戏剧观提出异议,故意用障碍观众舞台一体化的手法发挥其批评精神出于同样的目的(陈平原)。这些观点是试图从许多论者感到困惑之处看出鲁迅的积极方法而出现的,不论其正确与否,
至少可以说总算为跳出为解释而解释的老圈子提出了一条新路。①木山英雄:《〈故事新编〉译后解说》。
师徒两人在解释同一问题上,尽管方向不同——老师是前现代的进取,学生则是向西方的后现代资源靠拢,但在有意“超克”“现代”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这两种方向相反却又有着什么相互联系的解决方案,其内在关联的逻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未必有多少人能够懂得,但由于知识结构的未中断性,日本研究者在理解这一问题上似乎更加得心应手。对此,木山曾这样解释道:
布莱希特与中国未必没有某种因缘。纵不说他对墨子抱有的兴趣,关心布莱希特的人都知道,他在从纳粹德国流亡莫斯科时观看过中国京剧名角梅兰芳的演出。当时他发现京剧中有不少与自己的理论一脉相通之处,甚至还写了《中国戏剧的间离效果》(千田是也编译:《戏剧可以再现当今世界吗》)的论文。布莱希特对《故事新编》在日本的理解方法也有一定的关系。对日本人的鲁迅观有着巨大影响的竹内好并未能很好评价《故事新编》,而布莱希特的爱好者花田清辉却始终积极推崇《故事新编》。花田还与从事介绍布莱希特的长谷川四郎等人合作,得心应手地将《非攻》《理水》《出关》和《铸剑》等四篇小说改写成了剧本(《文艺》一九六四年五月号),并实际搬上了舞台。并且,竹内在晚年也留下了似接近于花田理解方法的言论(《文学》一九七七年五月号)。②木山英雄:《〈故事新编〉译后解说》。
以上引文中所提到的花田清辉是日本顶推崇《故事新编》的代表人物。他曾说:“如一国一部地列举二十世纪各国的文学作品,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提并论,我在中国就选《故事新编》”③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讲演稿:《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尾崎文昭曾经总结过日本对《故事新编》研究的三大思路,其中,花田的思路影响最大,“先回顾和清理日本鲁迅研究界过去对《故事新编》的解释,而分为三个思路:其一,竹内好的路子,其二,花田清辉的路子,就是对它比《呐喊》和《彷徨》还要重视,认为它是具有世界最先锋水平的杰作,其三,接受中国和苏联学者观点而展开的路子。”“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后看他们的成果,应该认定为第二种路子最可观,突破‘竹内鲁迅’的框架并打开了更丰富的鲁迅文学世界”④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讲演稿:《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花田的继承者们大都延续了第二种路子。桧山久雄认为,“鲁迅的作品里(《故事新编》)同《野草》最为重要,他的文学的归结;(作品里的)自我批评的干燥哄笑,来自于据自己病死的预感把自己一生对象化的觉悟。‘油滑’可算是对此哄笑具有信心的表明,同时也有对行动者理想化”⑤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讲演稿:《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木山英雄则认为,“作者在序中几度流露出对‘油滑’表示反省的话。然而实际上这种手法贯穿着《故事新编》的全部作品。关于此书,作者在书信中除说‘油滑’之外,还多次自我评说是‘玩笑’‘稍许游戏’‘游戏之作’等等。令人感到,这与其说是作者表示谦虚,毋庸说是在提醒人们对这一点引起注意。其中也许还包含着鲁迅在创作方法上的自负,故确实值得研究”⑥木山英雄:《〈故事新编〉译后解说》,刘金才、刘生社译,《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1期,第24页。。1990年代以后,尾崎文昭、代田智明等也大体沿着这个思路前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思路几乎可以总结为花田清辉的一句话,即“鲁迅通过它(《故事新编》)研究了用前近代的东西作为否定性媒介超越近代性的方法”⑦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讲演稿:《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按照木山的解释,也可以认为他通过布莱希特作为媒介,而已经触碰到了鲁迅由现代性的“文学”而向前近代的“文”退变这一“文脉”的走向了。
2015年2月19-21日于湖北黄州写于新年祝福声中
[责任编辑:曹振华]
L210.96
A
1003-8353(2015)10-0078-06
2015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鲁迅文章学研究”(项目号:15YJA751017)。
刘春勇,男,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