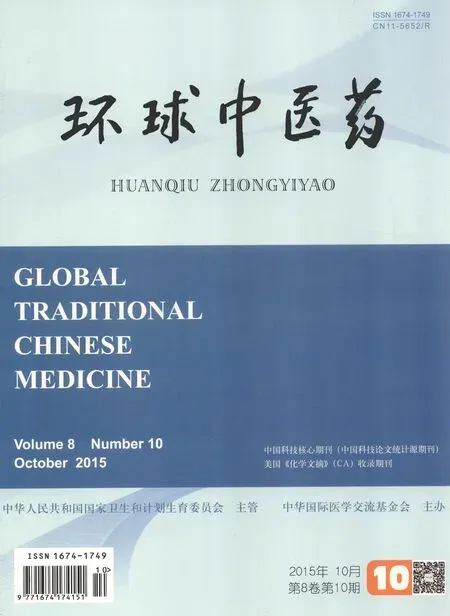周德瑛教授治疗白疕的临床经验
2015-03-22李楠林鸿春
李楠 林鸿春
周德瑛教授治疗白疕的临床经验
李楠 林鸿春
周德瑛教授认为白疕初为实证,以血热内蕴为主,随着病情演变以夹湿、化毒、气血两燔,转化为虚实夹杂证、虚证。临证重视皮损辨证与全身辨证相结合,在四诊合参的基础上,注重参考舌象而决定处方配伍。治疗上,内以加味消银解毒汤为主,外以安抚润肤为主;喜用性味甘寒之清热解毒药物,注重顾护脾胃,养阴护液;创立辨证施浴,在临床上取得良好的疗效。
周德瑛; 白疕; 舌诊; 血热内蕴
周德瑛教授出生于1950年,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知名专家,全国有独特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的中医药专家金起凤先生学术继承人。周德瑛教授传承及发扬了金起凤先生治疗皮肤病的学术思想。笔者跟随周德瑛教授学习十余年,现将周德瑛教授治疗白疕的经验总结如下。
1 局部辨证与全身辨证
周教授局部辨证常从白疕皮损的形态、颜色、薄厚、浸润程度、鳞屑等方面入手。寻常型皮损表现为点滴状斑片或丘疹,颜色淡红,鳞屑少,则多认为血热夹风热;若为点滴状斑片或丘疹,颜色鲜红或红赤,鳞屑厚,则多认为血热毒蕴。皮损表现为融合成大片的斑块,颜色淡暗,浸润感明显,鳞屑少则多认为血热血虚;若融合成大片的斑块,颜色紫暗,浸润感明显,鳞屑厚,则多认为血热血瘀;若大片斑块,仅见层层干燥鳞屑色白者,多认为血热血燥;层层鳞屑粘腻色黄者,多认为血热夹湿。
对于脓疱型白疕,皮损以红斑、脓疱为主,红斑较薄,浸润感不明显,鳞屑较少,多认为湿热毒聚,湿热并重;皮损以红斑、黄色痂屑为主,红斑色紫赤,脓疱较少,多认为湿热伤阴,热重于湿。
对于关节型白疕,无论皮损颜色如何,若患者关节红肿疼痛明显,关节变形较轻者,多认为湿热闭阻经络、关节;若关节变形,红肿不明显,疼痛不能屈伸,多认为湿热阻络,血不荣筋。
对于急性红皮病型白疕,全身皮肤红肿、色红赤,甚至有大量渗出,脱屑明显,伴壮热,多认为热入营血,气血两燔;对亚急性红皮病型,全身皮肤红肿、色淡红,午后低热,层层大片厚屑脱落,多认为热毒伤阴、余热未清;对于慢性红皮病型,全身皮肤粗糙肥厚,状如牛皮,质韧,色淡红或暗红,脱屑细碎,久治不愈,多为血热血瘀,气阴两虚。
周教授重视全身辨证,认为白疕初期未治,多为实证,随着病情迁延、变化,多为虚实夹杂证。周教授认为白疕病机初为血热内蕴,逐渐演变为血热伤阴、或用药伤阴,继而血热生风化燥,肌肤失于濡养,脱屑明显,发展为为血热血燥。病程日久,热毒伤阴耗气,加之药用清热解毒之品损伤脾胃,以致脾胃气虚,运化失司成脾虚血热证。病程迁延,或用药失当,致使脾气亏虚,阴液损伤,肌肤失养,以余热未清、气阴两虚证多见。后期气虚血行无力,加之血热煎灼阴液,则表现为血热血瘀,气阴两虚证。若进食喜寒、易口渴喜饮、大便干燥、无乏力不适、睡眠易多梦、情绪易急躁者,考虑多为实证,实热内盛。若进食喜寒、易口渴不喜饮、大便溏泄、腹胀、睡眠尚可、乏力倦怠,考虑多为虚实夹杂,脾虚血热。若进食喜热、口渴不喜寒饮、腹胀便干、乏力不适、睡眠易多梦,考虑多为虚实夹杂,余热未清,气阴两虚。
2 临证诊断技巧
2.1 注重问诊
周教授临床上喜问饮食宜忌、脘腹情况、排便情况、睡眠及性情。喜荤喜肥甘、辛辣刺激者,多系肠胃湿热,治疗上注重化食清热;喜素喜清淡者,多系肠胃虚弱,注重健脾益气。喜冷、多饮者,为中焦有热;喜冷、不喜多饮者,为中焦湿热困脾;喜热、多饮者,为中焦虚寒;喜热、不多饮者,为寒湿困阻脾土。食后脘腹胀满,多系脾胃虚弱;食后无不适,多系脾胃运化如常。若大便干、数日一行者,多系热伤津液,燥屎内结;若大便溏泻,日数次,多为湿邪困脾,运化不利;若大便呈香蕉状,日一次,则脾胃运化如常。周德瑛教授注重问入睡情况、睡眠时间、做梦与否,若入睡困难,多为心火上炎;若睡眠时间短,多为肝肾阴虚;若梦多、眠不实,多为心肾不交,肾水不能上济心火。周德瑛教授建议患者“子时大睡,午时小憩”,子午之时为阴阳交替之时,“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此时睡眠可调节患者阴阳平衡,又能保持经络通畅[1]。若性情急躁,多肝火旺盛;若抑郁焦虑,多肝郁脾虚;若性情温和,多心火不亢、肝气舒畅。
2.2 重视舌诊
周教授在辨证治疗白疕时,尤其重视舌诊。舌边有齿痕的患者多考虑素体脾胃虚弱,用药不宜过于苦寒;或已脾胃气虚,临证用药上,注意健脾扶正。舌边无齿痕者,多为脾胃未伤,临证用药上,也考虑顾护脾胃。周教授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若伤,不仅生化乏源,且一则水谷不化;二则中药不易吸收利用,不能达到治疗效果;三则伤及脾胃,则易出现兼夹证,对治疗往往不利。舌苔白腻多为湿邪内生,注意健脾化湿;舌苔黄腻,多为湿热合邪,注意清热除湿;舌苔少而乏津,多为阴液已伤,临证用药上,应用清热凉血药物的同时注意育阴保津;舌苔厚腻而少津,多为湿热伤阴,临证用药上注意清热利湿而不伤阴。周教授认为,脾主运化水湿,湿邪内生,舌苔厚腻,治疗上不仅要清热利湿,更重视健脾化湿;认为此病主要病机为血热内盛,热病后期,阴液内伤,舌质乏津,注重清除余热、养阴护液。
2.3 注重脉诊与全身症状、皮损、舌诊互参
周教授认为不能孤立地通过脉诊辨证,要参见全身症状、皮损、舌诊综合辨证。当脉证不相符时,往往是虚实夹杂证,辨证“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灵活用药;若脉沉细,全身泛发鲜红色斑片,舌质红赤,苔黄厚,考虑此为本虚标实,本为素体气血亏虚,标为血热炽盛,急则治其本,治疗上以清热凉血为主;若脉滑数,全身散在暗红色斑块,舌质淡红有瘀点,苔薄白少津,考虑此患者素体血热内盛,兼有气虚血瘀,治疗上在清热凉血的基础上,注意健脾养阴,化瘀消斑。
3 治疗特点
3.1 内以加味消银解毒汤为主,外以安抚润肤为主
消银解毒汤[2]为金起凤先生治疗白疕的名方,在犀角地黄汤基础上化裁而来。周教授在治疗白疕的过程中化裁组方——加味消银解毒汤,继承了金老“清热凉血”的用药特点,临证再进行加减运用,治疗白疕取得很好的临床效果。加味消银解毒汤由羚羊角粉、水牛角片、生地黄、丹皮、赤芍、金银花、拳参、土茯苓、半枝莲、茯苓、生薏苡仁、生白术等药物组成,水牛角片或者羚羊角粉为君药,水牛角性味苦寒,归心、肝经,具有清热凉血解毒之功效,一般用量15~30 g,建议先煎半小时;羚羊角粉咸寒,归心、肝、肺经,具有平肝熄风、散血解毒、清肝明目之功效,一般用量0.6~1.2 g,与汤剂冲服。羚羊角清热凉血的力量强于水牛角,适用于白疕进行期或红皮病型,以凉血熄风;另外羚羊角可清乎肺热,对于外感之邪诱发或加重病情时,用之清泄肺热以透邪外出;也可用与水牛角片同时合用,增强清热凉血的力量。生地黄、丹皮、赤芍为臣药;生地性味甘寒,归心、肝、肾经,具有清热凉血、益阴生津之功效,一般用量10~30 g,脾胃虚弱伴溏泄者,用量宜少或宜配健脾益气之品合用。牡丹皮、赤芍具有清热凉血活血之功,一般用量10~15 g,此二味清热而不凉遏血分,不宜留瘀。金银花、拳参、土茯苓、半枝莲、茯苓、生薏苡仁、生白术共为佐药,金银花、拳参、土茯苓、半枝莲以清热解毒利湿,茯苓、生薏仁、生白术以健脾益气利湿。诸药共用,起到清热凉血消斑,解毒健脾利湿之效。
有咽部不适者或咽部感染诱发加重病情者,喜用板蓝根、大青叶、北豆根,板蓝根用量可达15~30 g,大青叶用量一般不超过15 g,北豆根用量3~6 g,大青叶用时不宜过长,服用期间注意监测肝功;北豆根对咽痛、扁桃体红肿都有显著疗效,用量一般6 g,用时不宜过长;亦可选用金银花、麦冬、木蝴蝶、胖大海等量代茶饮,开水冲泡后,徐徐频服,缓解咽干、咽部不适。
高热者,选用白虎汤,清气分热盛;重用生石膏,甘寒清热,用量15~30 g,先煎半小时。对于急性红皮病型患者,高热明显,全身红肿、脱屑,宜选用清瘟败毒饮加减,以清热解毒,凉血消斑,并重用玄参以化斑解毒。但患者高热一退,面部皮损颜色变暗变淡,鼻尖变白,立即停用苦寒解毒之品,以防过于苦寒伤于脾胃;对于亚急性红皮病,往往以凉血清除余热为主,兼养阴健脾益气,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对于慢性红皮病、全身皮肤色红、反复脱屑、无明显发热者,往往在清热凉血的同时,兼用活血通络、养血润肤、益气养阴之品,此时药味较多,但药量较轻,注重扶正益气养阴。
外用药物以保湿润肤、温和安抚为主,避免激惹白疕的皮损。皮损瘙痒重,喜用复方苦参止痒乳膏清热止痒,不刺激皮肤;皮损鳞屑多,瘙痒不明显者,可选用白凡士林与郁美净1∶1混匀外用或是白凡士林与橄榄油1∶1混匀外用,既温和安抚,又有效廉价。皮损呈斑块,可以用中药软膏封包,或局部先用强效激素软膏涂第一层,再用10%水杨酸软膏涂第二层,促进药物吸收、渗透。
3.2 慎用苦寒药物
应用清热解毒药物以甘寒药物为主,慎用苦寒药物,且药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过长。周德瑛教授喜用金银花和草河车,金银花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祛邪,用量可达30 g;草河车,其性味苦凉,归心经、肝经、肺经、胃经、大肠经,既可清热败毒、又可消肿抗癌,抑制银屑病表皮细胞的过度增殖,苦凉而不易伤脾胃,用量10~30 g。
3.3 顾护脾胃、养阴益气
对于舌边有齿痕的患者,处方中常用生白术、茯苓、薏苡仁以健脾益气除湿;对于皮损处于消退期的患者若伴有腹胀便溏,处方常用炒白术(用量6~10 g)、茯苓(用量20~30 g)、炒薏苡仁(用量20~30 g)、炒白扁豆(用量15~30 g)以健脾除湿实大便;若伴有气虚乏力的患者,处方常选用生黄芪(用量10~50 g)、太子参(用量6~15 g),益气又不生温化燥。
对于舌质少津乏液、大便干燥、脱屑明显、口渴低热的患者,处方常用青蒿、知母、炒黄柏清余热、养阴津;常用天冬、麦冬、玄参养阴生津、润肠通便;常用白芍、生甘草酸甘化阴,养血润肤;疾病后期也可选用熟地黄填补真阴。
3.4 辨证施浴
由于白疕患者病情多复发,病程较长,周德瑛教授根据“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理论,创立了辨证施浴。针对不同的皮损特点选择合适中药进行药浴,有效地缩短病人治疗时间,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皮损进行期,颜色鲜红,重用马齿苋、紫草、大青叶、甘草清热凉血消斑;皮损静止期,颜色暗红,以海桐皮、川槿皮、大皂角、鸡血藤、首乌藤等活血消斑;皮损消退期,皮损干燥,颜色淡暗,则用当归、皂角刺、透骨草、苍术、威灵仙等养血通络消斑。红皮病型,全身红肿,药浴选用单一药味,马齿苋500 g煎汤外洗配合淀粉浴。药浴时强调水温不宜超过38℃,浸浴时间15~30分钟,浴中不可搓掉鳞屑,强调鳞屑自动脱落;浴后注意保暖,避免外感风寒,及时外用保湿护肤品及中药软膏。
4 病案举例
患者,女,45岁,2014年12月1日初诊。主因“全身皮损反复发作25年,加重2周”就诊,就诊时见全身弥漫性浮肿性红斑,大量黄色鳞屑脱落,双小腿重度肿胀,红斑基础上有脓湖及粟粒大小脓疱,伴有发热,双膝关节疼痛,口渴喜寒饮,进食少,纳呆,大便干,每天1次,小便黄,舌质红赤、苔黄腻,脉滑数。现代医学诊断:红皮病型银屑病;中医诊断:白疕(红皮病型)。证型:热入营血,湿热毒聚证。治法:清热凉血,解毒利湿。处方:水牛角30 g、羚羊角粉分冲0.6 g、生地黄20 g、牡丹皮15 g、赤芍15 g、草河车15 g、板蓝根15 g、金银花30 g、黄芩6 g、土茯苓30 g、半枝莲15 g、厚朴10 g、生薏苡仁30 g、焦三仙各10 g、川牛膝10 g。7剂,水煎服,每天1剂,嘱其早晚饭后分2次服用,外用药物白凡士林与郁美净1∶1混匀,早晚各1次。
二诊:服7剂后复诊,全身弥漫性红斑,浮肿已消,全身脱屑减少,鳞屑呈白色大片,双小腿脓疱及脓湖消退,轻度肿胀,无发热,双膝关节疼痛减轻,口渴喜饮减轻,进食及食欲正常,大便不干,每天1次,小便黄,舌质红、苔白腻,脉滑略数,调方去焦三仙,加木瓜20 g祛湿疏经通络,14剂,服法同前,外用药物同前。
三诊:面颈、前胸红斑消退,余弥漫性红斑颜色变淡,全身脱屑减少,鳞屑呈白色细碎状,双小腿无肿胀,无发热,双膝关节无疼痛,口渴喜饮,纳可,二便调,舌质红、苔薄白少津,脉滑,调方去羚羊角、厚朴、川牛膝,生地改为15 g、土茯苓改为15 g,生薏苡仁改为15 g,加玄参10 g、天冬10 g,茯苓15 g,14剂,服法同前。
四诊:上肢、躯干红斑消退,双下肢弥漫性红斑颜色变淡,脱屑减少,鳞屑呈白色细碎状,口渴喜饮减轻,纳可,二便调,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滑,调方水牛角改为20 g,续服14剂,痊愈,随访3个月,未复发。
按 周德瑛教授根据患者全身泛发红斑、舌苔黄腻等特点,辨此例属血热湿毒蕴肤所致白疕(红皮病型),此为白疕重症,因血热湿毒蕴阻肌肤,湿热之邪阻滞中焦,下注经络所致。周德瑛教授在治疗中使用大量清热凉血药物,兼顾利湿而不伤中,醒脾通络,清热解毒药物中病即止;热病后期注重清热凉血同时养阴护液,此方利湿而不伤阴,健脾而不化热,解毒而不伤胃,使湿热毒邪分消。
[1] 张响,史术峰,秦彦强.现代人更应注重中医养生[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21):80-81.
[2] 金起凤.消银解毒汤治疗银屑病血热型108例疗效观察[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2,15(6):30-31.
R249
A
10.3969/j.issn.1674-1749.2015.10.021
2015-01-12)
(本文编辑:董历华)
100078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李楠);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肺病科(林鸿春)
李楠(1981-),女,博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性病。E-mail:ima ginelin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