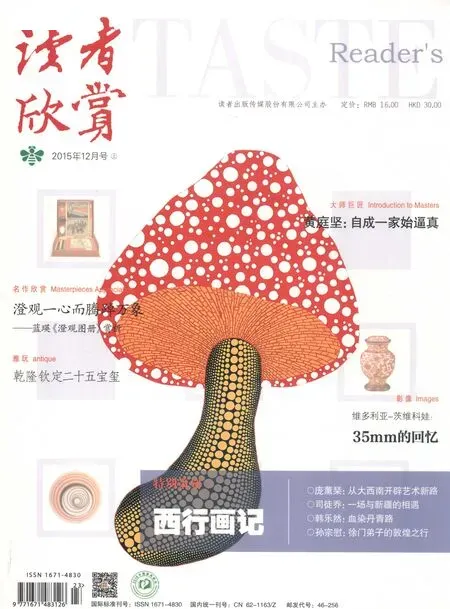乾隆钦定二十五宝玺
2015-03-21徐启宪
文/徐启宪
乾隆钦定二十五宝玺
文/徐启宪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凡皇帝颁布诏书,所钤用的印章均称作御玺、御宝或传国宝。因为皇帝的地位显赫、权力至上,帝玺往往质地精良、形制独特,是印章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重要部分,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清乾隆钦定二十五宝玺是印刻清代历史皇权的铭证,包罗中华玉玺之万象,囊括皇家御玺之百态,博群玺之威仪,显群玺之霸主。二十五宝玺在书法、篆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尽显皇家之贵。
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清承明制,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多民族特点的文化传统,清代皇帝宝玺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清代皇帝宝玺,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种,即代表皇权的国宝和为皇帝收藏、鉴赏用的宝玺。代表清代皇帝权力的国宝,最典型的莫过于二十五宝玺。从清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到统一中国后的顺、康、雍三朝,是清朝皇帝宝玺制度初创和形成时期。
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宝玺刻制尚无章法,其管辖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东北松辽地区。为了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努尔哈赤用当时的老满文刻制了两方后金汗国的宝玺,即“天命金国汗之宝”和“后金国天命皇帝”。当时的汉族和汉官在后金政权内还不占什么地位,因此,在这两方宝玺上,仅有满文而无汉文。
皇太极即位后,改后金为大清国,其统治范围不断扩大,除统一满族各部外,还得到了蒙古贵族的支持。在清政权内部,汉族成分日益增多,部分汉族豪强和士大夫纷纷做官,开始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皇帝权力的宝玺也发生了变化,其名称多依明制,玺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外,其他开始满汉文并用,数量亦有增加,出现了“奉天之宝”、“敕命之宝”、“饬命之宝”等。
顺治、康熙、雍正等清初诸帝面对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思想文化又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如何统治和管理这庞大的帝国便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统治者除了大力吸收汉官参政,实行满汉官员并用外,还不得不勤奋学习和吸收汉民族丰富的思想文化,按照历代王朝的礼制典章,结合满洲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实际情况,逐步塑造清王朝。皇帝宝玺的刻制和使用,基本沿袭明制。
清初皇帝宝玺为29方,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收藏在交泰殿的宝玺已有39方之多。其中许多宝玺名称与明代皇帝的前19宝相同或相近,初步形成了清代皇帝的宝玺制度。当然,这时的宝玺制度还不尽完善。其一,宝玺的数量和设放地点尚未制度化。乾隆皇帝弘历在《国朝传宝记》中即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尝考《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有九,今交泰殿所贮三十有九。《会典》又云:‘宫内所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今则皆贮交泰殿,数与地皆失实。”其次,用途不规范。清初皇帝宝玺,除少数如“皇帝之宝”“敕命之宝”有明确的使用范围外,大多数宝玺的使用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文献记载也不翔实。为此,乾隆皇帝批评说:“盖缘修《会典》,诸臣无宿学卓识,复未尝请旨取裁,仅沿明时所书册档,承讹袭谬,遂至于此。”其三,玺文篆刻不一。清初宝玺,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篆书外,其他宝玺皆满汉两文并用。按此前历朝皇帝宝玺皆篆书,清初国玺汉文亦篆书,而满文皆是本字,与宝玺皆篆书之制相悖,所以乾隆皇帝也认为清初国玺刻制不合规章,“因思向之国宝、官印,汉文用篆书,而清文则用本字者,以国书篆体未备也”。
清初皇帝宝玺制度的不完备,与其同时的各种典章制度不完备有密切关系。到了乾隆时期,清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各种典章制度必然要有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得以制度化、规范化。皇帝的宝玺制度也是如此。
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对当时所有皇帝宝玺加以整理。首先,考定宝玺的数量,“今交泰殿所贮,历年既久,记载失真,且有重复者。爱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其次,确定了二十五宝玺的名称、尺寸、纽式和用途:其质有玉,有金,有栴檀木;玉之品种有白,有青,有碧;纽有交龙、盘龙、蹲龙等;二十五宝玺分别用于政治、法律、军事、文教、宗室、外交等诸方面,反映了国家一切军政大权集于皇帝一身,皇权至高无上。其三,统一篆刻。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命内务府造办处工匠改镌宝文,满汉统用篆体,左为满篆,右为汉篆。乾隆皇帝在《交泰殿宝谱序后》说:“今既定为篆法,当施之宝印,以昭画一。按谱内青玉‘皇帝之宝’,本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自是而上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不敢轻易。其栴香‘皇帝之宝’以下二十有一,则朝仪纶绰所常用,宜从新制。因救所司一律改镌,与汉篆文相配。”其四,固定二十五宝收藏地点于交泰殿。清初宝玺大部收藏于交泰殿,至乾隆十一年前已全部收贮交泰殿,但制度上没有明文规定,乾隆十一年考定二十五宝后,才“详定位置,为文记之”,固定收贮交泰殿。其他诸宝,除重复十宝令贮盛京凤凰楼外,其他国玺则藏之别殿。从此,清代的皇帝宝玺制度始成定制。
乾隆皇帝对二十五宝玺的考定,反映了清代典章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化,也体现了他治国安民的思想,表现了其为一代有作为的皇帝的风度。
乾隆皇帝将皇帝宝玺核定为二十有五,取意于《周易》大衍天数之义。其义有说乎?乾隆皇帝自己作了明确的回答:“有说。盖天子所重以治宇宙,申经纶,莫重于国宝,而设笔记事之玺,即其次也。我国家礼服,饰以朝珠,祖宗所御,典礼仪存。定宝数之时,密用周姬故事,默祷上苍,祈我国家若得仰蒙慈佑,历二十五代以长,斯亦胜矣,此亦侈望。然郊娜定鼎,卜世卜年,已著其例。敬思自古以来,未有一家恒享昊命而不变者,此意恒存于心而不敢言。兹予以难期八十有六岁之侈望,而得符望传位授权,实赖鸿眷,或者侈望我大清得享号二十有五之数,亦可俯赐符愿乎。夫卜世卜年固在人,而赐世赐年则在天,叩天之佑,非敬天爱民别无道。”
这段发自内心的独白,反映了乾隆皇帝承认事物无不变化的历史观。乾隆通晓中国历史,看到历代王朝无一“恒享昊命而不变者”,多者二三百年,少者十几年或几十年,不是亡于峻法酷刑,就是在诸侯贵族割据混战中殒命,政权存在的长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由此得出了结论,偌大的清王朝能传二十五代之久,就算侈望,甚至可以说“实赖鸿眷”、天之“赐世赐年”了。
乾隆皇帝的历史观虽然不是唯物的,但他终究看到了历史的实际发展状况,而且能够承认这个现实,不再固守天命和万世不变的观点,确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也是乾隆经世之用思想在历史观上的表现,更突出地反映了乾隆德重宝轻的思想。
宝玺是皇帝权力的凭证,但这种凭证作用的大小不在宝玺本身,而在于皇帝的修养、道德和品质。不论是汉武、唐宗的盛世,还是元世祖、明太祖的雄才大略,都在于他们勤政治国的美德。乾隆皇帝引用唐梁肃对德与玺关系的论述,说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鼎之轻重,玺之去来,视德之高下,位之安危。”也就是说,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只有“日新厥德,居安虑危”,把国家的长治久安放在首位,才能更好地行使宝玺的凭证作用,并以此号令全国,此乃“德足宝重,而宝以愈重”。否则,皇帝宝玺再多也没有用。
清初几代皇帝都看到了这一点,注重勤政爱民,才出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稳定发展局面。清代中叶以后,由盛变衰,延至清末,统治者愈发昏庸,加之内忧外患,此起彼伏,皇位传至宣统帝溥仪时,清王朝终于被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所推翻,乾隆皇帝侈望传至二十五代的愿望终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