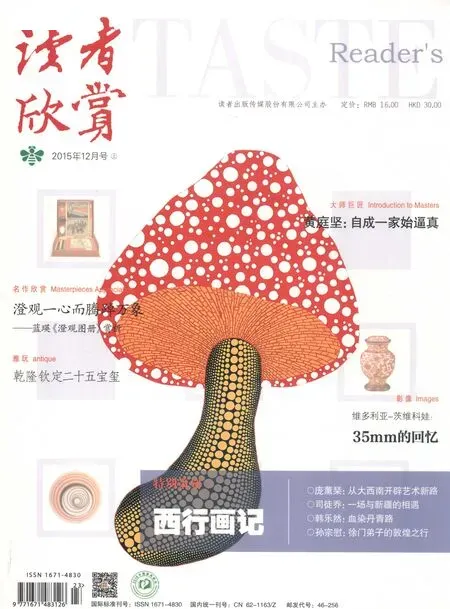无限接近透明的灰
2015-03-21杨时旸
文/杨时旸
无限接近透明的灰
文/杨时旸
这不是一种戏剧化的悲伤,只是他所呈现的这个国度本身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剧涂层。
大多数人最初爱上贾樟柯,是因为他身上与生俱来的呛人的尘土气息。很多人觉得,贾樟柯必须一直这样灰头土脸下去,像一颗绝望的钉子,有必要终生扮演那种边缘决绝者的代言人,哪怕付出锈蚀自己的代价。但是,贾樟柯怎么可能困住自己呢?如果他的野心真的如此狭窄,那么他最初的作品也不会渗透出那样击中人心的力量。所以,贾樟柯的变化是注定的。他从叙述自身经验转变成一个可以对更庞大的世界进行虚构写作的作者,这种转身是成为真正的导演的必要一步。很多被寄予厚望的艺术片导演都困在了那道门槛之前,而贾樟柯顺畅地越过了那个微妙的鸿沟,而且并不是以损伤自己的特性为代价。
和《天注定》相比,《山河故人》口碑的共识度可能会高一点,但也不太可能完全被调和。喜欢它的人会认为贾樟柯已经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国际化地位,而在不喜欢它的人看来,这部空间线横跨大洋,时间线又直指未来的电影,简直就是很能“装”的一桩铁证。
其实,即便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中拍摄了海边别墅和私人飞机以及具有科幻色彩的平板电脑,但这部戏仍然特别“贾樟柯”,因为你顺着那根线索找到的那只锚,仍然深深地扎在山西的县城里。
一度,贾樟柯想远离县城,他曾经反问:“难道我就只会拍县城吗?”其实,他并不太在乎拍摄的是县城还是都市。因为从整体意义上讲,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县城—肆无忌惮,野蛮生长,不伦不类,活力非凡。贾樟柯对于这一切的呈现,不喜不悲,灵活而具有调试性。他可以放松地行走在欧洲的红地毯上,也可以瞬间回到县城的小面馆里,在他身上,你几乎看不到文化时差。有太多的导演只能顾及一种文化语境,而贾樟柯可以用标准的中国视角拍摄中国,但与此同时却具备奇妙的世界味道。这来源于贾樟柯对于中国的态度,混杂着旁观和亲昵。他高度理解这个国家,却又天然与其保持着警觉与疏离。
这种呈现中国的方式在《山河故人》中异常明显。有时,甚至同时具备高度的陌生化和高度的亲近感。比如,那段有关未来的设定。其实,甩向未来的那段故事一点也不装,那是自然而然生长出的时间线。与其说其中的细节有科幻元素,不如说更像现实缝隙中挤压出的魔幻,像幽灵般的一笔,如同《三峡好人》中那个突然窜上天的火箭。
《山河故人》从《天注定》那种短促的、爆发的气息和节奏中彻底还魂,又一次有了绵长的喘息。它是一幕舒缓、隐忍却到处密布着残忍的故事。而这一次的残忍,不是来源于社会冲突和身体层面的暴力,而是来自于更无法言说的命运和时间的研钵。
电影中三个人的命运呈现了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三种分裂。最初,是时代的变革分裂了他们,他们自己选择命运,有意识间杂着无意识。有人觉得自己可以骑在时代身上,志在必得;有人觉得自己可以更加高妙地看待命运,好像处乱不惊但最终一败涂地;有人在随波逐流中做出了效益最大化的抉择。而当时光流转之后,他们不但被命运分裂,三个人也开始了又一次的自我分裂。
最终,孩子成了最悲剧化的象征,犹如漂浮于这个世界中的一颗无辜的原子,从山西的县城飘荡到上海,又飘荡到澳洲,在大洋的边缘囚禁与挣脱,在天空中展开一段绝望的忘年之恋。而那个与之亲昵的女人的身份也高度象征化—老师、母亲、情人、人种意义上的亲近者……两个被自己的世界放逐的人,在异乡用肉身的焊接寻求精神上的贴近,但最终注定更进一步疏远了彼此。他们想买票回到山西,但最终因为一次争吵无法成行,这不但是现实中的困境,也是精神上的隐喻。人,怎么可能真的回得到过去呢?从某种程度上说,最后那段有关未来的呈现,已经残酷地告诉我们,曾经亲昵的人们被时光搅散了,他们不光隔着物理意义上的大洋,其实还隔着精神上的次元。在空旷的屋子中包饺子的涛,在大洋岸边独自站立的儿子,二者哪还在同一个宇宙中?
人们总以为自己是被地域分隔,其实,当中国的变化速度超越常态的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犹如离心机,早把我们甩进了不同的虫洞。最悲哀的是,我们总觉得彼此尚有重逢的可能,但永久分别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当缠着丝巾的儿子从飞机上被空姐送下来的时候,当他在姥爷的棺椁前迟疑着无法下跪的时候,当他叫着妈咪的时候,就已经注定,妈妈和儿子永远失去了彼此。最终,这个黄皮肤的孩子忘记了母语,被种植在了澳洲,只留下一个叫做“美元”的名字,这个名字残留着中国转型期粗暴得毫不掩饰的野心,像一个伤疤,让孩子在哪个文化中都不得安放。
大多数中国观众无法接受那种高度还原生活本貌的电影,这源自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回避—有太多忌惮和不满,但他们想扭头不看,充耳不闻。他们无法接受银幕像镜子一样反射残酷的现实影像,而贾樟柯的作品有一种无声的逼迫感,逼迫着人们通过巨大的银幕,望向自己无处可逃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贾樟柯的作品在当下中国,永远无法取得票房回报的原因。对于说出真相的人,有些人称颂其为英雄,而有些人则斥责他揭掉了自己虚妄的保护色。
贾樟柯不是那种故意拍摄黑色事件以刺破中国的导演,更不是那种用鲜红色幕布遮挡中国的导演,也同样不是用粉红的艳丽涂抹中国让人遗忘现实的导演。他是无限接近透明的灰,他一直在中国遍布着痰迹、尘土、机遇和小广告的地面上贴地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