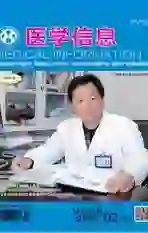肝纤维化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
2015-03-20余慧江峰
余慧 江峰
摘要:长期以来,慢性肝纤维化机制复杂、病程漫长,极大威胁人们的健康。其形成机制主要为肝脏受损害时细胞外基质( EMC) 合成与降解的失衡,并导致纤维结缔组织在肝细胞内的病态沉积, 而各类细胞因子与其对应受体,及各类炎症细胞均对纤维化的发生发展有极为重要的的促进作用。肝纤维化在一定程度上可发生逆转,而逆转肝纤维化的关键即对其早期精确的诊断及治疗。肝纤维化诊断的金标准为肝穿刺活检,但其有创性及不可复性,极大限制了在临床诊断应用,而诊断肝纤维化的的实验室检查项目尚不能准确反映其严重程度;影像学检查对于早期肝纤维化的诊断的敏感度仍难以满意。新型分子标志物的的研究为肝纤维化早期诊断提供了可能。本文主要就近年来无创诊断肝纤维化,尤其对其早期诊断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肝纤维化;早期诊断;TGF-β1
1研究背景
肝纤维化(hepatic fibrosis,HF)是慢性肝脏损伤后的一种组织修复反应,继发于多种病因。其主要病理过程是肝脏持续损伤后组织发生修复反应,因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的合成、降解与沉积不平衡,促进纤维瘢痕的形成,导致肝脏结构发生变化,致肝纤维化的形成,并随着肝脏结节再生,进一步形成了肝硬化[1]。
肝纤维化的损伤因素多种多样,如病毒、乙醇、寄生虫、缺血、缺血自体免疫攻击、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药物治疗及肝毒素等,可诱发肝细胞损伤, 致肝多种细胞,如Kupffer细胞、肝窦状内皮细胞、肝成纤维细胞等以及迁延的炎性细胞活化并释放大量的细胞因子和可溶因子, 促使肝成纤维细胞(myofibroblasts, MFB)或肝星状细胞(hepatocellular stellate cell, HSC)活化、分化与增殖, 合成大量ECM, 并逐渐沉积导致肝纤维化[2]。
1.1肝纤维化可逆性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四氯化碳(CCl4) 或乙醇等肝毒性物质诱导的肝纤维化动物模型构建技术的的成熟,对肝纤维化的的病理机制及治疗的研究已达基因水平[3]。研究证明,即使晚期肝纤维化也具有可逆性,这极大的挑战了传统观念中肝硬化不可逆的认知。
1.2肝纤维化的发病机理 肝纤维化的进展与细胞外基质成分及含量改变有关[4]。随着病变的进展,肝脏所含的细胞外基质蛋白,包括I、Ⅲ、Ⅳ型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纤维连接蛋白、等,蛋白含量总量比正常的多5倍。由于合成的增加和降解减少,导致细胞外基质的过度沉积。
肝脏受损伤时,细胞外基质产生的主要细胞即肝星状细胞[5]。正常情况下,肝星状细胞主要存在于细胞间隙。当各种致病因子持续损害肝脏时,机体将启动一系列机制,最终,肝星状细胞被激活,通过多方面的作用,形成肝脏肌成纤维细胞(myofibroblast,MFB)。活化的肝星状细胞聚集在需要组织修复的部位,分泌大量细胞外基质并调节其降解。肝星状细胞在转录时及转录后水平调节胶原的合成[6]。因此,在肝纤维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炎细胞与纤维发生细胞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
近年来分子与细胞水平的研究结果指出,细胞外基质 ( ECM )代谢基因调控的失调是导致肝纤维化的重要原因; 可通过检测血循环中基因产物的含量来诊断肝纤维化的程度,而肝纤维化的基因治疗的主要方法即正常调控基因的表达。
1.3诊断肝纤维化的多种方法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目前对于肝纤维化的诊断主要依靠以下几种方法:①影像学检查,②超声引导下肝组织病理活检,③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检测。但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完全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肝纤维化的影像技术诊断方法在临床上被广泛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计算机断层扫描及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均能通过检测肝实质中到重度改变[7],来评估肝纤维化的严重程度。超声检查由于其价格低廉,检查方便,一直以来被视为一种优越的检查技术。根据肝脏大小、形态、肝缘走行;肝内回声强弱、粗细分布均匀程度,肝尾状叶是否肿大及其形状;肝静脉、门静脉走行及显示清晰度等分为四类:即无或轻微肝纤维化、轻中度肝纤维化、重度肝纤维化即早期肝硬化以及肝硬化。然而,超声依赖于医生临床经验和仪器的性能,主观性强,可靠性低。
肝脏活组织穿刺病理检查是评估肝纤维化程度的金标准[8]。组织学检查对肝脏病变的炎症分期和纤维化分级进行更为精确的评估。通过形态计量学的方法及细胞外基质蛋白的特殊染色方法,可将肝纤维化程度进行量化,提高了检测的信度和效度。然而,肝脏活检是一种侵入性检查。据统计学研究,受检的患者中,40%出现疼痛及其他不良反应,0.5%出现内脏出血等较为严重并发症[9],这对部分受检患者身心带来一定伤害并对此项检查产生恐惧心理。此外,由于无法重复取样,动态观察病情的变化,活组织检查无法预测并监控病变的发展。因此,急需一种可靠又简便的非侵入性方法来评估肝纤维化的严重程度。
有学者提出利用常规实验室检查项目,研究其与肝纤维化的相关性。目前临床上较为普遍推行的一些肝纤维化进程的直接相关蛋白的血清水平的检测[10],也可作为肝纤维化的替代指标,主要包括透明质酸、Ⅲ型胶原蛋白的N端前肽及I型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等。这些指标对于晚期纤维化(肝硬化)的诊断及极轻度或无纤维化的鉴别有一定作用,但无法区分中度纤维化,目前在临床上还无法替代有创的肝脏活组织病理检查。近几年,随着对肝纤维化机制的深入研究,技术水平不断成熟,肝脏疾病的非侵入性诊断方法逐渐成为临床诊断常规。
2多种细胞因子致肝纤维化的发生机制
肝纤维化的病程进展的核心环节即HSC的活化增殖。细胞因子在参与调控活化的众多因素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们相互影响, 并参与HSC、ECM之间的作用, 共同构成了调控网络。其中,TGF-β1促进肝纤维化的作用尤为突出, 能有效抑制肝细胞的正常增殖, 同时可促进HSC的活化、诱导ECM的产生及在肝纤维化组织中的病态沉积, 并调节肝细胞的凋亡。
2.1 TGF-β1的提出及生物学的作用 TGF-β1是目前研究最多的与肝纤维化密切相关的细胞因子。TGF-β1隶属于TGF β超家族,包括TGF-β1-3。其中,TGF-β1是具有多种生物功能的蛋白多肽,对细胞的生长、分化、组织器官的创伤愈合及纤维病变等多种生理、病理过程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通常情况下,TGF-β1在正常肝脏组织中基本不表达,它主要分布于Kupffer细胞及肝星状细胞;而当肝脏受到各种外界因素损伤时,肝星状细胞中的TGF-β1量增高较显著,主要在纤维间隔、肝窦内皮细胞及窦周细胞等部位进行表达,并参与调控细胞周期,促进血管及胚胎的形成、免疫调节及参与诱导细胞凋亡等过程。
TGF-β1具有多重的生物学作用, 主要包括生命各个进程以及多种细胞反应, 主要涉及细胞发育、生长、凋亡、分化以及细胞的黏附、迁移、细胞外基质的沉着和免疫应答以及调节细胞外基质蛋白的生成、降解。
2.2 TGF-β1与肝纤维化的相关性 肝细胞受有害因子攻击导致损伤时,肝星形细胞(HSCs)将活化,产生大量的ECM,并合成、分泌过量的细胞外基质,沉积在间隙组织并最终导致肝纤维化的形成[11]。
HSC的激活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在整个激活过程的不同阶段,TGF-β1均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12],①起始阶段:肝细胞受外界各种刺激后,受损伤的肝细胞通过Fas途径激活HSC,促肝纤维化形成。另一方面,凋亡的肝细胞也可释放凋亡片段,作用于Kupffer细胞,促进TGF-β1及相关因子的分泌,通过旁分泌途径间接促进肝纤维化的形成。②持续阶段:TGF-β1通过相关细胞自分泌或旁分泌方式产生,并与HSC膜上的TβR结合,诱导下游相关的信号转导,整个过程中主要通过HSC的不断增殖完成量的增加及HSC合成ECM能力的提高完成质的突破,进一步加重肝纤维化程度。③消退阶段:主要通过活化的HSC逆转至静息状态及利用凋亡途径清除活化的HSC两种途径来减少活化HSC的数量。在此过程中,TGF-β的相关活性的改变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
TGF-β1在肝纤维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提示利用TGF-β1的失活可成为治疗肝纤维化的一种新型方式。
3展望
肝纤维化的机制不尽相同,但其始动因素均为有害因子对肝脏的持续作用引起慢性的炎症反应,并进一步诱发细胞因子的产生,其中心环节则是多种细胞因子诱发HSC的活化。随着对肝纤维化的机制的深入研究,肝纤维化无创诊断有了长足的进展,联合应用多种无创指标可克服单项指标在不同方面的各种不足,为临床肝纤维化提供早期诊断提供参考依据。随着许多致纤维化的关键环节及相应的调节基因被逐渐发现,抗肝纤维化的目的基因高效性、靶向性、低免疫原性转导,可明显阻止或逆转肝纤维化进程。随着科技水平提高,肝纤维化基因治疗有望成为重要的临床治疗手段。
参考文献:
[1]王宝恩.肝纤维化的诊断与严重度评估[J].中华肝脏病杂志,1998,6(4):193-194.
[2]Friedman SL. Molecular regulation of hepatic fibro-sis, an integrated cellular response to tissue injury[J].J Biol Chem,2000,275: 2247-2250.
[3]蔡瑜,沈锡中,王吉耀,等.用cDN A微矩阵研究肝纤维化基因表达的变化[J].肝脏,2003,8(1):18-20.
[4]Ismail MH, Pinzani M. Reversal of liver fibrosis[J].Saudi J Gastroenterol,2009,15:72-79.
[5]Omary MB, Lugea A, Lowe AW, et al. The pancreatic stellate cell: a star on the rise in pancreatic diseases[J].J Clin Invest,2007,117: 50-59.
[6]Bataller R, Brenner DA. Liver fibrosis[J].J Clin Invest,2005,115: 209-218.
[7]MANNING D,AFDHAL N.Diagnosis and quantitation of fibrosis[J].Gastroenterology,2008,134(6):1670-1681.
[8]Gaiani S, Gramantieri L, Venturoli N, et al. What is the criterion for differentiating chronic hepatitis from compensated cirrhosis A prospective study comparing ultrasonography and percutaneous liver biopsy[J].J Hepatol,1997,27:979-985.
[9]MUNTEANUM Non2invasive biomarkers fibrotest2Acti -test for rep lacing invasive liver biop sy: the need for change and action[J].J Gastrointest LiverDis,2007,16(2):173-174.
[10]徐铭益,陆伦根.非创伤性诊断肝纤维化临床研究进展[J].传染病信息,2010,23(3):129-132.
[11]Geerts A. History, heterogeneity, developmental biology, and functions of quiescent hepatic stellate cells[J].Semin Liver Dis,2001,21: 311-335.
[12]Tahashi Y, Matsuzaki K, Date M, et al. Differential regulation of TGF-beta signal in hepatic stellate cells between acute and chronic rat liver injury[J].Hepatology,2002,35: 49-61.
编辑/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