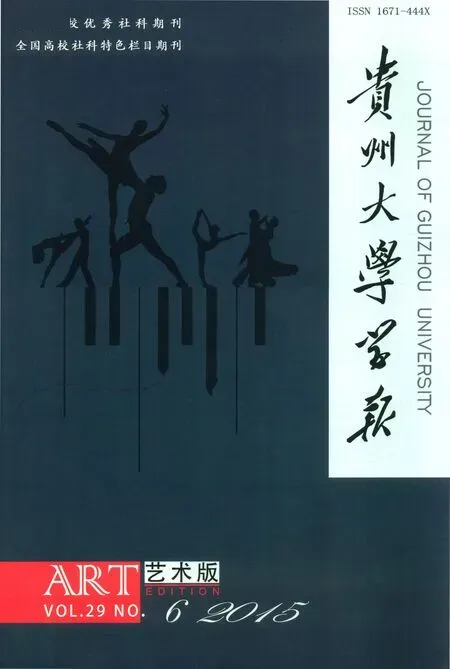“样板戏”研究:缘起与思路
2015-03-20[法]王曌,李松
[法]王 曌,李 松
(1.弗朗什 孔泰大学 文学院,法国 贝尚松;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王曌(以下简称王):李老师您好!我拜读过关于您的很多“样板戏”研究成果。从您的著作不难看出,您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样板戏”专家。围绕您对“样板戏”的研究,我有一些问题想要跟你探讨一下,第一个,为什么您会研究“样板戏”?又是怎样的契机使您开始这个领域的研究呢?
李松(以下简称李):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这当中呢,必然性是由很多的偶然性促成的。而就我个人而言,我研究“样板戏”的必然性是由以下的偶然性促成的。
首先,我攻读博士阶段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十七年的文学批评史,即1949年到1966年期间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状况。我主要是以文学经典为核心来考察批评观念的演变。而当我聚焦十七年这一阶段,这个博士选题需要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就需要找到与他相关的其他话题。那么,从时间上和观念上,以及文学发展的现象和线索来看,关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自然而然会延伸到文革时期的文艺生态,也就是从1966年到1976年间文艺创作和观念与十七年之间的延续和断裂。在2003年,我开始考虑研究“样板戏”这个领域的时候,发现学术界出现的成果并不是很多,尤其是真正的学术成果比较少,而报告文学类的著述比较多。关于文革文学的研究,从美学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最具有价值的就是“样板戏”了。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在做长篇小说研究,还有地下诗歌等等研究。我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本身,以及文革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些状况之后,发现学术研究必须寻找一些可以发掘的空白地带,或者说还有待扩充的领域。之所以“样板戏”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对象,理由在于:第一,从文学史的角度,“样板戏”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旧戏改革的延伸,也就是“改戏、改人、改制”——所谓“三改”的成果之一。而“三改”中的改戏,就从对旧戏的改革推进到了对戏曲现代戏的创新,以及新编历史剧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从“两条腿走路”(戏曲现代戏剧目与传统剧目齐头并进),到三者并举(传统戏曲、戏曲现代戏与新编历史剧),再到文革期间百花凋零唯独“样板戏”一枝独秀、独占舞台。从“样板戏”的艺术谱系来看,它属于吸取现代戏的一个部类。而从戏曲史发展的长远过程看,“样板戏”的发展还有一个深远的渊源,即1938年延安时期开始的“旧剧革命”,包括《夜袭飞机场》、《刘家村》、《赵家镇》等抗日题材的京剧现代戏。
王:是的,我在您的书里读到过这一段,您说延安时期是“样板戏”的起源阶段。
李:对,那是“样板戏”的一个前史阶段,并不是“样板戏”正式出现的时间,但是,它是一个酝酿时期。从何种意义上这么认为呢?迫切要求戏曲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和时代主题,从而发挥文艺的政治功利性作用,直接为现实政治目标服务,也就是审美的直接功利化。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上进行了权威阐释和论证,从此这一《讲话》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方向和功能。延安时期也可以算作是当代戏曲现代戏的渊源。从文学和艺术角度来看,样板戏是延安文艺的延伸。另一个方面,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政治领袖、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或者说一些政治思想的观念与样板戏主题、人物、题材、情节之间的深层关联。政治史的研究有很多透视的方式,如果去透视政治史的精神生态的话,那么,戏曲、或者说“样板戏”是一个很好的标本。“样板戏”从起步到鼎盛,毛泽东、周恩来、彭真、周扬、林默涵等大批中央高层领袖或者说中宣部、文化部、文联等各个部门的领导人物,他们都曾经积极关心推动“样板戏”。“样板戏”集中了当时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这多领导的关心推动,这在中西方艺术史上都是特殊的现象。从“样板戏”这个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对于中国艺术文学发展的方向,对于“样板戏”改编、创作、艺术发展方向上的一些观念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内在的分歧,例如江青与彭真、周扬等人的对立。总而言之,通过大量的“样板戏”史料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样板戏”凝聚了几代戏曲艺人的智慧和心血,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和时代标记。而“样板戏”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印记,即激进革命、不断革命的政治思路在艺术作品上的形象化传达。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许可以换个角度,不再从领袖英雄人物出发,不再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看政治事实,而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解析它。从这个角度我发现,从艺术和美学角度理解“样板戏”其实是个很好的窗口。
王:我非常认同老师的观点。我在弗朗什孔泰大学文学院选择这个课题的原因,也和老师一样,分为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缘于在一次演讲报告里跟我的戏剧哲学老师的谈话,我无意中发现了“样板戏”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剧目在法国汉学研究中的缺失,因此引发了强烈的好奇。必然性,是在我遇到了那个偶然性以后对“样板戏”的深入了解,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强烈兴趣。在对“样板戏”有过初步了解后,我发现它的艺术价值相对来说是很高的,可以说小小的戏剧作品却包罗万象,融汇了中西艺术多种形式和元素。而我所倾向于的研究方向是,不做简单的政治评判的前提下,单从“样板戏”的舞台艺术入手。比如说,“样板戏”的舞台走位,舞台排布在塑造戏剧美学方面的效果。
李:你发现的问题是很好的,在这个方面还真的很少有人去研究关于“样板戏”的舞台走位,舞台设计方面。当时国家出版部门的确印刷了大量的“样板戏”编排过程的资料,但是还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入手研究“样板戏”的舞台形象塑造。
王: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方向,我想也是因为我的戏剧评论和研究是在国外学习的,处身于一种中西交汇的文化冲击的氛围之中,我试图从艺术对象寻找我的文化身份。而我的研究方法与视角,是从西方戏剧理论的惯有角度出发,在法国的戏剧研究里舞台的设计、排布、演员的走位都是很受重视的。因为这种形式的设计会表达出剧作家的想法,会通过舞台的设计来表达一些自己不敢写、不能写的思想和情感。
李:你的这些观点对我也很有启发。不仅可以文学艺术史和政治史的角度来分析“样板戏”,还可以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看待。其实“样板戏”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而流行歌曲恰恰能够最鲜明反映一个时代的人们内心的愿望、情感以及寄托,在这样一种寄托当中体现出一种内在的、深层的精神结构。如果从文革的深层精神结构来说,“样板戏”视野中的当代人的心理状态可以看得很清楚。人们的领袖崇拜,对于京剧的那种狂热,对于英雄人物的讴歌,以及崇高、庄严的情感的抒发。所以说“样板戏”是一种与当时的政治热潮高度统一的艺术形式。如果从意识形态管制的方面来看的话,“样板戏”很好地实现了意识形态凝聚社会情感、形成社会动员的社会功能或者说政治功能。“样板戏”剧目包含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当然也会有人觉得样板戏并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关于“样板戏”,如果不认真仔细地去勘察材料跟剧本,或者进入剧场、进入剧本结构的话,产生以上的那种想法一点都不奇怪。这是对“样板戏”的偏见和盲见,也还有一些认识方法上的问题,觉得我不喜欢“样板戏”就不想去研究。
王:老师,会不会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因为患有PTSD,也就是创伤后遗症,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导致他们对“样板戏”的排斥以至无法接受。就好比我在老师的书里看到的,巴金听到“样板戏”就会心惊肉跳。
李:是的,确实也存在这个方面的问题。情感的判断会影响对“样板戏”研究的学术判断。所以,任何学术上的判断都应该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将学术立场与情感体验分开来看待。当然,不是说学术判断不可能受情感判断的影响,但是两者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理性距离。
从2003年开始,我关注样板戏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比较少,当时我发现这个领域具有潜在的发掘价值。很多人不愿意去做文革文学这一块,认为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讳莫如深,甚至谈虎色变。确实,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存在文章不好发表,著作不好出版的问题。有时会因为这些障碍而感到沮丧,但是,当大家都觉得此路不通的时候,也许最难的路就会变成最简单的路,因为竞争者相对比较少,发现问题的机会就比较多。其实,这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不涉及国家机密,不进行人身攻击,与我们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并不冲突,所谓的政治敏感只是无知导致的偏见而已。解放思想,开放心胸,立足学术,讲究方法,才会具有学术勇气。科学研究往往需要一种怀疑精神,当大家都觉得此路不通的时候,当大家都去追赶学术主潮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到底什么是主潮,是一种什么意义的“主潮”?
王:我想,其实研究工作有时候也会存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情况,因而,制约了研究进程的并不是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本身,而是我们的思想局限与偏见。
李:是的,有时候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思维与道路给堵死了。既然这个领域的开发价值很大,为什么要以禁忌为借口作茧自缚呢?
王:我觉得,您应该说是勇敢地开辟了一条荆棘之路。就我自己的“样板戏”研究来说,资料的收集过程我花费了好长时间,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您的著作以及您的联系方式。谢谢您帮助我邮购了《“样板戏”编年史》、《“样板戏”的政治美学》、《“样板戏”记忆:“文革”亲历》等书籍。也许对您来说这些史料不过是您研究计划的一小部分而已,可是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很宝贵的资料。而对于法国汉学家来说,其实他们现在最感兴趣的并不完全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留下来的那些文化遗迹,还有新中国建国以后所诞生的那些新生的文化与艺术。外国学者对于我们经历过文革那场浩劫以后,但却能迅速发展起来的原因感到十分好奇,对于我们文革发生的原因当然有更多的新奇。而这些问题恰巧是您所研究的范围,也许您自己并不知道,您所做的资料收集为海外学界提供了多少帮助与便利。您所收集的这些材料是“样板戏”研究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参考。而且相较于欧洲传统的希腊戏剧,其实国际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我们当代的戏剧作品以及这个方面的研究成就。我所了解的法国的太阳剧团和中国的“样板戏”,都是20世纪带给我们震撼与感悟的戏剧。
李:其实你在国外的这种生活经历,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你在留学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并且体会到西方研究者对发现东方的一些需求和动向。了解西方需求心理是中国文化西行的必要准备,我希望你利用海外背景的学术优势,架设起中法戏剧交流的桥梁。
王:老师过奖了,我希望能够中国当代戏曲研究的海外学术推介工作,希望我们的文化能够走出去。老师您在前面谈到过研究“样板戏”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那么,在您研究“样板戏”的过程中,最大的感触又是什么呢?
李:最大的感触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样板戏”是京剧发展的巅峰。近百年来京剧从徽班进京到慈禧大力推举京剧的发展,到1930年代中国京剧四大名旦的出现,另一个高峰可以说是1960年代“样板戏”的出现。第二,人们对“样板戏”的认识还并不全面。从历时性发展来看,“样板戏”分为前后三个批次;从是否定型来看,既有成熟的典范,也有试验演出的渐进型,还有计划中的作品。“样板戏”的数目可以分别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来概括。从狭义角度来看,“样板戏”包括第一批8 部和第二批10 部,合计18 部。从广义角度来看,它包括第一批和第二批,试验演出中的7 部,以及第三批尚未出笼的7 部,合计32 部。第三,我觉得32 个“样板戏”里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京剧,京剧里的唱腔、行当、角色、扮演等等方面,我认为艺术成就最高的就是音乐,京剧的音乐。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样板戏”是个特别有价值的剧种,而且是京剧艺术里的一个高峰,并且这个高峰是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很难说已经赶上和超越。如果说我们现在回头去听京剧,最经典的还是1930年代的那一批,然后就是“样板戏”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春晚都会安排“样板戏”的片段了。这应该不仅仅是为了勾起那个时代的人的回忆,也确实是因为它是我们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当然,艺术作品也不能简单地分出绝对的高低水平,我只是从相对的角度认为,从一个艺术品流传的价值看来,“样板戏”并不会很容易被埋没。
王:这方面我非常同意老师的观点。就我自己的家庭来说,我的父亲母亲都是1963年出生的,我的外婆是1937年生的。他们对“样板戏”的记忆都是很深的,当我跟他们提起我所研究的课题后,他们都是张口就可以唱的,虽然会有些什么词遗忘或者跑调,却都是朗朗上口的。您的著作里所收录的那些“样板戏”的名言名句,他们也都是记忆犹新的,例如“人走茶凉”那些话。从这里看出,其实“样板戏”对我们的影响并不能单单从政治上面看,也应该从艺术成就方面出发,它是一个深入到了我们生活中并且根深蒂固,伴随了我父母亲他们那一代人的成长。“样板戏”在他们孩童时期进入他们的生活,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生活以至于以后的人生。如果从社会学这个角度来说,“样板戏”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后续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这些影响就恰恰来自于它那非凡的艺术成就。
李:确实如此,看来你也从你父母那里感觉到了。那个时代“样板戏”的影响真的太大了,太深入人心了。可以说是深入人的灵魂,从灵魂上影响了几代人,所以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对于“样板戏”的认识还远远不够,现在“样板戏”的研究做的最多的就是8 个,对于第二批的10 个涉猎不多,那么后来在文革快结束的那几年里面还在打磨、锻造之中的那14 个,研究者的关注就更少了。如果说纯粹从审美自律的角度来看它的价值的话,这些作品也许乏善可陈,因为过于浓烈的政治色彩往往会遮蔽艺术的自由,可是如果说结合社会史、政治史、艺术史,还有人们的精神接受史去了解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样板戏”作为一个学术的问题是值得去深入研究的。
另外一个很大的感触,对文革社会运动的惊讶。我自己并没有经历过文革,我出生于1974年,那时候文革已经接近于尾声了,我对文革的印象就只停留在了那些大字报、旗帜还有标语上,当然也听过很多过来人的说法,但懂事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政治运动了。所以,我没有亲历过文革,只是知道一些文革在语言以及实物方面留下的痕迹。带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通过后来的语言和文字,通过报纸、杂志还有书籍。那个时代真的有太多疯狂、荒谬的东西,所以我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惊讶。惊叹于竟然有这样一个时代,这些惊叹带给了我无数的疑问,这些疑问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些慢慢从理性理解。在《“样板戏”记忆:“文革”亲历》的回忆录里你也看到了,巴金听着“样板戏”接受的批斗,我想要是这个场景用我们现今的电影技术表达出来的话会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一方面,崇高庄严雄壮的“样板戏”音乐作为背景,它要面对的敌人却是那个时代的缔造者、推动者以及再现者——巴金,巴金在颤颤巍巍、胆战心惊接受革命小将们的批斗;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庄严的音乐却被用来抨击这个社会的推动者和建设者。真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我个人其实是有点历史的窥视癖,对于很多历史问题有很多自己很特别的想法,也有去发现的欲望和冲动,——为什么历史上的这些人会这样。
王:在我看来,老师并不是有什么历史窥视癖,只是因为感兴趣,所以不舍得放开一点点的蛛丝马迹,才会这么细致的研究这段历史。
李:也可以算是吧。做历史的研究的话,对于材料的掌握,还有历史现象的摸爬就变得很重要了。任何一点历史风云的波动,都会对自己产生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保持这种对历史变动的敏感性以后,自然就会发现历史中的那些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细节。
王:我和老师算是不谋而合吧,对于“样板戏”,我觉得它的大起大落也是由于这些历史上的波动而引起的。文革为“样板戏”带来了巨大的辉煌也为它带来了无法避免的灭亡。
李:是的,文革给“样板戏”带来了无可比拟的辉煌,同时也注定了无可挽回的宿命,所以它的退出也是必然的。从这些看来,其实“样板戏”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种艺术发展应该具有的常态。
王:艺术应该是慢慢地缓缓地像京剧那样经过沉淀而留存下来的。
李:“样板戏”的衰亡与落败其实都是与政治有关系。实际上“样板戏”充当了激进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推广者、宣传者,所以它确实是成为了一个工具。“样板戏”创作者如何处理好政治说教和艺术熏陶,这是一个难题。
王:这应该就算得上“样板戏”它本身所包含的那种两极矛盾了吧。其实我之所以把“样板戏”选择作为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因为我觉得“样板戏”是很有意思的戏曲,它本身包含了很多的艺术形态,这些艺术形态有很大部分是两极化的,自相矛盾的。它的文化包含了西方和东方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然后它的艺术形态又是自相矛盾的,感觉上就是把两个相同的磁极硬塞到一起去。“样板戏”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自身的矛盾结合和不可调和性。
李:是的,确实如此,“样板戏”其实算得上是一个古今中外艺术观念上的结晶,包括了艺术技巧,艺术思想方面。所以它就体现了毛泽东说的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比如说芭蕾舞就融合了“样板戏”,虽然芭蕾舞是西方古典艺术的高峰,可是“样板戏”打破了芭蕾舞的陈规。再说交响乐不是西方音乐的高峰吗,“样板戏”给西方音乐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以说在东西文化混合上,“样板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您在从事“样板戏”的研究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呢?
李:要说遇到困难的话,我觉得首当其冲的是原始文献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文献资料大都只是剧本。可是与剧本相关的研究资料就相对比较少了。当时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实际上就是“样板戏”在艺术舆论上的宣传品。无论是在武汉大学图书馆还是国内其他图书馆,这类的资料都不多,所能找得到的无非就是剧本、乐谱以及小部分的研究资料,有些结集而成的这种论文集,大多能在报纸、杂志上找得到。而这种论文集其实是对于这些文章的联合整理以及出版,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这些资料远远不够。况且这只是文字方面的资料,而另一方面的则是音频、影像方面资料的匮乏,虽然可以找到一些,但却不全。能找到的主要是最著名的八个“样板戏”,市面上有卖,还有图书馆的音像部一般也找得到,但是不全面。因为样板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比如在1963年、1964年“样板戏”崛起的过程中的各种版本都是缺失的。总之,第一手的“样板戏”资料是很难得到和掌握的。这是在研究“样板戏”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第二个困难,应该算是我自己个人的困难。我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会想,我研究“样板戏”时,对于文本的细读、思想的分析,到底科学与否呢?这涉及我个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所以引起方法论的自我质疑,是因为存在太多关于“样板戏”的多种多样的看法,不同立场、不同判断彼此对立,而这些不同看法都源于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所以我想,有没有一种客观的、中立的、有说服力的、又有学理依据的研究,或者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可以让大家都坐得下来心平气和地对话并且接受它?如果说我自己的研究也是一种片面的偏见或者盲见的话,或者说一种自以为是的看法的话,那么,我觉得就称不上是学术研究。在我眼里学术研究拥有的是那种理性、严谨性、普遍性以及对话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应该可以形成共同话语的对话平台。我从方法论的反思中认为,到底如何看待“样板戏”应该有四个方面:一是文本本身的艺术性在哪里;二是从作家创作的动作来说,他到底希望表现什么;三是当时“样板戏”诞生的那个时代,以及滋养它的土壤到底是什么;四是作为观众和读者,他们对于“样板戏”的看法说明了什么。我想从这四个方面重新解读“样板戏”,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在形成对“样板戏”的认识和判断。
王:这么看来,您在研究“样板戏”的过程中既遇到了硬性条件上的困难,又遇到了软性条件上的困难。有材料缺失这些方面的硬性条件,也有思想方法方面的软性条件。
李:是的,也就是说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困难都存在。主观方面,有读者、观众的心理之类的,而文本资料和剧本以及史料属于客观方面。应该认识到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有它的客观性。
王:是的,但我想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存在的这段历史资料也是不充足的。
李:是的,大家可以找得到的资料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里面的艺术材料给发掘出来。而艺术门类也就包括了以下的这些方面,它在发展过程中演变的各种音频或者影像文本。由于“样板戏”的演出场次很多,所以导演、创作者也进行了巨大的改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文本,文本主题如何变化的?研究这个过程需要大批的材料,比如说音频、文字。“样板戏”是如何被卷入了这场政治热潮当中的?这些都需要艺术材料来解答,这些疑问就只能通过艺术材料来体现。在我所出版的《“样板戏”编年史》里就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我现在正在编排一本《“样板戏”编年史》的补编,也是对这段艺术史资料的一个补充了。我还在编纂《“样板戏”版本整理与研究》,不同版本的文本都收录到一起,比如好几个版本的《红灯记》和《沙家浜》。收集不同版本的文字资料也是研究“样板戏”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王:您付出的99%的努力,换来了1%的展示成果,可谓厚积爆发吧。
李:你过奖了。我觉得研究过程开心就好,如果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正确的、有意义的事情,再多的付出都不会去计较得失成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