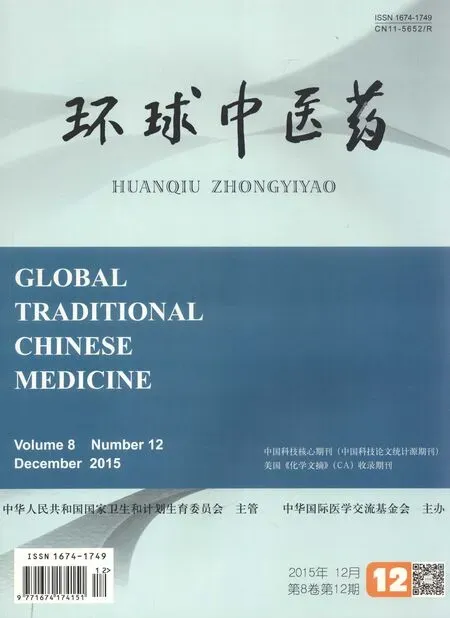中西医“脾、胰”翻译源流考
2015-03-20刘弘毅
刘弘毅
当前中西方医学对于脾脏的功能和胰腺的认知与定位是具有较大差异的。笔者在学习期间也多有疑惑。回顾历史,中西方医学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在近现代的交流中,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且相对成熟的医学体系之间的碰撞,那么对于不同医学之间的知识和内容上的认知和转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其思路必然也能为中医学者在现代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思考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提供一定的借鉴。为此,笔者通过回顾相应历史时期的中西医文献,对中西方医学关于“脾”“胰”的翻译源流进行了研究。认为中西医对于脾脏的对译和对于胰腺功能的认知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是具有其合理性的。谬误之处,还请方家斧正。
1 早期中西脾脏对译的合理性
据学者研究,近代西医传入中国始于明末清初,1568年,葡萄牙天主教徒卡内罗(Melccior Carnero)在澳门白马庙设立“癫病院”,成为将西医传入中国的第一人[1]。最早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专著是邓玉函、罗雅谷、龙华民译述的《人身图说》(约成书于1640年),邓玉函译述、毕拱辰润定的《泰西人身说概》(1642年),前者专论人体解剖学,后者除人体解剖学外,也兼及生理学知识[2]。当然,一方面由于当时西方医学正经历从传统医学向现代科学西医转变的过程[3],现代医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传教士作为宗教人员,无论其主观上还是客观方面,对当时西方医学知识的掌握上较专业人员相对薄弱;另一方面自明万历年间以来,多有反对传教之言;且处于明末朝代更替,战乱之际[4],诚如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所言:“此期传入之西洋医学,其影响我国诚无咸同间之大”。[4]5
尽管当时西医学的传入对中医学影响不大,但是还是有一些中医医家在不同层次上接受了西方医学的解剖和生理知识,比如清代医家王宏翰在《医学原始》一书中就大量吸取了当时的西洋医学观点,另外就是清代医家王学权世以医为业,亦采用西说[4]244,对其曾孙,清代著名医家王孟英产生过重要影响,王孟英所著《重庆堂随笔》一书,是在其曾祖王学权未完之稿《医学随笔》后由王孟英阐发而成,其中不少中西汇通之论就是直接受其曾祖的影响。可以说第一批开始认识和接受西学的中医学者,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深入阅读相关史料发现,当时西方医学对消化的生理过程,尤其是西方医学当时对于脾脏在消化系统中的作用,对后世关于中西脾脏的认知和对译的合理性,具有结论性的地位,可以说一直影响至今。
《泰西水法》一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1612年),由熊三拔(P.Sabbathinus de Ursis)协助徐光启所著,《泰西水法》是一本谈取水蓄水之法的书,其中卷四曰水法附馀中附以疗病之水,在药露中谈到了人体的消化功能[5]:“凡人饮食,盖有三化,一曰火化,烹煮熟烂;二曰口化,细嚼缓咽;三曰胃化,蒸变传送。二化得力不劳于胃,故食生食冷,大嚼急咽则胃受伤也。胃化既毕乃传于脾,传于脾之物,悉成乳糜,次乃分散达于周身,其上妙者化气归筋,其次妙者化血归脉……”
可以看出,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对消化的认知,是需要脾脏参与的,在范行准先生的进一步研究中,明末所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著作的内容,本于希波克拉底(Hippcrates)和格林(Galen):“……格林则谓消化由肝之热力作用,但又言脾除具有净化血液作用外,又能从食物中摄取其浓厚土样之成分,而成黑胆汁。有小关,先输黑胆汁至胃,由胃至肠,随粪排泄于外。此当时医家对于消化机能之见解也。……《人身说概》已采其说,是可证也。至于希波克拉提斯与格林二人倡食物消化三段说,《泰西水法》、《性学粗述》亦祖之……”[4]167
在《血液之生理》一段更加明确进行了叙述:“……格林言由食物变成血液之历程,大概如次:盖食物消化之过程,先分三段,一胃,二肝,三血液,其残余者如汗、尿、粪等,排泄体外。肝脏之热力,助胃消化食物,在小肠之乳糜,由门脉系统输至肝脏,受自然灵气之作用,而变为血液时,又有脾脏行其净血作用。……《人身图说》论血液生理,几全据格林此说也。”[4]170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在西医学传入中国以来,将西医学中的器官spleen翻译为中医中的脾,是有其充足的理由的,在当时的西方医学认知中,脾也是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同中医学认知中的脾有很大的相通之处,换句话说,在第一批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的中国学者,在对于spleen的翻译时是没有含糊和疑惑的。不过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更加进一步认知了spleen的生理作用,时至今日,才造成了中西医认知上的偏倚。
2 早期中医界认知胰腺功能归属于脾
清朝前中期,由于西方传教势力的影响,以及满清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统治的需要等原因,清政府采取了封关禁海的政策,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医学,尤其是现代的西方医学与中国的交流。直至19世纪初英美新教传教士再度来华,掀起西学东渐的第二次浪潮,西医书的译介才得以重来。而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一般以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开始,被称为“第二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6]。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西医医院不断延伸至内地。尤其是以西方医者、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翻译的医书系列《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博物新编》《妇婴新说》等中文的现代西医学内容较系统地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尤其是中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医学界的有识之士,比如著名的中医学家王清任也在同时期对于中医的传统认知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中西方医学——两个相对独立的且均比较成熟的医学体系之间产生了碰撞。抛开中西医间的争论不看,从中西医的认知的互相交流层面来看,中医学者对于当时传入的西方解剖、生理学中“胰腺”知识,在定位上主要形成了“胰(膵)为新脏腑”“胰属脾”,功能上“胰属脾”的认知。
2.1 胰的中医命名和定位
王清任在其实践中,运用对胰腺的认识,将其命名为“总提”“总提俗名胰子”[7],但具体功能没有明确的表述。有学者指出[8],在中国,是王清任最早将胰脏划分出来。而在西方医学传入方面,胰腺(Pancreas)最初的中文翻译为“甜肉”(1858),“月臣,月臣腺”(1908)[9]。对于胰腺翻译为“甜肉”,合信认为这是一个中国自古不识的脏器,并且对翻译为“甜肉”的原因做出了说明,合信在《全体新论》中说:“甜肉者,中土无名。长约五寸,横贴胃后,形如犬舌,头大向右,尾尖向左,尝其味甜,故曰甜肉。正中有一汁液管,斜入小肠上口之旁,与胆管入小肠处同路。所生之汁,如口津水,未详其用意”[8]214。有学者研究认为[13],在合信之后,传教士所撰西医译著中基本都采用了合信的译法,如《全体阐微》第五卷中即用“甜肉”翻译“pancreas”。合信的译法一直沿用数十年之久,直到1885年德贞出版《全体通考》,在该书第五卷《论消化之具》中才将其译为“胰”,而德贞在1882年就已经撰文指出,中文实际是存在这个词的。他说:“胰”这个字指的就是pancreas,在中国北方,回民用羊胰、汉民用猪胰来制造肥皂(俗称胰子),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个器官在北方被叫做胰[6]。
另外发现,在中医学界,不少学者在其后的引述中,多使用“膵”一字。“膵”一字来源于日本对pancreas一词翻译[9]的引用,究其原因,考虑可能是胰(亦作“月臣”)在中国传统中主要是用指动物的器官,因此对于人体的器官多引用日本的翻译而作“膵”。亦有学者研究发现,1934年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讨论解剖学名词时,在“月臣”“膵”和“胰”三个字中最后采纳了“胰”字。日本医学界亦认为是好名字,选择“胰”替代他们自己发明的“膵”。“胰”是唯一被日本医学界接受的中文解剖学术语,“膵”的译名则永远留在历史的文字库中了[10]。
2.2 胰腺的功能和中医归属
关于胰腺的功能,在其后翻译的西方医学著作中,有了进一步的论述,主要是消化油脂类物质。比如有学者研究发现,艾约瑟(Joseph Edkins)所译《食品诸品分归合用》(《西学启蒙十六种——身理启蒙》1898年)就介绍甜肉汁(胰液)能将脂膏破分,与水和其他流质化成“乳油色黄细腻物”,成为有益人体之精质。笔者研究后发现,在当时的西医学的认知中,胰腺尝之味甜,是消化器官,且主要作用于消化,因此大多数中医学者对于胰腺功能的中医归属,基本上都倾向于中医对应的脾。比如王有忠说:“各脏腑皆以官名,推脾胃合一官,西人所谓消化器也。”[8]212
清代著名医家王孟英在《重庆堂随笔 总评》中指出:“人与物皆有月臣,医书未有及之者。王勋臣亲验脏腑,亦未论及。西士名曰甜肉,言其味甜而不言其功用,反以胃中化物之功归诸胆汁,此亦未可尽信者。又云西国曾验一人,见饮食入胃,胃出甜汁以化之。此即万物归土之义,正胰之功用也。公于豕脑条内言胰主运化食物,正与西士所验相合。”[11]
另一位著名医家唐容川更明确指出甜肉即脾之物:“中国医书,无甜肉一说,然甘味属脾,乃一定之理。西医另言甜肉,不知甜肉即脾之物也。”[12]其后民国时期的医家陈无咎根据胰的解剖位和助食物消化的功能,提出胰为脾之大络,散膏为胰液的观点[13],张锡纯提出脾为散膏,是脾的副脏的观点[14]。综上可以看出,当时中医学者鉴于胰在消化方面功能的认知,提出了结论性的脾胰之论且一直影响至今。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末期,合信编译的西方医学著作中,对于脾的功能,已经更新为“收聚往来剩余之血,以宽闲动脉而保护脏腑者也”[8]206。而与消化无关。
3 讨论
综上可以看出,中西医学对于“脾”的对译上,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具有合理性的,而对于胰腺的认知,结合当时的西方医学对于胰腺在消化功能方面的认知,提出了功能上“胰属脾”的论断,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时至今日,现代医学对于胰腺的认知也不完全等同于当时的认知,胰岛和胰腺、胰岛α细胞和胰岛β细胞在功能上显然是不同的,以及血糖、血脂等大量现代生化指标,对于这些“新生事物”,现代的中医学人如果只是单方面的回溯古籍,期待古人给答案是不可能的,或者根据古人的只言片语就简单地断章取义,说“某某”就相当于古人的“某某”,而不是系统地认知、继承古人的经验和认识新事物的方式方法,无疑会影响当今学者继承并发展中医学的勇气。以上为笔者的肤浅认识,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斧正!
[1] 李志庸.中西比较医学史[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195.
[2] 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56.
[3] 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
[4] 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243.
[5] 袁媛.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1(4):40-45.
[6] 孙琢.近代医学术语的创立—以合信及其《医学英华字释》为中心[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9(4):456-474.
[7] 清·王清任.医林改错[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3.
[8] 皮国立.近代中国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M].北京:三联书店,2008:203,206,212,214.
[9] 袁媛.近代生理学在中国(1851-192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67.
[10] 高晞.“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J].历史研究,2008,(6):80-104.
[11] 盛增秀.王孟英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620.
[12] 王咪咪,李林.唐容川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0.
[13] 姜宏军,徐旻,任宏丽.陈无咎医学八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195.
[14] 张锡纯.消渴症疗法[J].医林一谔,1932,2(8):14-15.